新疆集中營是個全球性問題
對維吾爾人的壓迫是全球史的產物,而不僅僅是單一國家力量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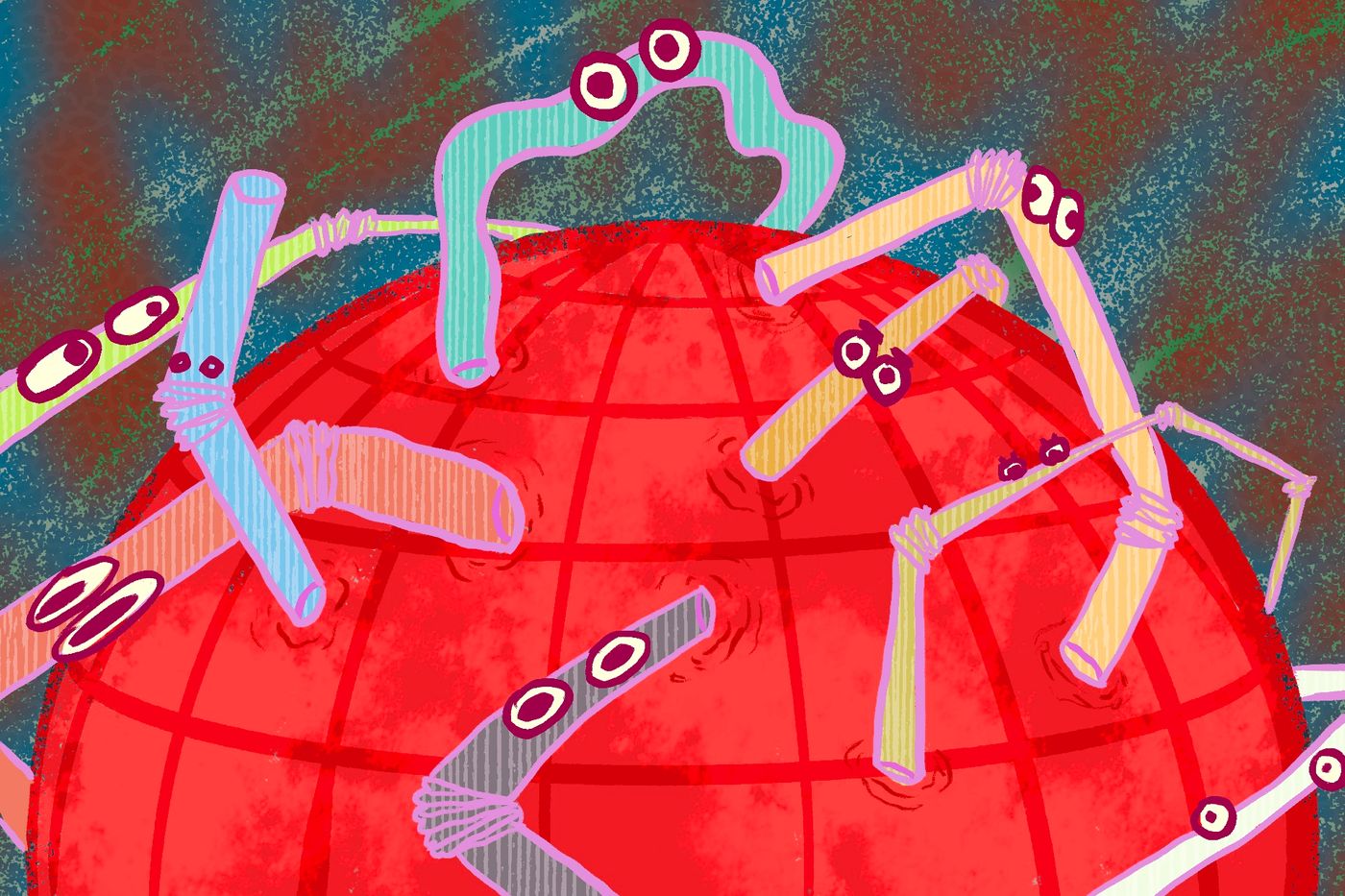
編者按:本文主要介紹維吾爾族人遭遇的大規模拘留。中共的大規模拘留和監視手段影響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又稱「新疆(Xinjiang)」、「西北(Northwest China)」、「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維吾爾亞(Uighuria)」、「伊犁(Ghulja)」、「塔爾巴蓋(Tarbagai)」、「阿勒泰(Altay)」、「宗喀則和阿勒泰沙爾(Dzungarstan and Altishahr)」或「宗喀則和塔里木盆地地區(Dzungaria and the Tarim Basin Region)」,以下簡稱「新疆」)。新疆的人口以維吾爾族為主,但也包含了眾多其他少數民族。
追溯詞源,新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專有名詞。乾隆皇帝最早于十八世紀使用該詞,並于十九世紀末左宗棠重新佔領該地區後正式將其命名為「新疆」。在普通話中,它的意思是「新的領土」、「新的邊境」、「新的邊疆」。身處於新疆以外的我們希望可以和更多同路人一起討論新疆被殖民的處境以及新疆解殖的可能性。為了最大程度呈現新疆歷史的複雜性,我們盡可能地使用準確的術語。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共的大規模拘禁和文化種族滅絕運動對整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眾多社群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如果您有進一步的問題和意見,請與我們聯繫。
2020年9月,民間和政界均有聲音譴責迪士尼在電影《花木蘭》的片頭中感謝管理新疆再教育營的吐魯番市公安局(Turpan Public Security Bureau)。知名職業運動員,如NBA中鋒魯迪·戈貝爾(Rudy Gobert)和數名法國足球運動員都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聲援維吾爾人。正如迪士尼,為了能夠繼續製作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三體》,美國的另一娛樂巨頭Netflix也選擇對劉慈欣支持新疆「再教育營」的言論進行辯護。
我猜許多外國的觀察家們大概不太知道如何將這些新聞標題轉化為政治術語。一方面,集中營的細節確實令人震驚。到目前為止,正在發生的事情似乎是不可否認的,基本的細節在很大程度上並得到了中國政府本身的證實。另一方面,這些事實常常被塞進一種二元敘述中:讓捍衛自由的美國與邪惡的中國對立起來。對於險惡的美國右翼政客和中國軍事主義鷹派,這種敘事正中下懷。例如,密蘇里州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利用《花木蘭》事件,宣稱迪士尼「決定將利益置於原則之上,不僅無視中共的種族滅絕和其他暴行,而且幫助和教唆他們;[這是]對美國價值觀的侮辱。」
在愈演愈烈的新疆問題上,我認為學者們需要擁有一種具國際主義的視角,提供一個不同於霍利等人粗暴的親美立場。目前的輿論態勢正在滋生極端的民族主義:要麼是反華恐華主義(與其說是政治家的利己行為,不如說是國家暴力互搏的展現);要麼是親華主義(該觀點拒絕承認新疆「再教育營」中存在的暴力,並以反帝為由引誘了不少中國左派人士)。例如,社會主義雜誌《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於10月10日轉載了一篇對中國在新疆地區政策令人髮指的修正主義辯護。
到目前為止,圍繞新疆「再教育營」的大多數討論都徘徊在兩種解釋之中:要麼是漢族人和非漢族人之間永恆的民族衝突,即是保守專家們認為衝突的源頭為「漢族中心主義」;要麼是歸因於與自由西方資本主義對立的專制亞洲共產主義。
雖然乍眼一看可能還有些道理,但這種解釋過於靜態,缺乏歷史分析。研究中國西北地方的人類學家白道仁(Darren Byler)曾寫道:「『種族滅絕』這一不加修飾的指控只是讓一個以文化主義的模式論證某(幾)個群體是壞的或邪惡的,並支配著另一個群體。這種指控不允許解讀問題的原由。」
而這「原由」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政治經濟發展其實息息相關:當時中國政府鼓勵國內公司在新疆發展基礎設施,開發該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以便向沿海城市供應能源。在此期間,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遷往新疆,吸收了該地區的經濟收益,並引發了維吾爾族當地人的反殖民抗議。雖然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此前一直存在緊張關係,但這些開發項目將它們提升到了新的水準。
政府對異議的回應是通過語言、宗教和文化教育等方式將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同化為一種「主流」的中華民族社會。2001年911事件後,中國政府立即明確地將美國自己的反恐戰爭言論(War of Terror)用於妖魔化伊斯蘭宗教活動;悉尼大學歷史學家大衛·布羅菲(David Brophy)對此進行了記錄。另外一個重大事件是2014年5月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爆炸;之後中共官員宣佈發動「人民反恐戰爭」。
對白道仁來說,「再教育營」與政府主導的資本剝削不可分割。這種剝削利用了新疆的自然資源和人力勞動。新疆地區供應了全國約20%的石油和天然氣,以及全球約20%的番茄和棉花。中國公司把新疆作為國家安全和網路安全技術的試驗基地,待這些技術成熟後出口到國外。新疆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節點,維穩新疆就是確保中國能夠順利進行中亞基礎交通的建設項目。據悉,再教育營中的維吾爾人被強制轉移到耐克、蘋果、Gap、三星等品牌的工廠進行生產活動;這些工廠分佈於新疆以及東部大城市,如合肥、鄭州、青島等。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到,「再教育營」不是根深蒂固的民族衝突或亞洲專制的必然結果,而是與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的勾連有關。「再教育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時中國政府轉向市場驅動的增長,並以低廉的價格向外國投資者宣傳其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
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意味著境外資本會獲取更高額的利潤、更豐厚的儲蓄、更優惠的信貸條件。這些吸引外資的政策背後是對勞動力的極端剝削。中國惡劣的勞工環境亦定期被曝光: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反對血汗工廠的運動、2010年代富士康深圳工廠工人連續自殺事件,以及現在關於維吾爾族勞工的報導。這樣的醜聞似乎從來沒有得到解決,只是在下一個醜聞出現的時候悄悄地被轉移。
這些問題的直接責任方當然是中國的企業和機構。但如果不看全球經濟動態,便無法真正理解為什麼這些問題如此普遍。
儘管美國政客們大談促進人權和與中國脫鉤,但他們知道,正因為美國公司從這種競相追逐的全球資本化中獲利無窮,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的分離並不會隨便發生。從這個角度看,新疆「再教育營」牽連的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而是全球資本以及其政治保護傘的產物。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不能再用民族主義的框架去討論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不能再簡單將中美的價值觀對立起來。這樣的二元對立,受益者始終是保守的美國政客,如霍利、特德·克魯茲(Ted Cruz)和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他們熱衷於煽動本土主義情緒而為己所用,卻不願認真審視中國新疆政策背後的全球合力。去年,不少聲音要求美國制裁中國以表達對虐待維吾爾人的譴責。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這些呼籲置之不理,因為他們會干擾美國與北京達成的貿易協定。儘管他的政府已經開始譴責新疆的虐待行為,但這似乎主要是一種贏取中國讓步的談判策略,也是一種轉移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病處理不當的指責的選舉策略。
美國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民族主義競爭最可能的結果不會是美國實現自己「改善亞洲人民生活」的承諾。這是一場針鋒相對的競爭,以懲罰無辜的人民作為一種國家政治的籌碼。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學生和工人的簽證政策,還是中國政府今年6月通過的《香港國家安全法》以及驅逐和拘留外國記者,都印證了這一點。
那麼,我們該如何前行呢?有跡象表明,國際壓力將至少迫使中國政府關閉一些「再教育營」(儘管現實情況尚不清楚)。此外,抵制與新疆「再教育營」有關的產品,無論是《花木蘭》、蘋果配件,還是H&M牛仔褲,都可能在短期內有所影響。
但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學會以一種更具國際主義的方式來談論新疆「再教育營」的中國勞工問題。這意味著要超越冷戰式的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框架。相反,專家學者們應該強調,全球政治經濟力量是如何成為再教育營的幫兇。
美國的觀察者們同事應該抵制把「再教育營」說成是與美國社會毫不相干的事件,因爲這種做法只會強化美國作為全球員警的合法性。相反,我們需要把美國的資本主義、霸權主義和新疆「再教育營」聯繫起來。我們應該極力譴責中國的伊斯蘭恐懼症,就正如我們以前竭力對抗布希政府血腥的反恐戰爭政策一樣。我們一面要大力指責全球供應鏈導致維吾爾人強制勞動的不平等體制,一面要譴責廉價商品生產網路剝削外籍勞工和監獄勞工。我們更要全力譴責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國家濫權行為,並譴責邊境巡邏隊和員警部隊在美國社會邊緣的暴力行為。
只有這種國際主義的框架才能抵禦冷戰教唆者和中國辯解者的冷嘲熱諷。更為重要的是,只有具國際主義的視野才能讓我們明白到新疆「再教育營」是我們共同要面對的問題。在全球化下的今天,我們必須要進行更加自省的對話。
文/ A. Liu
譯/ Yeejian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