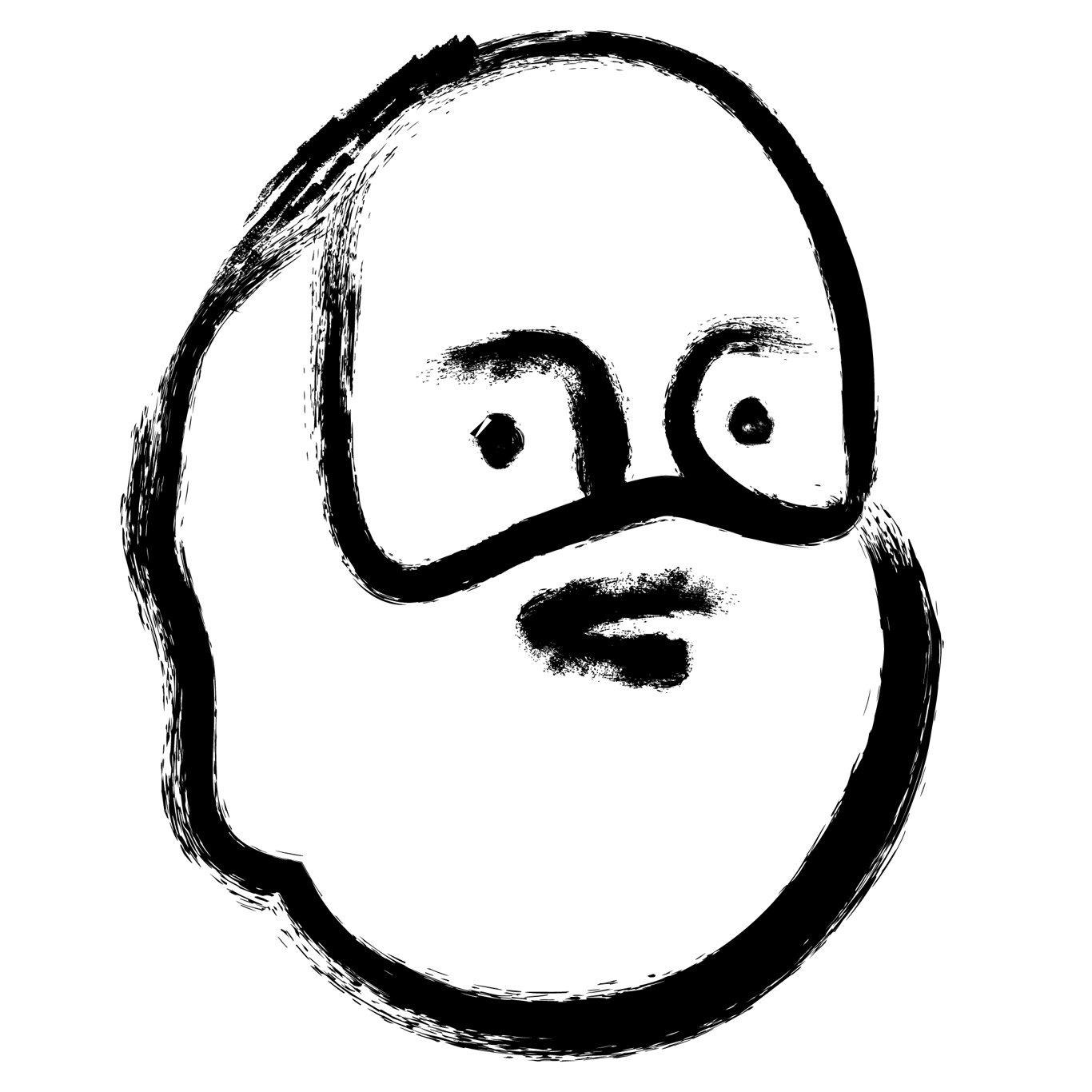現代人的輓歌 ── 讀黃碧雲的《七宗罪》

作者:Roger 難度:★★☆☆☆
一
人置身其中、承受無盡的苦痛煎熬的場所,稱之為「地獄」 ,而「罪」則是導致人下地獄的原因。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中,人因為犯罪而下地獄。從最基本的意義來說,罪源於人對上帝的背離。罪使人沉溺於世俗欲求而棄絕神,因而人要為此贖罪,在地獄永恆之火中輾轉呻吟。
但,假設上帝不存在,罪是否還有意義?地獄又會否存在?這正是黃碧雲在其作品《七宗罪》中所要探討的問題。作者透過七個獨立的故事,為人的「罪」和「地獄」賦予一個現代意義。她從新詮釋了中古時期基督教的七宗罪──「饕餮」、「懶惰」、「忿怒」、「妒忌」、「貪婪」、「好欲」和「驕傲」,描繪出它們在香港這個現代社會中如何呈現。她的結論是:現代社會的人,根本就是活在地獄之中,而且完全沒有出路。
現代社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會?構成現代社會的核心概念,就是價值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價值被視為只是個人主觀選擇的結果,而沒有普遍適用於所有時代地域的客觀有效性。人類理性的抬頭使得傳統倫理道德理想失卻了以往對人的權威與約束力。換句話說,人終於憑藉自己的能力,成功掙脫傳統的枷鎖,得到自由。另一方面,由於個人的選擇被看成是價值的根源,個人的地位大大提高。跟傳統社會中個人附屬於群體(國家/社會/家庭)不同,獨立自主性成為了人的本質、自我的全部。隨着人對價值和自我的觀念改變,社會亦由教化人民、培養人格的大家庭,轉化成個人追求自己欲望的場所。現代社會的這種特點,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上分別表現為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作者所要展現的,正是這樣一種個人主義如何產生把現代人拖進「地獄」的各種「罪」。
二
如上文所說,現代人大多接受價值主觀主義。往好的方面看,人終於成為自己的主人,自己價值的根源。問題是,隨着傳統(包括宗教)的權威消退,人也喪失了生命意義的寄託。如果一切事物──包括人生理想──都只是因為個人的選擇而有價值,我怎知自己有沒有選錯?而人是會犯錯的。理性能夠幫助我們達到既定的目的,卻似乎不能確保它們具有真正的價值。因此,談甚麼人生理想、終極關懷,盡皆成為不切實際的空話。另一方面,人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意味着個人跟社群的內在關係不再。人不能再從對家庭、社會和國家的效忠奉獻中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人,成為了一個孤立的原子。
在這種情況下,人可以真正依靠的就只有自己,可以切實掌握的,就只剩下追求自己當下慾望的滿足。每個人都只以自我為中心,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一切重要,以為單憑自己能夠解釋、解決一切問題,這就是「驕傲」。就像〈驕傲〉中的黃玫瑰,作者把她描繪成一個聰明理智、沉醉於數學(人類理性的最高表現),但卻完全不理會身邊人的一個數學教授。朋友說她「想自己的事情比較多」(頁219),母親也說她「沒有心」。實際上,理性會帶來悖論,而人是何其渺小,面對世界時是何等無能為力。黃玫瑰後來因抄襲別人的論文而失去教職,被迫重新投進社會,才驚覺自己的孤立,發現自己完全不能在現實社會中生存。她的罪是驕傲,而生活,便成為了她的地獄。然而,人的自我中心還會進一步引發出其他性向缺憾,造成更多更大的苦痛,最後使我們生活的世界本身成為地獄。在這個意義下,驕傲為一切罪之至大。
三
客觀價值理想不存在,人只有借慾望的滿足來填補理想的失落。於是,人便要不斷的、更多的佔有金錢(和權力),把一切變成我的。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將負債變成資產,將資產變成更多的資產,就是遊戲規則」(頁135)。人的尊嚴決定於他擁有多少,如〈貪婪〉中的戴芳菲要賺錢,「而且要快」,從而「有很多很多的尊嚴,很多很多的自主」。在這個不斷擁有更多的過程中,人會越來越害怕失去,因而好像方玉樹般失控地去懷疑身邊的一切,最後弄得甚麼也沒有。這種建立在擁有之上的尊嚴,原來「這樣便宜,甚至沒有一個價錢,人們隨手將之奉出」(頁163)。以自我為中心,結果竟然是自我的迷失。
最關鍵的是,可以佔有的東西有限,新的慾望卻會無休止地產生,且越來越難滿足。因此,「只有透過人與人的殺戮,我們才可以有更多」,在這個意義下,「我們都是劊子手」(頁172)。換句話說,每個人的貪婪使得所有人都處身地獄。
四
人的自我中心,使人連愛也不能。在〈饕餮〉中,子寒對如愛不饜足的需索,不單令得自己性無能,更把如愛扭曲成一隻要吞噬一切──子寒、冬冬、小喬和其他不知名的人──的暴食獸。當人只考慮自己,以為只要我對你好,你便是屬於我的,使愛也成為一種佔有的時候,愛原來可以是「所有罪惡的根源」(頁25),家庭這傳統社會的最後避風塘則化成人互相折磨的終極地獄。
當一個人不懂愛,得不到愛,便會因害怕受到傷害而越發封閉自己。〈懶惰〉所說的怠懈,指的是香港人式的勤勞。像篇首出現的男子:「做什麼事也全心全意,像每個香港人一樣很勤勞,同時做六、七、八件事情,他絕不會浪費時間,沒有甚麼好挑剔的。」但這種勤勞其實只是心靈懶惰的面具。人透過工作使自己對自己、對別人變得麻木,一切都無可無不可,無所謂。對自己逃避,其實便等於死亡。人都渴望與其他人溝通(如傳真人受了重傷堅持要撐回傳真房),而這漠不關心的冷淡會影響、傷害身邊關懷你的人,使他們最終也放棄自己。這內心的冷漠和不動,這懶惰,便如瘟疫般,一個一個,擴散開去,人間便成了地獄。
原子式的個人不單不能為自己的人生理想找到依歸,不能跟身邊的家人朋友建立真正的關係,更難在社會國家中尋得自己的身份認同。對香港人來說,這點尤為真切。〈好欲〉中排山倒海般湧進湧出的名字,反映着九七前後過渡時期,政客投機者對香港的愛慾,那種欠缺忠誠,只求剎那歡愉的一夜情心態。香港這沙崙玫瑰,只是大家滿足慾望的場所,而「混濁的世界何嘗有忠誠」(頁186)!問題是,沒有對國家社會的認同與忠誠,香港這個所謂家,就如一個單純肉慾上的性伴侶一樣,無論它多美麗,多能夠滿足我們的慾望,也不能救贖我們空虛寂寞的心靈,反而只會成為誘惑我們陷身其中不能自拔的放縱地獄。
五
作者筆下的地獄,最可怕的,在於其完全沒有任何出路,不存在──至少對現代人而言──任何救贖。
〈忿怒〉中居住在公屋的低下層市民,「各人有各人的眼淚」(頁64)。人與人之間的敵視仇恨,只是眼前可見的表象。背後壓迫着他們的,他們怨毒的控訴所指向的,是整個世界,這個由冷漠自利孤立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什麼世界不如燒了它」(頁65)。這個世界既是很大很大,大得把人壓得喘不過氣;同時卻也很小很小,小得把人困得無處可逃。人在這個世界中並沒有選擇,要生存便得承受這些折磨。或像九月一樣,「宣佈和這個世界從此決裂」(頁78)。都一樣。
〈貪婪〉的戴芳菲好像有兩條路:拾起或不拾起那個十元硬幣,追求或是捨棄。但到頭來,原來「救贖並不是捨棄」(頁174),只是殊途同歸。都一樣。
更可悲的是,每個人根本從來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地獄。〈妒忌〉中的張悅、無憂和可喜三個(一個?)少女擁有值得成年人妒忌的青春──一切都那麼新鮮;可以不顧一切,盡情表露自己的個性,「喜歡幹什麼便幹什麼」(頁91)。如此自由,是最幸福吧?我們妒忌。但她們自己呢?原來只是覺得「這麼多的第一次,令人疲於奔命」(頁88)、「真無聊」(頁96)、「自由得可以發瘋」(頁105),「……徬徨,……一無所有」(頁113)。成長呢?連那不值分文的個性也失掉(死亡),只剩下「說別人想她說的,做別人想她做的,而她亦相信,這就是她想的她做的」(頁124)的悲哀。青春的空虛暴烈,成長的迎合冷漠。都一樣。
六
總括而言,我認為作者成功地以獨特的手法呈現出現代人的困局:地獄之火就是人在現代社會中體驗到意義虛無,其根源在於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子論式個人主義自我觀。要離開這無邊地獄,我們似乎必須重新去思考:人,究竟是甚麼?
《七宗罪》
作者:黃碧雲
出版社:大田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