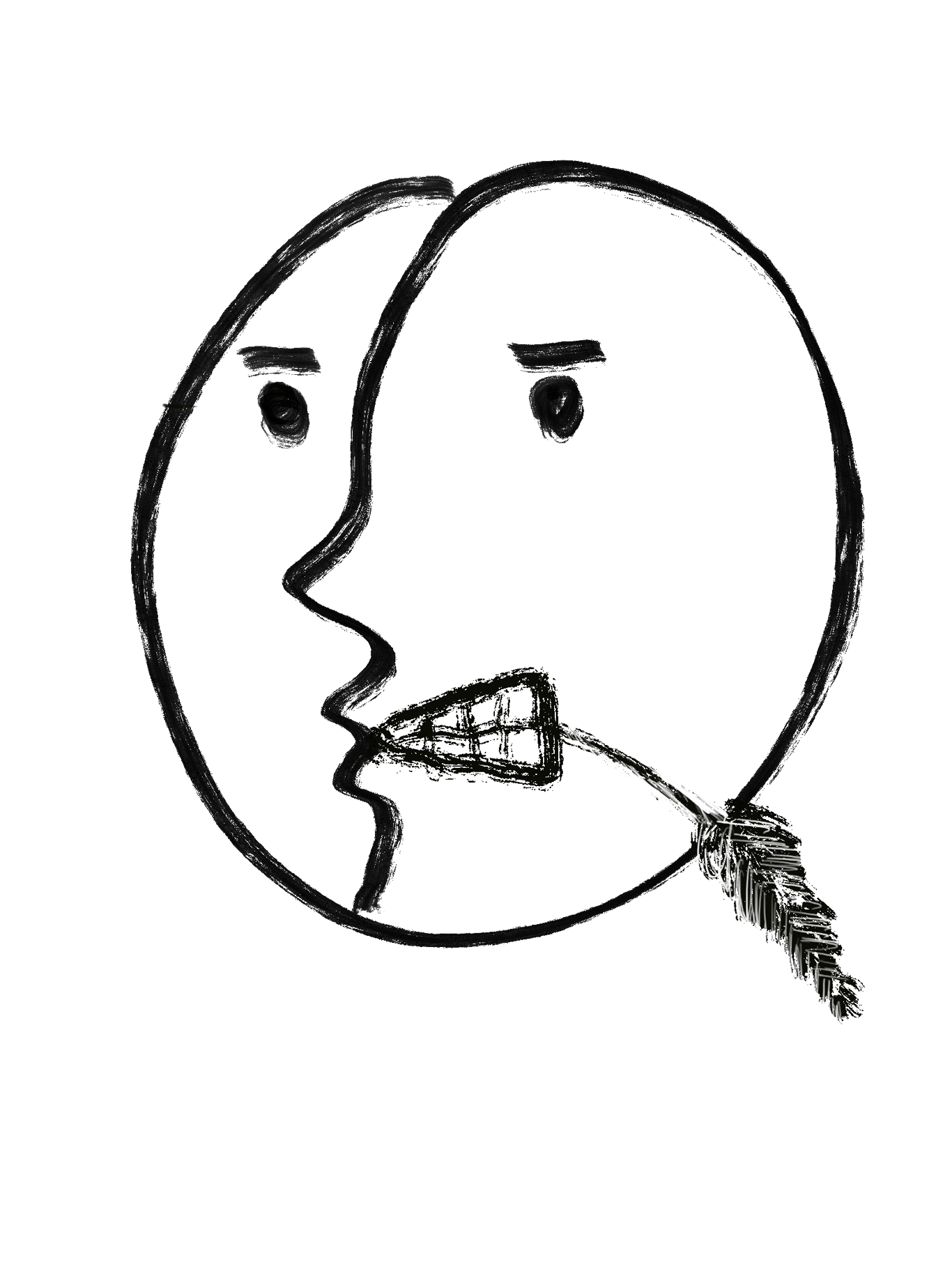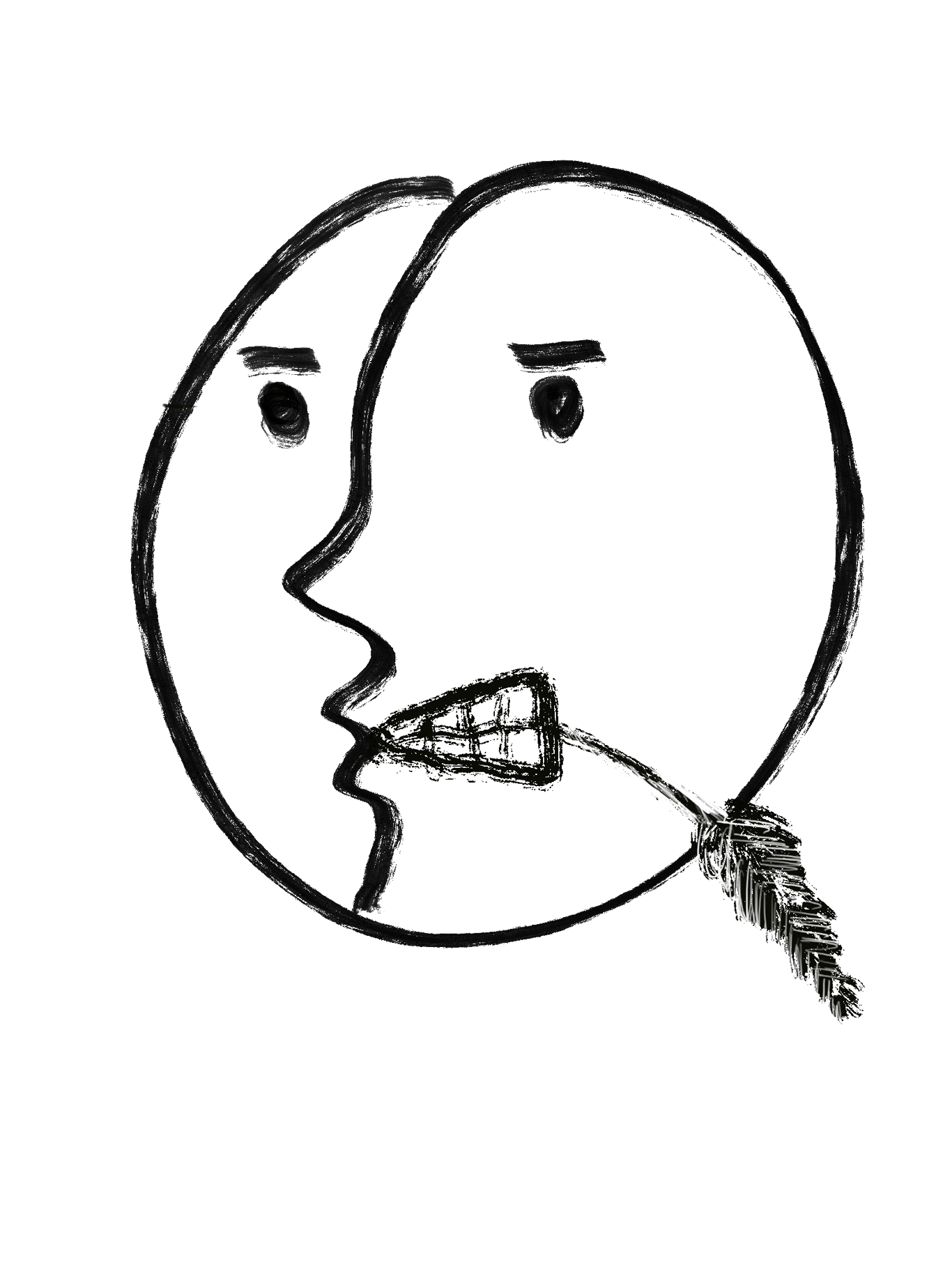寫作的人,冒的風險太少了
在《碎片》中有封信看起來是出版社要求費蘭特針對「當時的義大利時事」寫一篇政治寓言小說被她拒絕了,她認為這些並不會起到什麼作用,提到「一個寫作的人,當然會冒一定的風險,但不會有生命危險或會進大牢」,前提是指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受到保護的情況下。
我從以前就一直在思考這些事,寫作的人隔岸觀火,很容易信口開河,有的抓到議題時的貪婪,甚至讓人覺得在幸災樂禍(要借題發揮、蹭熱度),就像時政節目中出現的那些名嘴們,我幾乎沒有聽過他們講任何有建設性的話,費蘭特的說法就是「只是用手肘撞了一下那些心知肚明的讀者,他們的內心早就很贊同你了」,反過來說,讀者在接受資訊前也選擇了他們已相信的閱讀,寫作者冒的風險極其微小,甚至連被人討厭的風險都免除了。
費蘭特說到底是一位比較真誠的寫作者,這是我最近讀她的文字所得到的結論。她不願寫一個自己無法坦然面對的文章、發現自己對記者的問題感到虛榮時也不會接受採訪、她還會以很長的文字寫下擔心被別人誤解而作的解釋(這樣不夠酷,但她表達自己的在乎,是很真誠的)⋯⋯以上原因,讓我感覺這個不願意表明真實身分的作者才是真實的,說起來似乎是蠻諷刺的事。
上上週末我臨時住院,暫停了幾天的工作(只能做些聯繫的事情),考慮了兩天和Jeger說明無法擔任「碼色市」活動的推薦人,其實我已讀了多數投稿者的文章,有預感自己會因個人喜好而選擇,也可能因為要趕著補回工作進度而隨意地閱讀文章,雖然不是專業的比賽,但這樣總是不太公平,因此就小題大作的爽約了。
前面花了幾篇文章說明我讀費蘭特產生的共鳴不是由於將她視為偶像,更可能是我自以為的相信自己的想法和她接近,例如我不會想發表任何議題的文章而替自己掛上某某主義的支持者,在政治立場上也是一樣,前陣子法國老友叫我玩一個政治立場的評估題目,我做出來就不意外的是人道主義、偏右派但並非民族主義、資本自由、支持環保⋯⋯總總我認為很符合「我」,但又不符合一個合理人設的數個標籤。
我一直相信寫作者會從文字中表達出自己的思考脈絡,因此不用為了個別事件再去發表己見(發表也是好的,但我認為意義不大),很多又是隨著輿論的走向,成本實在太低了,像費蘭特說的報章雜誌中已充滿了指名道姓針對國家元首的評論文章,即便如此對於政治的走向也未必有作用,更不用有那些暗喻的文章——但我又為什麼扯到這一段,原本有一段想表達的意思,中途去忙點烘焙的事情又忘了——想起來了,是要寫媒體控制輿論,企業集團控制的媒體,本身就是一個政黨,但又不是在講美劇《Succession》的劇情,自動放棄這一段。
最近反省我對台灣女權的看法太樂觀且愚蠢了,雖然我一直不會把任何檯面上的人視為神,但也沒想到墮落程度是這樣,十幾年前我在校園中也遇到不合理的事情(教授要我半夜開視訊並說些噁心的話),當時以為就是一種調情,我也能很明確的拒絕,因此也沒太放在心上,但幾年之後才知道也有人經歷和我類似的事,而且成為「既遂」案——通常最初聽到這類事情都會是師生戀,之後才知道是被侵犯——若是我當初有通報,或許就不會有接下來的悲劇了?
以前我都開玩笑說那是學公關的專業技能,我蠻容易就能妥當的拒絕一個人也不會激怒對方,也許是這樣以前才不是很同理別人為什麼無法拒絕不合理的事,但不應該是要我們夠世故、夠圓滑才能全身而退,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在校園和職場中,絕不是像法國人說「調情和騷擾的界線不清」,那些行為人主觀上明明是很清楚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