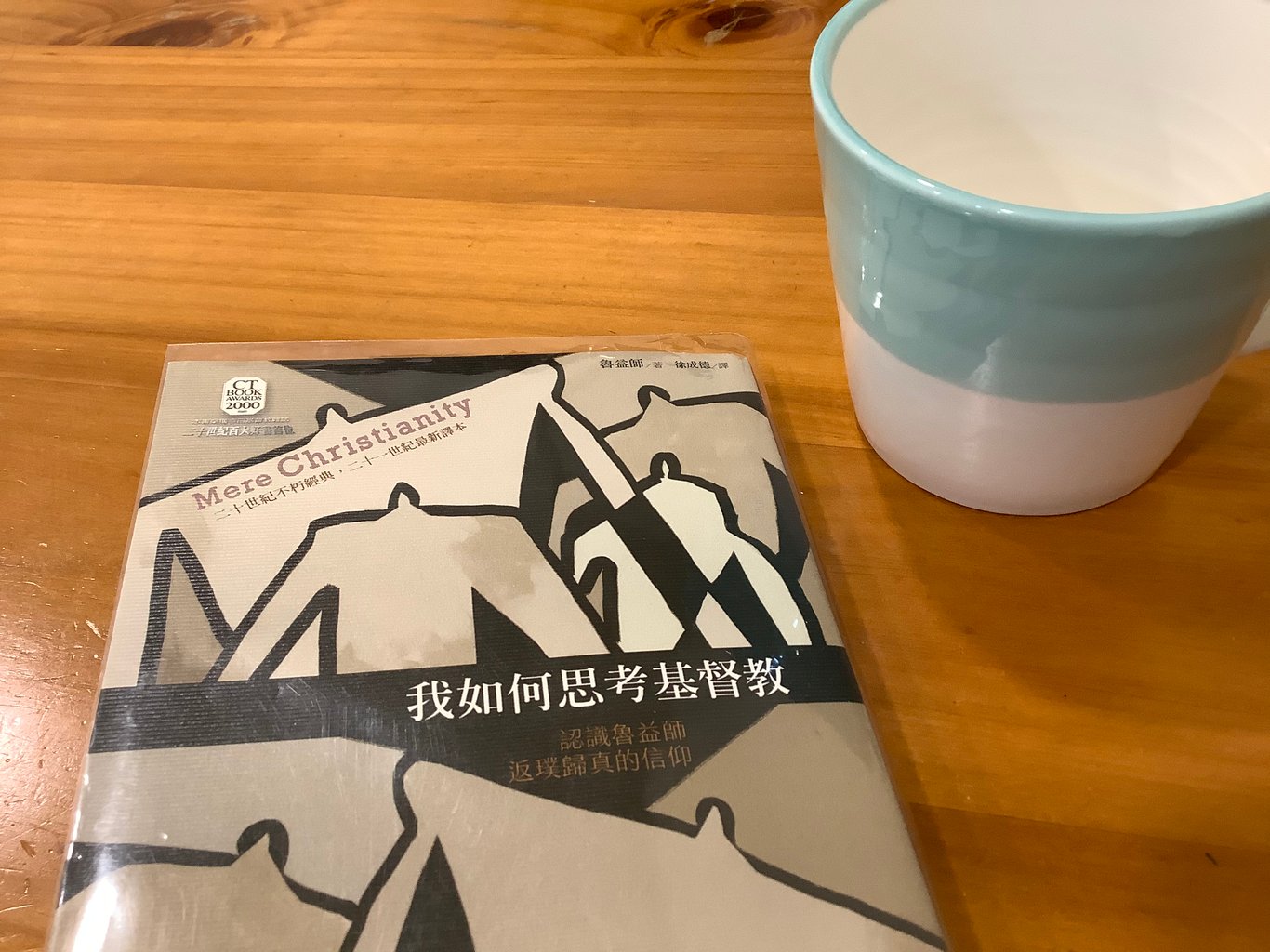自卑與超越--生命意義的追尋
阿德勒的這本著作,在心理學中應該算是樹木的粗枝這樣的存在。從1930年阿德勒離世以後,個體心理學在這粗枝上長出了許多的枝椏。在接下來的幾十年,發展出許多快將父母搞瘋的如何養育出心理健康的孩子的理論學派。在二十世紀初,阿德勒心理學提出的是心理學當代的一個新的方向與領域。阿德勒不同意佛洛伊德將所有心理上的問題都歸因於性慾的不滿足。他認為人並不是單純被身體決定的動物。人有一種奇異的需要,就是對[意義]的需要。人類在心理上需要與環境、與他人、與自己發展出一種有意義的連結。當這些連結能夠被有意義的發展,就能發展出健全的心理。
個體的心理健康,被他與群體的關係深深影響著。個體渴望是對群體來說有意義的存在,青春期應該是發展出這個[創造性自我]的重要時期。一些需求在此時變得迫切而急切:我是誰?我對別人來說是可喜愛的、重要的存在嗎?他會發現,他無法完全的自我,也無法完全地忽視別人對他的要求,他必須在他的內在要求,和周圍的重要他人對他的要求之間,找到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平衡點。事實是青少年常常痛苦的在這當中擺盪,為了保護那脆弱的自我認同,不得不對一切的質疑抱持敵對態度。
在取得認同,於任性的自由之間,青少年會逐漸找到妥協的平衡點。這件事多半發現在不知不覺之中。有一天,他會忽然發現自己長大了,感覺到自己放棄了什麼,失落了什麼,也得到了什麼。這些折衝與磨合是在感覺快滅頂的掙扎中完成的,所以幾乎不像是有意識的結果。
陳丹燕在[一個女孩]裡,描寫她在八歲到十八歲之間,在文革當中度過的童年。在那個周圍的價值體系,被全然推翻挑戰的時代,一個孩子如何艱難地找到自己的認同並長大。你可以讀到那個變動的時代背景裡獨特荒謬的故事,但是就一個青少年在這個時期所經歷的,即使沒有大時代的動盪不安,也是同樣波濤萬丈的過程。所以這個故事不管在哪一個時空背景下的人,應該都會心有戚戚焉。
"在我十五歲的時候,時常急切地希望擺脫眼前死寂而且空空如也的生活,我那麼著急地找著,可總是什麼也找不到。"
渴望生活的[意義],因為這是,按照阿德勒所說的,和性慾一樣,是左右人基本動力的需求。
在我們夠小、夠年輕的時候,都會思索尋找,生命是否有值得傾注一切代價追求的事物。這個事物似乎不是周圍的人,不是從父母能告訴我們的答案。有時我們會找到一個偶像,然後忘我的投注所有喜愛,這是作為一種練習,將來找到那個我們生命真正的熱情的事物時的練習。
生命是否有值得為之活並且為之死的事物?這個問題,父母或其他的大人無法給他答案,因為他們已經找過他們的答案也已經妥協過了。對於每一個個體來說:[如果那不是自己的,那就不是真的。]
[一個女孩]裡那個懷著獻身的熱情自願下鄉的朋友[鈴兒]。
"鈴兒說,我們現在只是活著,而不是真正地生活著,而我們應該要真正地生活。可我們卻不知道怎樣去找一份真實的、有信仰的生活。"
阿德勒說,每一個個體所找到的那個答案,不能對群體沒有意義,否則無法產生有意義和諧的連結。和與群體產生和諧的連結,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條件。妥協一定會發生,這是為什麼最後我們所有的表達都帶有某種目的:要不就是為了被了解,要不就是為了被接納。這兩者有時是如此的彼此衝突,令人絕望。
如果沒有一種信念,那就是我們的被造本身,就是有目的,並且又意義的,這些意義的尋找無法避免它扭曲的結果。會不會我們的自我並不是如阿德勒所說[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原本就在那裏的?當我們被造的時候,意義就已經產生了?
阿德勒說:"真理意味著人類眼中的真理。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真理,即便還有其他的真理存在,那也與我們人類無關,我們對其從不知曉,那麼此真理也就毫無意義。"這是阿德勒的看法,但是個體心理學發展到今日,更多的心理學者在研究當中發現的是人在靈性上的需求,靈性的需求關係到人更根本的需要與滿足,不是過去的心理學能夠涵蓋的。
阿德勒說對了一件事,人並不是被欲望所驅使的動物,而是被意義所驅使的存在。意義的建構關係著個體是否能在他的生命當中自我實現。你認為你是誰,就決定了你能做到什麼、你的決定、你與人的關係。
或許[我是誰]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我們能告訴自己的答案。或許是一個我們需要去提問的答案。因為這個問題是[高過我們的]。那個內在最根本的有意義的連結的需要,存在於我們和創造主之間。
很多時候我們掙扎著要成為一個別人眼中有用的人,成為一個別人眼中成功的人,在這當中付盡一切代價,卻至終感到[被利用、被損害、被剝奪]。有多少可能我們付出一切追求的,最後卻使我們感到空虛?原來那個意義與價值,對於我們個人,並不具有真實的意義。
也許那是一個值得被認真看待,被認真提問的問題。[我是誰?][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問對了對象,在終點時,我們會滿意那個曾經活過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