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日落之地:讀Paul Rabinow《摩洛哥田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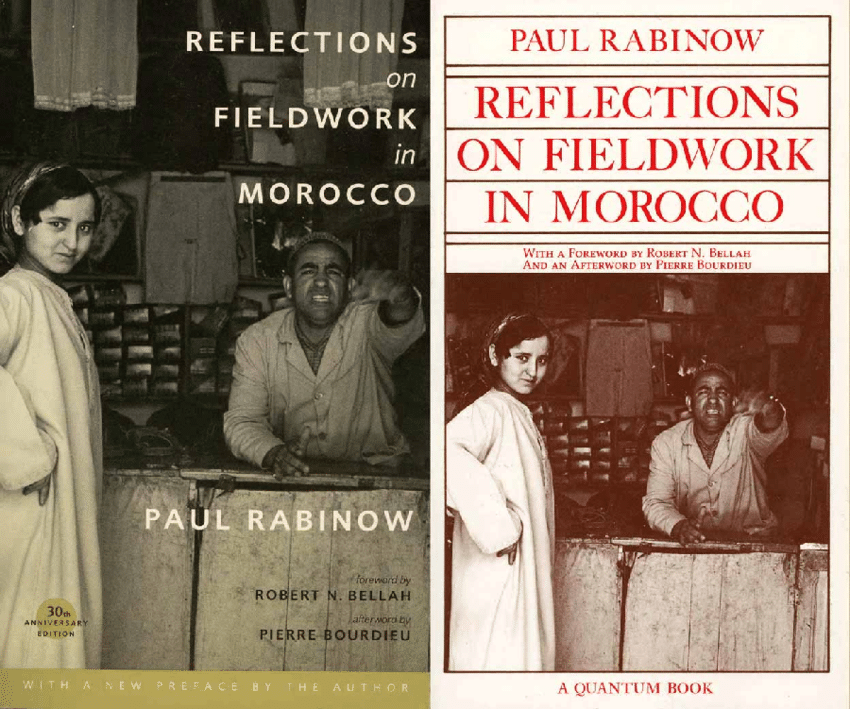
Paul Rabinow,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有段時間我偶爾會經過Rabinow的研究室。門常開著,但燈總是暗的,牆壁漆成藏青色,他獨自坐在深處,像一尊沉思的雕像。我們曾經有過一次真正的交談,對我拋出的好幾個問題,他沒有一絲不耐煩,但顯然也沒有半點興趣。他一字一句回答我,有禮、精確而冷冽。加州明朗的陽光從窗戶照了進來,是那個藏青色的房間唯一的光源,早晨也像是黃昏。
我可能是幸運的。一位朋友在大學時期讀了《摩洛哥田野反思》後,興奮地預約了Rabinow的晤談時間。「教授,我很喜歡你的書。」「你讀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嗎?」「沒有。」「那你根本沒有讀懂這本書。」崇拜一去不復返,由愛生恨只需要一句話。他奉勸我們:「有一整段關於一夜情的內容,最好直接跳過。」
書裡確實有即使從今天的標準來看,都令人不禁懷疑「這樣真的可以嗎?」的描述,最難以置信的包括人類學家與報導人女性親戚的性關係。就讓讀者皺眉的程度來說,《摩洛哥田野反思》的坦白恐怕離馬凌諾斯基的私人日記不遠;就寫作主題而言,它卻更像李維史陀曲折的《憂鬱的熱帶》。

兩本書的出發點都是作者對自己所屬的西方文明的厭倦,然後在熱帶無盡的折磨下等待這份厭倦昇華。只不過《摩洛哥田野反思》沒有肆意生長的叢林、惱人的蚊蠅與狩獵採集部落,而是貿易商隊往行來去、盛產橄欖與無花果的北非大地。
泉水豐沛的山麓被摩洛哥人稱為dir,字面上的意思是乳房,因為它孕育出豐饒的農田、果園與橄欖園。氣候宜人的城鎮沿著斷層帶上的dir分布,是周遭柏柏人部落的貨物集散地,塞弗洛(Sefrou)就是其中一座城市。高聳荒蕪的阿特拉斯山脈聳立在背後,讓塞弗洛看起來像是一片綠洲。
若你繼續往山的方向前進,會先遇到仙人掌環繞的小鎮阿塞巴(Azzaba),一個座落在高原上方、土壤貧瘠的商業中心。過了阿塞巴,就是阿特拉斯山腳的丘陵地帶了。道路變得陡峭而崎嶇,聚落緊貼著水源分佈,最後,你將會抵達綠意盎然的村落西迪拉森(Sidi Lahcen)。兩座雄偉的建築是村子裡最醒目的地標:巨大的白色清真寺,以及一旁以綠磚砌成的聖人之墓。《摩洛哥田野反思》裡的時空,便是沿著Rabinow將田野地從塞弗洛轉移到西迪拉森的這條路線上展開。
除了截然不同的熱帶地景之外,《摩洛哥田野反思》與《憂鬱的熱帶》還有一個明顯的差異,那就是Rabinow賦予了報導人立體的面貌。他與幾位當地人物的結識、互動與道別,推動了敘事的進行。這些人慷慨地給予他幫助,卻也常是痛苦的來源。我們都知道「報導人」是田野工作的基礎,但報導人不僅活在另一套文化邏輯中,他們在自己的社會裡也佔據著不一樣的位置,有各自的動機與盤算。

報導人Ali與Rabinow的爭執是全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潮。在塞弗洛經營小本生意的Ali是Rabinow最可靠的夥伴,也是引介他進入西迪拉森的關鍵人物。一天,Ali邀請Rabinow到鄉下參與一場婚禮。Rabinow因為身體不適而猶豫,Ali向他保證只待一小時、打個招呼就走。傍晚,Rabinow載著Ali出發前往婚禮地點。婚禮在傳統格局的大宅院進行,宅院中央的空地鋪滿稻草,是歡慶群舞的場地。客人們享用熱茶、橄欖油燉山羊肉與剛出爐的麵包,人類學家慶幸自己沒有缺席。不過,時間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山區的氣溫開始下降,他想告辭,但Ali不見蹤影。
在鼓手烘烤手鼓的中場時間,Rabinow在人群中找到Ali。「沒問題,再待幾分鐘就好。」Ali說。一個小時之後,Rabinow得到了一樣的回答。凌晨三點,他忍無可忍,決定直接回家。Ali在最後一刻鑽上車。夜路上,Ali平靜地問:「你開心嗎?」人類學家據實以告,說他因為對方食言而不悅。「你開心嗎?你不開心的話請放我下車。」Ali堅持。Rabinow表示他只想趕快回去,其他無所謂,但Ali鐵了心要Rabinow承認他玩得開心,甚至作勢跳車。最後,瀕臨崩潰的Rabinow請他下車,Ali在漆黑的公路上獨行,拒絕再度上車。
隔天早上,Rabinow懊悔地醒來,以為他跟Ali的交情和他的摩洛哥田野一起完蛋了。難道田野工作者必須忍受所有的不便嗎?如果田野工作就是要訓練我們成為沒有情緒的透明人,那我不要了。他心想。他找到Ali,出乎意料地,兩人只花了一個下午就和好如初,彼此的關係甚至大有進展。
Rabinow試著從摩洛哥文化的角度來理解這個事件,Ali堅持要Rabinow承認自己有善盡主人的責任,因為慷慨(karim)是對男人最高的讚譽,直接連結到真主的美德。在摩洛哥的平權社會,邊緣策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受慷慨意味著屈從。從一開始,Ali便一再試探Rabinow的底線,人類學家的逆來順受被理解為示弱,只會引來更強勢的支配。車上的鬧劇宣告了Rabinow的底線,他的爆發反而成為兩人第一次真正有意義的溝通。

類似的情形不只發生在Ali身上, 沮喪、挫折與憤怒,Rabinow屢次被逼到極限,新的可能性卻又總是在極端之中浮現──然後,人類學家順利進入到摩洛哥文化裡更「深」的一層。最後,在另一位虔誠的報導人的引導下,他終於觸底,探到了那道無法超越的牆:作為一位非穆斯林,他與當地人的對話終究是部分的交換,然而,這樣的交換卻也已經彌足珍貴。
對Rabinow而言,「他者性」的存在不是因為任何本質上的差異,而是由於彼此不同歷史經驗的總合。全書的結尾是這樣的:「唯有在我們認知到差異、並且對自己的傳統所賦予我們的象徵忠誠的時候,對話才有可能。」人類學家對自身文明的厭倦有了著落,是時候返程了。五十多年過去,他以研究西方現代性為志業,沒有再回頭。
一路順風,Monsieur Paul。在馬格里布,撒哈拉的日落之地。
Paul Rabinow(1944–2021)是美國人類學家。在Clifford Geertz的指導下,Rabinow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取得人類學博士,以摩洛哥伊斯蘭村落的社會歷史為博士論文。他長期任教於柏克萊加州大學(UC Berkeley),關注理性、生醫科技與「當代」的人類學方法。除了《摩洛哥田野反思》,他的幾本代表性作品包括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1989)、 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 (1993)與Anthropos Today: Reflections on Modern Equipment (2003)。在人類學之外,Rabinow也以引介傅柯的作品聞名,例如他與Hubert Dreyfus合著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關鍵字:田野方法、反身性、自我、伊斯蘭、北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