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金宇澄《繁花》:卑微的說書人與「不響」的策略(一)
讀書一向慢,寫字拖磨再三,加之對趨勢的鈍感,等到繁花熱冷卻了,才慢慢把閱讀筆記整理出來。從王家衛拍《繁花》的消息出現,到我從研究所畢業、工作,中間聽聞角色替換、停拍,種種傳言,劇集面世的聲息一點也無(甚合王氏作風),去年底海報出來,像我一樣一度迷戀王氏美學的人,不知道是不是也難免對影劇《繁花》失望。喜好構不成作品好壞的原因,改編當然是創作,都是可以接受的理由,何況我只看五集就棄劇——但對一個鐘愛小說《繁花》的人,著迷於書裡那些疼痛、狂熱、斑駁陸離拼貼混揉的年代,那許多平凡之人無從想像的瞬刻(小說魅力如是),而對劇裡俗透的商戰、言情與浮誇做作感到不耐,當然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劇集《繁花》組織種種懷舊意象詮釋某種「滬上文化」,再延燒成路人皆曉的話題前(且不論參與擴大風潮的大眾是否曾在此一上海時代中「在場」),小說出版之初,高高低低的討論聲量就有不少。整理手邊的資料,關於小說/影劇《繁花》的論述,無論新穎或重覆的,大體均可歸入三類:《繁花》影劇版優劣、方言(滬語或上海話)、滬上都市文化。
《繁花》影視化、滬語與摩登都市文化
王氏版《繁花》開頭,講了中國九〇年代改革開放期間,股市新制下,普通人阿寶在上海炒股、做貿易致富的暴發戶傳奇,恰好是小說省略的人物經驗。小說中,阿寶發達背景,至多以滬生口中「一個老朋友,做非洲百貨,也做其他」一句輕輕滑過,影劇大概是掌握住了這段空白,以「前傳」形式將它嵌入故事宇宙。
王氏繁花的跌宕起伏充滿戲劇性,從滿屏負評到一片贊美,延燒出滿城商機。不說網路效應,歷史學者讚揚它鏡頭語言、台詞和敘述脈絡的利落巧妙,而「老上海」的象徵,與商業、現代化、文化之都連結,又一次成為過往繁華的追憶焦點。這場禮讚盛典中,零星有一些嚴肅的質疑,批評影劇架空真實歷史基礎,直指它迴避的內容。識者言:「我們不能清晰地看到劇版阿寶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如何塑造了他的價值觀。他毫不遲疑地縱身躍入了改革開放的大潮,無比順滑地接受了新的時代邏輯……同樣被拋卻的,還有原著小說的平民視角。」或謂此劇迎合「說好中國故事」的官方標準,自我審查、篡改歷史記憶,美化殘酷過去:「假裝改革開放不是因為十年文革而民不聊生,假裝南巡講話前沒有發生89也没有89後的搖擺(筆按:89=64),男主只要跟著好政策即可發家致富……這才是劇版《繁花》的主邏輯。」亦如外媒觀察,劇中的海上繁華雖非失真,只不過,我們的懷舊者多是當年奢華黃河路艷羨的旁觀者。
隨劇集走上潮流的還有滬語。方言創作並非新事,論者往往比較金宇澄《繁花》與晚清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二者自有共通處,同為長篇、連載出身、在宏大背景下專注講上海情事、自覺用滬語創作。但方言的彈性允許它隨時間人事變化,《海上花列傳》的上海話(時屬吳語範疇)屬該說部出世的上海,自與20世紀上海的上海話存在差異(張愛玲將《海上花》譯成普通話本目的之一即此),更別提韓邦慶在方言對白上刻意造字;相反,《繁花》基於寫作策略與現實層面,用的是消除了閱讀門檻的「改良滬語」。有趣的是,《王家衛鏡頭下沒拍出來的:從小說到電視劇,兩種「繁花」裡的上海話》提到漢語學家沈家煊以真正「漢語腔」高度評價小說《繁花》,言自白話文運動後,白話書寫以英語的句式與文學為參照系,現代中文創作普遍受「翻譯腔」影響,而《繁花》人物語言(口語、方言)和敘事語言(書面語)卻成功擺脫了這一影響。立論新穎,值得一覽。
至於劇集中的老上海城市文化,人們關注熱議的無非是「作為生活方式的文化」(特里·伊格爾頓提到的四種「文化」詮釋面向中,最易被過度詮釋的一種),無非是城中的娛樂、商業、科技;李歐梵《上海摩登》指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乃「生產—消費」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涵蓋了新的文化活動形態及其表達方式。
影劇、方言與城市化,評論已多,無需錦上添花;關於原著小說創作的議論,相形下冷落了些。《繁花》與寫實觀、寫作傳統、小說評點的影響關係,它的技藝、寫作策略背後的意味,可談處太多,要一一講來,也非易事,不如找個小小的起點,看看能否引出點什麼有意義的討論來。
作者論與寫作原則:卑微的說書人,及其現實主義
金宇澄數次提論「小說作者」含義,《繁花 · 跋》曰:「我的初衷,是做一個位置極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取悅我的讀者——」(頁608)書末附錄專訪,再次強調:「我一向認為,作者其實不是那麼重要的,他們並不是上帝般的無所不曉。……作者太容易自信、自戀,高高至上了。我認為寫作者絕非是『人類靈魂的設計師』,只有上帝才是。人不該自擬為上帝。……讀到全知視角小說,總讓我疑慮多多。作者真有辦法切實地瞭解一個人?」(頁613~14)
並列以上引文段落,似乎含糊,如果仔細梳理,這一「作者論」大致可如下劃分:
一,作者無需在小說中教化讀者,或訴諸真理。
二,作者的視角有限,因而在小說敘事中呈現為全知全能,並不合理。
第一點涉及小說家講故事的姿態,其結果形塑了作品調性。據其說法,小說作者是講故事的「說書人」,不是將思想或真理傳遞給讀者的「人類靈魂的設計師」(註1),作者和他筆下人物、讀者地位平等,作者要對讀者抱有敬意。這可能與金宇澄過去長年的文學編輯身分,及《繁花》的誕生過程有關:也許是一個編輯審視大量作品與作者後形成的判準,或與《繁花》初連載於網路時吸收各路讀者回饋的創作經歷有關。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謙虛的創作者對讀者群體的仰視姿態,更重要的是:圈出了他對小說本質的定義。
但這並非什麼新觀點。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普通讀者》引述山繆·詹森(Dr. Samuel Johnson)《格雷傳》一段話,以創作者∕讀者的雙重身分肯定普通讀者的審美能力:「我很高興與普通讀者們意見一致;因為,在所有那些微妙的高論和鴻博的教條之後,詩壇的榮譽桂冠,最終還得取決於未經文學偏見污染的讀者們的常識。」或許還可看看阿城如何以「世俗」精神連起中國史事與歷代文本的一脈性:在《閒話閒說》中,從商周甲骨文記錄生活疑難雜症解決之法、儒道思想重實際問題、秦始皇不燒實用工具書,一路往下,將唐宋元明清各類文學體裁均包納到世俗品格中,明代章回小說、話本小說「無一不是描寫世俗的小說,而且明明白白是要世俗之人來讀的」;而世俗空間的失落,無非是「禮下庶人」的後果,無非「權力的道德規範延入俗世」。
第二點與敘述角度有關。顯然,金宇澄對全知視角的運用不以為然。同樣要強調的是,作者隱退小說幕後,意圖消除全知全能敘述者自由議論的權力,採用這種做法的小說並非前無來者,福樓拜即典型一例。如同第一點的前提,按金宇澄說法,小說作者同讀者一樣都是凡人,他的認知是片面的,來自其經驗背景、直覺或個人判斷,只能看見部分真相而不可能超脫自身局限以超人之眼通觀一切、知曉人事物全貌,就此而言,作者的全知敘述視角悖離了現實邏輯。進一步說,作者不能知悉一切,所以敘事自然應呈現為限知視角。
據此我們推論:正因作者是一普通人,故無需居高臨下,職責只是講好故事,讓讀者在閱讀中愉悅滿足;正因作者是一普通人,不是窺見全局的全知全能者,所觀必有所限,唯能以有限的觀察和瞭解推進情節、發展人物。這兩點構成金宇澄創作觀的基本元素,牽引出一種小說技藝上的、金宇澄所謂現實主義的寫作原則。
只是,現實主義充滿歧義,你能從任何角度與目的加以詮釋,其意義可任意延伸、堆疊增刪。倘若將所有疑問推向極端,不免要問:假如取悅讀者是小說的本職,是否凡能取悅讀者的小說都是好小說?按照第一點的邏輯,取悅讀者的同時,小說可不可以有作者的觀點?或把問題拋得更遠:小說有可能不存在作者的觀點嗎?寫實應抵達何種程度,因人而異;懷疑作者無法全然瞭解自己創造的人物(「讀到全知視角小說,總讓我疑慮多多。作者真有辦法切實地瞭解一個人?」),似乎又與創作常理背道而馳——作者不了解他的人物,創造出的難道不會是模糊概括、片面不全的形象?
思考的梳理仍要回到金宇澄理解的現實主義中去。他說:
小說雖說是虛構,有一種更客觀的訴求。我現在但凡看到小說人物在想事情,內心在折騰,或再看托爾斯泰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寫,我會覺得假。人物在想什麼,想具體非具體的事,别人能知道嗎?
這段論說規定了虛構的權限,主要的強調是「客觀的訴求」。小說邏輯在此與現實世界運作劃上等號:和真實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無法全然互相瞭解一樣,人物內心世界隱而不彰,我們如何可能透視人物所思所感?看來,不僅無法預期作者透露情節與人物的一切,人物亦無法向讀者吐露他所不知情的面向。另一訪談中,金宇澄的現實主義具體內容更清楚地顯現出來:
現實主義的寫法,也就是透過細節,逼近一個人的存在,讓他的真實感自然出來,也表示出作者的熟悉度,所掌握的細節有多少,我自己想想,最真實的部分,寫到三分之二是最好的,太過緊密的就不大方便寫了。最真實的、最有份量的,很難真的下筆。文學還是要有所保留的。
拆分成三段,這番話可作此理會:一,細節使人物立體,所以產生真實感;二,掌握的細節越多,越說明作者對其人物的瞭解程度,人物也越真實;三,即使掌握充分細節,作者創作過程中不得不受各種實際環境因素框束(依前所言還包括個人視野的限制),無法盡訴所知,此為小說之局限。
應該這麼說:作為一種寫作策略,金宇澄的現實主義原則,最終追求的是小說讓人感受到的「真實的效果」,亦即故事與人物之真實感、可信度。正因敘事存在不可言傳與無法觸及處,作者唯能以手中掌握的細節,有限度地讓小說中的敘述者和觀察者(作者∕敘事者∕人物)進行表達或披露事件、人物言行面貌,同時製造一種似真的幻覺:取材自生活知見的枝節、有所屏蔽的視野,給出細節卻又使我們無法徹底看透一切,比如人物的過去未來、比如內心活動,因為現實即是,你只能由可見的事物表象琢磨眼所未及處——「真實」於焉而生。金宇澄另有番對敘述角度抉擇的闡述,提出「文學的欺騙性」,亦說出其寫實觀,可為上述引文補充:
文學常帶有欺騙的意味,其實它是處處有保留的,最有人性深度的內容,往往被作者燒掉或者咽進肚子。這樣推論下來,作者應該給出合理的「空白」才對,讓讀者知道,小說裡很多「留白」是正常的——寫作的追求就是,透過無數細節和回憶,最大程度告訴讀者其中的一部分。
故此,與其說金宇澄否定作者對其人物的真正瞭解,不如視之為一深思熟慮的方法論,一種將讀者角度和閱讀方法代入創作過程,進而對敘事和人物各個部分進行汰選、接合、剪裁的技藝。
至於《繁花》是否確實為了小說的真實效果,擯棄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以及在放棄全知視角後(假如確實放棄了的話)採取哪些角度觀察故事,皆需回到小說中一一考察驗證——畢竟在文學批評來看,作者評論不過是眾多評論聲音之一。有趣的是,金宇澄的現實主義創作論結成了《繁花》多處刻意留出的空隙,讀者津津樂道的「不響」即書中留白之一種,隨地可拾,形成此書的體貌風格。空白書寫對其故事、情節、格調與人物特質的建立,豈不值得細論一番。
◑ ◐
註1:「人類靈魂的設計師∕工程師」這種常見譬喻到底從何處來,十分好奇,順手搜索了一下網路資源,發現這一流傳廣遠的譬喻居然來自於斯大林。據說,他召來蘇聯一群著名作家,聲稱作家的角色對蘇聯發展極為關鍵,促請作家們創作有助於改革的文學、歌頌國家的建設,並稱作家們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engineers of the soul)。 參考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1/aug/19/engineers-of-the-soul-review。
另有一篇文章對「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譬喻進行了有趣的辯證: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95355.html 。
◑ ◐
❈ 參考書目 ❈
1. 金宇澄,《繁花》,臺北:東美,2019年。
2. [英] 特里 · 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著,張舒語譯,《論文化》,北京:中信,2018年。
3.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著,瞿世镜譯,《普通讀者》,上海:譯文,2022年。
5. 阿城:《閒話閒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請我喝杯咖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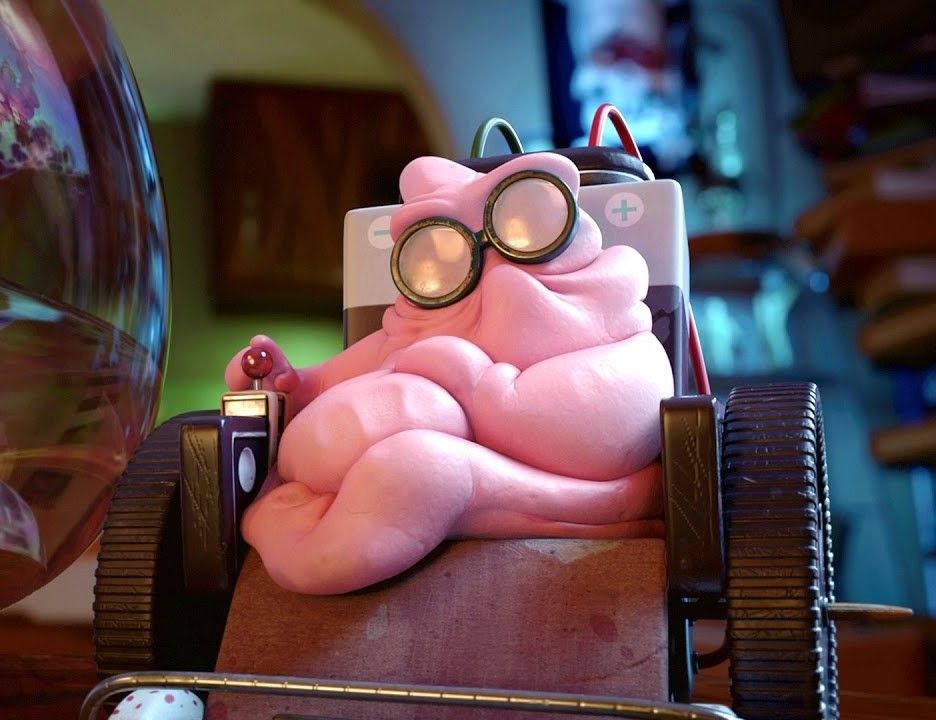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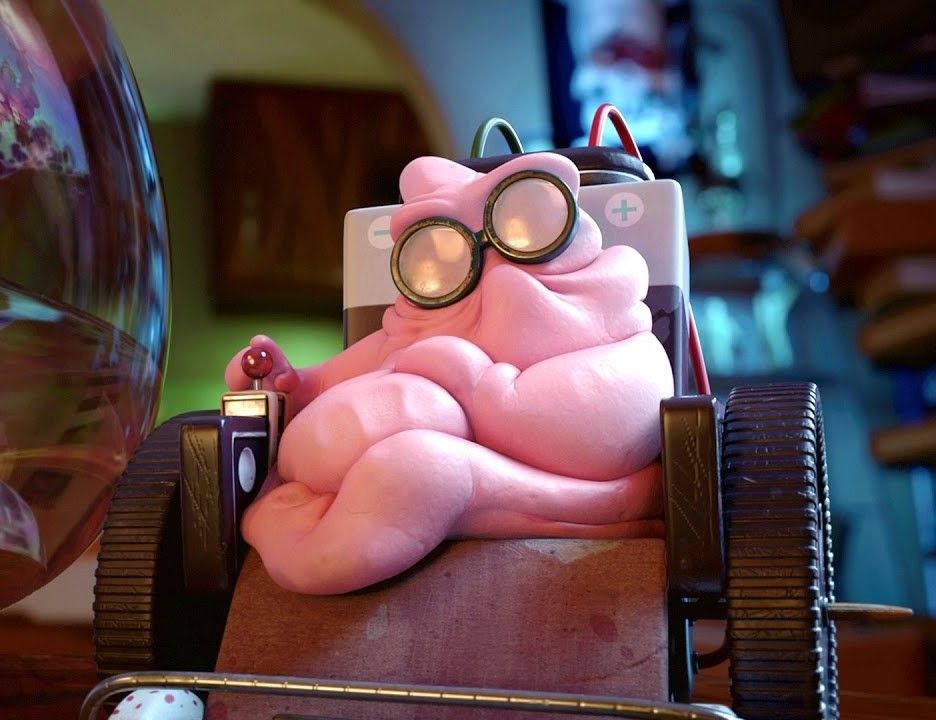

- 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