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狂熱何以流行—— 讀斯泰賓《有效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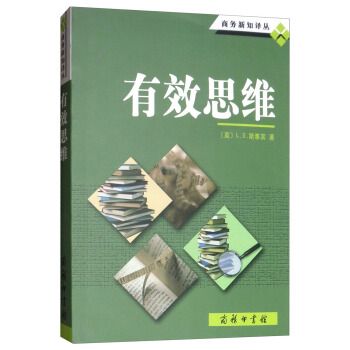
小時候我們村莊一位我喊「四公」的、懂文化的富農冉懋學,在改造的閒餘,替生產隊放牛時,常給我講《水滸傳》和《說岳》——這些名字當然是我後來讀書後憑內容才知道的,他也不曾告訴我——殺人越貨、忠奸分明、風生水起,聽得我好不快活。現在看來,他講的這些故事,不只是那些古代人活靈活現地在我面前走動飛舞,更無形中起動了我最早的思維訓練:好壞二分、非黑即白的思考路徑,早就深植進我們習焉不察的說部裡,讓那故事滲入龜裂乾涸的心田,使過度概括和簡單二分這樣的邏輯思維,成了我們的血肉而不自知。
你的思維和想象本來是蓬勃葳蕤的,像大自然一樣多姿多態,豐富曼妙。但有的人不樂意你活得如此開心有趣,偏要將你的思維搞成壓縮餅乾,成了一個斯泰賓意義上的「罐頭思維」。「罐頭思維」怎麼培養的呢?在書中斯泰賓並沒有言及,但依據他對「罐頭思維」的形成機制的言說,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它的培養理路。
「罐頭思維」的形成就是盡量使民眾不知邏輯為何物,人為製造信息不對稱,屏蔽事實真相,省略論證過程,沒有有效證據鏈,最終只有給定的結論,不管是這結論是何等荒謬。但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要使普羅大眾大規模地形成這樣的「罐頭思維」並不容易,而在專制社會形成「罐頭思維」彷彿是娘胎裡帶來的,因為文化積澱和集體無意識,使得「罐頭思維」的誕生有極其豐富的土壤。
如今我們中國人的「罐頭思維」是怎麼練成的呢?其基礎之一是家庭教育,父母的「罐頭思維」使得兒女多姿多彩的想法受到抑制,甚至打壓,因為很多父母已不習慣一個在思想上自己不能主宰的孩子。當孩子與他們爭辯時,他們會認為大逆不道,即便錯了也用權力來壓制對自己的批評意見,更有甚者,死不認錯。
也就是說,中國的父母大多已經在行為和心理上內化成為大制度的一部分而不自知,他們的愛裡有的只是強迫約束,有的只是借愛來控制孩子,以便滿足自己的權威。聽話成了很多父母判定孩子的一個乃至唯一標準,以「好孩子」、「孩子真聽話」而沾沾自喜,其實這只不過是給奴隸主培養奴才,殘害孩子。在他們眼裡,當然不知道愛與自由缺一不可,才是使孩子健康成長的不二准則。沒有自由的愛,常是以愛的形式呈現出的一種精神綁架和身體禁錮。
復次,中國的學校多少是培養「罐頭思維」的大溫床。從小學的思品課到大學裡的思想政治課,是洗腦的正面主攻戰場,而歷史、語文諸課則是相對隱蔽,但影響更為湛深的洗腦地盤。老師和家長一樣是被洗腦和內化成制度一部分的,但對青少年影響很大的一群人。
老師在知識上的相對優勢成就了他們在學生中的權威地位,但他們本是受洗腦教育的人,言論和行動裡無不帶著「罐頭思維」的痕跡,自然會把這樣的負面影響傳遞給學生。最為重要的是,我們的考試中注重標準乃至唯一答案的陋習,是培養「罐頭思維」的利器。不管前提是否正確,論證過程是否經得起考驗,只要你能背得了唯一答案,那麼你就是考試尖子。如此選拔和激勵機制,不需要思考,最終會廢棄你的思考能力,使你不知質疑和批判為何物,的確成了學校教育的主要任務。
為什麼許多人或者我們的教育機制,希望你成為聽話、會背誦、不思考的機器呢?那是因為如果你思想不羈的話,不便於那些想佔你便宜的人管理。一個常問為什麼,且問為何只給我們吃罐頭食品,不讓我們吃新鮮食物的人,這會成為他們的大敵。他不希望你的思想像新鮮食物,不便攜帶,不便管理,便要製成壓縮餅乾,使不循常規的活躍思維,納入他們的鐵屋之中,這樣他們才放心。你不能亂長,你必須被剪得與冬青樹一樣平整一般高,不可以旁逸斜出,更不可以繁柯蔽日,因為這不符合他們整齊劃一的美學觀。
於是眾多的學生都成了工業化教育下,成規模地生產出來的、其思想的尺寸與口徑都被質檢員老師嚴格檢驗過的產品。是不是有鮮活的思想,充足的個性,不羈的創造,快樂的身心,那不是他們所操心的,至此,青少年的「罐頭思維」在出社會前便已大功告成。特別主張「思維的樂趣」的王小波曾說過:「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思維被罐裝化,思維的樂趣便喪失,偷懶和思考所帶來的疲倦,使得「罐頭思維」越來越鈍化,最終喪失了有效思維的能力。
著名語言學家呂淑湘先生晚年心系斯泰賓《有效思維》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在他重病不能譯畢之後,更委託給信得過的人叫其一定要將此書譯出來,可謂有深意藏焉。真正研究語言學的人,很少有不涉及邏輯學和哲學的,反過來我們也不難理解維特根斯坦為什麼曾經有著名的命題曰「哲學是語法研究」。
呂先生一生有不少可堪讓人記住的事功,但有一點卻極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他曾是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的教員。斯泰賓的《有效思維》是他譯來作為禮物獻給該校學員的禮物,雖未能親蕆其事,但其情之深,令人難忘。「我翻譯這本書,是有鑒於常常看到一些說理的文字裡頭隱藏著許多有悖於正確思維的議論,希望能通過本書的譯本使發議論的文風有所改進,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就使八十多歲的老人把已經極其有限的工作時間用在這個譯本上不為無益了。」(斯泰賓《有效思維》P261,商務印書館2008年11月版)
呂先生經歷建政後諸多運動和風雨,說話自然是有保留的,邏輯學教授斯泰賓這本《有效思維》的小冊子,豈止是對改進文風有用?呂先生所說的「發議論的文風」,在我看來就是說話(特別是開會)、寫稿時要有相當的邏輯、要避免那種一上來就濫用全稱判斷、偷換概念的假大空的議論風氣。
我讀了呂先生上面的那段話,很感他對邏輯學遭遇全盤覆滅的痛心,事實上,在如今的學校教育裡和我們的公共生活中,邏輯學依舊名存實亡,付諸闕如。如若不信,你只要觀看一天的官方傳媒報道、領導講話,其間的邏輯謬誤,用層出不窮來形容都不為過。為何如此呢?因為從奧威爾的新話到無邏輯的大忽悠,使人們走不出觀念洗腦的魔掌,成為清醒而自主的公民自然就沒有可能。
斯泰賓對於有效說理和邏輯實證,不只是談到「罐頭思維」的問題,而且談到成見(「戴上眼罩的心靈」)、換位思考和反證(「你和我:我和你」)、語言的準確和有效性(「不好的語言和扭曲的思維」)、洗腦術(「宣傳:一種障礙」)、偷懶與不思考(「聽眾的種種為難」)、誇張的語言垃圾(「節制之道不行於時」)、故意欺騙(「利用我們的愚蠢」)等,使得一本小冊子對於如何正確使用語言與邏輯方法,使思維的有效性達到一種可以期望和衡量的高度。
由於斯泰賓所舉皆是幾十年前英國的例證,對於我們來說,其有效性和針對性不足是自然的。因為他所批評的諸多症狀,在英國大多是一種隱性存在,在中國卻有更為典型的表現。可惜的是,至今無人做這方面的工作,許多人寧願把自己的才智耗在不知所云的語言迷霧中。
語言之外,自然存在著一個有待我們了解的世界,但我們人類不能不承認,我們是通過理解語言來理解世界的。這樣一來,就注定了語言是表達與遮蔽的連體嬰兒,要想分割開幾乎沒有可能。所謂情到深處人孤獨,是指語言在情感深度方面的無能。這種語言的無能,不只來自語言本身,更來自對語言的故意扭曲和其間所蘊含的信息的人為遮蔽。最強大的語言製造器,是真理部製造的奧威爾新話。
我們所處的現實比奧威爾的小說來得更為殘酷而真實,強大的宣傳機器製造的模擬現實,在人們的理解能力和心靈溝通上製造了一張無所不在的精神鐵幕,包括許多比較清醒的知識分子在寫作上,至今都仍處於「楚門的世界」裡,而不得破門之匙。這就是培根為什麼說:「人們自以為他們的心靈在操縱語言,可是往往適得其反,是語言在統治他們的心靈」(《有效思維》P178)。
當你想說真話並批評這個社會的時候,你想過沒有,你所使用的語言是不是奧威爾的新話?是不是被新話包圍了,不知不覺使用了而不自知?如果你意識不到這一點,那就是件極其可怕的事情。哪怕你正在從事批評由新話組成的意識形成,你也被新話所組成的意識形態所裹挾,不自覺地複製新話,從而被它包圍得嚴嚴實實,還自以為衝出了樊籠。其實你就像「楚門世界」一樣無所逃逸,自以為逃離了它的包圍,其實它有一塊更高的「天花板」在那裡等著你來跳。由於你使用它的話語體系,所以這管制思想的「天花板」經得起你無數次看上去充滿戰鬥力的衝撞,最終「天花板」毫髮無損,而你卻從此心恢意懶。
六十四年來奧威爾式的新話,在我們國家無法遍舉,因為這些語言垃圾多到你清掃起來相當麻煩的地步,但我們卻不能不因此一點一點地來揭示其真相。如「三年大飢荒」的官方說法是「三年自然災害」或者「三年困難時期」,可以說官方在這樣表達的時候,就是存心遮蔽真相。遮蔽真相的目的,是為統治合法性打基礎,同時也表明瞭為什麼在官方的當代史研究中提倡「宜粗不宜細」的深刻用心。把不可推卸的人禍打扮成不可抗拒的天災或者一場「蘇修」的逼迫,就可以不為成千上萬的餓死者負責,也使得多少餓死的生命變得無足輕重,甚至與暴屍荒野的野生動物一樣,不足掛懷。
比如,倘使你在提到三年大飢荒時,還用的是「三年自然災害」和「三年困難時期」這樣的新話式語言,那麼你的揭露就會矛盾和遮蔽,你的語言邏輯和真實事實之間就會出現不配套的衝突,從而減弱你的言說力量,也使得看你文章的人充滿許多不解的疑竇。當然這不是說你在下結論時不應該審慎,而是說你應該用真實的語言來表達你的數據及論證過程,而不是率先進入「新話體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不意識到這一點,有關建政後的研究就會變得糾結而喪失真實的言說起點。
這樣說,並不僅是為了反對官方的「新話」,而自己再製造一套完全對立的意識形態來對抗它,從而完成對它的變相複製。這就像仇恨具有很強的反噬性和自我複製能力一樣,「新話體系」及其反對者,一不小心就容易用反對姿勢來對此加以複製,從而進入一套不為說清事實的意識形態魔圈之中,可謂正中「新話意識形態」的下懷。
如一九四九年,大陸官方說「建國」,台灣國民黨說「淪陷」,都是基於自身意識形態的表達,用一九四九年這樣的時間概念來表達這個分界點,更為平實而罕帶意識形態的自我防身符。如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三年戰爭,共產黨叫「解放戰爭」,國民黨叫「剿匪勘亂」,而在我看來,比較中立而真實的表達是「國共內戰」。
我認為在釐清事實的基礎上,再作價值判斷,那是每個人的權利。但一上來就在事實中先入為主地夾雜著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就會使得研究變成一鍋難以下嚥的粥。換言之,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分離與合觀,要使讀者比較瞭然,而不是誠心欺世,並自以為得計。
本文上篇提及的「四公」,在三年大飢荒前,他工作於都江堰。三年大飢荒川西平原也餓死了不少人,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兒黃》就記述了溫江地區餓死人的慘況。但總體說來,離大城市較近,比我們僻遠的山區餓死人的概率要低。「四公」執意要回家,死也要與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從此就沒日沒夜地成了我們村莊的整肅對象。
文革時他的改造方式之一,就是寫大批判標語和塑劉少奇的泥像,來讓大家批判並認清其「醜陋嘴臉」。劉少奇嘴臉醜惡到什麼地步,我後來讀書學到「青面獠牙」一詞,就立馬想到小時在自家門前的「躍進門」旁邊看到的劉少奇塑像。劉少奇塑像不僅難看,而且很矮,使得童子如我等就可常常在此跳躍一過,狗自然也少不了要在上面撒尿尋歡,獲得一種侮辱他的快感。
仇恨教育的要義在於,使自己做了下流的事,還自以為正義滿腔,成功地顛倒了是非和煽起了人性之惡,使得你做惡事時喪失了羞恥,沒有敬畏感和做人底線。當你返轉身來意識到自己所習得之惡時,你已在惡的深淵裡隨眾起舞,跳出這被製造的仇恨糞坑已是極難。
除了「奧威爾新話」對我們生活的全面籠罩外,還有就是會議和領導講話的垃圾語言遍地「開花」,對漢語的有趣優美、表達的精確性造成極大的傷害。所謂垃圾語言,就是語言由權力所帶來的粗鄙化——我這裡並不批評民間語言的鮮活和粗鄙性,因為這樣的粗鄙性是一種哈耶克意義上的「自發秩序生長」,即來自民間的土壤與創造——語言由權力所帶來的粗鄙化,是一種官方強力介入的惡果,其實這也是對語言在民間自我生長的「自治傳統」的干預和破壞。其粗鄙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標語口號遍地,從通衢都市到僻野鄉村,無遠弗屆,直接參與以至玷污民眾生活的細部。
口號治國,在吾國有悠久的傳統,近世更是愈演愈烈,加上標語,成為洗腦和管制社會的大殺器。口號就是光禿禿的話,沒有必要的論證,不需要你思考,只需要你接受結論。口號有很多種樣式,但常用的製造方式無非是重復法、傳染法、斷言法。斷言法中沒有比「沒有……就沒有」的句式,更能製造不容置喙的心理效果、泰山壓頂的恐懼傳染了。好比那些對孔夫子敬愛到無以復加的人所說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沒有他們,中國好像不曾存在過。
毛澤東的語言被很多人讚美,說他簡潔鮮活,不少人都讀得懂。我承認毛澤東的語言有感染力,因為他深得標語口號的三昧。他的名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就頗得標語口號「斷言法」與「重復法」交叉感染,最後加入了「傳染法」的精髓。但你若是稍懂點邏輯,你還會讚賞他這樣的話麼?
「凡是」這樣的全稱判斷,其邏輯漏洞可謂俯拾即是。但懾於毛澤東的權威,不會有人指出來,但至今仍沒有人對毛澤東語言進行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分析,這就實在太令人遺憾了。
敵人反對吃糞,你擁護吃糞嗎?敵人擁護冬天穿大棉襖,你反對並且要去裸奔嗎?把話說得絕對,不留餘地,可謂是其語言的一大特點,如「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那些對毛澤東亦步亦趨的人,可能心裡面也打鼓。中國歷代的皇帝總有所畏懼而有點裝飾性,毛卻被讚美到無以復加,這就是其語言對民眾心理造成的恐懼及其權利傷害之魔力。
斯泰賓說:「我知道我應當指出我們思想中一個普通(我沒看過原文,或許此處應譯為「普遍」更為準確——冉註)的缺點,就是很自然地不願意說些有節制的話而遭人譏笑。願意承認一個問題正反兩面都有點道理,就難免被人責備,說是在需要採取有力行動的時候缺乏熱情」(《有效思維》P133)。在我們這裡把話說得狠,說得無理,邏輯不通的大有人在。
其實毛式語言若是還有邏輯,那就是遵循權力的邏輯。他們的潛台詞是:我就是要這樣說,你能把我怎麼樣?你其奈我何?毛式語言與一九四九年後官方運動而搞的「群眾運動」,可謂天作之合。很多人被毛式語言的狂熱煽起的群眾運動所吞噬——應該有比勒龐的《烏合之眾》、霍弗的《狂熱分子》、賴希的《法西斯的群眾心理》更精彩的著述出籠,才對得起我們在四九年後所受的苦難——而身首異處,可是那些尚健在者和受害者的後代,卻很少有人有真正的反思。
為何我說不少人是狂熱的漿糊呢?那是因為漿糊濃稠而分不清組成物,即無法辨別價值與事實、是與非、真相與謬誤。按理說,漿糊即便煮開了,也不會像水那樣沸騰,但狂熱使得漿糊更加盲動,好像一個龐大的群體,可憐亦復可怕。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