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鹿音苑的厂牌主理人曾宇,在他41岁生日时聊了聊
今天是曾宇41岁的生日。他是双烽镇酉时《把青春唱完》的第十位人物,不过他没有出现高原的书中,因为他活跃年代开始于2000年,没赶上收起镜头的1999年。他的身份承上启下,传承光大了九十年代的音乐精神,在新世纪以不一样的面貌继续为好的音乐扑腾。因此,他也是高原拍摄全新的《把青春唱完》系列的第一位。从他起,新一轮的文化人物肖像拍摄和访谈在2020年开始了。

新的《把青春唱完》系列的第一幅:暴雨和暴风骤雨式的采访后,曾宇躺在双烽镇头等舱里休息。高原摄于2020年5月。
第二次采访是在晚上九点多。
曾宇出现在55TEC录音室的前台。他要了一杯咖啡,双份的双份意式浓缩。距离睡觉的时间还有八个小时。他习惯晚睡,久而久之,朋友们和工作伙伴也不在上午约事。他把补充采访约在了此刻,此地。

这里是北京最好的录音棚之一。荣誉挂满墙。最左侧的是崔健亲笔签名送来的专辑《光冻》。
他的生活场景并不复杂。不在家,就在公司,要么就在录音棚里。这三个地方都找不到,那肯定是在德扑桌上。他从2009年起打德扑,有段时间还在线上打三十秒一盘的快速局挣生活费,但从来没有打过金额超过100元的。多年来,他总结战果,觉得小赢。

录音棚里的曾宇,胡须和带皱漫画t显得不修边幅
老员外把第一次采访约到了下午三点的双烽镇上。高原下了命令,「曾宇你来的时候可得穿上西装,年纪大了拍裸照不好看」。
时间刚到,曾宇推开了门。他穿着一件白体恤衫,脸上挂着银框眼镜、蓬乱的胡须还有新到某处的不好意思的微笑。身上没有一处有年龄感,看起来像个大学生。西装也带了,不过是一件优衣库风格的单西,拎在手上,攥成一团,丢进了椅子。
他曾经西装不离身。
2016年前后他频繁现身一些音乐财经新闻网站,在行业、资本、风口等浅显而宏大的字词之间,穿插着强作气势雄宏照片。图里,他在深灰色渐变的背景里身着黑色西装环抱手臂。据说,人不知道怎么摆姿势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会做出这样的动作。那时文娱行业正好是所谓的风口,他的飞行者音乐厂牌被资本竞逐。
这段时期极大改变了他。
他从前不爱讲话,至少不愿意侃侃而谈正从事的行业。他见过不下一百位投资者,参加过一只手数不过来的音乐产业论坛后,找到了表达的欲望。这与大多数人的想象相反——先有表达的欲望,才有表达的场合。事实上这才是自然的顺序,在事情没有发生前,没人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在几年前最低沉的时候,他每天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不适合开公司做更大的事情,只能做个制作人。
而今,曾宇有了明确的答案。
曾宇其人
曾宇能回忆起某年某月经谁之手听了哪盘磁带,也记得曾在何时何地为谁人做过唱片。他的音乐记忆力极好,小时候跟着父母去听音乐会,比台上的演奏者还紧张,生怕听到对方弹错一个音符。但音乐之外,记忆任由时间冲刷,许多都变得模糊,从建构的自我认知中消失,鲜少被提及。
关于童年,有两件事记忆犹新。
一件是母亲说的。四岁时翻来覆去听的一盘日本男生四重唱的磁带。曾宇对这件事没有印象,却也记住了自己在在双卡录音机里混录的歌单。
另一件则是那时家中的声音。母亲每天至少要接三个练琴的学生。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外边噼里啪啦地弹巴赫。周末家里响彻的是约翰·威廉斯还有喜多郎之类的作曲家。父亲把音乐当成专门的消遣,而不是背景音。
他侃侃而谈庞大的音乐接受史。听小虎队张国荣,也听达明一派,升初中还沉迷表哥送来的NWA。
少年的音乐兴趣在九十年代初的重金属浪潮前迅速垮掉,混迹五道口的打口店。听到的第一个上头的金属乐队是Motley Crue,后来有Guns N' Roses, Bon Jovi。

Motley Crue
帅过之后,开始追求技术流的Steve Vai、Dream Theater,再之后又迷上英国的前卫摇滚乐Emerson, Lake & Palmer还有艺术摇滚乐队Yes。据说他是五道口一带收集Yes专辑磁带最全的人,有足足三十多盘。
定稿后插入音乐 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Emerson, Lake & Palmer
高中时一下课就霸占教室后的录音机,强制同学们听。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有了弹吉他的心思。像Slash和邦乔维那样才算酷,弹钢琴太不酷了。

演奏中的曾宇
这把琴将他带进了华纳。
对此,曾宇的记忆留下来得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去报账,华纳的财务人员一定去度假。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度假不同于旅游,更不同于休假,是一个相当洋气的词汇,让人联想起黄沙白云蓝天碧海,不远处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因为这里是华纳,世界唱片工业中实力最雄厚的一方,在一些执着流行音乐的人看来,这里甚至没有加上之一的必要。
高晓松发现了年轻的曾宇还有黄少峰。他把二人所在的缓冲乐队推荐给了宋柯。在一个酒吧里给宋柯播放一次后,曾宇带着自己的乐队成了麦当娜的同门。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大陆的一支大学生乐队和流行天后差多远,但签约时工作人员信誓旦旦,让新来的年轻人热血沸腾。
血很快凉下去。曾宇和伙伴们急吼吼做好了新的Demo,发给了公司,但迟迟没有录音安排。年轻人们担心是不是要被开除,生怕好不容易得来的饭碗消失。每当焦虑泛起,他就去找宋柯。
宋柯设身处地为乐手着想,聊他们的困惑和困境,即便问题没有解决,还是老样子,但一定表示关切和认可。曾宇不再焦虑。多年之后,当做起了飞行者唱片,和宋柯一样直面乐手时,曾经的谈话浮现,上演了一轮又一轮。
身份一直在叠加。
他去录音棚里实习,刚刚学会电脑录音,但已经为丁薇录制唱片。最早是签约华纳的乐手,很快成为出不了自己的歌但要为别的艺人服务的制作人。
他的乐手身份没有丢,大学生乐队解散后,加入了糖果枪。2003年起,他跟着乐队各地演出,发现最受观众欢迎的,一定是主唱声音大的乐队。因为人们不关注器乐,只看主唱的声音能不能把歌词唱出来击中心思。

曾宇与黄少峰在演出
差不多同一时间,他拉着黄少峰做起了火星电台,整合起音乐人和制作人的双重身份。二人为周迅做过两张专辑,也为老狼做了两首歌《喜悦》和《未知的旅程》。
火星电台名字的确切来源已不可考。黄少峰喜欢Radiohead,所以必须要有电台两字。那时他们经常录一些超前的音乐,不为众人理解。当时的网络流行文化里充满了周星驰式的港台无厘头,总用「地球不合适,我要回火星」之类的说法表示不合时宜。浸泡在这样的文化中,也许大家无意识借用了这个说法来表达音乐上的超前。
他在2017年和老朋友黄少峰以火星电台的名义,在北京的BlueNote录制了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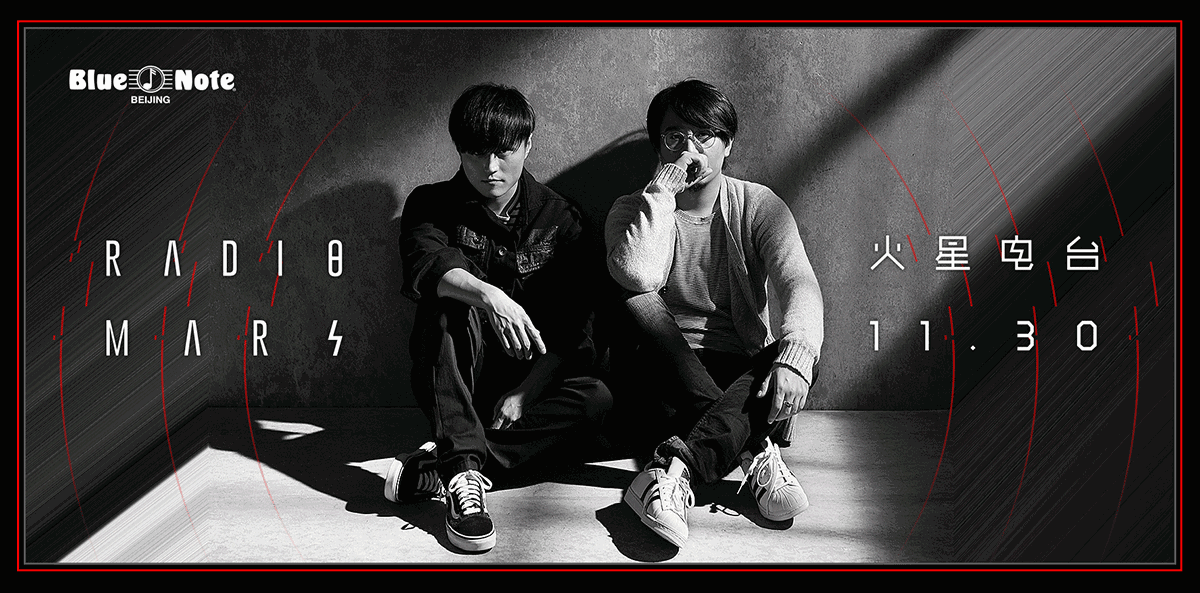
现场录音,一气呵成,夹杂了台下观众的叫好还有空气流动的声响。这是他喜欢的录制状态,而不是现在流行的一轨一轨修补声音。

曾宇在Bluenote
定稿后插入音乐
几年前的一则采访里,他提到自己有时候故意弹不准某个音。「电脑编曲已经如机器般严丝合缝了,但音乐需要人味儿,包括只有人会出现的小毛病」。曾宇觉得人工智能会最终取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至少在音乐创作里如此。「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搞不定的百分之五上」。
飞行者
曾宇是个乐手,也是个录音师。还是个学生时,追求的只有录音室里用得上的设备。那时北京的房价只有两三千一平米,他花4000买一台鼓机。为了防止花光钱没办法生活,给自己立下死规矩——只用收入的一半买设备。
不过,最重要的身份,是唱片厂牌的老板。
离开华纳后,曾宇只觉得音乐市场不该大公司当道,流行的艺人只有周杰伦和孙燕姿,无数有才华的音乐人进不了视线。于是,他想做一个厂牌,把无名歌者组织起来。

曾宇在模块爱好者交流活动上
廿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尽,所有人都隐约嗅到了唱片工业的垂垂暮气。曾宇并非不知道这点,只是根本没把它放在考虑范围内。
他想到的全是手里的好牌。
自己是经验丰富的制作人。
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资源和人脉。
创立厂牌时也足够理性。大义凛然,没有叫最好的朋友黄少峰。「他是个单纯的艺术家,只考虑创作,我考虑得多些,一方面想保护这份单纯,另一方面会担心事情能不能最终实现,当时在华纳的时候,我就有些微的项目管理意识,还知道帮公司省成本」。
为了办好公司,他和前上司宋柯请教多次。宋柯思忖良久,给了条至简的建议——保证现金流,别的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他才28岁。曾宇信心满满,坚信只要坚持,一定会成功。
行业经验丰富的老员外惊诧地笑:「你二十八岁了,还觉得坚持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曾宇挠了挠头,说:「我一直比较幸运,还没吃过什么苦,大学没毕业就有工作,然后做制作人,一路风光,总觉得干什么都会顺风顺水」。
他坚信「牛逼的东西最终自己就会牛逼起来」。曾宇当时受邀做乐队比赛的评委,碰到了一大堆新乐队。他想,「一个乐队现场反响很好,再来上几首流行的歌,轻轻松松都能走起来」。
在当时的音乐市场环境下,怎么做都是错的。然而,这块苦田总给人希望。几乎是同一时间,迷笛音乐节爆火,让快要绝望的飞行者输送了一波签约的乐队。
这成为历史的循环。每年,去年的希望大都落空,新的希望伴随着新项目接着冒出来。
再往后,资本涌入文娱行业。曾宇经历过大公司的风起云涌,签约了一线艺人,做过演唱会和音乐节,他的生活也变成了一天八小时会。

不断吸收,不断推翻早已成为曾宇的常态
那几年,一睁眼,自觉和所有失败的创业者一样,对局面无能为力。管理战略层面,除了自己还有别的股东,公司的决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具体的业务也没办法掌握,营销、宣传都有专人。2014年的时候,接到了陈奕迅的编曲。当时公司里各个部门开会吵成一团。他关起门来编曲。
不管有多不顺,曾宇一定不和家里说,要全部自己扛。这是底线,不能让家人感到不对劲。他整晚泡在编曲里,忘记白天的不快。
而今回想,如果来一个沉痛的打击,也许自己幡然醒悟,但一切的成本都不高,包括失败的。他总有办法解决眼前的麻烦,让事情不至于崩溃。
就这样, 别人用两年时间就能经历的成长,曾宇花了十年。

从大三组乐队一口气在音乐行业打拼了20年的曾宇,Ruá上眉梢
他承认自己的理想主义是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做厂牌前看的只有外国同行光鲜的一面,对背后的烦恼和波折一无所知。
第一次和曾宇碰面的时候,他正准备和黄少峰还有《大内密谈》的人做「火星好朋友」(这档节目主打不准备不设防无禁忌的闲聊畅谈,并设有「甭管嘉宾是否愿意都强行让其唱Live」的惊喜环节)。金志文做嘉宾,轻装上阵,提包、外套还有手机由工作人员携带。
定稿后插入视频
录制就要开始,器械还没准备好,两位工作人员在大厅站着,各自盯着手机。曾宇先是跑到楼上取相机支架,后下楼忙活布置线缆。他一边念叨如何搭线安装,像是下达命令,一边自己动手,把活儿干了。

曾宇在录制现场的准备工作
李荣浩曾经在飞行者的录音棚里泡着。当时每天进出这里的乐手茫茫多,曾宇友好地接待一个又一个,没有什么不同。曾宇没有心机,从没有想过其中那一位在未来会商业上大成功而去更友好。他同样没有想过给那位小眼睛的歌手优待。多年后,李荣浩火遍大街小巷,曾宇掏出手机,只是看着他的视频,回忆当年录音的点滴。
他唏嘘,如果能回去应该不会做飞行者这个厂牌。但内心中另一个声音适时反驳,就算没有飞行者,自己也会在另一条路上摔得更惨。年轻精力旺盛,总想往前冲,一定会冲进某个地方,被某个不曾料想到的存在摁翻在地。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在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下,做出什么选择都不应该被指责。
大陆音乐20年
本世纪初,曾宇跟着一位美国回来的制作人学编曲,夹杂电子音乐的元素。这种风格流行是2015年以后的事情。但那时有赏识他的人。青春的周迅听过他和黄少峰做的Demo后,指定要唱。
当年的中国人还处在听歌而不是听音乐的阶段。歌词中的某句击中自己,就会为此叫好,音乐的旋律反倒是次要。人们都知道最好的作词人是林夕,但没人脱口而出最好的作曲家是谁。
现在流行古风,小年轻们高呼找到了精神家园。曾宇只能看着苦笑:「我要是周杰伦,就冲这帮家伙去收版权」。
中国人听的太少了,不知道自以为是古风的音乐的根子都在周董那儿。
这么多年,互联网起来了,音乐平台起来了,但音乐没起来。
正常情况下,小厂牌遍地开花,录制唱片。媒体去发掘大众视线外的东西,原本地下的乐队获得成功,被大公司签下,连带着小厂牌长大。
现实情况是,互联网干起了唱片公司、媒体、经纪公司的活儿,但他们做的不是去发掘人没听过的,而是紧紧贴住用户,努力给他们喜欢的东西以留住。音乐市场的活力消失了。
中国可能有数千个音乐厂牌,都要依赖平台,但不奔商业而去的,可能不到五十。曾宇也没办法摒弃平台,「全靠平台出预付款」。

鹿音苑里价值不菲的设备
音乐平台上市了,但音乐行业因此变得更好了吗?没有,平台依然还是过去的思路,做大了吸引用户,然后收割。平台在资本的压力下,向大流量作品和艺人倾斜资源,扶植新的音乐和创作者的花费不成比例。
曾宇不认为这是出于吝啬,而是他们意识不到。「我们行业是要砸钱的,要有人做建设才能发展起来」。但这个钱不一定是音乐人自己去砸。
各大音乐、视频平台的老板有能力去发动所能,创建一个良性的音乐业态。创作者的第一动机绝不是挣钱,而是表达。作品需要在健康的商业社会里得到回报,激励他们。
但现在没有音乐工业,只有娱乐工业。所以,他们依然用流量多寡、盈利思维去管理,而不是为创造者打造友好的商业环境。
毕竟,一个音乐家的成熟需要十到二十年,没有一个资本愿意等这么久。平台的高管们往往是唱片时代的遗老。他们从不扮演创作者的角色,脑子里盘旋的也是业务和增长那一套。

曾宇在舞台上
曾宇笑言,要给财阀的下一代洗脑。现在的资本都要求三年五倍五年十倍的回报,而这点时间对于音乐行业养成绝对不够。只有有了不追求快速回报的钱,音乐行业才能真正在未来赚钱。
当三十秒的短视频也被嫌弃冗长的时候,花五分钟听完一首歌就变得奢侈。音乐在逐渐消失,躲进游戏、综艺、电影的掩体,与它们融为一体。
音乐在哪里能自己立得住?也就是网络神曲了。
神曲传唱有它的道理,为了传唱度牺牲了编曲的复杂度。他的女儿喜欢听网络神曲,跟着唱,他也不拦着。每个人都在选择所处环境里最好的东西。
曾宇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热爱的摇滚乐,反叛又反商业,其实就是最大的商业。「在磁带和CD的时代,一张唱片的利润极大,赶上了卖毒品」。年轻时追捧的摇滚明星,和今天年轻人迷恋的偶像有什么区别呢?都是一波商业和艺术的精英包装出来赚钱的产品。

最畅销的摇滚专辑
大众越爱神曲,曾宇越觉得音乐市场需求旺盛,未来有指望。但转念一想,他又绝望,甚至怀疑在九十年代末的某天,一个反派按下了一个按钮,音乐行业里所有的事情都错了,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时间线。
他现在给自己的任务是保存、传递火种,「我积累二十年了,知道什么是好的,一首歌做成什么样就符合标准,那么,我去传递它,让大家用两三年掌握我们这么多年的摸索」。
55TEC录音室来过一个美国孟菲斯的高龄录音师。他操纵旋钮自有一套,按的参数大家都一头雾水,效果却出奇得好。等工作结束,中国的小伙子们请教原理,老人家拍了拍脑袋,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六几年的时候师傅就这么教我」。

55TEC里器乐设备的一角
同样在这里,一个圈内有点名气的录音师,不知道电吉他连接音响的时候还要插上转接头。一个人鼓捣了半天,探出个脑袋,大喊:「你们这儿机器是不是坏了」?
十多年前,曾宇站在日本涩谷的街头,身旁经过的十个年轻人至少有两个背着吉他,一脸匆忙去排练的模样。抬头望去,高楼上的幕墙广告,最好的位置一定属于唱片。

涩谷街头
曾宇感慨,我们和美国技术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背后音乐文化上的积淀,差了一百年。「我们是种地的,资本们来菜园里割,不反对你割,但你想多收,就得多种几亩,而不是割得更狠。国外的资本们也逐利,但深谙此道的老钱们总愿意做些看不到回报的傻事。他们不是干傻事,是知道如何更赚钱」。
很多年前,他去过澳大利亚,也在新加坡陪着老婆孩子住过一段时间。要不移民算了,曾宇想。一天,他溜达去了三里屯的脏街,那时它还没有改造得像被切好的蛋糕。他看到了「小咖啡」里熟悉的面孔们。突然间,他发觉哪儿都没有脚下的土地好。
男人四十
被世事摧残的成年人不会幻想。只有半大小子才会强调自己是大人。曾宇最近发了条朋友圈,以「四十岁的人的感悟」开头。他对这个年纪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有种不属于此但混入其中的狡黠。
他梦想和坂本龙一聊聊天。七十年代,坂本龙一按部就班考进了音乐学院,却被学校对面的美术学院打动,觉得那里的年轻人更酷。如果没有那群离经叛道的亚文化青年,坂本龙一也未必会兼收并蓄。
他想请教扎克伯格。曾宇相信世界上有天才。从零开始,做到管理几万人的大公司,扎克伯格的一定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这就是天才的秘密所在。过了一会儿,曾宇回答了自己,「扎克伯格也会崩溃,只不过是我们没看到他脆弱如常人的那一面」。
他也会生白日梦,想象突来横财会怎样生活。他的幻想摆脱了稚气,不会渴望这笔钱用之不尽。他不会贪心多要,「有多少钱,干多少事」。
他其实刚刚成熟。

饮酒似乎是大人的事情,模仿甚至逞强则是即将成熟的人的专利。曾宇多年来滴酒不沾,但他最近开始喝酒了。第一次采访的前晚,他在双烽镇畅饮金汤力。采访期间,北京突降暴雨,天变墨色。老员外说下雨了总得喝一杯吧,开了一瓶朋友送的Casa Mendes微泡,曾宇犹豫几秒,主动说那我也来一杯。他要了不止一杯,而且喝的不比老员外慢。
在过去的十年里,曾宇主要工作就是与音乐相关的人缠斗。
教不懂音乐的媒体人如何写稿,向不关心创作的录音师阐释观点,对着不理解厂牌的音乐人协商公司的难处,还和不懂音乐的投资人打交道。
他看讲创业故事的电影,觉得一群人做事应该是发挥所长,作出新的东西。但他感到的只有悲戚——来来往往的人首要目的不是把事情做成,而是先端起架子证明自己牛逼。
他发现,广告圈、资本圈、商业圈,所有人的处世方法都不一样。互联网行业的人和音乐行业一样单纯,只不过多了层冷酷和机械的味道。凡事一定要聊出具体的执行框架,一丝不苟执行,哪怕真到了那一环有不合理之处和人情世故,也不变通。
他练就了一项技术,能从一个人的表达上看到需求和困境。不同的人需求涌入大脑。他想方设法去磨平。
员工之间的矛盾,领导之间的矛盾,员工和领导之间的矛盾,谁惹恼了客户,谁得罪了艺人,数字平台有什么不满意,像一根根红色的警报线,而他像穿梭期间的特工。不光要穿梭,还要努力把它们弄得平行。就像《美丽人生》里的主人公,把别人因为吃不下而不置刀叉的整盘餐端给深夜到访的饥肠辘辘的客人。
他心力憔悴,但觉得所有事情都能解决,没有好结果一定是因为没找对人和门路。他以为自己会这么灵活勇猛下去,不知疲倦。

曾宇和他的两个娃
三十岁之后,世事都能解决的假象如风蚀过度的壁画般片片剥落,露出真实的面目。曾宇猛地发现,日后越来越多的事情,不管如何奔走,其实都没有改变。
他感觉身上绑满了枷锁,要为生活负责,要管理公司,什么都放不下,必须亲力亲为。2017年底,他跟周迅去了印度的瓦拉纳希,一座北方邦的古城,也是印度教的圣城。印度教的信徒笃信在这里死去并在恒河岸边火化能打破轮回的循环,获得救赎。

恒河行舟与鸟
除了在恒河上漂,他向宗萨仁波切请教,急切地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好运」?
「无为」。
曾宇决定让一切顺其自然。「万物都是碰撞出来的,能走到一块就走到一块,碰爆炸了就爆炸」。有时候解释一句就能过去的事情,他也无动于衷。老员外说这就是四十岁的人Ruá起来的样子,Ruá就是无为。
人总要栽几个跟头,接下来要么死去,要么成长。他决心远离那些不能无为的环境,只做不勉强自己的事情。
他与一个在美国行业经验丰富的朋友,做了未来壹娱乐公司,紧跟综艺的时代潮流,想推出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面孔偶像。同时,他把没有必要的成本都砍掉,音乐公司也重回作坊。他和伙伴们一起,做出了全新的厂牌鹿音苑。他拉上了当年觉得太艺术的黄少峰。「黄少特别擅长和人交流,有他在和艺人打交道最好」。
不被商业牵着走的鹿音苑,名字来源于印度名寺鹿野苑,释加牟尼第一次讲法就在这里。这里经过多次宗教战争,曾被大火烧平,但依然温和地存于世,代表一方宁静。

鹿野苑
他强调这是一个无害的存在。没人会因此赔很多钱,也不会因为这里的事务耽误发展和主业。
做之前,曾宇不指望这个厂牌能发展得很大,也不做纯商业的歌曲,靠流量赚钱。尽管他知道用音乐赚钱的方法——调整合成器上的高低,生成人愿意跟着扭动的旋律。但直言自己没能力赚,「我实在下不去标准去竞争」。
老员外指着双烽镇那面黑胶墙,说把一半留给曾宇出的唱片。

这张专辑已经上了唱片墙了,去店里喝一杯的时候记得放一放
这很有可能实现。去年后半年成立鹿音苑,他和黄少峰在半年内写了六十多首歌,哪怕受到疫情冲击,也为签约的艺人出了6张唱片。
定稿后插入音乐
他觉得现在是时候做些事情了。年轻人听得到更多元的音乐,这就是最大的机遇。自己也摸爬滚打,知道如何在各方周旋,撬动更大的资源。他不再觉得民众对低质的音乐趋之若鹜。音乐最具魅力的地方在于,即便是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人,也能被精良的一曲打动。今天,「牛逼的东西最终自己就会牛逼起来」那句话依然刻在心上。
曾宇今年四十一岁了。午夜,在55TEC录音室里,他穿着白色体恤衫,手插灰色卡其裤的兜里,靠在墙上,说:「我妈五十岁事业上才有了转机,我还有时间」。他花了二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终于做好准备,开始等风来。
双烽镇世界中与曾宇有关系的人
1
王学兵作为签约艺人,在去年九月的鹿音苑制作音乐。
2
曾宇梦想和坂本龙一聊聊天,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和丽都坂本龙一盛志民聊聊还是有机会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