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葉梓誦《斷層路徑》:一個overthinker的溝通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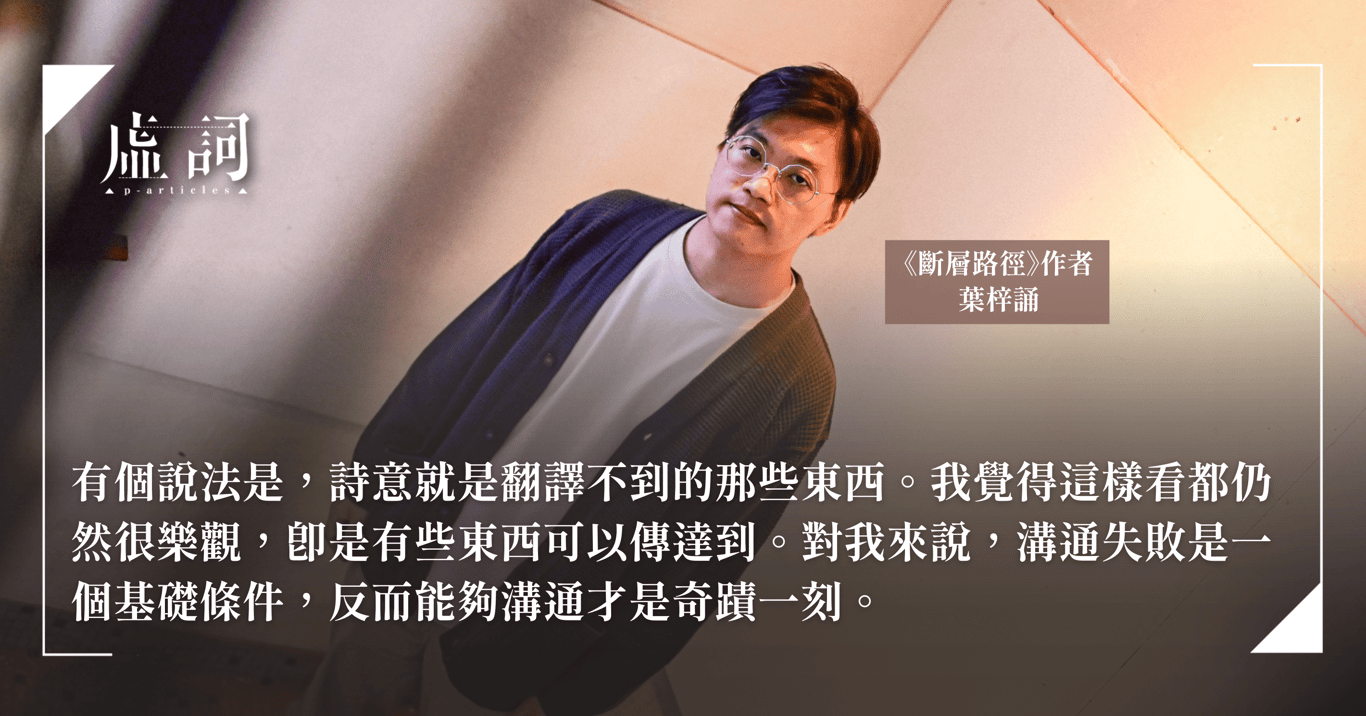
文|黃柏熹
我們相遇在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隨著交通和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人的遷移和訊息流通早已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手機屏幕上,世界彷彿縮減成一個可以輕易抵達的平面。偏偏,離別與區隔化為低頻噪音或一股震撼,突然穿過一整個城市的我們。一個晚上宣告一個人的離別,原來斷層早在生活之間,人們在夜幕下找尋路徑。
年輕作家葉梓誦曾共同創辦本地文藝評論雜誌《SAMPLE樣本》,近來出版了首本個人文集《斷層路徑》。他在書裡寫書信,寫哀悼,寫人際和寵物的離別,夾雜不同的哲學和文化理論,又回過頭寫陳奕迅的〈不來也不去〉;旁徵博引,據說曾讓編輯和校對看到頭昏腦脹。但葉梓誦說,他要講的東西一直都很簡單:「就是一種溝通的慾望,想跨越的慾望,想在叢叢雜訊中找到可以連結對方的可能。」
回信之難
葉梓誦曾被形容不旁徵別人就不知如何說話。據他的說法,其實是混沌,近來甚至覺得愈來愈難說話:「可能是某些器官退化的跡象。」
如何混沌?在訪問裡他分別提到:以往乘小巴不敢叫落車、餐館上錯菜不會跟人說、口吃、適當的時候找不到適當說話……如此種種。內向,典型的overthinker,他自覺自己的語言系統跟別人不同,無法輕易對接。《斷層路徑》的後記也提到,有些寄到手邊的獄中信件,回信對他來說卻份外困難:「或者因為各自的世界很不同?神奇的是,你跟另一個人在不同世界才有溝通的需要,但又會覺得溝通不到;在同一個世界又會覺得大家的經驗差不多,很多事不需要開口。」
正正是無法寫信,把葉梓誦引領到「書信體」這個寫作形式上。葉梓誦說,他的寫作模式往往是先有一個人設或設定,有一個實際的框架或結構,才能把無形的混沌框在一個透明瓶子裡,然後說話。這個方法多少有點像編輯的角色。而《斷層路徑》裡一系列寫給F的信件,源於多年前開始的「瓶中信」系列。對他來說,書信體為他提供了一個幻想自己正在跟人對話的基礎,這個對話可以超越區隔,甚至生死,是一種傾出的姿態。
「馮內果有個說法是,如果你打開窗屌個世界,你只會得到肺炎。當你有對象地做一件事會更加鞏固,這是其中一個解決我寫作煩惱的方法。甚至書裡的F講明很討厭理論,我都會講,但會按照這個形象再調整。這跟文學評論不同,我知道對象是甚麼,令所有事都恰如其分。」
哀悼的信
當然,很多事情都並非可以計劃好的。譬如書裡第一篇文章〈Rigor Morris〉,寫他離世的小狗「大師」,由17年寫到成書之時才完成,關於死亡,如何哀悼,總是欲言又止。
文中既穿插小狗由離世到火化的回憶,也旁徵包括德希達、布朗肖、羅蘭.巴特等哲學論說;看似博引,實際是面對哀傷不知如何自處,所以東拉西扯,顧左右而言他,總是接近又遠離事發的核心。這篇直到後期才加入的文章,為整本書增添了一種情感渲染,以離別和哀悼為中心,散發出去。「悼念和死亡的部分是後期才加入書裡的事,本身不覺得是一件事,甚至開頭沒想過跟Rigor Morris(屍僵)有關,後來才發覺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明白那麼力量如何作用在我身上。」葉梓誦說。
文中寫到「悼念是種工作」,恰好貼合這篇以小狗為對象的悼文。說法來自德希達的著作《悼亡之工》(The Work of Mourning),是寫給同代哲學家的悼文。悼念是種工作,代表失去的哀傷不是可以輕易道別的情緒,只能透過日復日的工作來舒緩:「這是關於一個叫crypt(指地下室,也指密碼)的問題。有人死了,你把他放在墓穴裡,同時是一個encryption(編碼)和decryption(解碼)的過程,逝者會散落到生活上的不同地方,你會在世界裡看見很多幻影,令你引發相應的情緒。這個由內化到外化的過程,就是悼念的工作。」
而旁徵博引,顧左右而言他,不就是重新編碼和解碼,一種致哀,和死亡和缺失溝通的過程嗎?換句話說,悼文,也是一封寄托情感、幻想有一個對象的信。「德希達有個說法蠻有趣,寫信的當下我甚至不需跟你區隔很遠,可以睡在你身旁,轉身寫在便條紙上;最重要是你讀信時跟我有區隔。距離是令話語可以出現的基礎,正正因為要跨越某個間隙才要寫很長、用很多方法完成溝通,因為這個距離本身作用在你身上。」
以寫作實踐翻譯
當過多年的藝文雜誌編輯,又是一名譯者,要為葉梓誦加上一個標籤,或者就是「翻譯」── 總是有一個對象在前面,而他翻譯。
大學本科讀翻譯系,他形容學業上的實務作業相對枯燥,而中文世界在翻譯的理論上也停留在較普通的討論。「實際上二、三十年前已經有研究說,翻譯作品不一定指對著原文寫出來,世人認知它是翻譯就是翻譯,甚至說翻譯是原文的死後生(afterlife)。」他說,「翻譯不只是把舊有的東西傳達一次的舉動,而是令它重新獲得生命,賦予更多價值,類似重新創作一次。這些對我來說都是蠻有趣的概念。」
對他來說,寫作更似以一種翻譯的實踐,在個人情感和普世經驗之間,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創造新的連結,新的意義。從小狗的死寫到悼念之為工作,既通向哀傷的迴路,也通向更多哀傷,由具體事物通向一種共情的可能:「就像林夕說只需要失戀一次就可以靠那件事寫出千首歌,這可能就是文學的部分,一些具體的事物可以影響不同人對一件事的看法。我要關心這件事不是因為你,而是像〈不來也不去〉裡說『剛巧出於你』,然後可以透過這件事代入一些位置。」
他也不認為作者必然等於一個最原初的創作者,反而是別人寫過的,他藉此翻譯與重複,尋找斷層之間的路徑:「散文對我來說不是把自己的經驗轉化,換成文化商品。太強調作家本身反而限制了解讀的可能性。它就只是剛好在你身上發生,而你寫了出來,是一個技術工人多於我要告訴世界我的經驗有多獨特。」比起作者,他更認為自己是譯者和編輯,不斷衡量翻譯的準確性和可閱讀性。
文學與迂迴之用
話說回來,作為一個overthinker,少不免被人形容「你好撠」,有糾結和迂迴的意思,它的反面或是乾脆和直接。而有甚麼不能直接地說、爽快地做,得要在轉身後才寫在那張便條紙上?
「有個說法是,詩意就是翻譯不到的那些東西。我覺得這樣看都仍然很樂觀,即是有些東西可以傳達到。對我來說,溝通失敗是一個基礎條件,反而能夠溝通才是奇蹟一刻。」自認「麻煩友」的葉梓誦並非「悲觀」,而是認為溝通只能透過不斷去講、不斷迂迴,找不同方法嘗試去搭建一條路徑,「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扭收音機時,從不同雜音裡找一個剛好搭通頻段的時刻,其實雜訊佔的百分比更多,你要經過深沉的思考和努力,才溝通得到。」
文學之用其實就是迂迴之用,只能透過看似無關重心的話語去靠近,行更遠的路,也是必要的路。「譬如有親近的生命死了要悼念,更懂表達的人會有限度,中間的處理你忍受就好;但當中的細節可能就是我們沉溺更久的部分,我覺得是一種舒緩的方法,你必須要迂迴才可以完結這個路程。」
我們相遇在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忽然發現我們所關愛的,並非如我們所想的那麼接近。每個人都有很難溝通的對象,區隔和離別成了生活的斷層,連結的可能更似祈求多於常態,「接受它作為基礎條件,往後的溝通才能沒那麼理所當然。」葉梓誦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