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或留肝膽照應」——廖偉棠《詩的隱遁術:香港中青年詩的新變》講座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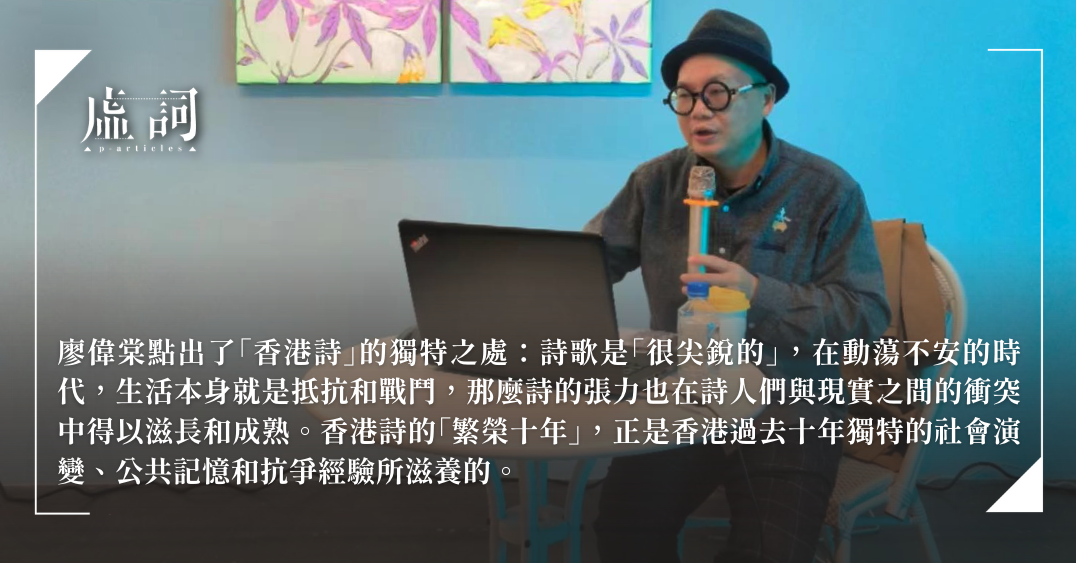
文|李盲
恢復通關後的香港百物騰貴,哪怕特首隔三岔五就呼籲我們要振興「本土消費」、恢復「本土經濟」,但似乎沒有人對疫情後和戰亂中的世界有信心,大家都看緊了錢包,唯等週末過關上深圳消費。如果用廖偉棠的話來說,這應該屬於「小遁」——一日來回,只求酒足飯飽。11月17日,週五,傍晚是深港關口最繁忙的時候,廖偉棠正是混在這樣的洶湧人潮來到深圳。
廖偉棠在深圳飛地書局以《詩的隱遁術》為題,向內地讀者介紹香港近年湧現出來的中青年詩人。廖偉棠或許是繼梁秉鈞和西西之後,大陸讀者最熟悉的香港詩人之一,他有多本簡體版著作在大陸出版,有詩集,有散文集,還有現代詩導讀;同時他也是香港詩人中最熟知大陸文學現場的人之一,他與胡續冬、韓博、馬驊、馬雁、侯馬等大陸七〇一代詩人的友誼,是最重要的文學記憶。作為增進兩地詩歌相互了解的使者,廖偉棠非常合適。
繁榮和動盪中的「隱」與「遁」
「隱遁術」是「隱術」和「遁術」的合稱,廖偉棠用這兩個詞歸納香港詩歌的新變,即面對表達空間一點點被壓縮、支持和資源一點點在減少的香港時,兩種可能的選擇。使「隱術」的是那些留下來的人,而使「遁術」的是那些離開的人;但在廖偉棠看來,無論是「隱」是「遁」,他們都在堅持寫詩這一項「窮人的事業」。彷彿是一種幽默的巧合,廖偉棠演講所在飛地藝術空間,也正是在香港藝術家勞麗麗(Lo Lai Lai Natalie)的《光明卻沒有背離黑暗》展覽現場。一「遁」一「隱」的對照,彷彿也是廖偉棠與勞麗麗兩種書寫方式的對照:前者遠赴台灣教書、寫作,又穿梭於陸港台三地為增進三地的相互了解而奔走,而「香港詩」的印象在交流和對碰中變得清晰、獨特;後者回歸土地,回到郊野、農田和勞作當中,以田壟和山野的植物為主體進行影像創作,通過重塑人與土地之間的親密感去反思香港的城市化和現代性。無論是廖偉棠的「遁」向台灣,還是勞麗麗的「隱」入郊野都在提醒著我們,一種我們熟悉的香港經驗已然消逝,詩人們和藝術家們必須重新變換自己的位置才能重啟有效的書寫。
廖偉棠認為,香港詩歌的過去十年是「繁榮的十年」,相對而言台灣卻是散文更顯發達。兩相比較,廖偉棠點出了「香港詩」的獨特之處:或許因為散文更擅長表達「小確幸」美學,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成為書寫平靜、安定生活的選擇;但詩歌是「很尖銳的」,在動蕩不安的時代,生活本身就是抵抗和戰鬥,那麼詩的張力也在詩人們與現實之間的衝突中得以滋長和成熟。香港詩的「繁榮十年」,正是香港過去十年獨特的社會演變、公共記憶和抗爭經驗所滋養的。在這「繁榮的十年」湧現了不少優秀的作品:周漢輝的《光隱於塵》(2018)聚焦香港階層和社會問題、葉英傑的《時差繁衍》(2021)以中環為起點體驗香港不同時光和命運、洛楓的《頹城裝瘋》(2022)書寫當前時代香港人的「佯狂」姿態、李顥謙的《夢或者無明》(2022)書寫香港人殘酷物語等等。同時,這「繁榮的十年」少不了如《字花》《聲韻詩刊》等文學刊物的支撐:《字花》是香港最著名的「中青年文學雜誌」,也是香港本地青年文化與「嚴肅文學」的接駁點;而《聲韻詩刊》則是一本有「近半篇幅都是翻譯」的詩刊,它的國際視野為香港寫作者帶來許多啟發。
香港詩的新變
接下來,廖偉棠選取了十餘首香港詩去呈現「中青年詩」。所謂「中青年詩」,實則是一種斷代,區分於前輩梁秉鈞和西西等早已成為世界文學經典的老一輩寫作;同時,它也指代那些承繼了梁秉鈞和西西的香港城市和文化身分探索,又在新的歷史境遇里對前輩有所反省和批判的更年輕的探索。
廖偉棠首先朗誦了陳滅最新詩作〈香港未睡〉,一首「很正派、很主流的香港詩」。「陳滅」是著名香港文學研究者陳智德德筆名,以研究「新文學史」著稱於學界,如今也在台灣教書。陳滅的詩延續梁秉鈞和西西開拓的本土意識,即努力地去記錄平凡香港人的生活,「香港永遠是他的主題,不管身在香港還是身在台灣,他永遠地在書寫香港。」但陳滅的詩學又比梁秉鈞多出了一抹激進的底色——「市場!去死吧!」既是他那本著名的詩集之題目,也是他的寫作立場。讀陳滅的〈香港未睡〉,廖偉棠想到了自己的〈香港小夜曲〉,兩人都以香港夜色各自隱喻著香港的未來,陳滅祝香港在幻滅中重新定型,而廖偉棠則以哄女兒入睡的口吻祝香港晚安。
陳滅的同代人中,周耀輝則代表「中青年詩」的另一條美學線索:香港流行音樂和歌詞。廖偉棠表示,「香港的詩不能少了香港的詞」。廖偉棠分享了周耀輝的為達明一派寫的新詞作〈1+4=14〉,拆解了題目這條等式背後周耀輝的批判立場:「1+4=14」借用了《1984》中「老大哥」的「2+2=5」之典故,同時有超越了原著對 權力的批判,將批判的目光集中於AI等信息技術對真實與虛擬的顛覆性重構中。像周耀輝和黃偉文的詞,都能夠將嚴肅文藝的批判能力揉合進流行文化的表達中。而周耀輝的詞更是受現代文學名著影響很深,他詞作中的頹廢、淒美,又反過來影響了廖偉棠的創作——美學上的革命與社會上的革命是同樣可行的,後者並不是抵抗的唯一選者。
香港「中青年詩」新變,也體現在強烈的性別意識、女性或性少數的生命經驗經進入香港詩歌的呼吿和表達,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游靜和洛楓。游靜是一位戰鬥性很強的女權主義者。她的〈母後〉玩了有趣的「雙關」:「母後」音同「母后」,是香港人對媽媽的一種帶有玩笑意味的稱呼;同時,「母後」在游靜的詩中指「母親去世」,但以「後」字指代至親過世,通常只有「父後」,游靜的「母後」則是對更常見、更正式的「父後」的顛覆。〈母後〉一詩寫母親的病與死,也寫游靜作為「女同」對父母期許的反抗以及和解。廖偉棠欣賞游靜傳遞出性別意識覺醒在香港社會的複雜性,「戰鬥很容易,但和解是困難的」。洛楓則是香港著名「榮粉」——以研究張國榮的明星形象和香港流行文化著稱的文化研究學者,同時她把「特別『港女』的做派」帶入詩歌語言和抒寫姿態中。〈愛在異托邦〉一如洛楓的許多以情詩為名的香港書寫,以一個經濟和知識獨立的女性視角,揭穿愛情的荒謬的同時,也揭穿了香港城市和公共生活的荒謬。
「中青年詩」的回聲:在兩代人之間
在同代詩人的寫作中,廖偉棠還挑選了池荒懸的〈扎染〉、曹疏影的〈春祭〉、鄧小樺的〈黑色的歌〉、周漢輝的〈龜苓膏〉、和陳子謙的〈短歌〉,展示「中青年詩」的多種面向:如池荒懸的寫作帶有強烈的當代藝術和實驗音樂氣息;曹疏影的詩則不斷將自己的離散經驗塗抹在北大「學院派」寫作底色上;鄧小樺的詩在有著對時代氣息極度敏感的同時,卻又保持一種「介入與否」的曖昧姿態;周漢輝「是真正的梁秉鈞傳人」,延續了梁秉鈞對庶民食物和生活的書寫脈絡,用食物體察香港精神,帶出社區的小歷史和香港小人物的生存史詩;陳子謙的寫作大量吸收了先鋒詩歌的修辭,不同於老一輩寫作中「敦厚溫吞」的鋪陳,他的詩歌充滿了張力。圍繞著同代人的寫作,廖偉棠點出一個共同的困境:「我們太過依賴隱喻了,太會保持『介入』與『抽離』之間的平衡了。有時候,我們不用隱喻就不會說話了,不會溝通了,只能用隱喻去講述社會的悲哀。我們希望這種詩學能夠終結於我們這一代,下一代可以沒有這麼依賴隱喻。」
而香港新一代的寫作帶來了更多可能性,廖偉棠分享了四首「年輕朋友們」的詩作:關天林的〈夜總會〉、熒惑的〈議題〉、李顥謙的〈雞〉和黃潤宇的〈你有白髮——悼蔡炎培〉。廖偉棠指出,不同於梁秉鈞這一代詩人直接閱讀英法等歐美現代文學原文,年輕一代的寫作者更多通過翻譯接觸歐美現代詩淵流——這並不是說年輕一代的外文功底不好,而是年輕一代發現了翻譯的魅力,「通過一個語言高手去發現和觸碰另一個語言高手」。青年詩人中如關天林和李顥謙就是在這樣的語言磨礪、切磋中建立自己的風格,他們的詩中充滿了「語言的暴力」。讀關天林的〈夜總會〉讓廖偉棠想到了電影《智齒》(2021),肢解的身體意象貫穿了整首詩;當然〈夜總會〉不只有「暴力美學」,還玩了蔡炎培式的「字蝨」——「夜總會」既有夜生活俱樂部(nightclub)之意,也有「夜總是會⋯⋯」的意味。這裡一語相關帶來的張力,賦予了「暴力美學」在都市中的不同面向。李顥謙的〈雞〉改編自「雞,全部都係雞」的香港流行文化迷因(meme),以「雞」隱喻人作為社會中的囚徒,以犀利的語言書寫「作為一個大監獄」的香港社會;〈雞〉代表著李顥謙的「青春殘酷物語」美學,一如他詩集中強調的「無明」狀態——這既是致敬商禽的詩集《夢或者黎明》,也是延續香港電影《一念無明》中「一念不覺,於諸事理,迷暗愚痴,無所明了,故曰無明。 」的佛家按語——「無明」的香港,徘徊在如「Limbo」/「靈薄獄」/「陰間」這樣的曖昧地帶,既非完全絕望,同時也難見曙光。
回到母語
最後,廖偉棠以自己的新作〈盲文辭典〉和〈毋語日〉結束今晚的分享。〈盲文辭典〉充滿了廖偉棠所追求的「絕對隱喻」,也就是說無法解釋也沒有必要解讀的隱喻。廖偉棠引用他在許鞍華紀錄片《詩》中講的一句話:「『詩既是表面的也是深層的』;也就是說,一個詩人應該最表層地讓別人理解,又應該最深層地觸動別人。」〈毋語日〉則設置了一個對詩歌語言的解構式批判:以「母語」(「毋語」/「母乳」)反思「父系詞」,以「雌辯」反思「雄辯」⋯⋯「毋語」通「母語」和「母乳」,是廖偉棠近幾年來在詩歌、詩學探索上特別關注的概念。廖偉棠希望引導讀者重新思考「母語」這一個概念,來反思社會對女性的語言、地方性的語言邊緣化、瘋癲化。
廖偉棠對語言的反思,引起了讀者的共鳴。有讀者指出普通話取代方言,令青年寫作者逐漸喪失了方言對詩歌創作的滋養;廖偉棠補充道,被取代的可能不僅僅是聲音、文字、詞語,思維、意象等等方面。但廖偉棠沒有那麼悲觀,「聲音的規範或許是不可逆的,但思維、意象的規範是可以抵抗的」,所以青年詩人更應該找到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經驗;而對於成熟的詩人而言,應該寫得「濁」一些、「澀」一些,跳出自己習慣的語用。另一個讀者則注意到「獻祭」這一個意象重複出現在香港詩人的作品中,便以周漢輝〈龜苓膏〉中一句「活在文明和規律,他沉入凌晨畫火」問廖偉棠:「當火焰熄滅後,在香港留下什麼?」這個問題令廖偉棠想起魯迅的《死火》,火焰雖然結了冰,但一揣在懷裡又燃燒起來了;廖偉棠形容香港的這團火能像魯迅筆下的「死火」一樣,經過一系列風波,依舊有留下來的朋友在很努力地維繫著這座城市的光榮。
李盲,一九九四年生於廣東新會。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碩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比較詩學和媒介理論。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2023)、「光華詩歌獎」(2022),詩作見《聲韻》、「虛詞」、《詩歌月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