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胡雪岩不是個成功的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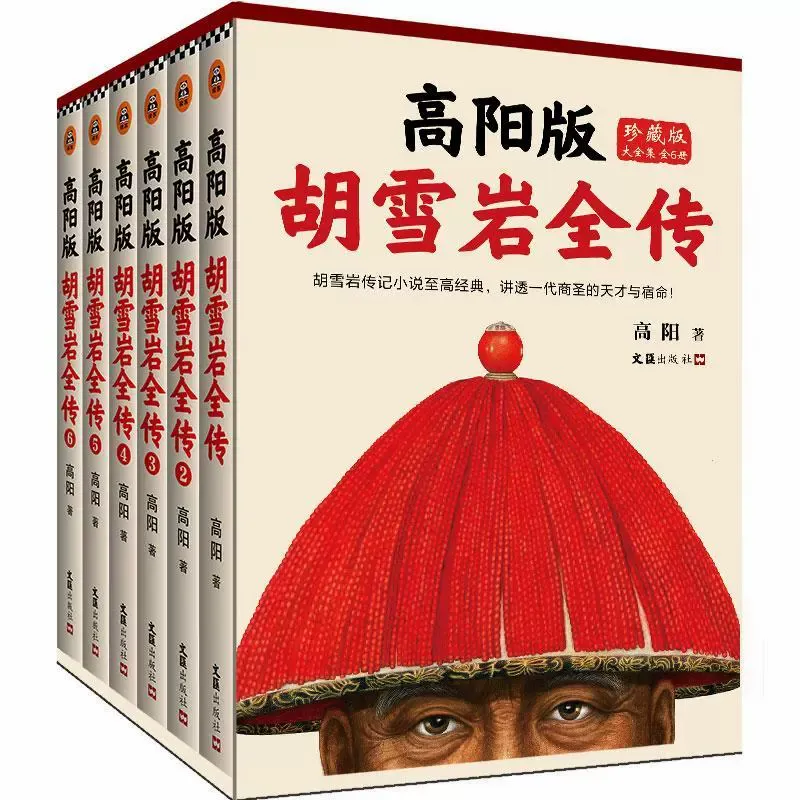
大約三十年前,台灣作家高陽的小說《胡雪岩全傳》剛在大陸紅火起來。某天朋友與我聊起該書透露的「商道」。我說,不就是主人公常說的「花花轎子人抬人」嗎?不就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後半夜想想別人」嗎?他笑笑說,老弟你看淺了,高陽這書的真諦是「四通」。
「四通」是當時流行的中文電子打字機品牌,這和胡雪岩扯得上關係嗎?朋友神情詭秘地伸出四個指頭比劃:「通官、通商、通匪、通夷!」
此後以胡雪岩為主題的各種小說和普及性勵志作品不知處出版了多少,卻未見有人提煉出這樣的金句。而細想胡雪岩的勃興和失敗,確實卻與這幾點息息相關。
胡雪岩的本名叫光墉,雪岩是他的字。他是近代浙江最著名的商人。年輕時任錢莊夥計,傳說他用追討回來的一筆「死帳」,資助落魄朋友王有齡赴京補缺。後來王有齡發跡,官至浙江巡撫,胡雪岩獲其提攜,承攬官款興辦錢莊。王在太平軍進攻杭州時自縊,胡雪岩又投靠新任巡撫左宗棠,為其籌措給養和軍費,辦理賑務和善後。清軍克復浙江後,大小軍官將所掠錢財存入胡系錢莊。胡以此為資本,從事貿易,在各市鎮設立商號,廣泛涉及典當、絲、茶、藥諸業,利潤豐厚,短短幾年,家產超過千萬。
胡雪岩為左宗棠辦洋務,協助創建福建船政局、蘭州織呢局,訂購西洋軍火。他還為左宗棠籌措「西征」經費,尤以協助其借外債而出名。最後官至江西候補道,銜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戴,服至黃馬褂,由此被稱作「紅頂商人」,在晚清被看作異數。
清末的大官僚身邊,都有長袖善舞的親信為其理財,提供各種資金幫助,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做他們的「皮夾子」。比如李鴻章用盛宣懷,左宗棠用胡雪岩,就連張之洞,當了幾年山西巡撫,轉任兩廣總督時,也帶着平遙「百川通」票號的人手南行,到廣州後,公私業務都讓其代理了。
詭異天象
光緒九年十月初五(1883.11.4)起,杭州天氣奇壞,連綿下雨。老天象水桶漏了底一樣,無日無夜連續下了一個月,僅有十六日一天放晴。
而上海卻是另一番景象。從十月初一日起,每當夕陽西下,便有紅光現於西方,燦爛直至夜間。後來,黎明之前,東方也出現同樣景象。甚至在小雨中,紅光也顯露身影。《申報》報道說:
初七日微雨,紅光伏於雲中,幾同不夜之城。行人可勿持燈也。初八日晨不見,日入後滿天紅黃之色,覺詳明而愈顯,是紅光因陰雨而日長也。十日晨,紅光如前晚,其紅愈甚,月光不能奪也。十六日寅正,月落參橫,紅光徐起於東方,雞不過初鳴而已。而紅光煌煌然如炬火高懸,照至半天,月為失色,頓作慘白之光,照地無影。而向東之粉牆白壁,儼若塗朱也。至本月廿三日晨,紅光尚未隱,午正視日之南尚有紅光隱隱隨日不散也。
這種奇葩天象,最早見於福建,後來出現多地。住在北京的翁同龢記載,十月十四日 「黎明日未出時,東方天赤如火」。二十二日,「黎明仍有紅氣如火,照窗皆赤」。次日「天明時赤氣半天,吁,可怕也。黃昏時,西方亦赤」。這樣狀況持續了一個多月,至十一月十三日,「早晚赤霞如昨而加甚」。
這是個什麼鬼?有人猜測是在潮濕的氣象條件下,陽光經過含有大量水滴的雲層,藍、紫系光均被濾去,留下的是波長最長的紅色。這是從特殊區域角度分析陽光與水霧的氣象關係,是否準確,希望方家教我。試想隆冬季節的京滬,早晨四點來鍾,忽然滿天大紅,那情形何等詭異,也引起飽讀史書的大臣們普遍憂慮。南宋時吳曦叛亂之前,就見「天赤如血」。翁同龢說:「臣以為非吉,但不敢實以占驗書耳,《宋史》南渡後屢有此。」御史吳峋以日色赤如血,責諸樞臣皆疾老瘦病,請派醇邸赴軍機處稽核,別簡公忠正大,智略果敢大臣充樞密云云。入對時,恭邸及臣等皆謝奉職無狀。
風潮乍起
國家確實處在外患內憂之中。
外患是中法在越南軍事對峙,局勢正在惡化。
1860年代,法國武力侵佔越南南部,接着由西貢出發,向越南北部擴張,企圖利用紅河作為入侵中國雲南的通道。同治十二年十月(1873.11),法國派安鄴率軍侵襲並攻陷河內。越南國王請求當時駐紮在中越邊境保勝的中國黑旗軍統領劉永福協助抵抗法軍。年底,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軍,擊斃安鄴,法軍被迫退回越南南部。次年,越南在法國壓迫訛詐下,簽訂《越法和平同盟條約》,向法國開放紅河,並給予法國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種權益。光緒元年(1875),清政府復照法國,對該條約不予承認。
光緒年間,法國繼續在越北擴充勢力。清政府派軍隊出關援越,又訓令清軍不得主動出擊。光緒八年三月,法軍派李維業率部再占河內。七月,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主動請纓,入越促成援助劉永福抗法。九年二月,法國進一步策劃將越南南北圻全部納入法國保護的計劃。四月十九日,劉永福指揮黑旗軍於河內西郊紙橋設伏,斃傷法軍二百餘人,李維業被打死。此後法軍增援,在從德到丹鳳一帶與黑旗軍作戰,又與越王簽訂《順化條約》。越王改抗法為順法,下令停止抵抗,使黑旗軍陷入困境。法國遠征軍總司令孤拔籌劃,準備進攻黑旗軍的大本營山西。國內關於前線的消息莫衷一是,上海常常傳出法艦將來襲擊的傳聞,搞得市面上風聲鶴唳。十一月十二日,山西之戰爆發。
內憂則是國內的金融形勢陷入巨大動盪,因歲在癸未年,史稱「癸未風潮」。
光緒九年,上海和全國的市面都很緊張。在洋務運動中剛剛起步的證券市場,經歷了一輪樂觀上升後,開始激烈調整。100兩票面額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股票,上年八月十五日分別達到253兩和216.5兩,本年九月,跌到90兩和70兩。使得投資人損失慘重。加上風傳戰爭消息,外資銀行決定收緊銀根,在香港和上海抽走約2百萬現款。山西票號亦決定月底收回在上海融出的百餘萬兩銀子,以觀動靜。市面上銀根緊張,前所未有。輿論認為,「百業之盛衰,視錢莊之興替。錢莊以放拆息為生意,而外行店鋪藉此轉運。錢莊之獲利則百業之鼎盛可知。」一旦收緊頭寸,市場必然顛簸動盪。
其他生意也很難做,其中尤以蠶絲的出口為最。蠶絲是胡雪岩在和洋人打商戰。過去外國人來華採購生絲,定價權在老外手中。胡雪岩從光緒七年起,大量囤積生絲,迫使洋商出高價購買。到光緒九年春天,胡雪岩囤積生絲達到15000包,造成大量資金積壓,而國際市場上,因意大利生絲豐收,外商在對峙中並不退讓。迫使胡雪岩於十月三十日將存絲折價賣給怡和洋行和天祥洋行,但價款需陸續收回,一時未能悉數到手。
以前傳說,胡雪岩在生絲大戰中投入二千萬資金,所以商戰失敗導致其破產。近來有人研究,認為胡囤絲資金不過四五百萬,損失也不過150萬兩。但生絲商戰落敗使他的信用受到極大影響,引發各處錢莊出現擠兌。
十月初六日,胡雪岩設在杭州的泰來錢莊因周轉不靈倒閉。接着,上海泰來錢莊亦倒,司帳人員逃避一空。十一月初二日,杭州清河坊內之阜康錢莊閉歇,滿城皆為驚駭,「貿易場中咸以為不寒而慄」。同日,上海阜康雪記錢莊,因有客戶提款數十萬兩,而上海市場銀根甚緊,一時無從調補,掌柜竟避往寧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彌縫,遂亦停歇。初五日,北京阜康亦倒閉,再次引起恐懼,富室巨商凡在錢莊票號存款者,紛紛前往擠兌,全城皆處於岌岌乎不可終日之勢。阜康為胡雪岩事業之始基,影響特別重大,《申報》稱作「銅山東崩、洛鍾西應之勢」。
追討存款
阜康攬存,既有公款,亦有達官貴人和中小儲戶。忽然倒閉,追索存款,也要化出大力,動用權力關係。
十一月初六日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京都阜康銀號,大賈也,昨夜閉門矣。其票存不可勝計,而圓通觀粥捐公帑六千兩亦在內,奈何奈何?」已故刑部左侍郎常恩,是同治十年辛未科的副考官,也就是張佩綸的座師,他家托張佩綸找李鴻章想辦法。李回信說:「昨委員赴浙清理阜康津號所欠公項,屬代商常宅存款,未卜能為力否?」張佩綸表示:「常宅之款,能在公款外先日清理方妙,不敢請耳。」
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有私蓄存於阜康,也托張佩綸轉請李鴻章關照,李鴻章回覆:「胡光墉擬先清公款,京外私存各項,再徐議折扣歸還。然聞江浙各典當已盡數查封,備抵各省公款尚有不足。順天府尹周家楣近因所允五典不能盡抵公款,蓋亦情見勢絀,此外家產似不甚多。承屬孫詒經侍郎存頊,浙江巡撫劉秉璋既允設法代進,當不至竟歸無着,容與劉通問時便為催促可耳。」
劉秉璋的兒子劉聲木也回憶:「孫詒經侍郎,乃父親庚申同年。有萬金在其銀肆內。張佩綸學士來書云:『孫詒經得失尚覺坦然,而家人皇遽,慮無以為生計,乞為援手。』亦已承諾。」有人認為,倒胡事件是淮系對胡雪岩的阻擊,這種說法,卻沒有過硬證據。
私款項中,還涉及恭親王和協辦大學士、總管內務府大臣文煜的存款。恭王的數目不詳。文煜被都察院左都御史畢道遠查出,在阜康存有36萬兩銀子。朝廷要文煜明白回奏,講出巨額財產來源。文煜解釋說是以前當粵海關監督和福州將軍時攢下的。太后認為「尚無掩飾」,但為數較多,責令捐銀10萬,納入官款以充公用。此時文煜甚得慈禧寵信,所以未被深究。次年甲申易樞後,他還頂替寶鋆,晉升武英殿大學士。作為抵債資產,文煜得到胡雪岩的藥鋪胡慶餘堂一半的股權。
追款就要強力逼迫。十一月初七日朝廷發佈上諭:
阜康商號閉歇,該號商經手公款及各處存款甚多,亟應嚴切究追。著畢道遠、周家楣提訊該號伙汪惟賢等,將公私各款逐一清理,並著何璟、劉秉璋密速查明胡光墉原籍資財以備抵償虧短公款。至各省有無寄頓資財,即由順天府咨行各該督撫,一併查明備抵。
錢莊票號
其實信用喪失,逼迫還錢,恰恰會激化和擴展金融風險。
19世紀80年代,正是中國經濟向西方近代體系轉型的初期。除了外國的商業銀行,尚無中資銀行。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的,只能是票號和錢莊。
所謂票號,是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信用機構。其最初的功能,是匯兌銀票。明清時期流通貨幣是銀兩,輔幣有銅錢、銀元,其共同缺陷是不易攜帶。異地交易,大量現銀不僅沉重,也不安全,需要委託鏢局押送。若能把錢存在出發地,拿着一紙憑據到異地兌換銀兩就方便得多。經濟活動的需求催生出匯兌業務。19世紀50年代,山西商人在全國二十多個城市設置了票號分支機構,從而聯成業務網絡。後來,票號又增加了存款和放款服務,向錢莊融出資金,在經濟運行中,承擔着類似銀行的功能。
錢莊也稱銀號,最初盛行在江南一帶,早期業務主要是銀錢兌換。當時的實物白銀,由於產地和冶煉手法不同,造成成色不一。又由於市場上流通的銀兩五花八門。明代中後期起,隨着中外貿易量大增,外國「洋元」、「鷹洋」在市場上廣泛流通。為了方便交易,市場需要一種能兌換貨幣的中介機構,可以統一銀兩和銀元,或者把銀兩兌換成銅錢、銀元,這樣錢莊就應運而生,業務也拓展至存貸款以賺取息差。
錢莊還與票號合作,為其承兌匯票,後來更推出 「錢票」業務,自己簽發票據,持票人可以拿來兌付現金。這種錢票流向市場,被其他金融機構用作貸款的抵押物。起初,市場只認可知名錢莊的錢票;後來隨着貿易擴張、投機盛行,實力較弱錢莊的錢票也被拿來抵押放款。
和票號不同,錢莊多是本地經營,總體規模較小,資本金充足率不足。為了逐利,平時接受外國銀行和票號的放款再轉貸,還放大槓桿,簽發出去的錢票超過自身資本的十幾倍、幾十倍,一遇風浪,就承受不住。錢莊在金融風浪中扮演着推波助瀾的角色,也在風浪中遭受到嚴重打擊。
當年沒有央行,財政的銀兩,存在戶部和各省的藩庫里不會升值,所以部分流入票號錢莊。一些地方上繳戶部的稅收和給各地的協餉,亦托其匯兌。但公帑不能壞賬,一有風吹草動,首先收回資金的,必是官方(票號亦然)。金融風潮或危機發生之初,往往是信心和流動性出現了問題,但官方和票號急於抽回銀根,錢莊只能倒閉。
大失敗
危機時刻,信心只能自己艱難地維持。
十一月初二日,杭州的阜康錢莊歇業關張,持票索錢者數以百計。浙江布政使德馨率杭州知府吳世榮親抵錢莊穩定局面,與莊伙約定明日還需開鋪營業,所出各票千洋以下者照票付訖,其餘存款暫緩三日。這樣才將喧譁的人群勸散。
初五是胡雪岩女兒出嫁的日子,親家是胡雪岩數十年的老友王六先生。《申報》報道說:
是日彩輿儀從盛極一時,觀者為之傾街塞巷。晚間尤形熱鬧,前驅則以明角高照數十對,次則燈牌數十對,間以各式玻璃燈,四五堂後則彩亭一座,有花燭亭、送子亭、和合亭等,共計四亭。每一亭則各式玻璃燈四堂,間以高照燈牌等件,望之竟如火樹銀花,如入燈市。最後則大紅統玻璃彩轎一乘,四面俱以彩燈結成,轎前則有家人執事數十名,或提燈,或宮燈,或子孫燈不等。加以清音樂工,長吹細樂,旗鑼傘扇,官銜執事。官亭後擁入人等統計約有二百餘人。聞是日行人之上街者,每名喜包共有三百數十文,計共有五百餘名之多,故小夫人等無不欣然得意也。
這是冰海沉船前的最後狂歡,也許還在向市場傳遞信心。但喜慶的場面依然擋不住擠兌。在北京,東四牌樓最著名的錢莊「四大恆」(恆興、恆和、恆利、恆源)門前人群鼎沸,街衢為之塞途。上海的錢莊,年初有78家,年底僅剩10家了。金融風波也造成市面的蕭條,杭州各衣莊、緞莊、皮貨莊、扇莊生意清淡如水,各絲行停秤不收。署理杭嘉湖道佘古香,因綱鹽局官款和私蓄十五六萬皆存於阜康,愁急交攻,竟一病而逝。十一月二十五日(12.30),總稅務司赫德在致駐倫敦稅務司金登干的信中寫道:
中國人大失敗!滙豐銀行的老朋友胡光墉在中國各地的買賣都失敗了。2800萬兩!北京這裏兩周內有44家錢莊倒閉。1兩銀子只能換11吊錢!
若將舊曆化為西曆,1883年的年底真是光景慘澹。那杭州所下的霏霏霪雨,京滬上空的詭異紅光,似乎都提前預示着不祥的凶兆。
戶部下石
二十七日是西曆元旦,都察院左都御史延煦上奏,稱「阜康之為害不止一方,所沒官款私款不下數百萬」。建議先行革除胡雪岩江西候補道一職,解交刑部監禁。勒令其儘快交出所欠公私各款。次日,清廷下令將胡雪岩革職,著左宗棠飭提該員嚴行追究,倘敢延不完繳,即行從重治罪。又稱胡雪岩有典當二十餘處,分設各省買絲若干包,值銀數百萬兩存浙省,著該督咨行各該省督撫查明辦理。
光緒十年正月初七日,兩江總督左宗棠上奏,胡雪岩所欠部款和江蘇公款,業經封產備抵。二月初八日,戶部又奏,請旨飭令各省督撫,今後所有應解部庫銀兩、以及各省協餉 ,概令委員親齎,不准再由銀號匯兌。還詳細規定了運送餉鞘(裝盛送繳稅收銀兩所用的木筒)若有丟失,對相關官員的懲處辦法。正在走入近代金融匯兌體系的官方財政,遭遇到市場風波之時,不是設法管控、救助、完善,而是倉促撤退,返回古代。
此時擔任戶部尚書者,是公認的理財專家閻敬銘。閻不懂現代金融,他的理財,無非儉省、剋扣、集權而已。李慈銘誇他「清操絕俗,其入掌邦計,仿國計簿,綜括天下財賦,勾稽出入,世頗以斂聚目之。然為國家計久遠,竭盡心力。」還說他「逮捕浙人大滑胡某(雪岩),尤快人心!」
晚清小說家李伯元則記載,軍機大臣每天上朝辦事,茶房照例在值廬里提供兩款點心。閻敬銘認為糜費,裁減了「點心錢」,同行皆枵腹,他「於袖中出油麻花僵燒餅自啖,旁若無人」。
當初和張之洞一起,通過李鴻藻力薦閻主掌戶部的張佩綸,在光緒十年四月借慶賀岳母大壽的《朱外姑馬夫人六十壽序》中,先回憶老人一生勤儉持家的美德,然後筆鋒一轉說:「然則儉者,君子之未節,而婦人之美德也。平津布被脫粟,荊公衣垢不浣,偽儉耳。」文中「平津」為西漢平津侯公孫弘,「布被脫粟」,指其蓋布被,吃粗米,形容生活儉樸。「荊公」即王安石,《宋史》說他「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公孫弘、王安石皆官至宰相,有人看出這是在影射閻敬銘。——當然這是題外閒話,但閻敬銘在收回官款、追查胡雪岩時痛打落水狗,使其再無翻身之日。
胡雪岩發達時,生活驕奢淫逸,娶有數十房姬妾。破產消息傳來,他斷然做出處置,某日早晨坐在客廳中,召集諸妾進入,然後所有臥房下鎖。每妾發五百兩銀子揮之出府。其中有人已經梳妝,則首飾珠翠可值數千金。有人猝不及防,除遣散費外一無所有。
關於胡雪岩如何籌款抵債,可見資料甚少。左、胡二人從前關係緊密,官場有目共睹。擔任過蘇松太道的邵友濂回憶,一日接見下屬,僚屬滿坐,左宗棠忽捶胸嘆曰:「君父之恩,略已報矣,胡光墉之恩,未能報也。」頓時四座駭然,繼以匿笑。
此次風潮中,左宗棠曾借戶部追討西征借款中一筆早已報銷的費用賬,給閻敬銘寫信,為胡緩頰:「茲據胡光墉來稟,浙省勒追,急如星火,大有性命之憂。」左宗棠明白,所有人其實都關注從前胡雪岩為他籌集外債,利息奇高,懷疑其中必有巨大利益。左宗棠指出「借用洋款本為不得已之舉,而甘省餉糧兩缺情形,珂鄉密邇,諒所目擊。軍情緊急之時,不得洋款接濟,真有朝不謀夕之虞,實為胡雪岩一人是賴。斯時軍事平定,弟不敢作昧心之談。」現在「窘迫危急,家產盪盡,縱令嚴追該革道,不過一死塞責。若其遽死,則夥友星散,於現在作抵之典當等項,反致有損無益。」但閻敬銘未予理會。
此後左宗棠因病去職,由曾國荃繼任。同屬湘系的曾國荃對戶部追討也不以為然,直截了當地回覆:此款「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以視戶部現辦章程,系在舊案准銷之例,應請戶部鑒核,轉予斡旋,嗣後不得援以為例,以昭大信!」
煙消雲散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閻敬銘上奏:
竊從前虧空各案在於官,官所侵者國帑,而不及民財。近來虧空流弊在於商充官,復以官經商,至舉國帑民財,皆為所侵佔,而風氣乃大壞。敗壞風氣,為今厲階,則自已革道員胡光墉始。查胡光墉籍隸浙江,也身市儈,積慣架空罔利,最善結交官場。一身兼官商之名,遇事售奸之術,網聚公私款項,盈千累萬之多。胡光墉起意侵欺,突於光緒九年十一月間將京城、上海、鎮江、寧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處所開阜康各字號同時全行歇閉,人心浮動,道路囂然。
閻敬銘說,經過兩年追討,胡雪岩欠款尚未繳完。當初胡雪岩開設銀號,就是用計侵取官私銀兩,其罪行重於錢鋪侵蝕票錢。又同時歇閉,遍及各省,官民受害者極多。他建議將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將其浙江原籍財產及各省寄頓財產查封報部,變價備抵。奉旨允准。
正在核辦時,忽然又得消息,胡雪岩已於十一月初一日(1885.12.6)在杭州病故。當日知府吳世榮率仁和、錢塘兩縣知縣,前往胡宅查封,見停柩在堂,所住之屋,租之朱姓,僅有桌椅箱廚各項木器,並無銀錢細軟貴重之物。其家屬稱,所有家產已變抵公私各款,現在人亡財盡,無產可封。並聲明胡雪岩生前統計欠繳京外各款共銀159萬2千餘兩,以其二十六家典當貨幣器具房屋抵償收繳清楚。虧欠紳民私款,除文煜充公銀10萬兩已繳解外,其餘也已據折扣變抵歸還,並無控追之案。所以浙江巡撫劉秉璋奏請免予置議,不再深究。
通過資產處置,最終對於公私存戶並未造成大的虧損,閻敬銘前奏顯然言過其實,但商界傳奇的豪傑胡雪岩,就此煙消雲散了。
今天看來,玩融資、玩槓桿,是市場經濟和資本運作達到一定階段的必有之物。對於官方和企業家來講,都尚無經驗,有許多經驗值得記取。
當時人認為,雪岩的字義就是冰山,他的發家暴富和敗落,前後不過二十餘年。這使人想起孔尚任 《桃花扇》中的那段名曲:「俺曾見,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但往更深裡看,金融危機也是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雖不見刀槍,卻更殘忍和血腥。這樣的故事,後來還在不斷重演。
「四通」秘訣
回頭再想胡雪岩發家的「四通」秘訣。通官通商,當無疑義。通匪指與江湖勢力勾結,此或當有,未見實據。至於通夷,那是肯定的。胡與洋人有很深交情,人稱「同治間足以操縱江浙商業為所外人信服者,光墉一人而已。」赫德也說他是「滙豐銀行的老朋友」。他的「絲戰」是場商業投機,未必需要提升到民族大義的高度。
胡雪岩悟通這幾個做生意的關節點,顯然是他爆發性成長的秘密,他的失敗,未嘗不也和這幾個方面有着直接關係呢?
研究胡雪岩興衰成敗,困難在史料不多。他如今在國內享有大名,與高陽七卷本小說塑造出來的藝術形象直接有關。我曾請教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陳絳先生怎麼看待這部小說,他說王有齡是他家的前輩姻親,家族中對王的具體事跡所知不多,想來高陽所知更為有限。但讀完《胡雪岩全傳》,還是能夠接受這個形象的。同樣,作為小說主角,胡雪岩的刻畫也很成功。我想陳先生的話是中肯的評價。
去年羅青在《文匯報》上載文,回憶高陽創作《胡雪岩全傳》,傾注了極大的心血。高陽說:「我就是胡雪岩!」甚至為他題寫《高陽代胡光墉書贈羅青詩》的條幅,以胡的口氣寫詩送他,雖是筆墨遊戲,卻見其入戲甚深。高陽之後,關於胡氏的勵志類財富類傳記頗為泛濫,甚至有「做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岩」的廣告語令我詫異。但胡雪岩畢竟是民族資本家的先行者和失敗者,他所遭遇的大時代,他的失敗的教訓,才是更值得總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