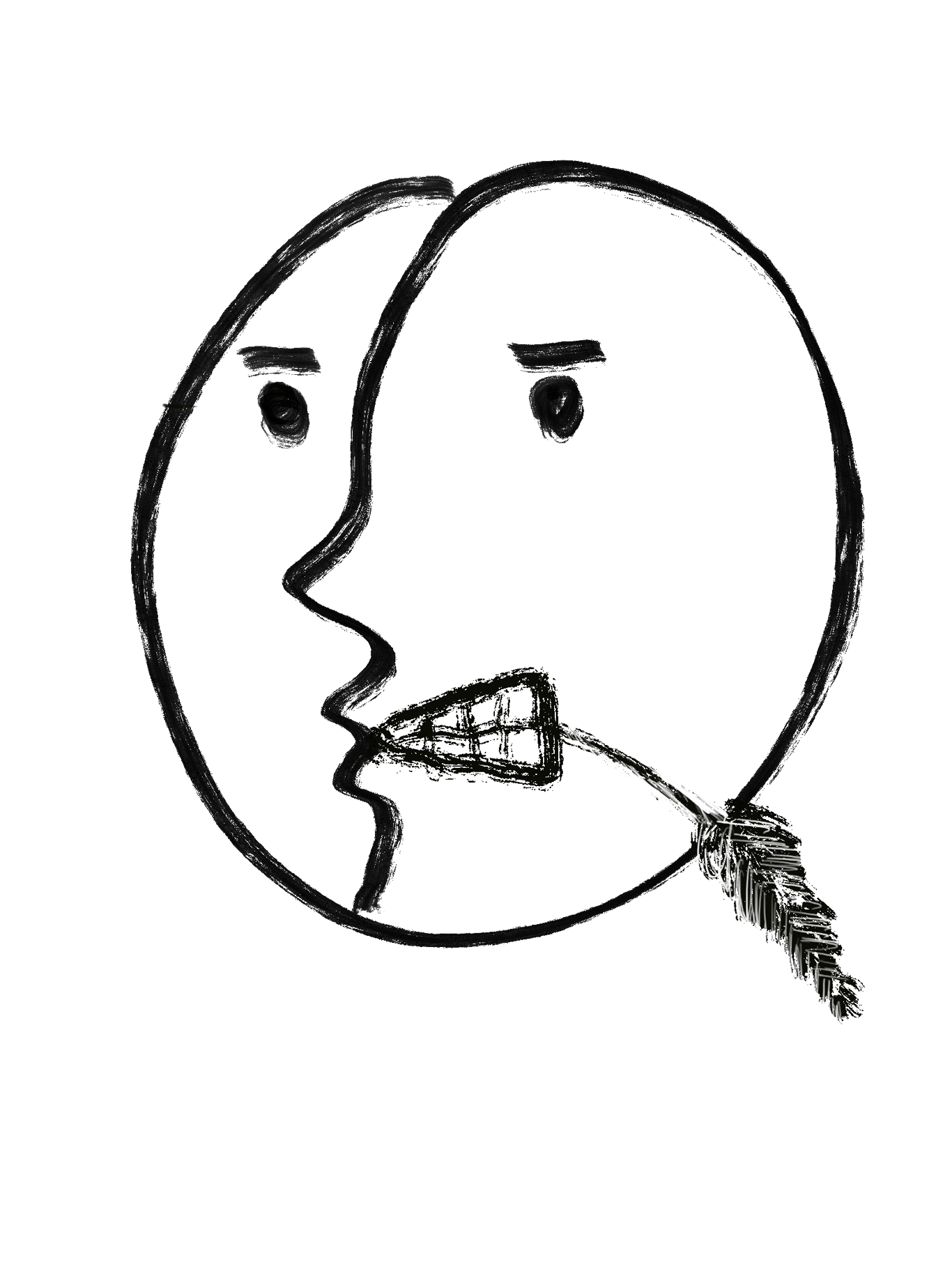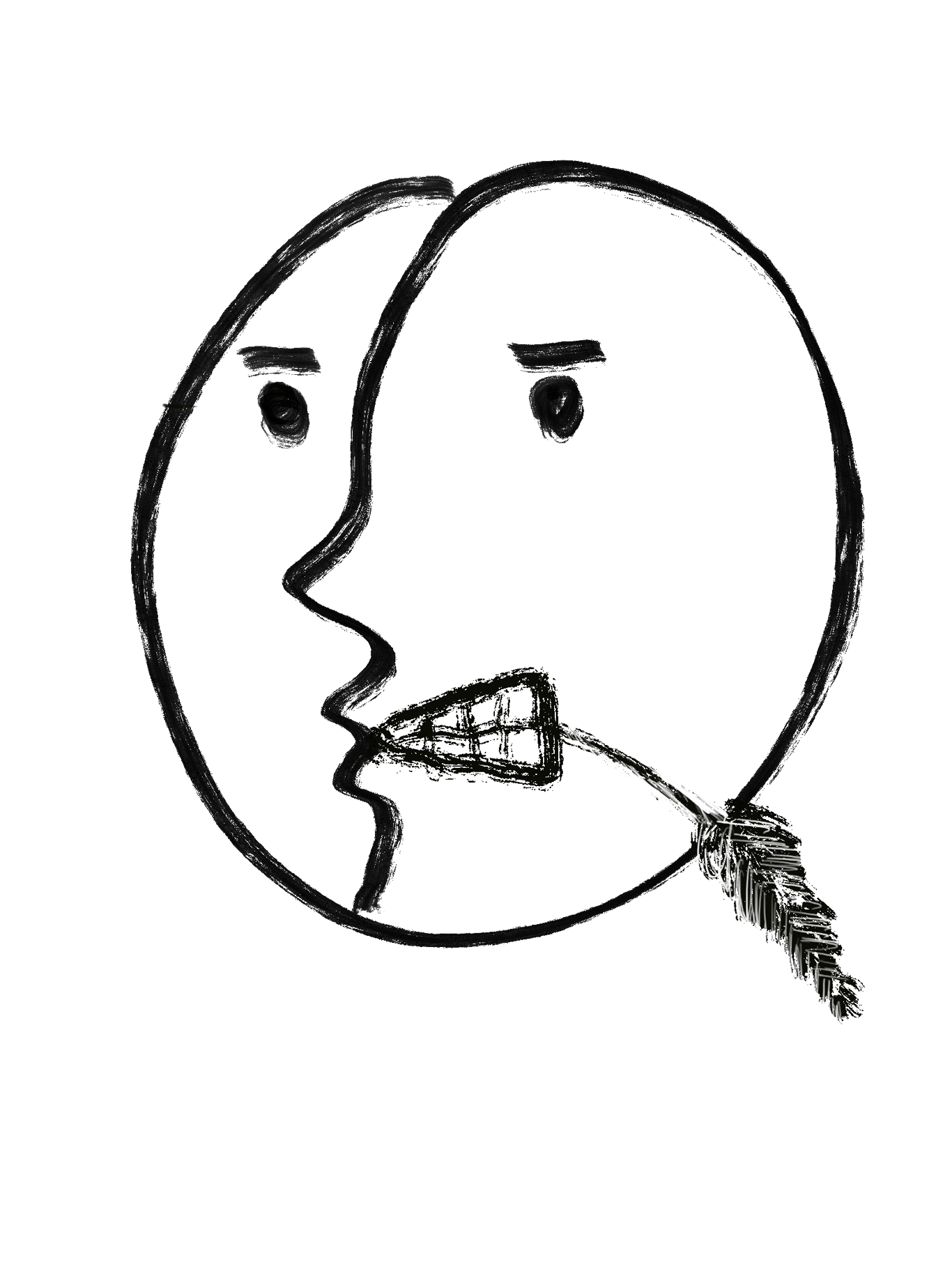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位置》:願我們都有屬於自己的
抱歉,這又是篇廢話很多的文。
我購買一本書時很少留意作者的性別,通常反而會避開過度強調以女性觀點的敘述,實際上沒什麼邏輯只是個人愛好的養成,大概是曾經閱讀幾本令我卻步的女性作家寫的散文,後來開始有些排斥(如文中所述),或許對有些人而言,身為女性有這種想法是很可恥的吧?
雖然沒有刻意選擇,這兩個月讀的幾本書幾乎都是女性寫的(部分也有寫文),有小說、回憶錄、歷史研究、社會學理論和女性主義研究——小說的陳述者能跨越性別應該是更好的,回憶錄的作者性別是很重要的關鍵,而社會學類型的書,有的主題大概是女性特別愛研究的,印象中我以前法學教科書就沒有女性學者寫的,如果是研究家事法和女性相關的權益等等的,就會有很多女性研究。
前面廢話了很多,是為了說明為什麼在最近讀的許多女性作家之中,有必要選擇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肯定的安妮艾諾——上個月讀完「記憶」和「嫉妒」,前幾天讀了《位置》——前兩本書的書寫只有女性能做到,確實激勵了我,女性也不再因為有人將心裡的感受說出來而感到羞恥(用詞不當)。但曾有人誇獎我寫作像莎岡、思考像德波娃,當然自愧不如(很多很多),同時心裡總是想著「為什麼類比的不是一位男性?」、「女性的書寫角度有什麼特色?」。
@左右言她 的徵文是介紹一位女性作者的一部作品,「只得」選擇出安妮艾諾的《位置》(台灣譯版為《位置》加上另一篇〈Une Femme〉),否則我是想直接介紹作者。艾諾在書中一開始就表達了在父親過世後想著手寫關於父親的生平,以前不敢寫是怕別人覺得「我們不夠好」,我讀到這裡時被刺痛了一下,相同的陳述在《那不勒斯故事》中也有,她們花了幾十年的努力才離開原來的階級,如今又要把自己成長背景寫出來,但對於每個寫作者而言想逃避的不全是「階級」,也都有自己的陰暗或不想揭開的一面⋯⋯
關於階級
她大多的著作是以女性觀點而主,這篇著重於社會階級。
艾諾說,寫作是一種政治行為,報復她所屬的階級。我曾在另篇文章寫過不喜歡這種意識形態,她不正因為讀書改變了自己的階級,為什麼要報復?承認是我想得太理所當然,外婆和她是同代人,外婆不用透過出色的讀書成績來跨越階級,而是把讀書當作不得不做的「努力」以維持階級的體面(這在某些人眼中也是「那個階級的特權」,她還能追求其他興趣),打趣的說這種特權對於不愛讀書的人而言是一種幸運。
艾諾和《那不勒斯故事》的主角都有類似的背景,為全額獎學金而選擇就讀高等師範學院,我以前覺得這種應該在歐陸法系國家都有的師範學院公費生的體制是一種「幫助」窮人脫困的「好方法」(我知道這個主被動詞看起來很傲慢),一定有許多人家境因素不得不選擇師院而放棄兒時的夢想,或者是他們從小的目標就是這個唯一能解套的方法⋯⋯他們會感謝這種制度嗎?
艾諾提到祖父母只會說土話,父親的法語和寫作能力不太好,她小時候經常會指責父親說話的方式和粗魯的行為,後來讀得越來越多,和父親間變得無話可說,這成為她寫作的一個理由。即使無法理解自己女兒讀的書,父母還是明白她必須受教育,把她送去中產階級和大農戶的女孩居多的修女住宿學校。
我經常能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工人階級的子女類似的敘述,或多或少有些埋怨自己迫於與自己的原生家庭畫線,如果出生於中產階級,就不會有這種「不妥」的感受?但每個家庭還是會有各自不得碰觸的點。舉例說,根據《巴黎評論》記者的側寫,莎岡想擺脫「富家女」的標籤,但十九歲的她穿著真皮平底鞋、八面玲瓏的接待記者喝威士忌也就破功了,恰好艾諾寫到她父親慎重其事的接待她的同學是很鄉下人的行為,中產階級同學們的家庭則是將接待朋友當成很自然的事。
不過,我覺得不論是性別寫作或者是關於階級的自白對於台灣現代的讀者而言應該都不是很難得的,可能是戰爭年代出生的歐洲讀書人比較需要注重老派的體面,台灣的鄉土寫作反倒也曾是一大主流,突然覺得自己讀普魯斯特的作品太不應該了!
艾諾原本想用小說形式寫下父親的一生,後來發現只能直接憑著記憶將其紀錄,她也提到在倫敦時與父母親通信,盡量不要舞筆弄文以免和他們拉開隔閡,我想這就是她寫作選擇樸實敘述的原因,為了站在自己曾經的那個階級中。
位置
徵文主題是介紹女性寫的一本書,我想沒有人能反駁艾諾作為女性作家的角色,但可思考《位置》這書一定得是女性來寫嗎?
如果換作一位跨越階級的男性,是否能寫出一樣的東西?我的想法是各階級、性別的作者都會有自己的位置,但當然沒有一個人能跟艾諾一樣,也沒有人是一樣的。為身為女性,我還是認同十九世紀的莫泊桑在《項鍊》中說的(大意),「女性本沒有階級之分,她們各憑本事(因美貌、才華或社交手腕)取得更好的地位」,雖然很陳腐但女性依然比男性更容易跨越階級,假設是一位男性讀到高等師院也就是一名教師,而女性可以(以下自行造句)⋯⋯
讀安妮艾諾的非虛構或艾琳娜‧斐蘭德的小說都有提到那年代工人階級的小孩因家長反對無法繼續讀書,老師會對學生大發脾氣,說「你父母不要讓你們讀書改變階級嗎?」。卡繆為艾諾的上一代人,他很幸運在殖民地長大還能遇到願意和他外婆說道理而不是羞辱文盲的老師,他靠獎學金完成中學教育,在《快樂的死》中提到財富的重要,能想像他們在讀書時對於金錢的迫切性,他需要的遠比女性作家吳爾芙要求自己的寫作空間或自己的收入多更多,這是位置的問題而非性別。
不過那時代的人還是幸運的,他們確實能因為教育而改變階級,但我想的是現在的階級已不再明確,更多的差距在於資產,而不是否定教育帶來的改變。
之前我讀過原文版的《Les Années》,有很多句子看似沒完成,好像是艾諾的特色,在《位置》的中譯本中還是有一樣的感受,翻者沒有多事的把句子填滿還蠻令人欣賞的。
後記:
我每年生日都會寫一篇文章順道提到世界讀書日,甜點店第三年在四月中開始舉辦「盲選書」的活動,想藉此說明買書不要被書皮的設計與行銷語所影響,一直很喜歡自己的生日是在世界讀書日這天,雖然我並不喜歡過生日。
對於「4月23日與好幾個作家的生卒有關,但他們都不是女性」的想法,我認為只是剛好4月23日可以扯出很多文人(我小時候只知道與莎士比亞與和塞凡提斯有關,後來又有了馬奎斯),而放棄了使用剩下的364或365天當作世界讀書日,其實沒被選上的日子裡的男性作家還是多於女性作家的(畢竟男性作家比較多),大概是因為我不太意識到性別這件事⋯⋯不過「男性作家比較多」這當然也可以是個議題。
也可以試想,如果要更公平的選擇一天與多位女性和男性作家有關係的日子,那會是哪一天?
(封面照是諾曼底地區的某個小鎮)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