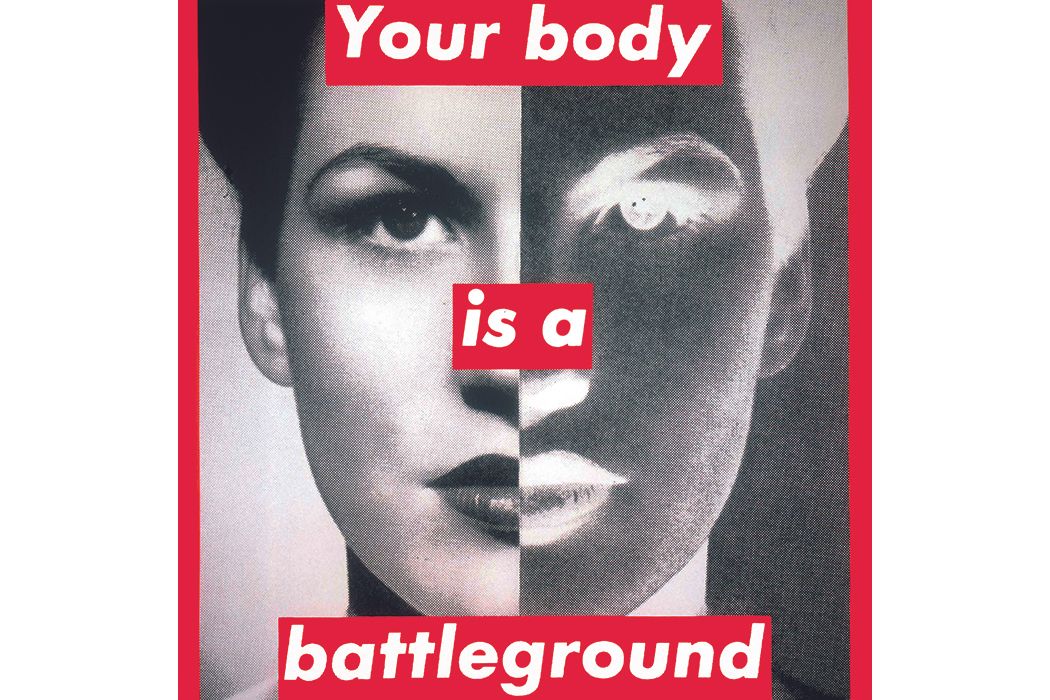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七月下旬到八月底的时候,我回国了一个月,先后去了上海、西安、成都、深圳、张家界和北京。我和朋友两人一起,沿途在各个城市做公共活动,顺带考察一些当地的社会组织或是涉足社会创新领域的公司。
原本,这一个月只是为我后续的回国做预热的,我希望多了解一下国内相关产业的情况,顺利的话对接好之后的工作,这样九月份再回到纽约,我就可以直接卷铺盖回国了。
我不是没有做好回国的心理建设,然而没想到的是,我全部的心态都在这一个月内崩坏了。现在我回到美国已经两个月,并且打算继续赖在这边一段时间。
很难讲是具体哪件事情导致了我的变化,压力是不断累积的,自我消化的过程也用去很长时间。今天我之所以要写下这篇非常不阅读友好的长文,是因为认同张洁平说过的一句话:
“旋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旋涡的样子。”
1. 公民教育公民
刚开始我们也有过一段特别充实的日子。因为我的习惯是每次回国都要做几场公共活动,目的是多联结人民群众,分享对时下一些公共议题的知识和见解,而不仅仅是吃喝玩乐走亲访友。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了策划,准备活动的内容、联系国内的场地和资源,前后忙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凌晨四点的纽约。我每天下午都会去朋友家一起工作,常常要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才进入状态,我们有时在临近午夜才吃晚饭,再继续工作到凌晨四点钟左右,然后我走路回家,在天亮时上床睡觉。
想想挺魔怔的,两个无业游民几十天如一日地通宵,干着吃力不赚钱的活儿。
在策划活动内容的时候,因为正赶上国内推行强制垃圾分类政策,我们觉得正好以这个为主题,引入一些环保和社会创新、公民教育的内容。而且考虑到国内紧缩的舆论环境,我们认为至少这个内容是安全的。
后来,就如很多参加过我们活动的朋友所知,我们还算顺利地在上海、西安和成都做了六场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张,我和朋友几乎天天窝在旅店赶工,连做梦都在看PPT,游玩或者社交的时间留得太少,感觉比在纽约还忙。
上海的第一场活动因为各种原因不尽如人意,让我连续几天情绪低落得不想说话,陷入一种过度反思的状态。所以到了西安后,我们立刻把已经过了好几遍的PPT拿出来一张一张检查,逻辑一个点到一个点地推敲,有时几句话的衔接都要反复调整,感觉脑神经都被一根根捋清楚了,居然在这个过程里出现智识高潮,精神都振奋了起来。后来我们有了一场很好的讲演,观众互动积极,传播效果也达到了预期。我如释重负,还莫名地有种一雪前耻的快感。
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
我回复ta:“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拍出《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有好奇心和研究、学习的方法论,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
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stake,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要推进这一理念,就必须先打破公共参与的迷思——你需要有“资格”才能介入公共议题。当一个人抱持这样的想法,ta就已经剥夺了其自身的能动性。
公共参与是一段自我赋权的旅程,这绝不是轻松的,每个人都可能从一窍不通开始摸索。我也由衷体会着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杂人等”,特别是一个女性,在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中,遭遇到的质疑、调侃、嘲笑、轻视。或者在某些男性眼里,欣赏也只不过是将其看做一种花样,而他们仿佛有天然的义务去当评委。
我认为敢于公开地失败是重要的,对于个人,对于社会来说均如此。放弃粉饰完美,是任何成长的起点,所以承受这种创伤是有价值的,但并不代表我们理应受虐待。
支撑我的,除了对“公民”这一角色的理解,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还有每次被挫败的时候,都会对自己说:“下次我会做得更好。”
我永远都有下一次,而我会在下一次翻盘。你没法吓阻我,因为你将继续固步自封顾影自怜下去。
2. 像防贼一样地防民
我们的活动高峰是在成都,毕竟是自己家乡,我在那里有更多的社群基础和资源。我们在成都做了四场活动,包括两次全天时长的社会创新工作坊,系统地把我们在纽约学到的一些社会创新方法论和工作经验带回了本土。我们甚至还去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工作会议上介绍纽约市的废弃物处理经验,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建立相关体系。
可能是因为在成都太活跃,所以我们也是在那里被人盯上的。一开始是和我们合作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们,活动的海报一贴到外面,就有警察上门来盘问,原因是我俩的名字看上去很像外国人。
我们以为这就到此为止了,后来活动也有照常举办。但是警察却在继续纠缠我的朋友和那个组织的负责人,并要求他们提供我们的背景、活动内容和参与者的名单。
因为主题的关系,来参与工作坊的人大多都是成都当地的社工、NGO成员,其中也有几个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同行。介于当时的时局,我朋友怕给我们造成麻烦,就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去除了。
朋友尝试过帮我们打听警察调查我们的由头,后来在交谈中,才发现对方其实是国安。所以我们明白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海外背景所以受到了重点关照。
我有一些不安,但也期待能和他们正面接触,毕竟我没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有什么问题大可如实道来,也权当一个人类学田野经验了。但让人恼火的是他们并没有光明正大出现,而是鬼鬼祟祟地骚扰着我身边的人。
我也觉得非常可笑,为着有关当局像防贼一样地防民。可他们的行径又比我们更像在做贼。
我没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爸妈,不是因为怕他们教训我,而是作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大饥荒、六四、大下岗等各种政治灾难的知识分子,现今的政治氛围已经让他们高度紧张。我不想让他们一把年纪了还要再为这种事情操心。
原本我们在北京的书店还会做一场活动,场地都安排好了,文案也发出来了,但因为有了这一出,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本着对彼此负责的态度,我还是把活动给取消了。
3. 什么是噤若寒蝉
离开成都后我们去了深圳,一座我以前从来没有造访过的城市。我们本来打算从这里去一趟香港,也没别的计划,就想过去旅游、会会朋友顺便了解一下当地情况,也见证一下这段历史。但是因为被我爸妈极力劝阻,最后就只在深圳停留了几天。
记忆中那几天深圳非常炎热,我见到了在当地工作生活的陈纯,而且很不巧,正好是在他被小粉红举报后疯狂网暴的时候。
之前我读过他很多篇文章,觉得非常受用,而且也一直感念他在刘强东案和中国MeToo运动里的义举,但真正建立联系并没有多久。没想到就在见到他几天之前,他曾经发在朋友圈里几张去香港参加传媒人和平散步的照片被别有用心的人截图,并在反送中运动白热化的时候给扣上了“港独”的帽子加以曝光。我记得几乎是在同一天里有好几个公众号发文炒作此事,并且两次把他推上了微博热搜,真心给安排了回明星才有的待遇。
他后来写了篇文章分析小粉红们的极端行为,但说实话,这事背后没有推手我是不大信的。
网暴开始后他紧接着就被全网封禁,公众号、微博号、豆瓣号都炸了,连以前出了本书好像都给下架了,只留了个微信号还能保持私人联系。一个写作者被这么个搞法,简直是五花大绑了按在地上摩擦,也不给人任何申辩的机会,就着这滔滔污名就地一埋,就等于判了个社会性死刑了。
我们是有天晚上在一个粥铺里见面的,一起聚会的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一位也是MeToo某个案件的当事人,还有一位端传媒的记者。陈纯的精神状态看上去不错,说他前一天刚被警察叫去问话,对方还算客气,但考走了他手机里的所有信息。他说自己并不心虚,因为从来就没发表过任何和港独有关的言论。
印象很深的是,他说起自己朋友圈被截图的事,提醒我们都要小心。于是我们三个都立刻拿起了手机去翻朋友圈,检查自己有没有发表过任何和当局不一致的言论,然后该删的就删。
回想起那一刻,才理解什么是噤若寒蝉。
但厄运仿佛是注定的,后来相似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了我身上。我被一个前同事截了图,同样扣上了“港独”的帽子挂在朋友圈里破口大骂,下面评论里还有一个我相识了十多年的朋友在叫好。
我也不是没责任的。起因其实是我那天偶然刷到这位前同事在朋友圈训斥翻墙的学生“思想不端正”,并告诫他们“不要给国家拖后腿。”我百思不得其解,想到要是我没辞职,她的学生就也会是我的学生,便多管闲事评论了一句:“你应该就这段话对自己的学生道歉。”这就踩爆了她的雷。
人们就像是传染了什么失心疯的病毒似的,我都没觉得生气,只有一种超现实的荒谬感。
陈纯的处境在短时间内更加恶化,在深圳第三天的时候我约他去逛书店,顺便多聊一下,但他仓促回复说自己暂时不便出门,我再问就没有回答了。
直到当天深夜的时候他才回复了我,说又被警察找了,说自己在被几个部门盯着,暂时没有行动上的自由。
“如果我来见你,你也会被盯上的。”他说。
之后我去微博上搜了下,发现是因为他去facebook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末了仍旧提醒周围的人要小心,不幸的是这个post又被截了图,被粉红头子挂在微博上继续煽动,才又加重事态。
为他抱不平的人也受连累,陈纯的读者被粉红们在网上人肉,一个个曝光了照片、真名、学校和专业,甚至被举报到学校去。因为我俩有一些共同好友,所以我也遇到了一个他的读者向我求助,说被粉红举报然后网警直接找到了学校,他毫无抵抗力,最后只能被迫退学,还是在父母的协调之下学校才同意不给处分。
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绝望无助,却无计可施。陈纯也只能在朋友圈呼吁大家不要再为他出头。
听说有人被政治迫害,和身边的人遭到了政治迫害的感受程度相差很大,后者是一种紧逼的危险,和切身的恐惧。
所以我们也没有再见。直到风头过去之后,看见他有继续发表文章,偶尔还在朋友圈发个自拍,说些风花雪月的话,才觉得放心了些。但作为那场网暴的旁观者,亲眼见证了一个有良知的人在这个社会里被如何对待之后,我的心已凉去大半。
陈纯并不是第一个。我曾经深受他们鼓舞,也曾因此愧疚过自己的胆怯,但久而久之,我的心已凉去大半。看到面前的人正承受着数倍于我的重压的时候,甚至只能保持某种冷漠,以便说服自己继续将疯狂看做常态,否则不知如何应对彼此的情绪负担。
在成都时,我们曾和一个公益机构合作,在其面向公众组织的一期女权夏令营里担任讲者,而我们的朋友大兔也参加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国内见到她。那天大家做完活动,凑在一起说说笑笑特别开心,可就在她一次查看手机的时候,突然情绪崩溃,掩面大哭起来。
我立刻猜到是和她丈夫小危有关的事——小危之前因为从事帮助尘肺病工人维权的工作,已被警察拘留了数个月。看着大兔伤心欲绝的样子,我的心也跟着沉到谷底,可我的反应却是无动于衷,说不出话,身体也完全动弹不了。
分开之后,我才发信息安慰她,得知小危已被控寻衅滋事罪正式批捕了。
4. 想放声尖叫
我似乎一直在逃避书写这个夏天发生过的很多事,即便它们曾经重创了我,并永久性地改变了我相信过的一些东西。
那时整个人的脆弱和内心的动荡,我现在会觉得难以想象,但是当我终于开始动笔,眼泪竟不受控制地流个不停,使我难以继续下去。然后我才明白这些创伤并没有被好好处理,我也不能把自己或他人遭遇的暴力当成什么常态。
在夏天刚来的时候,我写了那篇《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有丧家之犬的感觉》,想抒发一下心中的孤苦,却意外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后来再也没有去看过那篇文章,因为那时发出的疑问,我现在也并没有答案,反而向着更无边无际的混乱里陷落。
如果那时,我还是在回国与不回国之间挣扎,现在的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你举目四望,夜幕茫茫,连一处道标都看不到。倘若心中的羁绊已被割舍,身在何处又有什么区别?
可我常常又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一次次地选择,都总是走向少数?这条路像是越走越窄,一步一步都越发感觉到被掣肘。我尝试突围,却在这个过程中,一次次体会到了自己的软弱。
后来我明白了,我在三十岁那年选择辞职、离家而跑来纽约,就已经决定了要和大多数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有朋友对我说,也许你不需要去刻意做出选择。当一个人在不断地践行着信念时,外界的反馈会将你推到那道唯一的门前,使你和自己的命运不期而遇。
我从未感到后悔,可我也会害怕。当我遇到可以带我回归主流的契机的时候,当我想要朝自己向往的事业更进一步的时候,我都不断动摇,却仍然无法抵抗这种宿命一般的吸引力,要去撞击高墙。
一切虚伪都禁不起这撞击带来的冲击,它使得我生命中那些真实得残酷的事物一件件显现,只要我咬紧牙关睁大双眼,谎言便越发无处遁形,这种快感竟让我欲罢不能。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明白,为什么父母这么想把我保护在他们所构建的舒适圈里。前三十年的我仿佛是个盆栽,直到自己打碎了花盆,去了外面的世界野蛮生长,才体会到人生中有那么多求之不得的渴望、无法挽回的失去、难以为继的联结、愈合不了的创伤和没有反转的悲剧。
才体会到在时代湍流、国家暴力面前人的渺小和无力。
想放声尖叫,反而被困顿在失语之中,然后是更漫长的失落,久到我几乎已甘于自我放逐。内心在承受冲击后遗留的惊颤反反复复不能退去,有时候整个人魂不守舍,心不在焉,难以集中注意力在当下的现实中。
5. 哪里也不是故乡,哪里也不是异乡
离开深圳后,我决定暂时消极避世,找个风景区游山玩水一番,好好地进行自我疗愈。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行程里会多出一个画风迥异的张家界。
而我爸妈得知我要去玩,也都像松了口气,积极地给我介绍当地各种景点和美食。感觉他们巴不得我天天当个游手好闲的废柴,只要别再关心政治。
出发之前,我妈叮嘱我她在张家界遇到过比较刁蛮的当地人,叫我小心不要惹是生非,于是我就先入为主有了“当地民风彪悍”的印象,再加上我也很久没在国内旅行,平时听多了坑蒙拐骗的小道消息,心里总有点戒备。
没想到那一路遇到的人还挺让我意外,从半夜载我去旅店的出租车司机,到旅店老板的一家人,到路边餐馆的老板娘,都对独自一人的我表现出来了超常的好奇和关心,使得习惯了独来独往的我,由衷体验到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世故的温暖。
准备去武陵源森林公园那天,由于所有人都担心我找不到路,搞得我认知焦虑,也以为自己真会找不到路。所以我就偷懒跟人拼了个团,找了个导游小妹带我进山。
导游小妹是高中生般的低龄感,穿了件全身印满了“我爱钱”三个字的T恤。她的解说风格就像所有中国导游的出厂设定一样,内容主要由当地的仙侠志怪传说和党内领导的访问事迹组成,然后添加一些软色情和成功学的段子。然而好学如我,还是努力从她那里挖掘出了一些地理数据。
跟我拼团的是一对贵州来的情侣,男的特别喜欢插科打诨,但为人随和大方,竟然还有几分绅士风度;女的也很友好,会关照别人,一路上都看着我,生怕我走丢了。
她和导游小妹都说我一个人出来玩很厉害,都不怕危险。
“遇到事情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啊。”
晚上被他们拉着去看了个当地的土味文艺晚会(一开始我是抗拒的),领略到了各种包装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牛鬼蛇神,各种打色情擦边球的风俗节目,和传销现场既视感的大师才艺秀,他俩看得一会儿拍手一会儿大笑,我有点尴尬,仿佛不想扫他们兴一样跟着笑。刚开始还觉得新鲜有趣,在意识不断跳脱后终于完全出戏。
于是之前我们建立起的亲切感便又疏离了。若不抱着猎奇的心态,我已经很难和这些前现代味道的scenery互相关联和认同。相较之下,纽约对我来说好像更为熟悉,画廊,博物馆,爵士酒吧,百老汇,中央公园,都是我日常所习惯的文化生活。
是啊,我的身心永远都没法合二为一了,它们注定一个在此岸另一个就会去向彼岸,哪里也不是故乡,哪里也不是异乡。
第二天我就脱了团,自己去玩了。
在张家界其实安生了没两天,就又经历一场彻底的撕裂。毕竟作为一个朋友圈网红,我时刻都要靠点赞维持自尊,一天都没法不营业。
环球记者付国豪在香港机场被示威者围堵的事件爆发后,平时从来没见关注过香港议题的人也纷纷站出来表态,在短暂的震惊、质疑和迷惑之后,是此起彼伏的咒骂,一连几天,我都感到被铺天盖地的仇恨淹没。
因为不忍心看到几个香港朋友表达他们的痛苦煎熬,我想去尽量弥合那撕裂,所以转发了一些有助于降温和缓和矛盾的言论,包括示威者事后发表的道歉声明。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们很快都被墙掉了,就连我保存的很多香港朋友发的朋友圈截图,也一张都发不出来。我好像被困在一个真空里,又像被沉入了深水,目睹着周围人歇斯底里地张大嘴,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那一刻品尝到的屈辱和悲愤,几乎从身体内部捅死我。
如果不是香港出事,我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墙的威力,它十几年日积月累对国内民众产生的影响,其效果都在这一次得到了最大释放。我和很多朋友在认知上的鸿沟,只不过终于有机会暴露出来而已,但窥见他们的几分真实底色仍会让我心惊。
不出所料的是,我引来了又一波的人身攻击。有个人在留言里说:“现在我觉得你很可怜,是一条真正的丧家之犬。”
我觉得他说得好对。
6. 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
到达北京后,我已经非常想回纽约了。
我高中时代的朋友用自己的家收留了我,她曾经是极力劝我不要回国的人之一。她自己在北京打拼了十多年,也是坚决不撤回老家。每次我见到她,她的公司都不一样,跳一次槽工资就上一个台阶,不变的是都忙得昏天黑地。我在她家住了五天,没有一天她和她老公是在晚上十点前下班的。下班了两人也无话可说,瘫在沙发上各自玩会儿手机就去睡觉。
这工作强度,感觉也没法生养小孩。所幸她是个铁丁,家里养了两只猫就算了。
“大学毕业十多年了,我就没有一天不加班,实在太累了。我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使劲儿挣钱,争取四十岁前就退休。”
我忍不住说起之前国内程序员们发起的反996运动,她就像听了个段子似的轻笑了一声。
另一个陪我玩的朋友也是老相识,是首都某双一流大学的学生。她带我去学校里逛了一圈,开学的日子还没到,大批的学生就已经聚集在操场上从早到晚地练习走方队,为即将到来的70周年大阅兵做准备。朋友说,去参加训练有补贴,还和奖学金评优什么的挂钩,所以大家都很积极,她宿舍的其他人都去了,回来还教育她太不合群,不懂集体荣誉感。
我问她怎么不去,她说,害怕被同化。
“考大学的时候之所以想来北京,是因为很喜欢这里多元的文化氛围,最近北京都没有活动了,感觉很压抑。而且我也不看新闻了,反正也没什么能信的。”
我理解她的心情。北京曾经是我每次回国最常去的城市,我国内朋友圈子里的人除了在成都,就是在这里。然而最近两次来,作为一个游客经历了频繁的安检、查身份证、人脸识别后,我觉得它仿佛对我抱有敌意。
好在风景是无碍的,北京的秋天正是它最好的时节,每日阳光明媚,凉风习习。我和朋友去了颐和园划船,一边划一边用手机播放电影《颐和园》的主题曲,并跟着唱起来。眼前一派湖光山色,树影中点缀着亭台楼阁,竟然浪漫至极。
我们停留在湖中央百无禁忌地聊天。很奇妙的是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久违的放松,像是被这个漂浮的小岛保护着,暂时远离了整个大陆。一路上累积的愤怒,恐惧和悲伤,和对庸众难以抑制的厌恶,都交付给这方宠辱不惊的天地了。
出了颐和园我们又走去了不远处的圆明园。今年春天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的时候,网上曾有很多人为圆明园打抱不平,虽然不少言论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也有相当的情感是真挚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巴黎圣母院燃烧之时,我们为什么要重提圆明园?》,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的阶序,并在最后承诺下次回国要来圆明园参观。
只可惜这样宝贵的时刻,也并没有圆满。走进园子里不久,我就接到了我妈的信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美国。
我正觉得蹊跷,她就说,最近身边有奇怪的人在拐弯抹角打听你的行踪,实在太不正常了,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单独行动,尤其是晚上。
我心里一惊,意识到可能是国安还在活动,顿时有点怒火中烧,骚扰到我父母头上算几个意思?
我妈显然比我惊恐一百倍,生怕我即将被秘密绑架了似的,要求我出门随时报平安,还要把身边信得过的朋友的联系方式都告诉她,以防我出了什么事都没人知道。
但她前前后后没有问过一句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在网上发了什么,或是我闯了什么祸之类的,所以我也没告诉她我们之前做活动被国安盯上的事。但我们很有默契,一开始就对事情的性质心照不宣,没发生任何内耗。有一对具备了良好常识的父母真是我的万幸。
“直到你平安到达了纽约,我才会放心。”她最后说。
我怔忪了许久,感到如鲠在喉,浑身冷一阵热一阵,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激荡,让我没法思考其他任何事情。
临走之前,一个素未谋面的读者通过我的朋友交给了我一件礼物,是ta在看过我那篇《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有丧家之犬的感觉》后,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款T恤,正中央是一只黑色大狗的头像,上面是“流放感”三个字,下面印了一行“这个时代的丧家之犬。”
朋友说:“这狗子这么精神,一点都不像丧家之犬。”
它仿佛已成为了我的一种身份,而我也重新定义了它。我最后是穿着这件T恤走的,顺利从首都机场过了关,上了飞机,穿越时空后落地洛杉矶,又顺利入了境。
当躺在洛杉矶郊外一家旅店的床上的时候,我才终于觉得安全了。尽管未来将如何还完全没有轮廓,但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已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状态。
路还很长,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吧。再跑久一点,它或许会变成一只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