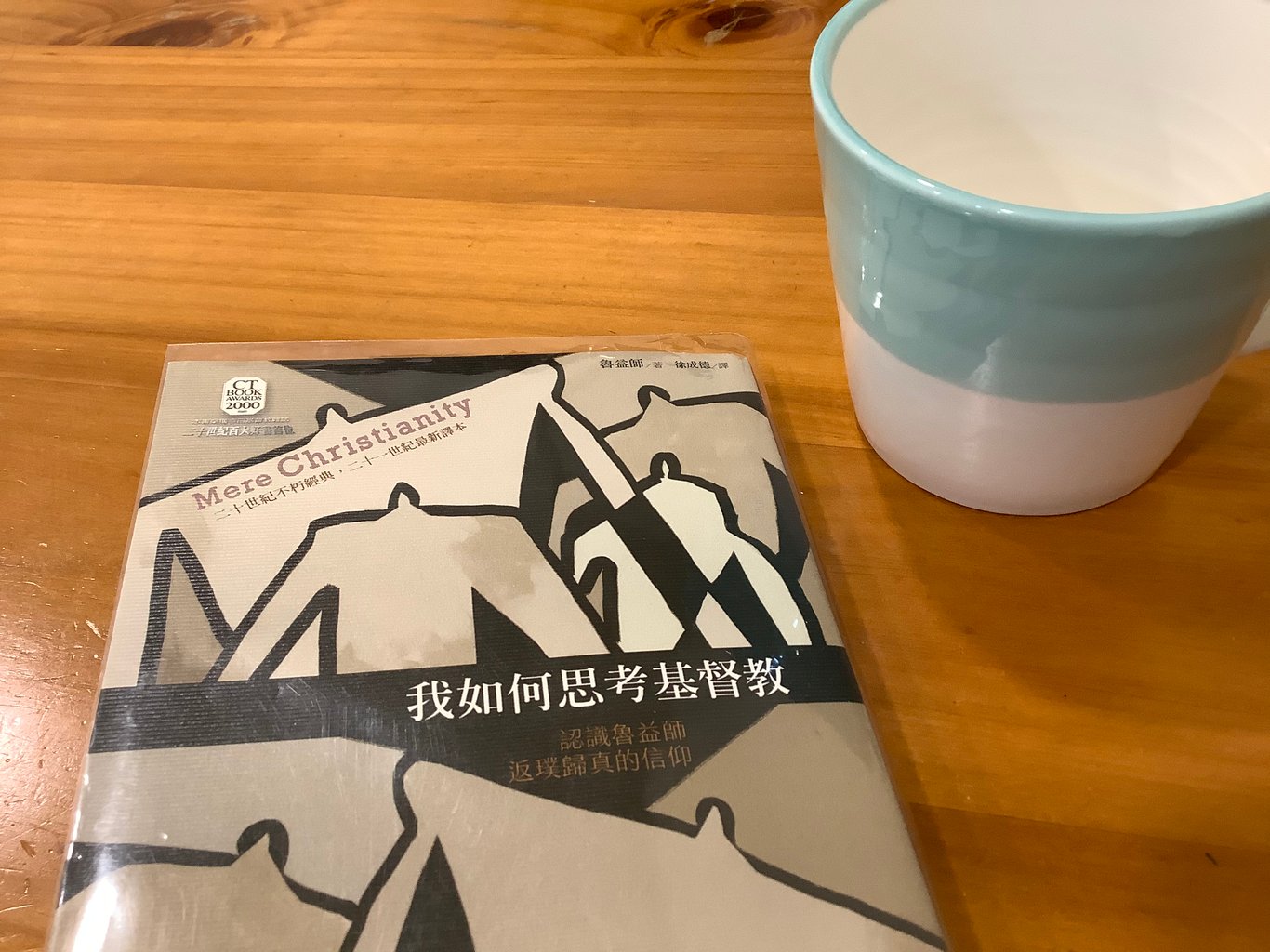一百年前的文學冒險—作品選文卷
「一百年前我們的冒險—文學冒險卷」以小說的方式呈現這些日本時代作者們的人生,在看了這本書以後,準備好了「作品選文卷」來滿足讀者湧現的想要閱讀這些創作者們作品的渴望,這兩本書不能說是先讀哪一本比較好,或許也有人是先認識作品然後再對創作者產生好奇的。大多數時候好像是後者,但不管是什麼順序,你好像不可能喜歡一個作品卻不對作者產生興趣,或對一個作者有好感,卻不想閱讀他的作品的。


我馬上翻到天才少女黃鳳姿的作品「冬至圓仔」、「七娘媽生」,因為想讀這篇傳聞中的名作已經很久了,但讀了有點失望,可能在日文原文裡的韻味較好,但在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佚失掉了。


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描寫少女間的友情,對婚姻的期待與忐忑、與父母想法不同的孤獨感、手足的理解支持,這些都自然地連綴在小說裡。
“但我已下定了決心,從此不再去擔憂左鄰右舍會投來什麼樣異樣眼光而受到拘束,我要明確地決定今後自己的生活方式。”
懷著這樣決心的少女,卻因為某種原因又辭職回到家裡(作家晚年寫的自傳「人生的三稜鏡」裡,對於在工作上發生的事有更清楚的描寫),之後收到同學的喜帖,接連而來的最要好的同學也傳來產子的喜訊⋯這些都是逐漸累積的壓力,一步步將少女推向那個不願意的人生方向。
書裡最關鍵的一幕是「那難忘的一天」。這個場景和小說其他部分和煦的色調不同,尖銳地透著陰暗、憤怒、無奈、苦澀的色彩。
是這一幕,透露出那在優渥環境下,無憂無慮長大的少女的內心,找不到出路的苦悶感。強烈到想要大聲呼喊、甚至將一切都拋擲、毀壞也在所不惜的熱情。
“那是一個颳著強風,風沙吹得叫人睜不開眼的日子。我們三人一起去八里海水浴場玩,也當作是歡送即將要結婚的朱映。”
“「回去吧?」
「不要!」我真是個十足孩子氣的少女,也顧不得朱映會擔心,撇下她,逕自朝相反的方向,疾行遠去。逆風中,我的眼睛、面頰、耳朵,被風沙颳著,刮得我好痛。”
小說並不是停留在陰暗颳風的海邊,而是結束在探訪剛生產的好友的醫院裡,畫面又回復和煦的色調,溫暖而和諧,但是在看過海邊的那一幕之後,你知道這只是表面,為了隱藏底下的波濤洶湧。
讀了花開季節,於是懂了楊雙子為什麼會以楊千鶴的故事為題材寫同志故事。因為裡面滿溢著女性的自我覺醒意識。
作者後來也選擇妥協走入婚姻,但她的婚姻並不幸福,傳統的家庭結構不是能讓一個自由的靈魂呼吸的地方,但為了孩子,她在一個幾乎窒息的環境中忍受了大半輩子,到了晚年才又重新開始寫作。「花開季節」這個結束在溫馨畫面的作品,其實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

翁鬧的「殘雪」
看這篇寫於一百年前出自台灣人之手的日文小說,你會以為自己在看現代的歐洲電影。頹廢、浪漫、物質、空虛、⋯但是在那個時代,就出現了這樣一部穿越時空的作品。
作者翁鬧是那個時代最「毋湯」的那種人,拿了家裡的錢說要去內地讀書,其實課也不上,成天泡在喫茶店和劇院,就是葉石濤在小說裡形容過的,只是去酒家和舞廳「遊學」的富豪子弟。
但翁鬧和那些人又有些不一樣,他是真的浪漫過了頭,可能比沈浸於少女漫畫的少女還要更無可救藥,腦海中除了戀愛情節什麼都沒有。
翁鬧在那個時代肯定像外星人一樣突兀。然後據說只有活到三十歲就死了,死因成謎。或許是又坐上飛行器回到外太空去了。
*****


在「文學冒險卷」中提到的兩位原住民作者,一位在台東耕耘教育,一邊從事音樂創作,平淡卻充實地度過一生,一位則在白色恐怖中喪生,他們的共同點是原住民的身分,和是同樣讀過台南師範學校的前後輩。最大的共同點是他們都身在那個時代,並且懷抱著創作的熱情與渴望,只是命運帶領他們走的是不同的路程。
讀到陸森寶寫的自傳:「我很想參加補習班,以便考上台東公學校,可是如果我去參加補習班的話,那麼誰來照顧我的牛呢?」不禁莞爾,這段短短的描寫,腦海中浮現那個純樸的原鄉,和一個胸懷大志的原住民男孩。
*****

周金波是我最好奇的一位日本時代作家,因為他的身分認同最具爭議。有的人將他的作品歸類為皇民化文學,但如果你真的讀他的作品,你會讀到一個作者真誠剖析坦露出的身分認同的迷失與掙扎。
你看到作者的內在有一個嚮往日本,甚至渴望成為真正的日本人的自己,也有另一個對這樣的自己感到不恥,渴望去愛自己的土地與血緣的自己。而他對於這兩個衝突的聲音完全無可奈何。只能任由這兩股力量在裡面撕裂拉扯,「鄉愁」就是一個這樣在衝突底下血淋淋的故事,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如果是稍微世故虛偽一點的人,就會拿一些謊言來欺騙自己吧,用一些表面的東西來掩蓋那些不想被別人知道的情感吧,但作家卻不具有那種欺偽的心。寄居在日本的時候,他有一個想像中的家鄉,是他的故土,是屬於他的族群,但回到台灣,他感覺到的不是接納,不是歸屬,而是冷漠疏離,在這個時候他又想念那個熟悉的日本文化。不管在哪裡,都充滿鄉愁。
在異文化當中成長的人,應該更能深刻體會這種沒有歸屬之處的異鄉感,不管在哪裡,都找不到自己真正的身分,找不到自己真正歸屬的地方。
讀了作者的這篇作品,更能夠深刻的體會,這不只是一種迷惘的感傷,而是一種會從裡面將人的感性撕裂的對立與衝突。不是台灣人,也不是日本人,如果在根源是空虛的,又怎麼能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呢?
祭典結束了,每個人都有可以回去的地方,自己卻沒有歸處。
“已經回不去了,實在是漫長的黑暗路,迷路啊!
我搖搖擺擺地,但這二隻腳還是像文字上形容的一般像棒子一樣在前後擺動著。”
*****

王詩琅的「十字路」描繪一個日本時代銀行員的生活,生動地紀錄了當時薪水階級的生活樣貌,心酸與小確幸。
榮町是當時銀行與百貨公司聚集的地方,一位銀行員領了年終(賞與金),在回家的途中買了一頂帽子犒賞自己。
這頂帽子買的其實不是犒賞,而是失意與空虛。只有公學校畢業的他,學歷不如人,比不上那些大學畢業的內地人。
職場上的失意讓他悶悶不樂,回到家又面對妻子的質問,心情更加不快,這時傳來入獄好友被釋放出來的消息。
這邊帶出當時許多台灣年輕的知識分子,不是像我們的主角這樣,汲汲營營於自己的生活,而是賭上前程,追求社會改革的理想而奔跑努力。
故事結束在太平町,熱鬧的台灣人街市,這裡有妻子叮囑他絕對不要再靠近的咖啡店(日本時代有女侍陪酒的地方)。
如今要追求什麼夢想都已太遲,只有咖啡店提供的享樂在唾手可及的地方。
“他無意識地手伸到頭上,扭一扭前天買的新帽的邊。不覺地苦笑。“
結果他還是會選擇走進咖啡店裡去的吧,反正“在麻木了的神經,已沒有去探求和鬥爭的精神和勇氣了“。
小說也記錄了像主角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休閒生活,是和朋友到草山(陽明山)泡溫泉。
叫「眾樂園」的公共溫泉,租了一間六領席的別室,換上日式棉袍(浴衣)。“浴室像羅馬王宮,高高的圓天井下,噴水池式的大圓浴槽中央,飛噴出乳白色的泉湯。”這些描述讓我回想起之前到北投參觀的舊公共溫泉遺址。
*****

作家有兩種身分,一個是小說家龍瑛宗,一個是銀行員劉榮宗,這兩個身分就像是兩種人格,絕大數時候,作家都以劉榮宗的身分生活著,這個時候的他就像是王詩琅所描寫的,那個汲汲營營於生計的銀行員,但他有另一個隱藏的身分,另一個思緒、情緒、專注,彷彿是另一個世界,在那裡所有的一切並不是圍繞著數字,而是以文字的方式呈現,一切也都因為被化為文字的形式而有價值。
作家是一個務實的人,和那些一頭將自己的生命栽進文學或藝術的人不同,他以一個安穩的角色生活著,一旦時局形勢不允許,他隨時可以換上另一個臉孔,畢竟,生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創作只是其次。
作家的考量不無道理,如果連生存都無法持續,又要怎麼進行創作呢?他必須先成為一個對生活負責的人,才能成為一個對藝術負責的人。
因此,我不覺得作家為了生計,人生大半輩子的時間放棄寫作是不值得的,因為作家即使沒有在寫作的時候,也仍然是一個創作者,創作是他的身分,而不只是他所做的事而已。
銀行員的身分只是一個偽裝,真正的他是寫作的人。
龍瑛宗在戰後曾短暫在台南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的編輯,這段時間他的生活應 與葉石濤有交集。因為這個時候葉石濤的作品也常投稿在中華日報上。在小說「紅鞋子」裡,描寫了主角到火車站前報社領取稿費,然後匆匆忙忙到米街去糴米的情節。
「不為人知的幸福」(知られざる幸福),是一部溫暖深刻的作品,描寫貧病夫妻他人無法得知的幸福。幸福不是外在的處境,而是「能夠感受幸福的心境」吧。被虐待逃離夫家的童養媳,和照顧母親貧窮的中年男子結為夫妻,最後丈夫終於因為身體孱弱而病死了,不管什麼人都會認為這樣的人生極其不幸,但是女子卻深深感到被丈夫所愛的幸福,而她也深知丈夫是幸福的,所有經歷的一切或是悲傷或是快樂,都是寶貴美好的生命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