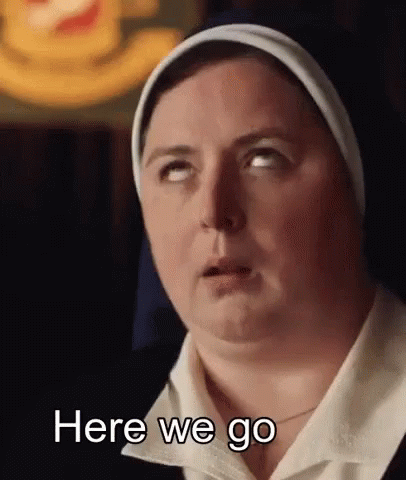一种生活
1.
江山娇是个幸运儿。她是个红N代,有北京户口。我猜她家里一定很有钱。有钱还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一定的道理,经济基础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江山娇也许也要上班,但是她有钱到可以给老板甩脸色,她家里的背景也让人敬三分,职场歧视什么的用钱摆平就好了。也许江山娇也要生小孩,但是她富裕的家庭可以承担私立医院高昂的护理费用,减少许多不便和痛苦。生了小孩之后,她应该可以请个菲佣啥的。甚至这一切都不用她自己办,找个代孕就行了。
江山娇哪会知道我们这些普通女孩的烦恼呢?我想,她应该也可以开着大奔进故宫吧。但可能她也有自己的一点点委屈和不甘。红旗漫是她弟,据说是因为她是个女孩,所以她家才生了二胎。可能她是很有钱,但能继承的家产还是没有她弟多。
江山娇也有点可怜,她只是一个虚拟人物,公权力借助二次元驭民的工具。这次本就愚不可及的宣传翻车了。女孩们混杂着不被当公民对待的愤怒情绪,加之连日目睹强制剃光头、怀胎上前线、流产抗疫之类同样弱智的宣传手段,向江山娇发起了海潮般的诘问。
但其实她们真的是在问江山娇吗?没有人会那么蠢,想着问一个二次元形象要答案。如弦子所说,这是女性对时代发出的檄文。
我之前在很多篇推文里提过,我研究当代中国女性作者如何书写女性的疼痛,而且是非病理性的疼痛,例如痛经、青春期乳房的胀痛、生产的疼痛、更年期的身体疼痛。这样连成一串,才会发现疼痛早已成为了女性的日常,而这种日常被宏大叙事与宣传机器征用,成为“伟大牺牲”与公权力为自己正名的注脚。这项研究让我总是很愤怒,而更愤怒的是看到我所研究的作为表征的疼痛,在现实世界也幻灭成了一个符号。
看到女医护的头发被粗暴的削下时,我想到Fleabag里的一句台词,"Hair is everything." 发型就是一切。
我还想到Kristtin Scott Thomas 那段穿透灵魂的,有关疼痛的独白,我简单翻译了一下:
“Women are born with pain built in. It’s our physical destiny: period pains, sore boobs, childbirth, you know. We carry it within ourselves throughout our lives, men don’t.
女性生来就有内置的疼痛。这是我们的身体宿命:痛经、涨奶、生产。我们一生都背负着疼痛,但男人不是。
“They have to seek it out, they invent all these gods and demons and things just so they can feel guilty about things, which is something we do very well on our own. And then they create wars so they can feel things and touch each other and when there aren’t any wars they can play rugby.
他们只能自己去寻找痛楚,所以他们发明了神和恶魔之类的乱七八糟,好让自己能有痛感,但在这件事上我们女人自力更生且更胜一筹。 然后他们发明了战争,好让彼此相互攻击并吃痛。没有战争的时候,他们就玩橄榄球。
“We have it all going on in here inside, we have pain on a cycle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then just when you feel you are making peace with it all, what happens? The menopause comes, the f***ing menopause comes, and it is the most wonderful f***ing thing in the world.
我们的痛都在这里,在里面,年复一年地循环,直到你发现自己终于可以与疼痛和平共处。然后呢?绝经期来了。操蛋的绝经期。这是世界上最他妈美妙的事情。
“And yes, your entire pelvic floor crumbles and you get f***ing hot and no one cares, but then you’re free, no longer a slave, no longer a machine with parts. You’re just a person.”
对,虽然你的骨盆会整个塌下来,你会燥热难忍,也没有人在乎你。但你自由了,你不再是奴隶,不再是拖着子宫的生育机器。你只是一个人。
我不想再阐释或解构什么了。我只想说些日常,我的日常,某种女性生活。
2.
大概三年前吧,在伦敦面试一份兼职工作。所有的面试者都要先在大堂等候,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来收我们的简历,到时间后带我们进面试间。收简历的工作人员是个华人中年男性,身材瘦小,戴眼镜。拿到我的简历后他瞟了一眼,“你接下来要读博士哦?念什么专业啊?”“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这个专业不好找工作哦。你具体研究什么方向?”
——“当代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啊。那你是个女权主义者咯?”
——“我是啊。那您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呢?”
“我是个男的,我当然不是女权主义者。”
——“我认为任何相信性别平等的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呵,你现在读博士,找对象怎么办?你不想找对象啦?”
——“这是我的私事。”
“你年纪也不小了,还在读书也不出来工作,出来做点兼职是应该的。”
——“我们家有钱。我爸爸妈妈都很宠我。”
面试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也进入了面试间,跟一排面试官坐在一起。做完测试后,对方问我有没有问题要问他们,我说:“刚才这位先生问了我很多私人事务,而且对我的研究随意评判,我受到了冒犯。我接下来要做的是女性文学研究,我想问在座的各位男士,你们是女权主义者吗?”
大概我的问题问得出乎意料,女面试官全都诡秘地一笑,男面试官则面面相觑。当然,我并不在乎他们实际上怎么回答。因为从他们躲闪的眼神和犹豫的神色里,我已经得到了答案。
后来我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但我并不意外。我拖着刚发完烧的身体去面试,整个人都不在状态,表现一般。我也不知道我问的那个问题是不是成了他们的扣分项。who cares,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出那句话。但我还是很委屈。回家的路上,我买了杯咖啡,站在站台上,还是忍不住哭了,把眼泪和咖啡一起喝进肚子里。
和我一起等面试的有我当时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我很感谢她,虽然中间没有交流,但她不时给我递过来鼓励的眼神,让我死死憋住的愤怒的眼泪没有流下来。事后她给我发短信安慰我,“我觉得你说得很棒。”
事后跟一个好朋友聊起,她惊讶于我的硬气,说如果是她应该不会这么做。我在当下的确是觉得那个朋友太过软弱,她似乎并没有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只是震惊于我行动的攻击性。但过后又觉得,不应太过苛责。这不过是一个女性的一生中,反复出现却又微小得不能更微小的插曲,不能期望所有人都能在被冒犯时开足马力回击,甚至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是一种冒犯。我可以轻松地说自己不需要那份工作,但还有其他女性,她们不能说不,因为要活下来,即便忍气吞声也要活下来。但这些一点一滴的微小,积少成多,若不是负隅顽抗,便会在某一天将你拖垮,拖回那个狭窄、逼仄、温柔哄骗你的壳。它用柔软的牙齿,一刀一刀地凌迟你。
3.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怎么定义这种幸运呢?或许是出身在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儿那种幸运。是不愁温饱,被悉心呵护的幸运。我父母没有在物质上溺爱过我,但我提出的要求,他们从来都毫不犹豫地满足。爱看小说,说要去买书,爸妈每次给钱都给得很爽快。偶尔也馋淑女屋的连衣裙,十几年前的价格,一千多块一条,真的不便宜,但我妈还是给我买了。但是吃零食管得很严,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超级想吃麦当劳,跟我妈吵嚷了半天,结果我妈给我买了杯甜牛奶。
不用当扶弟魔,大家都很宠我。我做什么爸妈都很支持我,给我最大的自由。没有什么需要我操心的事情,我可以很专注地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么想来,我还挺任性的。
但偶尔就是会很想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像是一种委屈被写入自己的基因里。我有时候一边哭一边骂自己娇气,你有什么好哭的?!你都这么幸运了,你特么哭什么哭?!有一股力量在撕扯我,一面是对一些微小时刻的抗拒与挣扎,一面又不断地在问,我是不是要得太多了?后来跟一些女生朋友聊起,才发现这种躲躲藏藏的眼泪,是很多人共有却秘而不宣的习惯。
在一些人眼里,我还算优秀。但他们对这种优秀的咂摸,总是复杂的。眼看着我的学历越来越高,开始有人像那位工作人员一样,对我的婚恋状况评头论足,并将高学历与年龄看作是女人贬值的象征。我一边念书,一边做着好几份兼职。钱没有赚很多,但足够生活。总有些人颇为同情地看着我的忙碌,把它解读为反叛者的失意。“这么辛苦有什么用?找个好男人嫁了就不用这么累啊。”女人的优秀和忙碌在某些人眼里,就意味着干瘪和不幸,意味着得不到男人的垂青。
同一个大院里的男邻居,曾猥琐地笑着跟我说,还在读书?书读太多了人会变傻。有爸妈的朋友闲聊时对我谆谆教诲,“女人啊不要太逞能。男人的事情就让男人去做。”可是如果我并没有在逞能,我就是这么能呢?家里的女性长辈无意中跟表弟说起,一般女孩子上了高中成绩就会变差的,你姐姐是个个例。有一次表妹在夏天穿了一条短裤,被男性长辈责骂,说穿着那么短的裤子在小区里晃,不怕被人非礼吗?出来工作的时候,会有男客户开不合时宜的玩笑,可我却无法再拿出那次面试时的勇气,只能冷漠地背过身去。饭桌上的中年男子说,男的天生就是好色啊,就是管不住自己,所以女人要自爱。12岁的时候,男性长辈对我说男人在外面彩旗飘飘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约会的时候,对面的男生肆无忌惮地评判我的外貌,在我拒绝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恼羞成怒。每当走夜路,我总是会下意识地害怕,汗毛根根树立,因为大家都说女生晚上就不该一个人出门。初中的时候,班上有顽劣的男生碰我的臀部,我愤怒地咆哮回去,却只换得一阵嬉笑。有人告诉我,身为女人,我只能忍。
可我忍不了。
这些都是我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是很多女孩的日常。类似的场景太多,我都无法一一列举。有些记忆有些年头了,我也不知道那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我为什么会一直记住。或许是一种叛逆的直觉,不时跳出来,要我为这些经历寻求一个合理的定义。一字字,一句句,一声声,叠起来,成了对所有女孩的软埋。一天天,一年年,织得紧紧的大网将你兜住,静若无声地消磨你的斗志,否定你的才华,蔑视你的自我。成为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遮掩一月一次的痛经,忍耐生产与养育的疼痛和劳累。也许看到这里的你,依然会对我的诉说不以为意,认为那些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玩笑。可是很多女孩的理想和翅膀,就是在一次次的无关紧要当中被慢慢折断。然后人们得出一个结论,你看,女的就是不行。
4.
其实一开始,我妈对我在英国读博这件事情也不是百分之百支持。我们为此起过几次争执。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也许她并不抗拒我追寻自己的理想,但她知道主流价值观对叛逆者的不友好。她希望我早点回家,安定下来,博士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妈妈想给你买房子,你稳定下来,像那个XX姐姐一样,可以一边在大学当老师,一边读博士。”“妈,那都是好多年前的形势了。现在的本科院校根本就不会招一个硕士生去当老师,下一步很可能就只招海归博士了。房子我以后自己买,但现在我得读书。”
我妈不是固执的人,看我坚持,她没有再阻拦。但如果没有那几次态度坚硬的争执,也许我也早早地回家,结婚生子。而现在,大学的确慢慢只招海归博士了。我并不讨厌早早稳定、成为妻子和母亲,只是这不是我想走的路。这也不应该是女孩们唯一能走的路。我选择了忠于自己的理想、留在我喜爱的城市,也选择了漂泊、在外的孤独与压力。人们总是假定女人无法独立,无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
我看着我妈,她简直是一个毫无瑕疵的模范,是家庭事业双丰收的范本。可是我知道她付出了多少,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付出这么多。我知道她有自己的痛苦,都被她的心性消化掉了,而我没有那么宽容。我总觉得她是用超出常人的善良和智慧换来了这一切,这意味着用柔软回应那些曾经印拓下的伤害。可是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始终没有办法像我妈这么这么完美。我妈总是很勇敢地作出选择,尽管有些选择我不一定认同。每个女儿都会觉得,质疑自己母亲的选择是一件残忍的事,但是每个女儿都曾暗自希望,如果自己也身处同样的困境,可以有别的路走,一条跟自己的母亲不一样的路。我妈说,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我会有个弟弟。我想,为什么是弟弟呢?万一是妹妹呢?
我妈就像《小妇人》里的马奇夫人,柔韧,消解一切愤怒。我以我妈为榜样,可是始终无法成为她。我还是太尖锐了,有些委屈我受不得,我一定要叫出来,呐喊出来,我有排山倒海的报复心理,想让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可能每个看《小妇人》的女孩都会自动代入Jo,我们执拗地选择,因为选择的孤独而失落,但努力不去后悔。
我跟我妈聊过这些问题。她说,有些事儿,不要想得太明白,不要看得太透,会比较好过一点。可我没有这种圆润与混沌。我想到红药丸和蓝药丸,你要吃下哪颗?你选择继续做梦,还是迈出重建自我的第一步,但承受推翻此前自己的痛苦?
我每时每刻都在质疑与推翻自己,但我并没有服下红药丸。我不需要红药丸,我只是被本能牵引着,大脑自然而然地让我记住一些瞬间。我可能是痛苦的,但我自由了。一个想要自由的女孩,要接受永远抗争下去的宿命。
5.
柴静在《看见》里,写过她去女子监狱采访的经历。她所见到的女子重型犯,无一例外,都是家暴受害者。她们在最为绝望的时刻,举起了手中仅有的武器。
跟她们相比,我的挣扎实在是微不足道。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值得写,因为里面的所谓痛苦和愤怒,似乎都太轻了,起码没有让我活不下去。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要跟那些垃圾计较”就可以完事儿的。
但这几天,我才意识到不是这样。无关痛痒的压迫也是压迫,而且映照出一种更为可怕的现实:原子化的性别规训与监控无处不在,平日里悄声无息,被人忽视。但正是这些被人忽视的日常,让我们本身都成了父权压迫的帮凶,让某个角落的人罹难。而女权也不只是与女性有关,这门学问,是对所有个体权益的关切。
我们的生活里不应有那么多理所当然。
We can't live like it's just another day. And I won't.
(首发在公众号上,但看到腾讯大家也炸了,觉得即便我这种无名小号也岌岌可危。以后会在这里写,也会把旧文搬运过来。只是想要一个不需要自我审查也能畅快地写的地方。)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