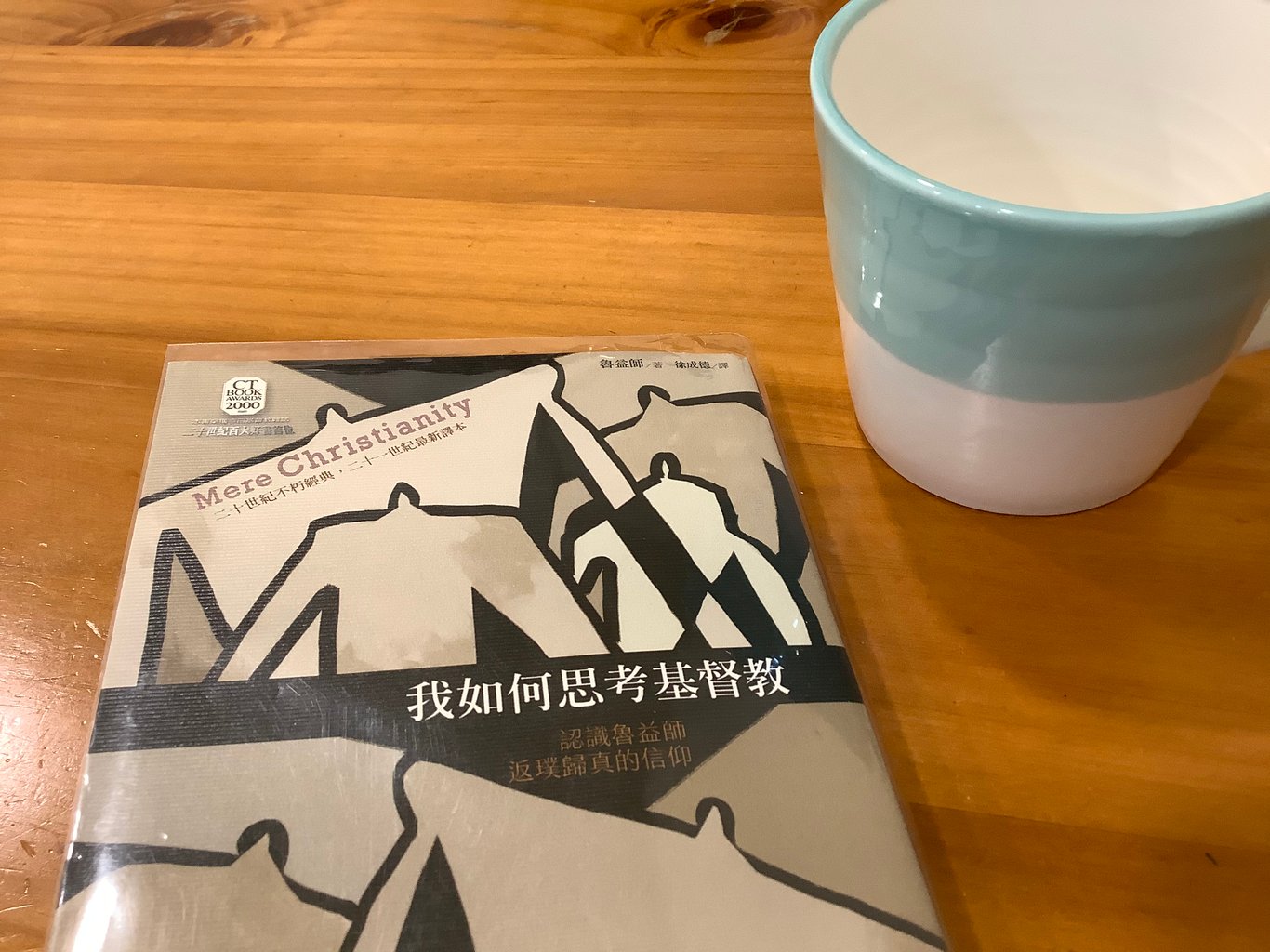自由與疏離的[在車上](DRIVE MY CAR)--村上春樹與契可夫都無法回答的問題
在車上(Drive My Car)這部電影長達三個小時,但是它的觀影經驗卻是讓人感覺沒有負擔的,或許是因為它具有日本文學作品中常常所追求的[透明感],在日本的文學中有時候會用[具有透明感]來描述一個作品,我覺得它所描述的是一種[沒有負擔的感覺],以食物來說就像是清爽的食物,不油膩厚重的,容易入口消化的。在車上的主題觸及背叛、死亡、甚至人生存的意義,這些沉重的主題,但是影片卻具有透明感,不讓這些厚重的主題令人感到難以消化。
電影以主角家福的妻子音的死為分界點,區分為兩個部分。在音死前,家福過著表面上幸福的生活,家福是舞台劇的演員,妻子是編劇,妻子在床上講述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像天方夜譚中的女子,以此來延長自己的死期。兩個人在女兒死後就活在這些虛構的故事裡,好像活著,但是卻又令人感覺不真實。因為他們都未曾面對自己內心對於失去孩子的悲痛,更無法相互觸及對方的。身體的結合更顯出孤獨的絕望處境,當中的空白只能用一個又一個的虛構/謊言填補。
家福在妻子生前就發現她對自己不忠,但是他卻什麼都沒有說,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妻子打算與他深談的那天晚上,卻忽然腦溢血過世,兩個人因為死亡而永遠隔離,再也沒有觸及對方的機會。在村上春樹的原著小說裡,主角家福甚至想辦法與妻子的外遇對象成為好友,為的是了解生前的妻子,因為再也無法與她對話。
電影除了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和雪哈拉莎德(天方夜譚裡不斷說故事的女人),使用的另一個文本是俄國劇作家契科夫的四幕劇作[凡尼亞舅舅]。契科夫是一個悲觀的創作者,他的作品裡常常洋溢著絕望、幻滅的色彩。[凡尼亞舅舅]也是如此,凡尼亞一直為教授工作,因為他相信教授是一個有遠大抱負、才華洋溢,而且了不起的人物,他貢獻自己的一生為教授工作,直到年華老去,白髮蒼蒼。但是當教授出現在莊園裡,他才發現原來教授是一個自私、愚蠢、膚淺的傢伙,他憤而想殺死教授卻沒有成功,他想選擇自殺,後來被外甥女索妮雅制止。
索妮雅在[凡尼亞舅舅]當中是一個特別的角色,她不像別人為著一己的私慾而活,單純善良,面對悲慘的處境,她安慰舅舅說:
[我們要繼續活下去,凡尼亞舅舅,我們來日還有很長、很長一串單調的晝夜;我們要耐心地忍受行將到來的種種考驗。我們要為別人一直工作到我們的老年,等到我們的歲月一旦終了,我們要毫無怨言地死去,我們要在另一個世界裏說,我們受過一輩子的苦,我們流過一輩子的淚,我們一輩子過的都是漫長的辛酸歲月,那麼,上帝自然會可憐我們的,而到了那個時候,我的舅舅,我的親愛的舅舅啊,我們就會看見光輝燦爛的、滿是愉快和美麗的生活了,我們就會幸福了,我們就會帶着一副感動的笑容,來回憶今天的這些不幸了,我們也就會終於嘗到休息的滋味了。我這樣相信,我的舅舅啊,我虔誠地、熱情地這樣相信啊。……我們終於會休息下來的!
我們會休息下來的!我們會聽得見天使的聲音,會看得見整個灑滿了金剛石的天堂,所有人類的惡心腸和所有我們所遭受的苦痛,都將讓位於瀰漫着整個世界的一種偉大的慈愛,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會是安寧的、幸福的,像撫愛那麼溫柔的。我這樣相信,我這樣相信。……可憐的、可憐的凡尼亞舅舅啊。你哭了……你一生都沒有享受過幸福,但是,等待着吧,凡尼亞舅舅,等待着吧……我們會享受到休息的。……啊,休息啊!」

這一段舞台劇中的台詞,原封不動地在電影中呈現,似乎同樣被當作電影中故事線的一個救贖性的終點。再也無法與妻子對話的丈夫,失去與母親和解機會的孤女,彼此之間因為相同的處境,而彼此共鳴、彼此了解。在這個奇蹟般的連結之中,湧現對未來新的盼望,還是可以繼續往前走,就像是坐上車之後,還是有可以前往的彼方。
索妮雅這段台詞的內容,充滿宗教性的氛圍,家福的妻子音,[家福音]這個名字也充滿宗教氛圍。村上春樹的小說和契科夫的[凡尼亞舅舅],包括電影[在車上]的濱口龍介,似乎都在作品中尋找救贖之路。
車內是一個奇妙的空間,在[Drive My Car]這個名字裡,當家福允許女孩開她的車子,隱喻了他允許了女孩進入他內在的自我,兩個人共享彼此某一部份的意識,是透過[在車上]這個獨特的空間才得以達成的。
電影裡兩個人從廣島開到北海道,整整兩天的行程,並不是為了到哪個目的地,而是在車上的這段時間,家福得以安靜地面對內在的自我,與自己和解。原來對他來說,重點不是再也無法對話的妻子,而是與自己重新的連結。家福饒恕了自己,找到往前走的力量。
悲觀的契可夫是懷著什麼心境,而寫下索妮雅這段充滿盼望的台詞呢?他似乎是在說著,只要活下去我們就需要在前方的盼望,否則一步都無法前進。因此有盼望總比沒有盼望要來的好。索妮雅的信念安慰了對自己人生幻滅的凡尼亞舅舅,在將來有慈愛、安息在等待他們,所有辛勤的工作都會得到報償。導演濱口龍介用一個無法說話的演員來詮釋索妮雅這個角色,她用手語比出這段充滿盼望的台詞,比用話語說出更充滿力量。這似乎也表現著,那些真正動人心弦的信息,往往不是被說出來的,而是無法言說的。
回到村上春樹的原著小說[Drive My Car],電影以小說中的人物為主要的骨幹,然後又融入了另一篇同樣是村上的短篇[雪哈拉莎德]。[雪哈拉莎德]是另一個奇妙而難以理解的故事 : 故事中的人物以女人在性交後說出的一個又一個虛構的情節彼此連結。身體真實的交合,與虛構情節的交流,似乎反而是後者,在男人與女人之間膠合起堅固不可摧毀的連結。電影將這樣的關係,放在家福和妻子音的身上,音是編劇家,是那個不斷說故事的女人。村上的小說總是以個人的自由與疏離的關係為主題,在心理學家河合俊雄分析村上著作的[當村上春樹遇見榮格]這本書中,以[疏離和現代意識]分析他的作品,發現大多數村上春樹的小說,登場的人物都是孤獨一人,尋羊冒險記中,主角是這樣說的:[我總是一個人孤零零的。……簡直就像生下來時,就一個人了,一直也都是一個人孤零零的,而且覺得以後也還是會一個人繼續下去。]這樣的生存狀態,是不需要為了解放或自立而戰鬥的世界,然而這是否就是人所追求的,所謂的[自由]?當人從被束縛的狀態被解放,是否就能達到自由的理想 ? 作家楊照分析村上的作品,說村上的作品總是有三個核心元素:
一、人與自由的關係。
二、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三、雙重、乃至多重世界的並置、拼貼。
人為了生存和對連結的需求,而不得不與周圍的世界產生某種連結,但這種結果是不得不失去自身的自主性。村上的作品似乎在這兩者當中,尋找另一種生存狀態,另一種可能性。
家福自認為與妻子的關係是滿足的,無論是在身體或是在心靈上,所以他無法理解妻子為什麼會需要其他的男人。這個謎隨著妻子離世而沉入海底,永遠失去被解開的機會。令家福最無法釋懷的,或許是他開始懷疑與妻子所擁有的連結/關係,是否真實存在,抑或是只存在自己的幻想中。
“不過最後,我還是失去她。從她還活著時就一點一點地持續失去,最後完全失去。就像因為侵蝕而持續失去的東西,最後被大浪連根拔起地捲走那樣……
對我來說最難過的事情是,我對她----至少可能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其實並不了解。而且在她已經死去的現在,那可能永遠也不被了解就結束了。就像沉入深海底下的小而堅固的保險箱那樣。一想到這件事,我的心就一陣絞痛。”
對人而言最原始而無法否認的連結,應該是在子宮中與母親的連結。家福的妻子在失去孩子,那個曾經和自己血肉相連的生命之後,就開始一個又一個的外遇。在這些關係裡,她索求的是什麼呢 ? 家福和女駕駛在車子的狹小的空間裡,也產生了某種奇妙的連帶感,就好像這個車子是一個子宮的隱喻,將他們用看不見的臍帶連結起來。家福失去的孩子如果還活著,剛好是女駕駛的年紀。

[Drive My Car]電影裡,家福和女駕駛似乎都因為彼此而找到了救贖,他們不再漂流,而屬於了什麼。但他們究竟屬於什麼,在電影裡並沒有很明確地表達。那個漂泊的終點,究竟在那裡可以找到,在電影裡是曖昧不清的。如同凡尼亞安慰舅舅的那段話,充溢著絕望色彩的盼望。在無意義中,我們都需要安慰,需要意義寄託之所在,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只知道自己不要什麼,卻說不清自己要的是什麼。
契可夫的作品,描繪了人類脫離[宗教的壓制]之後,尋求救贖的渴望。 失去[神],人用各式各樣的事物來取代所留下的空缺,卻始終無法得到真正的滿足。人與人的連結無法取代神,人對事物的迷戀或成癮也無法取代神,各種意義的追求,在失去了神這個意義的最後賦予者之後,也同樣失去一切的立足點。心靈的空虛用什麼也無法填補,這個自由似乎和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坐上車之後,我們彷彿什麼地方都能去,但是我們究竟要去哪裡呢 ? 到達那裡以後,是否又有可以歸去的地方 ? [在車上]這部電影的意象無可避免的具有宗教色彩。因為它所問的問題,除去神這個要素,無法回答。
看完了電影,在我們自己所開的這台車上,在人生這個旅程裡,終究需要決定自己所要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