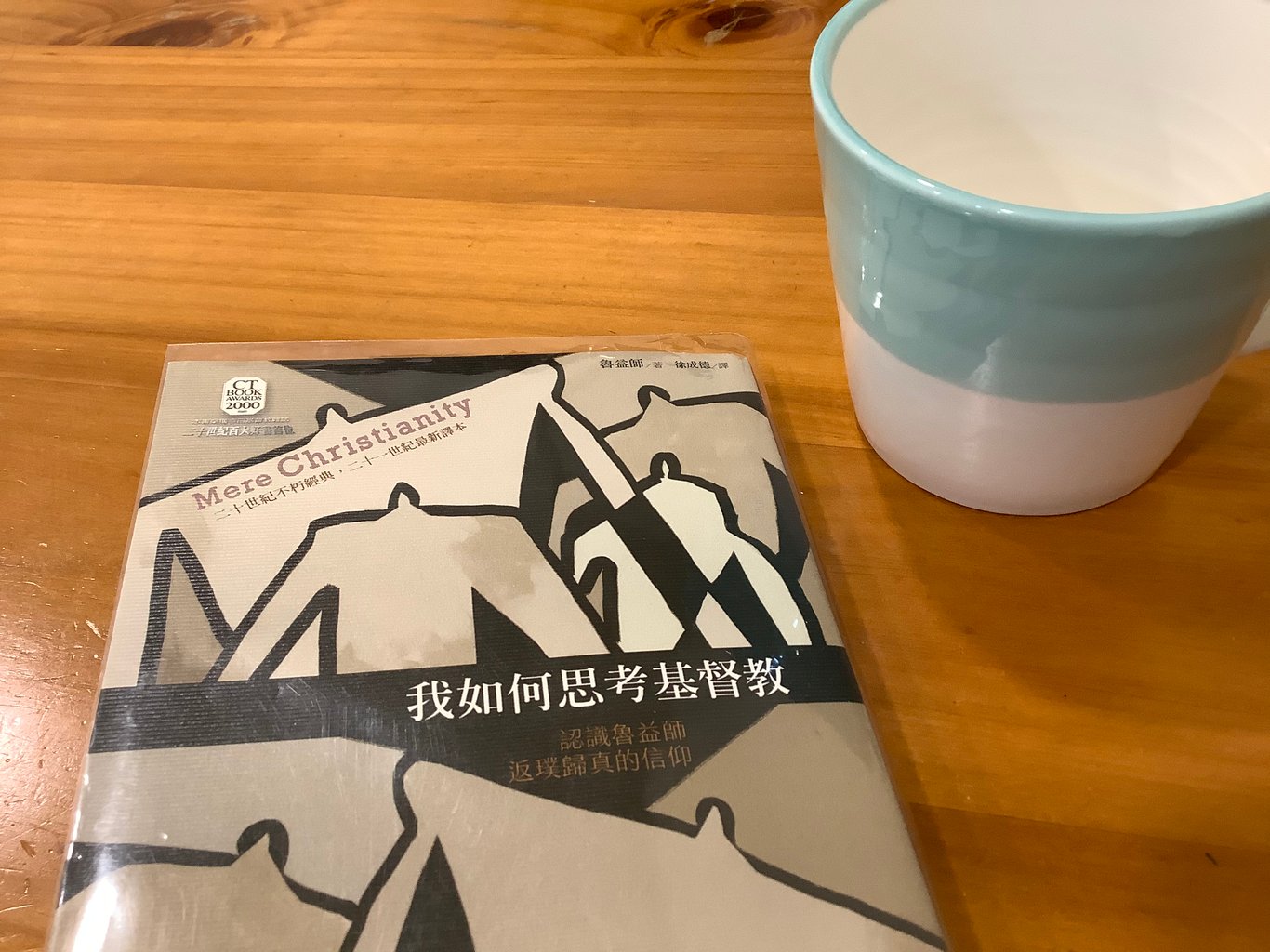未竟的夢想,無法付出的愛
我們裡面是不是都有一個需求,想知道「什麼是真實發生過的」?從我們有意識的從世界接收訊息以來,「分辨真實與虛假」就是一個基本課題。繪本裡會說話愛吃蜂蜜的熊是假的,即使它曾經對我們來說比任何事物都真實。夢境是假的,但是醒來的這個自我有時也感到有些虛假。別人眼中的我未必真實,而我所認識的自己似乎更為模糊。
假新聞的威力是因為其中有幾分真實,甚至是我們更想要相信的。然後我們發現自己上當了,被自己想要相信的事物所欺騙。
在歷史小說「魁儡花」裡,蝶妹是一個虛構的角色,她被創造出來放在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當中,讀了這個故事你企圖分辨那些人物是真實的,哪些事件真實發生過,但這件事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在歷史事件中嵌入虛構的人物或情節,或是在一個虛構的故事中,嵌入真實的人物或事件;像伊格言的小說「零度分離」裡提到「地平線航空Q400劫機事件」,及母鯨J35的故事(兩者都是真實的)。於是我忽然明白了,真實與虛幻之所以如此難區分,是因為真實具有比虛構更荒謬奇異的性質。你以為你需要創造有別於真實的什麼以創造詩意,卻發現虛構的事物遠遠及不上真實本身神祕迷人的故事性。
地平線航空Q400劫機事件發生在2018年,一名沒有受過正式飛航訓練的地勤人員偷偷開走了飛機,在用完油料之後墜毀身亡。起飛時他就沒有想要降落,他說自己的[零件]壞了,並且想去看看那隻因為失去孩子而揹著幼鯨屍體迴游一千六百多公里的母鯨。或許是共感了他在這隻母鯨身上想像出來的孤獨。
駕駛一架飛機,起飛,然後消失天際,是一種對死亡浪漫詩意的表現,像小王子的作者聖修伯里,或是電影「飛行的鋼琴少年」裡,最後熱愛飛行的爺爺的死亡的暗喻。我們真正希望的是脫離地心引力的自由,但又悲傷地感到,那使我們覺得自己像斷了線的風箏那樣孤獨、那樣無助。當死亡發生時,我們手上是否有操縱桿,可去控制自己的方向;是否有足夠的油料,可以去到我們要去的地方。
小說「零度分離」的文字不像封面讀起來那樣冷冽,至少對我來說是溫暖的、令人感覺安慰的存在。
背負著幼鯨,孤獨地在大海裡迴游的母鯨,令人想像的是那些親密、深刻、卻失去了的連結。
動物是否具有我們想像的心智、情緒、感受,懂得哀悼所失去的?能夠愛,就和人一樣?如果想到人與人之間對於事物感受的差異性,和彼此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我們和動物之間的距離也不過是另外一種距離。重點是連結,"神秘的、心靈相通的幻覺時刻",也就是作者所說的「零度分離」。"在那一瞬間,我們既是單一個體又絕非單一個體"。做為一個個體,我們深知與他者的歧異性,共同的是我們都渴望彼此交會的那一刻----幾乎是奇蹟般的連結。
連結是存在的。最好的表達,是我無法說自己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大概永遠也無法理解,但無論如何,讓我們相信有某種跨越了理解的連結存在,也許光是這一點便能帶來救贖。
在我心裡渴望擁有的連結,似乎總是不知為何在什麼地方斷掉了。我的不擅於表達情感的爸爸,總是以一種自我犧牲的態度辛苦的在表達他的愛。他有時無謂的使自己受苦,為使我們更幸福。我也是笨拙的,不知如何向他表達,我收到了那樣的愛。
我在想我一定也做過同樣的事,在我的孩子需要我的時候,殘忍的轉身離開。傷害不斷的在發生,失望不斷的在發生,即使是這樣,仍然堅持地愛著。有時我注視著青春期的孩子眼底殘存的對母親的戀慕之情,心裡猜測它們什麼時候會被破壞殆盡,或者他只能在會壞自己和毀壞我們之間的連結之中選擇一樣,如果是如此,我寧願他選擇毀壞我們之間的連結,就像那個不得不被切斷的臍帶一樣。
渴望連結,渴望分離。也許有一天我會學會,如何讓自己的愛不會造成傷害,也許我會學會,在愛的過程中不感到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