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是否叫我們做香港人,我們都是香港的一份子」 與Yuli Riswati的訪談。

轉自:流傘
譯按:本文原刊於《鬧清楚》;流傘獲授權自行發布。印尼文譯本見此。詳情請聯絡流傘義務翻譯團隊。
譯者:VL
2020年3月1日,印尼移民家務工(下稱移工),作家兼記者Yuli Riswati與Ralf Ruckus及Alina Kornfeldt談及了移工在香港反建制抗爭中的有形和無形參與。 儘管他們的工作維持了是次運動的勢頭以及整個香港的日常運作,他們自身對民主的要求卻不斷被忽略了。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聘請移工可能是身份的象徵。但在香港,聘請移工通常是必需的,並不是奢侈表現。 現在,香港八分之一的家庭(或三分之一有孩子的家庭)普遍僱用一名移民家務工來照顧小孩、老人和日常家務。香港是世界上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大多數家庭亦需要依靠雙倍收入來支付生活費用。眾所周知,香港的工時很長,社會亦缺乏普羅大眾負擔得起的託兒及老人服務。因此,對於基層家庭而言,聘請移工反而通常是最經濟的滿足照顧需求的方式。 這些移工確保了他們的僱主可以穿著乾淨的衣服去上班、保持家庭環境的安全和清潔,以及協助照顧他們年幼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 換句話說,他們的貢獻令香港不斷向前。
然而,香港的移民法和勞工政策卻與這些移工在社會上的關鍵作用並不相符。在政府七十年代制定的簽證計劃下,至今仍容許對移工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剝削。 他們的月薪不但低於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政府還規定了移工必須與僱主同住。雖然有規定他們每週可休息一天,但除此之外,他們的工作時間完全不受限制。另外,他們的簽證取決於與僱主的合約:如果移工或僱主終止其合約,該移工必須在兩週內找到新僱主,否則將面臨被驅逐出境。
在香港,來自印尼的群體是在移工中第二大的,一共有15萬名工人。他們組織起來,舉行示威和抗議活動,並向香港和印尼政府提出訴求。 但是,印尼政府並不鼓勵這些移工參與政治。 事實上,印尼一直依賴在國外工人寄回國的匯款,而這些資金只僅次於原油和天然氣出口的第二大外國收入來源。
2019年6月,引渡條例草案(送中法)引發了一連串的抗議活動,而這些抗爭亦受到香港社會上大部份人的支持。Yuli Riswati觀察並報導了在2019年6月至10月其間的示威活動。自2017年以來,她一直在社交媒體上為其他移工同伴提供諮詢服務。 在2019年3月,她設立了一個非牟利新聞網站Migran Pos,為香港的印尼社群發布重要資訊及新聞。 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時,印尼移工們大多依靠Migran Pos作可靠信息來源。
2019年12月上旬,Yuli被香港入境處驅逐出境。由於被指控逾期居留,她於9月時在家中被捕,並在11月時被拘留了28天。在拘留期間,她受到很多侮辱和不人道的待遇。 在她被驅逐出境後,有關團體在香港組織了集會,並指出了香港羈留所中被拘留人士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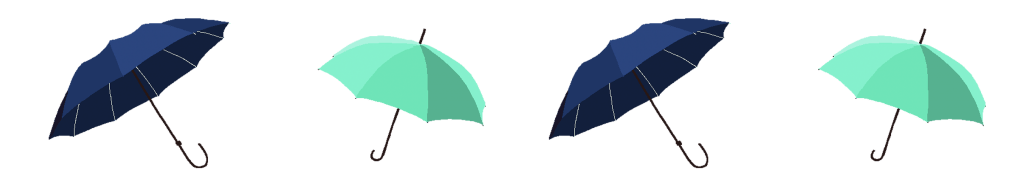
無形的支持
Ralf Ruckus/Alina Kornfeldt:移工們是如何參與反送中運動的?
Yuli Riswati:對民主有一定了解的移工大多都支持抗議活動,但他們沒有公開參加,因為對他們來說風險太大。他們擔心參加示威會導致歧視,被逐出境或被禁止在香港工作。 大多數的移工對政治沒有太深入的了解,也不太了解香港正在發生什麽事。
我曾經跟為這場運動作出貢獻的移工交談。他們致力協助維持僱主在參與抗議活動時的安全及生活:他們會準備食物帶到示威現場,或供給裝備(例如雨傘)以抵擋被拍照或橡膠子彈。 他們亦會提醒僱主和其他家庭成員戴上口罩或幫他們打包示威時需要的備用衣服。有一次我在街市遇到了一位移工。她正拿著五到六把雨傘。
我問她:「你出去買雨傘嗎? 為什麼買那麼多?」
她回答說:「是的,我是為老闆買的。 我們家裡的雨傘用完了。」
「真的,他們怎麼會沒雨傘?」
「他們把雨傘都帶到集會去了。 我正在為我的僱主和他的孩子們準備雨傘。」
「他們所有人都參加示威嗎?」
「是的,我的男老闆,他的女兒和她的兩個孩子都去上街了。而他們每個人都需要帶把傘。所以我為他們買了這些。」她補充說:「店主還問我為什麼要買那麼多雨傘。他是一個親建制的老人。 我跟他說我想把它們寄回家,因為香港的雨傘質量特別好。」
有一小部分移工以家庭傭工的身份直接參與了這場運動。一位工人曾告訴我她70歲的僱主想去支持上街的年輕人,但是因為她的丈夫病了而要用拐杖走路,沒有人能陪伴她到現場。
這位老婦人對他們的家傭說:「我想參加這些行動,但是我不能和丈夫一起去,因為他行動不便。我也不能與兒子同去,因為他會上前線。當抗爭者與警察發生衝突時,他一定要逃跑。」
那移工便回答:「如果您需要人陪您,我可以陪您去。」
「但這意味著你當天將無法休假。」
「我不介意陪您,重要的是您感到快樂。您對我真好。」
因此,幾乎每當她參加行動,那移工都會陪伴她。雖然她犧牲了一天的假期,但她的老闆也對她很好。當然,她亦有得到失去假期的補償。她們倆之間互相理解。當那老婦人無法提起大袋物資時,那移工會為她年邁的僱主搬運食物和飲料。她亦會確保她的僱主可以到達遊行地點,然後安全回家。他們很多時都要步行很遠的距離,當她的僱主筋疲力竭時,她會要僱主休息或吃點東西。
我問這位移工:「你其實是打算幫助這場運動的嗎?」
「嗯,不。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幫助我的僱主。 我知道她為許多事情而戰,所以我想幫助她。」
除了通過確保僱主的健康來支持運動之外,他們還提供了心理支持。例如當僱主與參加示威的孩子們爭執時,他們會安慰僱主。有些僱主將孩子踢出了家門,我和他們的外傭進行了訪問。
這些僱主曾對他們的孩子說:「如果你遇到麻煩,不要牽連我們」,什至「你不再是我的兒子。」
這些年輕人好幾個月沒有回家了,也沒有告訴父母他們住在哪兒,但會透過移工來看他們的父母過得好不好。因此,這些外傭漸漸地變成了調解人,充當著這些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溝通橋樑。當這些青少年選擇離家時,他們實際上沒有想過要這樣做。
當他們想了解父母近況,又不想直接打電話給他們時,他們便會聯繫移工:「媽媽好嗎? 她有定期吃藥嗎? 你必須好好照顧她。」
這些移工因此在情感上被牽涉。她給予示威者們支持和令他們感到放心,讓他們專注於抗議活動,而不用擔心自己的家人。
與此同時,僱主亦會要求移工作為中間人與子女溝通。在一個案例中,母子之間發生激烈的衝突,以至於他們甚至不會與對方打招呼,但這位僱主有時會購買兒子們最喜歡的食物,然後讓移工送給他們。
「請給哥哥和細佬。我肯定他們現在住的地方一定沒有這個可以喝。」
然後,她便會與僱主的兒子們聯繫:「你在哪裡? 我帶湯給你。」

冷待亦是歧視的一種
RR/AK:您覺不覺得移工為這項運動的貢獻有得到認同及欣賞?
YR:儘管我們做出了貢獻,但由於我們沒有足夠的機會獲得資訊和保護,我們仍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最初,政府和香港人都不認為我們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們認為我們並不需要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但實際上,移工們是有被牽涉其中的,即便她們未必意識到這一點。她們可能在外出時因橡膠子彈或催淚彈而受傷。但是合約規定,我們的健康保險不會涵蓋我們在休息日受傷的治療。因此,即使在外渡過假期是我們應有的權利,風險其實很高。誰會照顧我們的安全?如果我們沒可能受到合理的保護,那根本就意味著我們被剝奪了享受每週一次放假的權利,無論我們有否直接參與運動。
香港政府、印尼政府和香港人都覺得我們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因此,我們不被包括在內。為什麼我們總要像小孩子一樣,要別人告訴我們來做什麽和想什麽?如果我們有更多渠道獲取資訊,我們自己可以建立對這場運動的想法。我們如何看待這場運動是我們作為成年人的決定。現在他們僅期望我們完成某些任務,並遵守他人的意見和決定,但不能為自己說話或有自己的立場。在這方面,他們確實歧視我們。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被限制採取行動或表達自己的意見,好像我們與本地人(或香港人,無論你想怎樣稱呼他們)有所不同。但對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誰應該被稱為香港人?
這個「他們」是香港政府、本地人、印尼政府,甚至我們社區的大部分人。實際上,有些人已經內化這種歧視:我們「只是」女性,應該只做家庭傭工、服從僱主,以及聽取政府的呼籲。 當有人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時侯,他們會把茅頭指向她,責備她對社群造成的傷害並從而壓迫她,使她屈服,亦不再將她視為我們的一份子。
我個人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移民工人與香港的其他人其實是平等的。不論其移民身份,移工都是人,是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選擇的成年人,並能夠辯護自己對這場運動的看法。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被限制採取行動或表達自己的意見,好像我們與本地人(或香港人,無論你想怎樣稱呼他們)有所不同。但對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誰應該被稱為香港人?無論是自願或被剝削的形式,或因工作原因或個人選擇,我們的確在這場抗爭有所貢獻。雖然還沒有成功爭取真正立足之地,但到最後,無論你是否稱呼我們為香港人,我們都是香港的一部分。
RR/AK:當您在遊行時收集資料並拍照時,示威者有什麼樣的反應?
YR:有時候我會因為外表比較突出而被懷疑。我戴的頭巾和衣服的顏色也與示威者不同。
有一次我在一群記者中間拍照。 有人突然走近我,問:「你是記者嗎?」
我給他們看了我們Migran Pos的記者証,似乎滿足了他的好奇:「好吧。你是記者我就不打擾你了。」
還有一次當我拍照時,一些女人說:「嘿,你不能隨便拍照。」突然她們開始侮辱我。
我解釋說:「我知道,我不會拍任何有臉的照片,我知道什麼可以拍攝,什麽不能。」 我給她們看了我的相機。
我被質疑是因為我看起來與眾不同。我覺得他們懷有偏見,覺得我跟他們並不平等。他們感到不安,是因為與他們不同的人正處在這個抗爭活動的核心,正跟他們做一摸一樣的事。
我不僅受到抗爭者的排斥,也遭到支持政府一方的不友好對待。有一次,當我在收集有關金鐘抗議活動的資料時,一位老太太向我走來:「你為什麼要拍警察的照片? 他們正在工作。」然後她就動手打我。
我對她說:「你不能打我。」
然後許多人過來保護我:「你不要還手。如果你打了她,有人可能會報警。」
「她是家傭。她在這裡做什麼?」
但是,並非運動中的每個人都排斥我們。大多數抗爭者對我們的存在並不感到困擾。年輕示威者的接納程度也比較高。其中一些人真的很關心我們。有一次當警察來時,我正坐在商場的抗爭者人群之中。突然有人在我頭頂開了一把傘。我立即轉身。
他說:「警察在樓上,你必須撐傘。他們正在拍攝我們。我不想他們拍到你的樣子,你最好戴上口罩。」
還有一次,我正在報導在深水埗的抗議活動。我正在地鐵站內拍攝支持者在售票機上留給抗爭者的食物和備用衣服。突然間,示威者奔跑起來。
他們有一些人停下來對我說:「姐姐,你趕快離開這地方吧,這裡現在很危險。跟我們來,我們一起坐地鐵。」這些示威者感動了我,在面臨危險時仍在保護我們。
另一次,我目睹了一名移工被困在示威區。她因恐懼而哭泣。
一位年輕的抗爭者問她:「你在做什麼?」
「我想回家。我老闆的家在那邊,但我很害怕。」
這個年輕人脫下頭盔並戴在她的頭上,而他的朋友亦用雨傘遮住她的頭。他們兩個陪著她走出了示威人群。當我看這個場景時,我簡直啞口無言。我甚至感動到無法拍照。即使我們沒有參與其中,當我們需要保護時,他們仍是會關心我們的。
一些抗爭者還會對移工說:「不好意思,姐姐,我們必須經過這裡。對不起,打擾你了。」

不相稱的正義和參與
RR / AK:從您作為移工的角度來看,應該在五大訴求裡面增加哪些訴求?
YR:雖然移工在五大訴求裡並沒有被代表到,但是引渡條例也會影響我們,因為該條例將適用於在香港的每個人。同時,由於我們不是永久居民,因此普選的訴求並不適用於我們。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權這樣說,但如果要在五大訴求中增加一些內容,我認為那應是有關移工和香港其他少數族裔的權利。這代表要遏止歧視並提供平等的渠道以獲取資訊。
香港市民和少數族裔及移工之間的權利並不平衡。種族歧視一直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然而,要達至平等並不僅取決於政府,因為這也是香港市民的責任。我們支持運動,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是這個社區的一份子,縱使五大訴求內並不包括我們的聲音。我們聲援此運動,因為我們知道如果香港人失去其言論自由,我們也會同樣地被滅聲。
我認為,無論其目的如何,如果能解決社會排斥的問題,此運動必定會變得更強。鑑於2019年持續不斷的社會衝突也影響了少數族裔,「we connect」這口號於2019年10月首次出現,引發了有關香港少數族裔關係更廣義層面的問題。當時有謠言指有東南亞人襲擊了一位民主運動人士,令此社群成為了代罪羔羊。當警察的水炮車在驅散行動中用藍色染料噴射香港最大的清真寺時,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區都感到震驚。
我們支持運動,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是這個社區的一份子,縱使五大訴求內並不包括我們的聲音。我們聲援此運動,因為我們知道如果香港人失去其言論自由,我們也會同樣地被滅聲。
我認為,若運動的組成包括了基層的少數族裔和移工,我們將可填補在追求正義、對非公民的歧視,以及對身邊的人的無知之間的落差。如果你希望此運動能成功,請不要忽略移工為了延續此運動的貢獻:我們照顧了你家中的一切,並確保了你家人的健康。不要忘記我們可以說這並不是我們的工作範圍:我們的職責只是做家務,並不是與你建立感情。事實上,你是需要移工提供更多幫助的。這就是為什麼香港人應該讓我們和其他少數族裔參與抗爭。他們不應該以為只有他們最了解香港一切。

香港與印尼共同的掙扎
RR/AK:去年9月和10月,在印尼發生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摸的抗議活動,反對遏制反貪機構和言論自由,並限制個人自由及破壞環境的立法提案。這些抗議與香港的抗爭有什麼關係?
YR:香港的大規模運動啟發了印尼最近的抗議活動。自從1998年的抗議活動和蘇哈托 (Suharto) 政權垮台以來,印尼便沒有再發生過大規模抗議活動。自獨裁總統蘇哈托在統治32年後辭職,印尼人似乎都對過渡時期(reformasi)感覺良好。
實際上,印尼人有很多對社會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只是在等待一個成熟時機去發聲。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啟發了印尼人,並給了他們動力:「在香港,年輕人已經走上街頭。」 但與此同時,香港的運動也受到印尼先前的運動所啟發。他們發現蘇哈托和林鄭月娥有共同點,因為兩位領導人都拒絕下台,並準備採取任何措施來維持權力。在7月1日,香港的抗爭者有史以來第一次衝進了立法會大樓。 一些人在推特上說,他們是受到了1998年運動的啟發;當時示威者便是佔領了雅加達的國民議會大樓,從而導致了蘇哈托獨裁統治的終結。
從汽油彈到燒車胎,這兩地的運動在戰術上也有互相啟發,共同反對專制和爭取民主。
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啟發了印尼人,並給了他們動力。但與此同時,香港的運動也受到印尼先前的運動所啟發。
2019年9月,當雅加達民眾抗議政府時,「#reformasi dikorupsi」(改革運動已腐敗)的標籤開始在香港出現。我曾經拍過一些「reformasi dikorupsi」塗鴉的照片,而我可以肯定創造該塗鴉的人是不會說印尼語或非印尼裔的香港人,因為當中拼寫錯誤,而且似乎刪除了一些文字。
另外,我曾經聽過一些示威者討論:「在印尼發生的事令人感到惋惜。有些人被槍殺了。」儘管他們自己也正在面臨鎮壓,他們也同時覺得自己與印尼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所關聯。
他們關心印尼人,而印尼人亦關心香港人。兩地都面臨著腐敗的政府和殘酷的警察任意暴力。 儘管它們沒有直接的聯繫,但兩個運動之間卻開始形成情感連結。雖然在印尼沒有明確支持香港人的活動,但我在香港看到了支持印尼的信息:「我們與印尼站在同一陣線。」
我曾經遇到一名抗爭者,他說他對印尼在無能政府下遭受的苦難而感到同情。
「你是如何了解印尼的?」
「我什麼東西都會讀的,姐姐。我讀過印尼的歷史。現在我們可以在網上查找所有這些資訊,而我已經看過全部有關蘇哈托倒台的來龍去脈。」

聲援移民家庭傭工
RR/AK:當您被驅逐出境時,香港一些維權份子組織了聲援行動。當時有誰在支持你?
YR:支持者包括一些本地和國際的記者、一些香港人、一些難民,以及從事移民工人領域的組織人,例如合作社成員或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的成員。一些支持者來自Lensational:該組織通過教授攝影來支持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女性工人,而我曾經也在那當學生和導師。
一些參與者真的使我感到驚訝。我朋友發送了一段影片給我,記錄了一名參加聲援活動的12歲孩子的情況。
「你為什麼要參與這個聲援行動?」
「我想支持Yuli,因為我家裡也有姐姐,姐姐們對我們很好。」
「那你為什麼戴著口罩?」
「因為我不想讓父母知道。他們不支持遊行。」
RR/AK:「聲援Yuli」行動與以前有關家移民家庭工人的聲援行動有何不同?例如在2015年,外傭Erwiana遭到僱主的虐待,其案件在香港引發了關於移民工人的熱烈討論。
YR:「聲援Yuli」的行動質疑為何移工會被排除在香港人身份之外。活動的組織者提出,在香港常用的「外來家庭工人」(foreign domestic worker) 這個名稱應改為「移民家庭工人」(migrant domestic worker)。他們反對將外傭定性為外國人:「當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的一份子時,我們仍將他們視為外國人,是否對他們不公平?」 此舉引發了支持者之間的討論:將來我們應該如何對待移工?
有見及此,此聲援運動便開始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IC)倡議難民和被拘留者的權利;被驅逐人士通常在驅逐出境之前都會被拘留在此入境事務中心。為了保障被拘留者的權益,一個名為CIC拘留權關注組織(CIC Detention Rights Concern Group)的團體一直與政府爭論某些非法拘留的案件。我的案例反映了拘留中心內發生的不人道對待,而現在亦有更多前被拘留者開始分享他們的經驗。
Yuli Riswati其他作品
Afterwork (KUNCI & Parasite 2016) 精選收藏集,內包含Yuli的短篇小說。
Yuli在2020年3月8日於柏林舉行的國際婦女節遊行中的演說
Yuli在2020年一月29日至2月9日在紐約唐人街Chinatown Soup畫廊 “afterbefore: images and sounds from hong kong” 的參展作品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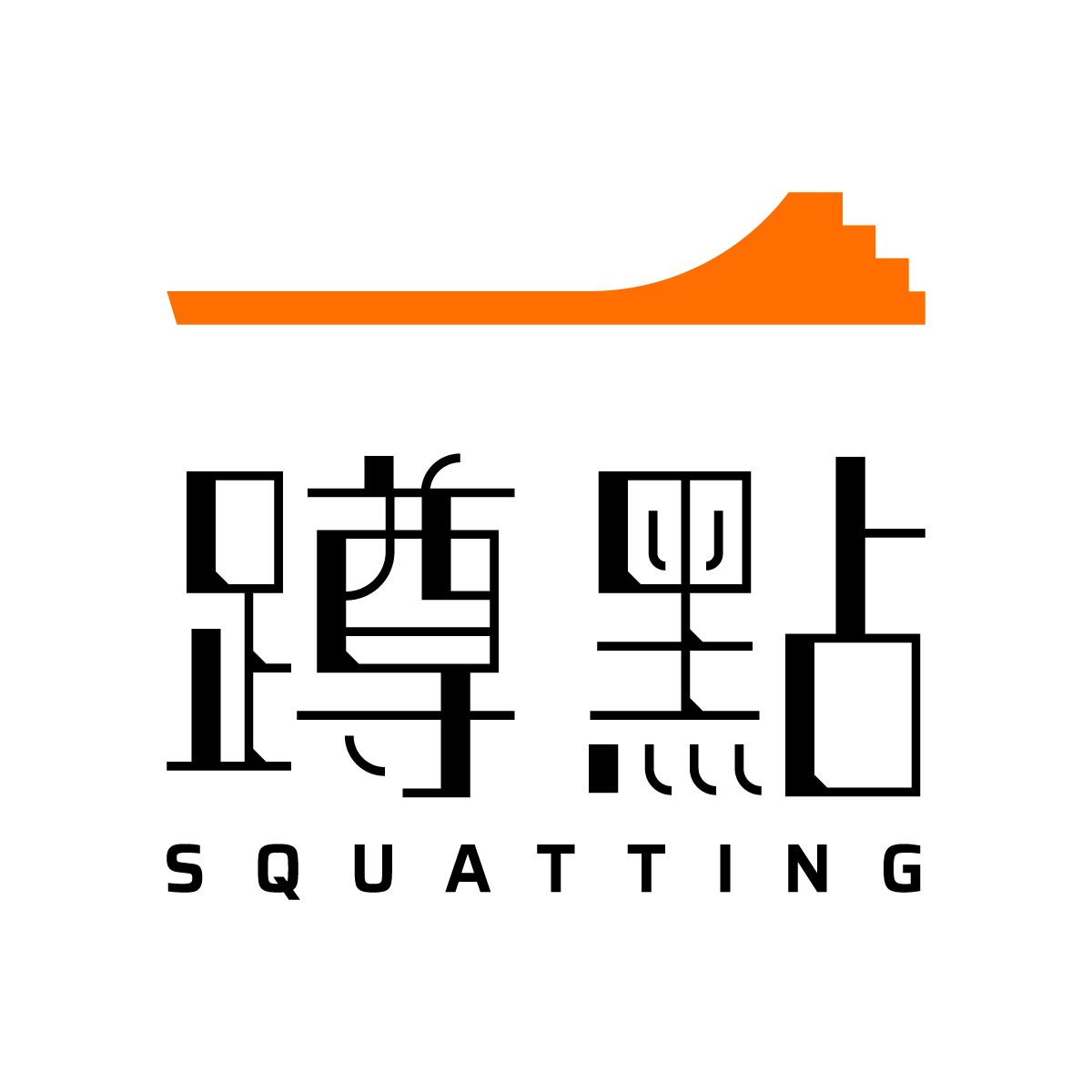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