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兩昧

作者:白水 難度:★★★☆☆
人生最好的事情
話說有一天,希臘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朋友兼老師西勒諾斯(Silenus)被人類捉到。人類知道西勒諾斯是一位智者,能夠解答許多人類不能回答的問題,於是他們就問這位智者,人生而在世最美好的事情到底是什麼。智者笑說,其實知道這件事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好處,反而只會令他們得不償失。智者續道,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你們已經不可能做到了,那就是從來沒有來到世上。不過不要緊,人生還有第二件美好的事情,那就是立即死去。
這段神話故事讀來總帶點無奈和諷刺,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希臘人對人類存在的徹底悲觀。對他們來說,存在就是一場苦難,很吊詭地,沒有存在過才是最好的存在。或許這種人生的悲涼,我們或多或少都感受過。
就在曾幾何時的一瞬,我們也許都會感受過人生的虛無。我們既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亦不知從何而去,而在來去之間那短暫的時光總不知道存在所為何事。或許真的有那麼的一瞬認為最好的事真的莫過於立即就死去。這種對於人生的感受可以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無病呻吟,只不過是因秋風落葉等無聊事而故作有感,但那亦可以是真正洞識到人生真實可悲之處而發的感嘆,哲學家就將這種感嘆歸為人生的荒謬。
日常的荒謬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偶爾會感受到一種荒謬的感覺。你很愛你的女朋友,對她無微不至,你曾經通宵達旦的為她排隊買演唱會門票,可是情走到盡頭時,女朋友偏偏卻毫無理由的要與你分手;他是個奉公守法的好市民,不過想安安穩穩上班下班,閒時去去旅行,平日吃點好的,可是當權者不讓他過平凡生活,當權者一而再再而三濫權,熟悉的地方不再熟悉,平凡的生活不再平凡;住樓下的婆婆她是一個老好人,閒時餵流浪貓,又會送飯給窮人,每次看見回家的你都會親切的點頭微笑,可是過了一段日子,你卻很久也沒有見過她了,後來你才知道原來她綠燈過馬路時被一個大意的司機不小心撞死了。除非我們已經麻木,否則相信遇到這種事情,我們都會大喊荒謬,大抵我們都會問豈有此理,又或者苦於怎麼人世間可以這樣的事情。
這種荒謬感其實源於人類的「應然意識」。人類是一種很有趣的生物,常常會認為或者期盼世界應該如何如何。這個世界應該是好人有好報的,這個世界應該是有公義的。雖然人類會講道理,但現實是不講理的,現實往往總是不如人意,並沒有符合我們想像中的如何如何。而這種現實和應然意識之間的落差就會令人產生荒謬感:世界不能是這樣的,世間怎會有理由是如此這般?
你對女朋友如斯照料,她怎麼可以跟你分手呢?當權者的權來自人民,他怎麼可以欺壓人民,人民又為什麼居然沒有能力收回他的權力呢?婆婆是個好人,好心為何沒有好報,怎麼偏偏好人死光光,壞人卻好端端?
當我們不能改變現實,又不能改變自己的心態去迎合現實時,等着我們的就只有無盡的荒謬感。我們無法接受現實,可是我們又卻不得不生活於如此荒謬的現實。
我們有這種對於人生中的荒謬感,但又等不等於人生本身就是荒謬的呢?其實我們是無法肯定應然意識與現實必然出現落差的。我們大可以想像有一個人由出生到死亡從來都未曾感到過荒謬,因為他一來以路都是事事如意的,現實總符合他的期盼。雖然這個機會是多麼多麼的微細,但它還是存在的。所以我們不能說,雖然人生時不時有荒謬的事出現,於是乎所有人的人生本來就是荒謬的。
又或者換句話講,人生有可能出現荒謬的事,但亦有可能不出現任何荒謬的事,所以生命的本質不能說就是荒謬的。因為一般而言,本質就是指使得 X 之為 X 的東西。如果要說荒謬是人生的本質,就是說荒謬是使得人生之為人生的東西,故人生應該必然荒謬,但正如剛才提到,生命不是必然荒謬的,亦有可能有不荒謬的人生,所以我們很難去說人生本身就是荒謬的。
哲學的荒謬
日常生活會遇到的荒謬不能顯現出人生本身的荒謬,但其實還有另一種荒謬可以勝任。某天,在繁忙的工作之中,你原本坐在文件成山的辦工桌前埋頭苦幹,可是忽然之間,不知什麼使得你從沉重的工作抽離。你忽然驚醒,看着手頭上海量的文件,你開始問自己:「到底我在做什麼?為什麼我要做這些東西?」又或者,某日你終於考進心儀的公司,你收到成功的消息之後開心了好幾個小時,整個人都浸淫在快樂之中,但熱情過後冷靜下來時,一陣空虛湧上你的心頭,你忽然的問自己:「其實這成功到底有何意義呢?」
這類荒謬感可能一閃而過,你轉眼間便將它拋諸腦後,但其實你有曾幾何時的一瞬可以接觸到人生本質上的荒謬,只是你跟它擦身而過而不自知。但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否則你就有可能跟古希臘人一樣,認為人生不如不活。
人除了是一種講求應該與不應該的麻煩生物,也是一種會講意義的生物,我們常常要為自己所做的事情尋找意義:我做這個那個是因為這般那般的意義,否則不僅僅是不如不做,做了更是生不如死。正正因為如此,薛西弗斯無了期地石再推石才令人感到如此的絕望,他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根本不知所為何事。
說做某件事情有意義的意思就是指做某事是有價值的,是值得我們去做的。但假如我們認真的去思考,我們就會發現平日所講的意義,到頭來其實根本無法被證實為什麼是意義,我們認為值得做的事情,亦找不到一個理由去說明為什麼值得做。哲學上的荒謬感就從中而來 ── 人一直強調意義,但偏偏所謂的意義其實談不上是「真正的意義」。
當要解釋一個意義之為意義時,我們要嘗試做的是給予一個理由去證明。要麼你就能夠指出這個意義本身就是不證自明的,那我們就不必找一個理由再去論證;要麼你就需要找另外的理由的論證意義之為意義,而我們往往都會引用其他的意義來支持先前的意義。
然而,這兩個方案都有其困難。一方面,前者是難以接受的:所謂不證自明就是指不必經過任何論證而要被論證的對象己經能夠成立。「整體必定大於或等於它的任何部分」一般都會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但談人生的種種意義時,我們往往難以有一種共識,一致地認為某某就是一種客觀的意義。比方說,你說救人是一種意義,這一來未必人人同意;二來假如你認為不必給予任何理由去支持自己,那同樣我亦能說例如殺人放火又或者強姦也是一種不證自明的意義,所以如果你想說服又或者反駁別人,似乎必須給予理由;三來就算你知道而且它真的是一種客觀的意義,但若然不能給予一個理由去論證它為何就是意義,它還是未經證明的 。
另一方面,後者會出現無限後退的問題。當你問自己為何要工作,你可能會答這是因為我需要錢,當你再問為何自己需要金錢,你又可能會回答因為你需要生活,之後又再問為什麼需要生活,你會發現彷彿可以不停的問下去,而可能你亦可以一直的回答下去,用意義去解釋另一個意義,但你最後會發現答案無盡,而問題亦可以是無窮的,以有涯隨無涯,豈止殆矣?而更有可能的是,你發現其實已經找不到更多的意義去解釋自己的行為,理性去到某個地步就已經無能為力了。意義本身其實沒有什麼意義可言。理性走到這裡就透顯了一種荒謬感 ── 人生許多選擇我們以為富有意義,但到頭來原來根本不明所以。
不知為什麼,所以不再為什麼。尼采說過:「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Twilight of the Idols) 你找到生活的理由,你就可以過幾乎所有的生活。但假如你已經不知道生活為何,人就會陷入無力的深淵,被虛無吞掉,很難很難才能夠爬出來。你會在辦公桌前,不停苦思為什麼自己在此,又或者在成功過後,困於尋找成功的真義。
這種追問意義為何而展現出的荒謬,正正是人生本身的荒謬。原來人生種種意義去到某個地步是無法以理性解釋的,而這是必然會遇到的無力之處。這種荒謬未必每個人都經歷過,但只要一旦嘗試不斷去追問,他就會感受到意義失落的荒謬之感。
思考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未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蘇格拉底如是說。現在我們恰恰去到這句話的反面 ── 思考過的人生才是不值得活的,因為要思考過才會知道原來人生的意義是很難說明的。所以在篇首故事中的智者才叫我們不要問,因為一旦問了,就很難回頭。如果現在再讓你選擇一次,你會選擇做痛苦的蘇格拉底,還是一頭快快樂樂而從不會思考的豬?
*文章參考自 Thomas Nagel 的 Mortal Question 第二章 “The Absurd”,但對其理論框架略有改動。若對有關荒謬的問題有興趣,建議參考原文。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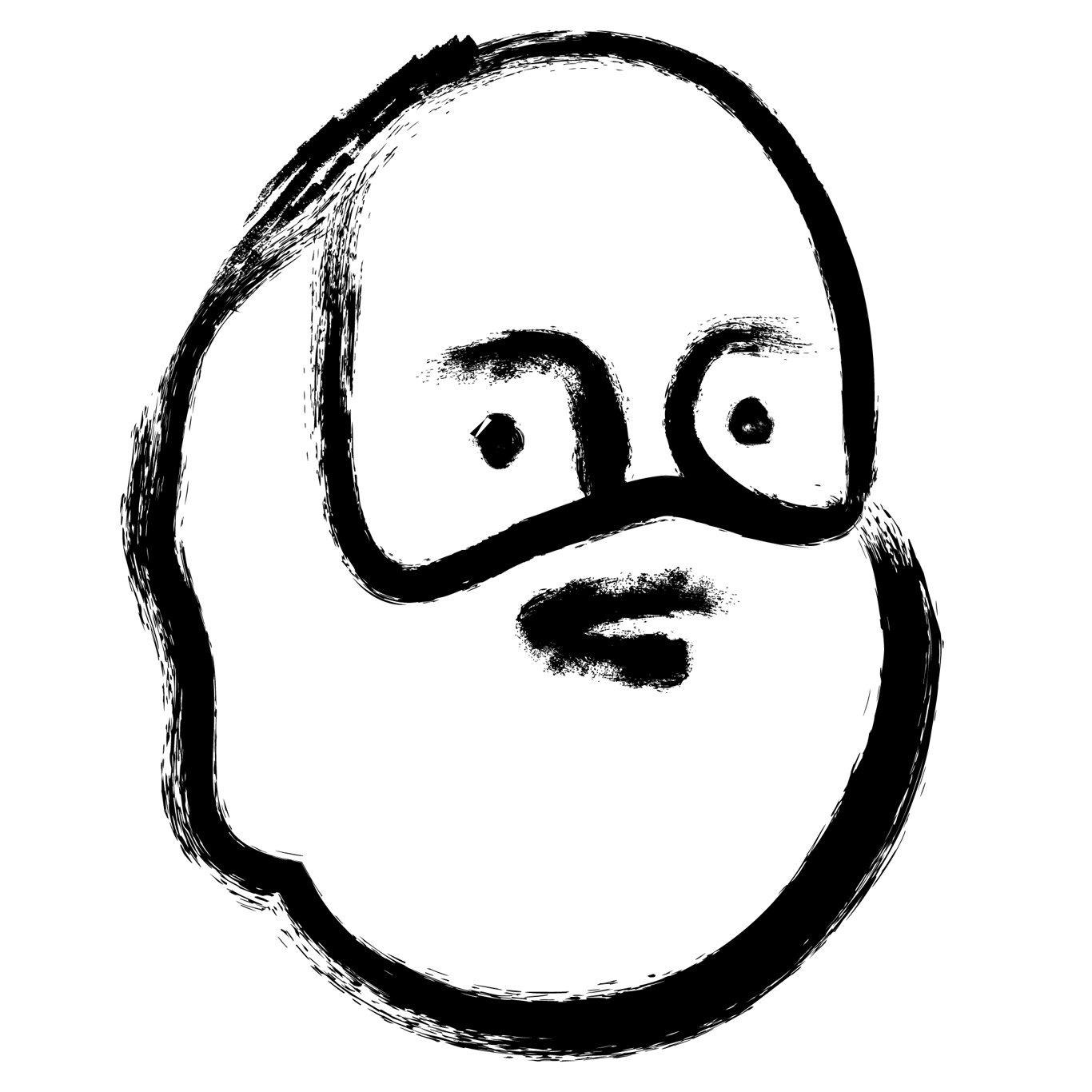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