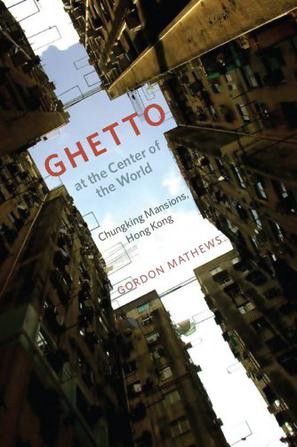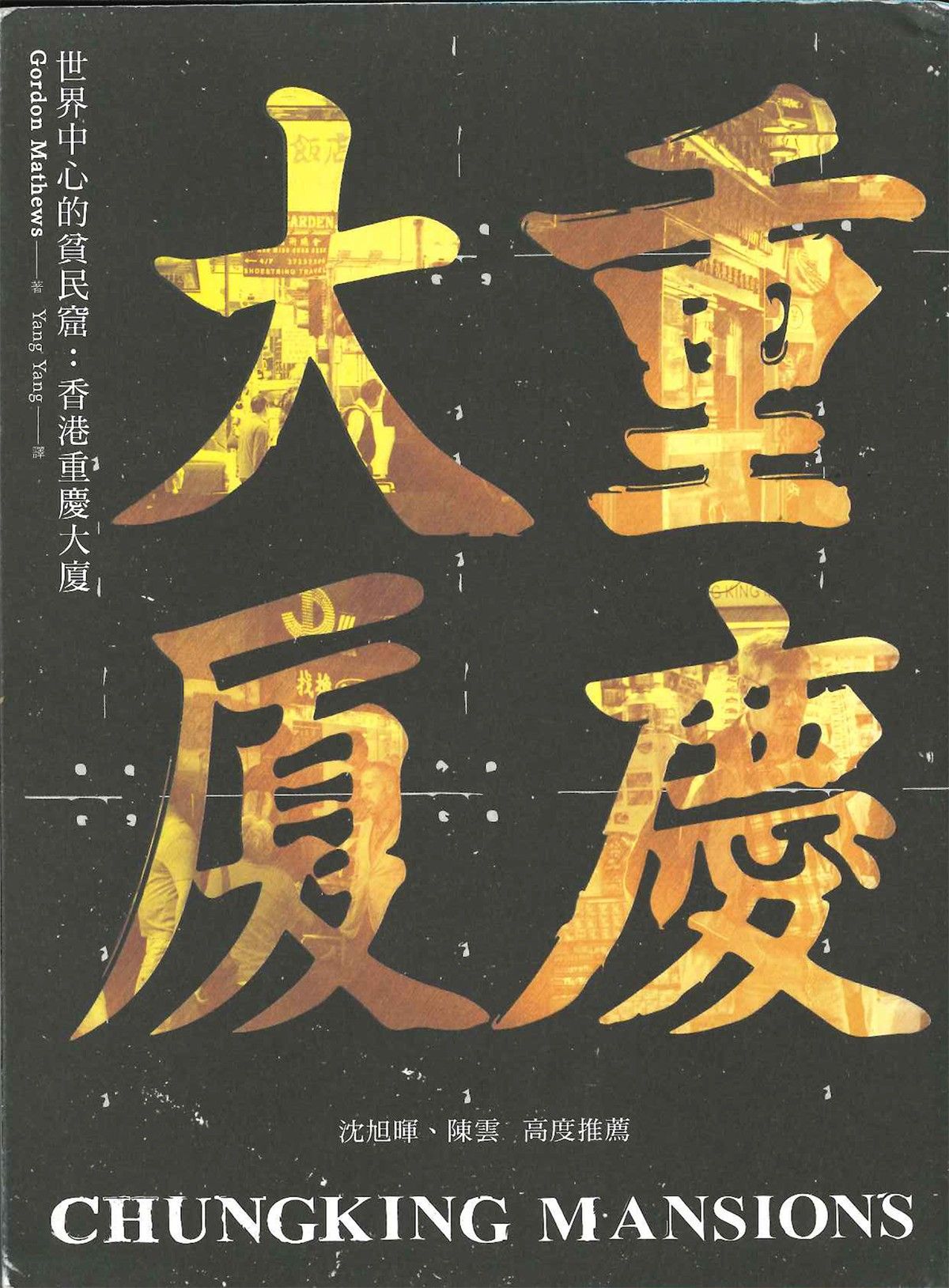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很可能是整个世界未来的样子
一直都很想读《重庆大厦》中文版翻译,一拖再拖,才托朋友的福,从他那里借到了薄荷实验出版的中文版。

原书的语言本身就十分朴实易懂,中文译本保留了这种通俗性,想来译者是花了不少心力的。有时候翻译理论术语反而要更简单,毕竟有点像通货,如何换算已经约定俗成,但要保留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朴实无华,而且还要贴合中文语境,反而更难。
书中并没有长篇大论的理论分析,更多是在讲述普通人的生活和处境,每一章节中都会包含几个亲历者自述的故事,小商贩、店员、游客,避难者、性工作者、吸毒者,警察、保安、官员,华裔、非裔、东南亚裔,锡克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难怪,在一栋大厦中,就能窥见世界。
这不禁让我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样的民族志才是有长久生命力的?每个作者的写法和研究方式,对于所研究的社区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他/她自己的研究轨迹又会有什么影响?
阅读这本书,也让我想起了很久一起与Gordon的一次无意的聊天。美国人类学协会下有一个分协会,叫作Society of East Asian Anthropology,简称SEAA,中文也可以叫东亚人类学协会。Gordon之前做过SEAA的主席,而我因为当时做了几年student councilor,每年会在年会期间遇到他,他几乎年年都参加,卸任后的那几年也一样。
那年会议在加州圣何塞召开,山火之后,空气中弥漫着尘埃颗粒,让人产生一种回到北京的错觉。
在一次集体活动后,将近晚上11点,路边到处是举着手机叫uber的人,我算了算,步行至我住的速8大概四十多分钟,等车可能也要二三十分钟,再加上研究生经费的窘迫,想想还是走路回去了。
不料,没走出几步路,发现Gordon背着一个很不起眼黑色书包,也在往同一个方向走。
“你住哪儿?” 他问。
“速8。”
“哦,我也住那里,那一起走吧。”
我看了他一眼,他大概看出了我的不解,”没错,很多像我这把年纪的老师都会住在希尔顿之类的酒店,对吧?不过,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有张床能睡,有个地方能洗澡就行。“
于是,我们一路走一路聊,除了抱怨天气外, 作为一个处于深度迷茫期、还在写毕业论文的人类学博士生,我当时还问起了学术写作和人生选择。
他说,《重庆大厦》虽然很受大众欢迎,但在人类学内部的评价其实并不高。并不是说这本书不好,而是不够”理论化“。在重庆大厦之后,他又和学生合作,写过一本关于广州非裔社区的书,也是大体上延续重庆大厦的写法。
“这就是我选择的风格,我也知道理论化很重要,可以让你的作品感觉更加’重要‘,或者说更’普世化‘,但是,你的读者也就受到了局限。”
说白了,到底是面向公众写书,还是面向行业内部写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写作的风格和语言。但不光如此,这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学者的学术轨迹。
Gordon坦率地说他没想过自己能去芝加哥、伯克利这些以批判理论出名的项目,亚洲才是他的研究地,也是他想要生活、教学的地方。
我记得快走到速8酒店停车场时,他说,“你问我建议,我其实真的没什么建议,要写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研究,其实也是你的人生选择。我选择了那样的人生,至少,我不后悔。”
那句“至少我不后悔”让我记了很久。这次读中文版的《重庆大厦》,突然意识到,或许那些也是重庆大厦中的人教会他的吧。
在非洲、东南亚经济更不发达地区的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社会,到香港寻梦,或为避难,或为挣钱,没有人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会怎样。
他们或许永远都进不了重庆大厦附近那些更为昂贵的酒店,无法融入当地华人为主的社会,90%以上的人永远赚到想要赚的钱,越来越多避难者无法离开也无法融入。
这座大厦可能会被拆,可能还会在那里,但时事变化多端,尤其是疫情之后,重庆大厦和其中各种人的命运,更不好说。
Gordon在书的结尾预言,“重庆大厦在其特定环境下必然消失,但就更深层意义来看,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也许不久将成为整个世界。”
确实,在疫情期间的世界,这种不确定性和脆弱感正在不断弥散。失业的,过劳死的,被抛弃的,被遗忘的,被剥夺的,被歧视的,分离的,拘禁的,挣扎而不得的,拥有却不自知的——这些普通人的挣扎,才是最值得被记录的吧。
顺便也分享一下不同的几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