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 哀恸的哲学:“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当灾难降临,人们如何达到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平衡?当死亡近在咫尺,而不是史书上一串串冰冷的数字,我们如何处理生死离别带来的复杂情感?
1914年12月,一战的阴影笼罩欧洲,与此同时,西班牙流感也夺去了百万人的生命。佛洛依德的子女或有上了战场,或被疫情夺去了生命。其中,1920年1月25日,他的女儿苏菲在孕期中被西班牙流感带来的并发症夺取了生命。佛洛依德和他的妻子无法见到苏菲最后一面,只能在葬礼上凭吊爱女。苏菲的过世,仿佛夺去了佛洛依德作为父亲的所有欢乐,这对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有什么深远的影响?而在对亲人死亡的反思中提出的理论,又会给百年后处于疫情中的我们什么启发?
本次选译的文章是英国学者Jacqueline Rose为佛洛依德忌日(1939年9月23日)所准备的讲稿。正如Rose所说,“或许,在我们这样的时刻,更难的是在面对死亡时,如同面对活着的时候一样,承认自己情绪的复杂性。”
原文作者 / Jacqueline Rose
原文链接 /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2/n22/jacqueline-rose/to-die-one-s-own-death
原文发布时间 / 2020年11月9日
译者 / 何啸风
编者兼校对 / 王菁
01.
“生命的全部目的就是生产死亡”
1924年,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弗里茨·威托斯(Fritz Wittels)暗示,女儿苏菲的死,跟《超越快乐原则》(1920)有某种联系。正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提出“死亡驱力”的概念。
弗洛伊德本人马上提出异议。他说,这种暗示不合乎常理。他在1919年完成了草稿,而那是早在爱女苏菲去世之前。1920年7月,弗洛伊德写信给马克斯·艾廷冈(Max Eitingon):“你将了解,在苏菲在世的时候,它就已经完成了大半。”这种说法反常得很——“完成了大半”意味着,苏菲死后,还做了很多补充工作。为什么特地澄清“苏菲在世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大半”这个事实呢?今天,幸亏有弗洛伊德学者格鲁布利西─西米提斯(Ilse Grubrich-Simitis)不懈努力,让最早的手稿重见天日,我们才知道他有所隐瞒。在后来的草稿里,补充了一个全新的章节(第6章),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在这次出版的章节里,第一次出现“死亡驱力”。在此之前,它只出现在1920年给艾廷冈的两封信里,就在苏菲死后几个星期。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这个前所未有的概念应该归功于苏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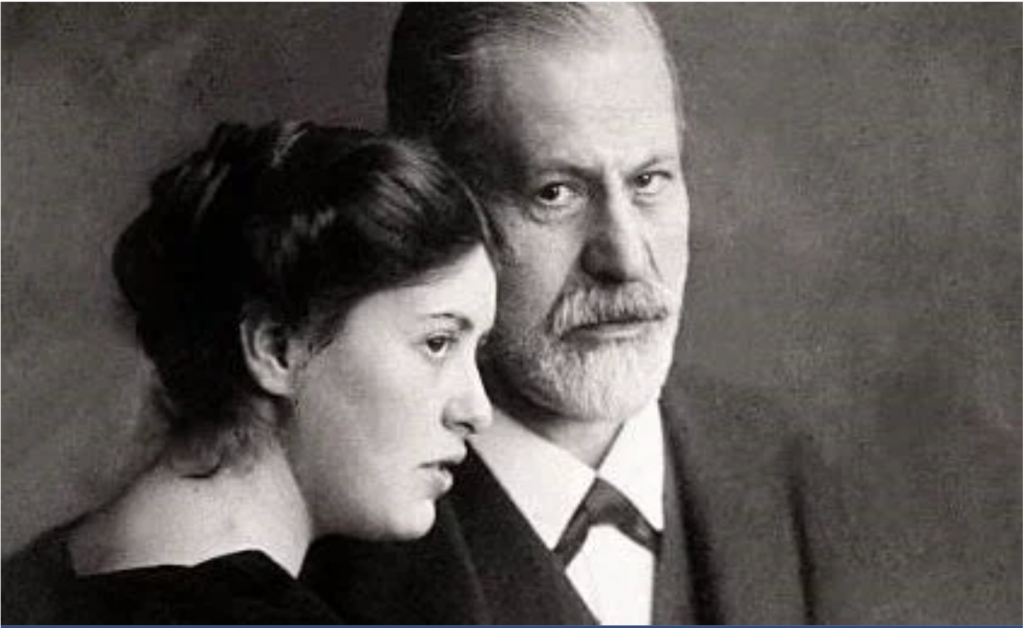
回应威托斯时,弗洛伊德只承认后来加了一段“讨论原始的生物的内容”。弗洛伊德在这里上演了一段无意识的“破釜逻辑”(kettle logic,被告给出多个说法,各个说法互相矛盾):
他早就完成了。他做的补充无关紧要。唯一的新内容是关于生物的生存和死亡(说的好像这样的主题和孩子的死亡不沾边)。
弗洛伊德给普菲斯特的信里说,苏菲“仿佛被夺走了……仿佛不曾来过”。“这赤裸裸的残酷现实,”他接着写道,“令人无法承受。”当人们在你身边如苍蝇一般死去,你如何能相信什么死后还有来生(不管是物质不灭,还是灵魂不朽)的说法?
《超越快乐原则》是弗洛伊德后半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弗洛伊德意识地形学(topography of the mind)的集大成,而且提出了新的驱力二元论。它既受到热情欢迎,也遭到激烈排斥。马克思·舒尔(Max Schur)尽其所能地对这本书进行抨击。这乍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舒尔的书探讨的是死亡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作品中的位置。不过,某种无意识的恶魔般原则扰乱了我们的心理,这样的想法彻底摧毁了人能掌控自己意识(man in control of his mind)的理念。
因为这个原因,这种想法对舒尔和其他人来说无异于某种诅咒(anathema)。舒尔是弗洛伊德临死前的医生。直到弗洛伊德的癌症已经令他的生存毫无意义,舒尔根据他们的口头约定,为他注射了致命剂量的吗啡。毫无疑问,这正是弗洛伊德想要的。在16年的折磨之后,弗洛伊德在生命结束之前获得了最后的尊严。可是,我的分析也许有些出格:我认为,只有坚信人能够让意志服从理性,坚信人总是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恰恰与精神分析的精神相反),舒尔才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所作所为。
哪些人会死?在当前的疫情下,我们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国家的救济、医疗供给、物资,还有人与人的隔离,都让我们感到死亡是人们(垂死之人,以及他身边之人)触手可及的。由于交通不便,弗洛伊德夫妇见不到患病的女儿:
她去世之时,夫妇都无法陪着她。这样一来,我们更能理解《超越快乐原则》的这段话:如果一个人第一次由于所爱的人死亡而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他宁可希望自己丧命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一种可以以某种方式避免的偶然事件。
在第5章中,弗洛伊德详细阐述了“强迫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概念。他首先在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身上发现这种现象。这些士兵总是在夜里和白日梦里回忆起那些可怕的经历。弗洛伊德从前线到咨询室一直调查这种现象,他得出结论:这种强迫是所有生物的某种属性。所有有机体的冲动都是重现事物过去的某种状态。这样一来,自我保存和征服的驱力(他早期的意识地形学的关键)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他认为这两种驱力服务于生物走向死亡的需要:“有机体只希望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死亡。”也许,弗洛伊德这个论断是最反直觉的:“全部生命的目的就是产生死亡。”
在这一理论思路(他自己说,这是他最为思辨的理论之一)上,他不停在哀歌和论文、悲伤和科学之间徘徊:他说,“诗人们的作品使我们在这个观点上得到了鼓励。”不过,对我来说,伴随着苏菲的死亡凸显出来的,是出现在他思想中的新的维度。悄悄到来的死亡,要好过从天而降的死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要好过不该(不一定)到来的死亡。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常常从内心世界提炼出他的文字,可是,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时候,他这样坦白地把心理底牌亮出来。作为一连串意外的死亡,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东西了。
在死亡无情的随意性面前,疫情和战争的受害者被剥夺了生命的本质。这就是弗洛伊德想还给女儿的东西,想让女儿得到应有的继承权。简单地说,如果不相信生命的目的是走向死亡,那么,他完全接受不了女儿的突然死亡(患病5天就离世了):“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一种可以以某种方式避免的偶然事件”。接下来,他引用了席勒的话:“这种认为死是生物内部规律的必然结果的信仰也许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形成这种错觉是为了承担生命的负担(Schwere das Daseins)。”
他试图用暴怒(outrage)来抵抗他女儿的命运带给他的悲伤。在今天,疫情冲击了各个阶层和种族的人们,弗洛伊德的愿景(prospect)应该容纳所有的人。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哀恸的哲学。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既是内心灾难又是外部灾难。在疫情之下,人们不得其死。
02.
“让父母活下去的唯一事物就是他们的孩子”
在和威托斯的通信中,弗洛伊德放弃了对物质不灭的思考。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在自己的孩子死后,似乎无法继续思考物质不灭这样的话题了。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在苏菲死后两星期写给威托斯的信里,他把女儿的死描述为一次“自恋式创伤”(narcissistic injury),把它深埋在日常工作里,好重新回归生活。苏菲死后两天,他写信给普菲斯特(Pfister):“这是对一个人的自恋深深的打击。”
在这里,我们仔细看看《超越快乐原则》的第6章(弗洛伊德在其中讨论生物的死亡),或许能发现一些踪迹。弗洛伊德的疑问在于,生物学能否证明死亡是有机物的固有属性?生物体内有没有某种不朽的东西?根据演化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只有多细胞生物才会死。每当生殖细胞以新的形式传递下去,它的体细胞就会死亡。反过来,单细胞生物不会死,因为它能自我繁衍。或者,我们也可以同意马克斯·哈特曼(Max Hartmann)《死亡与繁衍》(1906)的说法,认为死亡不能简化为死去躯体的样子,而不妨这样描述细胞结束个体生长的环节:细胞自我变换,让自己进入生命的下一阶段。
这里重要的不是,生物学是否真的支持弗洛伊德关于人驱向死亡的惊人理念。像以往的情况一样,关键在于这些前提能让他继续他的思考。弗洛伊德不无满意地写道:
在这个意义上说,原生动物也是要死的;对它们来说,死亡一律是和繁衍相一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被后者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母性动物的全部物质可以被传递到年幼的后代中去。
拯救有机体不死的唯一办法就是它全部传递到后代中去——有的人可能会说,死了这条心吧。把同样的办法运用到人的生命里,孩子的死就成了自恋型的创伤,因为父母只有通过孩子的存活才能抓住永生。弗洛伊德在这里说的再简单不过了:让父母活下去的唯一事物就是他们的孩子。
这样一来,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似乎在生命体中消失了。不过,与此同时,这种驱力进入了外部的政治世界:和通常的意见不同,这两个领域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是相关的。我们还记得,战争是提出“强迫重复”这一概念的基本背景(归家的士兵不断回忆外部世界的危险)。对有机体和世上危险的同时关注、对生物过程和外界遭遇的同时关注,都频繁地出现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关于我们不自觉地继承的东西(我们的性情)的讨论,关于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东西(生命的意外)的讨论,也同时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毫无疑问,是COVID-19疫情让我重新发现这些关联。像很多人一样,我试图让内心的痛苦和外界发生的悲剧在心理上协调起来。怎么让这两个领域关联起来,成了弗洛伊德生涯第二阶段的关注点。这就是战争对理论的贡献。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一位受创伤的士兵不断在忠实自我(让他想尽办法避开危险)和忠实国家(让他时刻准备献身)两种要求之间挣扎。

03.
“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对人类来说,战争和疫情是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吗?虽然这乍看起来是个荒唐的问题——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没那么疯狂——但是,它也回应了弗洛伊德给自己定下的任务。这就是,努力记录世界对主体的影响,以及过去的年代对当前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对生命的不朽、延续、传递的关注,贯穿了《超越快乐原则》第6章。在其中,弗洛伊德试图驾驭女儿的死亡,并且直面这一事实: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已经无可挽回地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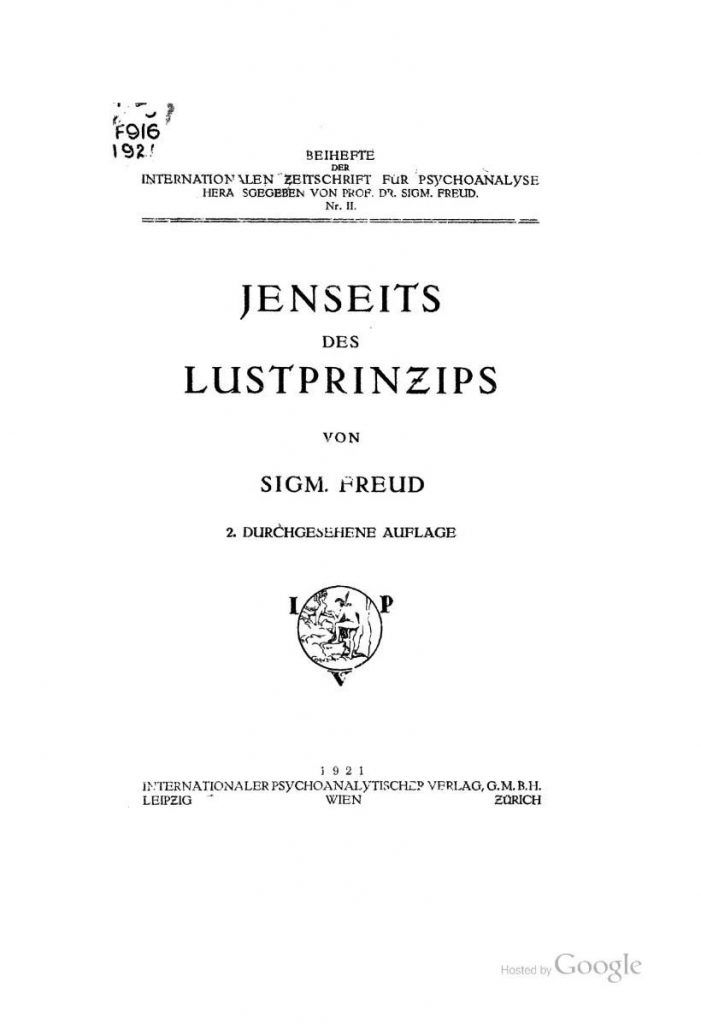
可是,在一战期间写的另一部作品里,弗洛伊德采取了一条不同的前历史的道路。他在其中谈论的不是生殖细胞,而是遥远的年代。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一个人间地狱,战争和疫情在它面前不值一提。我指的是弗洛伊德不希望公之于众的第12篇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ical)论文。又一次多亏格鲁布利西─西米提斯的学术奉献(1985年,她用“系统发生学的幻想”的题目发表了这篇论文),我们才能看到这篇论文。它是弗洛伊德放弃或销毁的7篇元心理学论文之一。
格鲁布利西─西米提斯违背了弗洛伊德的意愿,就像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意愿。她称这篇论文是“失败的证据”,可她也给这篇文章极高评价。她认为,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和创伤理论(人们通常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显示出深刻的联系。这篇《系统发生学的幻想》或《移情神经症概要》,让《超越快乐原则》的思考看起来像是严格的科学。文章开头,弗洛伊德叙述道:
冰河时代让人类成了焦虑的物种,此前总体友好的外部世界……转变为巨大的致命危险。食物不足以支撑人类聚落的增长,个体的力量无法让众多无助的生命活下去。
在这种“超出控制的”危急关头,人类给自己施加了繁衍禁令。这是因为,在这种缺衣少食的关头,繁衍物种无异于让自己处于险境:不会有孩子,不会有未来,看不到生命的存续。对于这种粗暴地压制人的驱力的做法,癔症就是他的反应:这就是现代“转换性癔症”的来由(在现代,性欲是一种需要克服的危险)。而且人成了一个暴君,因为他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所以奖励自己这种不受限的主宰地位:
语言成为他的魔法,他眼中的思维似乎无所不能,他根据自我来理解这个世界。
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就像今天多个国家的统治者(特别是马上要成为美国前总统的特朗普)有力证明的一样,暴君是灾难无声的同伴。他们好像在说:我可以救你们,可你们必须让我当国王。我也喜欢随之而来的另一个观点:暴君是最早的癔症患者。男权的潜台词是肉体的恐慌(bodily panic),这样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所有观点一样出人意料,而且无比激进。我们发现,在这样一篇被人(甚至被他自己)彻底视为幻想的文章里,他是多么具有政治性。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篇文章视为一次思想实验,它让弗洛伊德做出了巨大、前所未有的思想飞跃。
跨越无数个世代,深藏于人们内心的东西,就是焦虑。这种焦虑,既是对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的反应,也是对随之而来的暴君之权力的反应。这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传递的信息:“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孩子再现了人类物种的历史,支持了弗洛伊德关于系统发生学遗传的观念——“系统发生学的倾向压倒其他一切因素。”
这篇奇怪的手稿,让我们猜想,系统发生学的概念是他承认人类的脆弱状态(缺衣少食、穷困潦倒、举步维艰、历史的灾难、过去的重负)的某种方式。现代精神分析学常常谈论“上代人的还魂”(transgenerational haunting)。历史创伤在无意识中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把祖先在后边一路拖着,这也意味着,我们或许是为自己而死,但我们的死亡也代表了那些先于我们而去之人。弗洛伊德又一次超越了他的时代,把这一现实(它已经在临床上得到证实)注入人类的血液中。有机体会把全部的物质传递给下一代。在当时一片灾难的世界,这样做的代价,弗洛伊德这篇1915年的论文也告诉我们了。正如西米提斯1987年的演讲说的,弗洛伊德为我们的时代给出指导: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想象一个人造的新冰河时代,然后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思考核冬天(nuclear winter)的后果?
无论是当时的核冬天,还是现在的疫情或气候灾难,这篇文章都能引起振聋发聩的共鸣。
04.
人人皆可自由死去
不过,死亡驱力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弗洛伊德的论述中,死亡驱力不光属于静态的一面,不光是有机体缓慢、平静地回到无生命状态。死亡驱力之所以成为弗洛伊德最有争议的理论之一,不仅仅因为它给生命投下了一抹致命的苍白色彩,而且因为(也许更是因为)让暴力成为每个人的内在属性。这一层面的驱力,比弗洛伊德之前的观点(享乐驱力是生命的主要动力)更加骇人听闻。这是因为,它击碎了人们死守不放的幻想(世上的恶是全部人的责任而不是自己的责任)。1929年,弗洛伊德写信给爱因斯坦:
我们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外部世界,外部世界既潜藏着危险,也产生满足感。而在人的内心,我们只想平平静静。所以,假如有人想把注意力转向内心,就好像扭转它的脖子,那么,我们所有的组织都会抵抗——就像食道和尿道抵抗别人颠倒它们正常的流动方向。
这段话一定是弗洛伊德关于人们为什么敌视精神分析最发自肺腑的表述。1911年,他略显郑重地写信给宾斯万格:“想要分析人的能力,没有比精神分析更适合的了。”
同样的,这个观点(《超越快乐原则》第6章第一次阐述了它)深深地扎根于战争。我们也许可以猜想,假如他没有考虑战争如何粉碎人们天真的意识,那么,弗洛伊德的任务也太简单了,他的哀恸也太假了。驱使人在战争中疯狂的东西,就是人在毕生的压抑和克制之后对人发动暴力的能力。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杀戮向人展现了“人性的要求”和“国家战争的要求”的冲突,而是因为杀戮使得人们直面人之为人所具备的内在暴力成分。在《精神分析导论》第9讲《梦的稽查作用》(the censorship of dreams)中,弗洛伊德写道:
请看一看仍在蹂躏着欧洲的大战。试想一下大规模的暴戾、残忍和谎言还在文明世界里横行。你真的相信如果没有几百万追随者的同流合污,几个丧尽天良的野心家和杀人犯就能发动所有这些邪恶战争吗?
就像1916年一样,自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来,我们处在博索纳罗、莫迪、埃尔多安、欧尔班、杜特尔特这些人的时代。
我们特别强调人的邪恶只是因为他人对此加以否认,并且因此使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不能改善,反而使其更难以理解。
我在本文开头指出,当今的疫情从我们身上剥夺的一件东西,就是人的哀恸这种矛盾心理(ambivalence)。可是,随着本文的展开,我意外地发现,弗洛伊德应该作为一位灾难思想家。在这样一个在无能、谎言、虚假胜利的压力之下变得麻木的世界,弗洛伊德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当前事件背后的真相,然后(唯有在此基础上)揭示在无意识中上演的内心世界的阴影。

在《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一个不太受注意的段落,弗洛伊德描述了伦理诞生的阵痛时刻。在这个时刻,尚未受文明熏陶的原始人在死亡(尤其是心爱之人的死)面前,感受到各种情感(绝望、愤怒、仇恨、愉悦)的混合。从这些情感之中,诞生了第一条伦理诫命:汝不得杀人:
这条禁令产生于仇恨愿望满足之后,这种仇恨满足潜伏于对心爱者的哀悼后面。后来,这条禁令逐渐扩大其包罗的范围,适用于不为自己所爱的陌生人;最后,乃至适用于敌人。
不过,面对这场正在上演的战争,他指出,把所有人(包括敌人)包罗在一起的做法,还有伴随而来的“道德敏感的倾向”都被我们“文明人”忘记了。
我在向学生教授弗洛伊德时,拿这些话来证明,在关键时刻,弗洛伊德没有人们想的那样种族主义。不过,这些想法今天还有价值的地方是它隐含的信息。
在今天这个时代,心灵被放逐到生存的边缘,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一信息:只有承认自己心中(即使对心爱之人)的矛盾心理,我们才有一丝机会拥抱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眼中的敌人。
比如说中国,这个西方世界宣称敌对的国家;比如说黑人,他们在大街上被杀害;比如说别的国家的公民,他们在COVID-19疫苗的竞赛中领先;还有一切受苦的人,不管是因为战争或疫情而受苦,还是因为作为人类而受苦。
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当今这些自恋(主要是男性)的领导人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天性上的某种无能(constitutionally incapable),消除那种到处散播的有针对性的仇恨。1923年,弗洛伊德写信给罗曼·罗兰:
毫无疑问,在中世纪,我所属的种族是要为一切瘟疫负责的。
虽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同理心很难解释,同情也许是自恋的伪装,可是,在《超越快乐原则》的某些段落,我们能发现这样的同理心:
这个外层就是到死也能使一切更深层的东西免遭同样的命运。
即使某一个细胞不得不死亡,这个细胞共同体也能继续生存。
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产生了某种德里达所说的“原初场域”(socius primitive),某种共同生活的新形式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生活形式,它让我们摆脱单一自我的普遍陷阱。
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共同分担时代的痛苦。每个人类主体,不管是什么种族、阶层、等级、性别,都可以参与其中。也许,这正是我们为人人皆可自由死去(free to die their own death)的世界而奋斗的意义。
Reference:
[1]《超越快乐原则》的引文出自 《弗洛伊德著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2]《精神分析引论》的引文出自《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
[3] 一部分通信的引文出自《弗洛伊德传》(商务印书馆,2015年)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读书会第30期 |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 Corona读书会第7期 | 全球公卫中的跨国人道主义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夏季
- Corona读书会第28期 | 大坝与水利政治
- 特朗普人类学(一):手、谎言、#魔法抵抗
- Graeber丨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 黑色海娜:对苯二胺、孔雀与不存在的身体
- Corona读书会第32期 | 松茸的时日
- 编辑手记 | 《末日松茸》: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
- 影视造梦:横店“路人甲”们的生活群像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小丑”
- 哀恸的哲学:“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