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本专题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正如Mauss的《礼物》既是人类学名著,也是他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年鉴派诸友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此书的阅读和讨论皆是其回声。本专题通过编译、介绍这位学者/活动家来继续他的思考和实践。
本篇是格雷伯于2014年发表在Hau上的论文。本文首先讨论了在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职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的兴起以及这一阶层如何与大学院校相互形塑;接着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失败之处,尤其批判了(表演式)反身性思考的泛滥;最后指出一种“预兆式人类学”或许能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信与愉悦。虽然这篇文章主要与美国学界对话,但其观点意义深远。除了有关于金融化、阶层认同等学术概念的新颖分析,格雷伯的主张也激发我们最切身的感受与思考:如何面对学界的焦虑氛围和虚伪风气?怎样才能过上一种真诚、愉快、有价值的生活?
原文标题/ Anthrop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原文链接/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full/10.14318/hau4.3.007#hau4.3.007_fn1
译者/ 文彦
编校/ 叶葳
摘要: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大多数变化——尤其是1980年代的“后现代转向”——只有被置于大学院系存于其中的、关于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的更广泛变化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尤其是要考虑到大学在职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再生产中的角色,这一阶层最终取代了所谓主流“左翼”政党里的一切工人阶级元素。反身性(reflexivity)以及我称为的“庸俗福柯主义”(vulgar Foucauldianism),虽然装扮成行动主义(activism),但似乎反而代表了此阶层的一切意识。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政治以在学术领域结合对社会运动的支持和预兆式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
本文初步反思了当代大学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语境以及人类学在其中的立场。我将聚焦于芭芭拉和约翰·艾伦瑞克(1979)首先提出的“职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1]。作为工人阶级父母的孩子,我可以谈论很多学术圈里的阶级结构再生产,但我决定不再依赖我自己的经验(下文中可以看出理由)。相反,我将对人类学家所谈论的议题、甚至是他们不谈论的,提出具有更广泛意义的观点;以及我们的实践如何再生产了不平等的结构,哪怕我们声称是要挑战它;最后,我会展现至少是出路的微光。
以下是我的基本前提(我知道它在很多方面和艾伦瑞克们的有很大出入)。
我认为,1970年代以来,社会见证的不仅是资本的金融化,还有与之相伴的职业管理阶层的形式的改变;这一阶层由此逐渐取代了作为所谓“左翼”政党主要支持者的工人阶级组织。最后,像是克林顿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ts”)或布莱尔的“新工党”(”New Labour”)变成了公共和私营官僚(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crats)的政党,且日益企业化。(的确,在这个时期,公共和私人官僚机构越来越难区分。)这里不适合详细地提出社会经济论据,但是基本上,我从诸如Lazonick (1988, 2009, 2012) 或 Duménil & Levy (2004, 2011)等学者那里得到了灵感,他们提出:真正标志着所谓“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时代(或新自由主义)的开端,是大型企业结构内部的阶级联盟(class alliances)的转变。简单说,自从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在19世纪末的美国和德国兴起,这些企业的“技术专家体制”(technostructure)——J. K. Galbraith (1967)的著名用法——包括他们自己的官僚机构,已经开始主要关注内部。哪怕是香水或电子公司的高层主管,也普遍只对生产更多更好的香水或电子产品感兴趣。同时,终身雇佣制的保障让员工容易对公司产生认同。结果,工人和管理者都倾向于将金融家与金融利益视为局外人、甚至闯入者。[2]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一切都变了,高层们基本上改变了效忠对象,转而与金融阶层(financial classes)结盟。臭名昭著的合并和收购潮、资产剥离等等,在当时被广为讨论;而无论是放弃了以前关于终身雇用的保证,还是用股票期权支付高管和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是他们转变效忠对象的表现。它实际上走得更深远。在这一时期,金融精英和企业官僚基本上合并了:两个阶级开始“联姻”;他们在不同部门间来回变换职业;他们开始讲相同的语言,分享相同的品位,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这首先在北大西洋国家造成了深刻的文化影响,然后是所有的富裕国家。这里,我单说两点。第一,在我看来,标志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涉及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官僚化 (Fisher 2009; Hibou 2012; Graeber forthcoming)——在这种官僚主义中越来越难区分哪些是公共的、哪些是私人的——其源头确实要追溯到这一时期。第二,新的金融-官僚阶层(financial-bureaucratic class )的政治统治地位,因吸纳了大量的中产阶级而得到巩固(又是专业工作者和管理者:基本上,就是鼓励他们用投资者的视角看待世界)。(想一想,在198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美国报纸都摆脱了它们的劳工记者——他们真的曾经存在过!——电视新闻报道开始在屏幕最下方滚动最新的股票行情,搞得像所有人都会感兴趣。)

以上只是一个复杂论证的极简版,我只是想先做个铺垫。重要的是,这些发展给学术界造成极为特殊的困境。一方面,1960年代校园已是实际的社会运动焦点(甚至是革命运动焦点),现在被大幅去政治化了。另一方面,这些运动的大多数语言和情感被保留了下来,尽管这个时期大学成为某一阶层再生产的场所, 这一阶层的上层不再只是权力的辅助,而至少非常接近某一类统治阶级;其中层甚至也对其非常认同。
要理解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还要理解“金融化”现象的其他信息。我指的不是新金融官僚阶层的构成或政治联盟,而是其财富的实际基础。“金融化”的特点常被呈现为“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甚至在其最严厉的批评家看来也是如此:它从无到有地变出价值;是一个脱节于“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或者(如果习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实际阶级关系(actual class relations)的抽象游戏。但这绝不属实。实际上,金融化,(用粗糙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标志着剩余价值榨取的重心从工资和商品转为各种形式的收租(rent taking),也就是,直接抽取(direct extraction),通过半封建的关系(semifeudal relations of extraction)抽取——在这种关系中,金融利益与国家权力(委婉地说,“政策”)紧密合作,为大量负债创造了条件。在率先采用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美国,大学的确发挥了关键作用——仅次于房地产业——其方式是有意促成大量学生贷款,政府则扮演负责征收的惩罚性角色。因此,在抵押贷款、助学贷款、信用卡和银行费用与罚款之下,如今一个美国典型家庭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收入——具体数字很难获取——都被FIRE产业(金融finance,保险insurance,房地产real estate)直接挪走。而我们讨论此话题的语言极具迷惑性。我们其实从没见过金融行业被“放任自流”(deregulation),这个行业受到严格监管。只是大部分监管银行的法规是由银行自己制定的,通过被称为“游说”(“lobbying”)和“竞选筹资”( “campaign finance”)的合法贿赂制度。结果是,国家在使企业获利方面,其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不再仅仅通过保护基础架构(infrastructure)和产权关系来对工资进行间接抽取(indirect extraction);国家的强制机构——立法系统、法院、法警、监狱和警察的威慑力——在抽取中起到了直接作用。尽管在美国,很少会有人真的因为债务被关起来,但这个机器在此过程的方方面面生效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召入(大致上可以称为)“警卫劳动”(”guard labor”)中——保安、管理员、催债人等参与监视或监管其他劳工的工种——这是此过程的固有部分 (Jayadev and Bowles 2006; for the argument in general, see Graeber 2013)。
所有这一切也对大多数人想象自己的阶级立场造成深远影响。也许有人会说:中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向上推,以认同金融产业的远景;但金融化实际的操作是将人往下拉,让很多人越来越难以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
新自由主义始于1980年代对劳工政治地位的打击——英国矿工罢工、美国的PATCO(港务局交通公司高速线)罢工、日本铁路罢工的爆发——接着是主流政党里工人阶级的任何影响都被清洗。与之相伴的是这样的想法:公众的房屋拥有权、消费者信用卡的准入、401(k)退休福利计划等等,将让大部分人不再自我认同为工人阶级,而是中产阶级。但是,我想这里有一个陷阱。“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分类;它具有更多社会和政治意涵。成为中产阶级,首先是你觉得身边的社会基础机构——不论是警察、学校、社会服务,还是金融机构——最终是为了你的利益而存在。规则是为了像你这样的人而存在,如果正确遵守游戏规则,你理应预测到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可以策划职业生涯(甚至是为他们的孩子),他们觉得可以及时往前规划自己,预设这套规则会永远保持一致,社会的基石就在自己脚下。(很明显,上层阶级并非如此,他们认为自己存在于历史之中,而历史永远在变化;对穷人来说这也不是真的,他们很少能真正控制人生境遇。)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是,如果你在晚上在街头看见警察,因此更有安全感,而不是相反,你可能就是中产阶级。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大多数的——比如说在巴基斯坦或尼日利亚,大多数人觉得自己不是中产阶级,而大多数美国人,传统上,会认为自己是。但金融化一个吊诡的结果是,它造成了反转。最近有一个调查显示,史上第一次,大部分美国人觉得自己不再是中产阶级。其实不难看出为什么。如果你面临被扫地出门,只因为拿着一份非法机签的止赎合约(robo-signing foreclosure)——政府拒绝为此起诉,但全副武装的政府探员愿意大驾光临把你赶出家门——届时,你的收入水平已经不再重要。你不再会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成千上万的人此时正陷入这样或那样类似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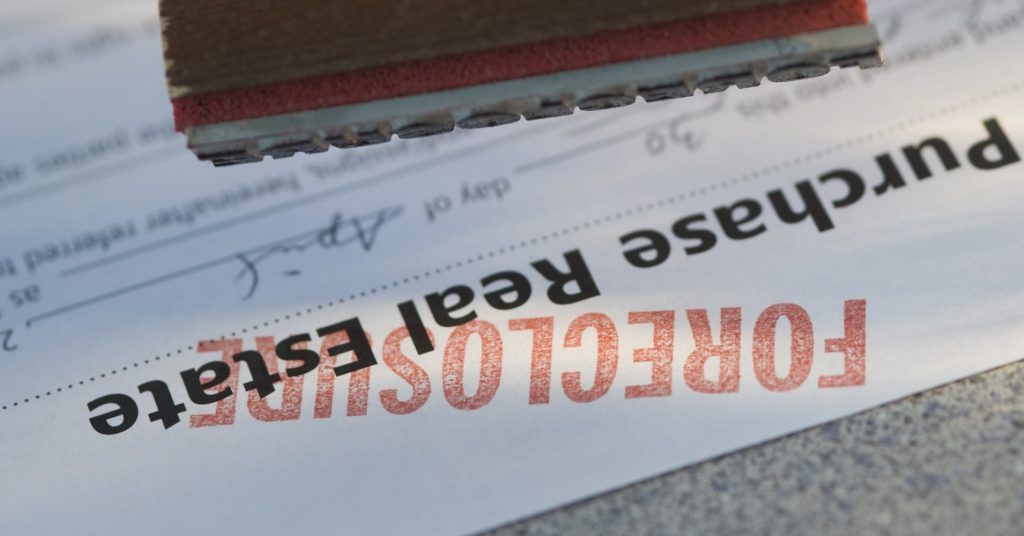
正是不断增长的职业管理阶层(一般居于收入水平的前五分之一),会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并且具有中产阶级的价值和情感。对于这些人来说,规则——无论是不成文的还是明文规定的——就是一切。他们也是工人阶级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正如激进的理论家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在1970年代所指出的,传统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对资本家并没有直接的敌意,因为他们从来不会相遇;大多数情况下,直接的压迫来自经理、主管、官僚,以及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等——而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会给这些人更多而非更少的权力 (Albert and Hahnel 1979; Albert 2003)。讽刺的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决定性胜利,造成了同样的效果。它导致不必要的管理工作和行政职位的持续膨胀——“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以及日常生活无穷无尽的官僚化,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互联网驱动的。这反过来又使得“民主”之类的词的主要概念发生了变化。对形式而非内容、对无数规则和流程的迷恋,让民主的概念变成了一套规则体系、一种宪法章程,而非一个通过社会运动(甚至民意表达)来推动的、迈向自治和自我组织的历史运动。
布莱尔和克林顿的政治是这种事态发展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实用主义左派”(pragmatic left)同时拥抱市场和官僚制,这对那些没有完全融入新的职业管理阶层情感的人来说难以理解,并且确实旨在脱离任何残存的工人阶级成分。同时,凯恩斯主义式阶级妥协的终结,意味着工人阶级组织或个体被拒绝进入这些机构,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成员(或至少在美国和欧洲的白人工人阶级)越来越倾向于认同右翼民粹主义,并完全否认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的价值。
显而易见,这一阶层的情感很大程度上由大学制造出来;反过来,大学也被这一阶层的兴起所塑造,基本上成为了培训各种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的场所,而非一个为了他们自身权益的自治机构。这很值得强调。现在(或者最好说直到最近),大学仍是从中世纪中期多少完整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机构。因此,大学依旧反映了中世纪基本的自我组织和自治概念;它是由学者管理的机构,出于对学术的追求、对本身就具有价值的那类知识的追求。19世纪时,这一点也没有从根本上被改变,当时大学系统与中央集权国家有不稳定的联盟,为公务员提供培训,以换取保留自治的基本原则。很明显,这种自治在很多实操方面都妥协了。但是,那依然作为理想存在。这很重要。它不仅合法化了由非市场价值驱动的生产自治领域的基本概念,还在许多非常实际的方面也起到了作用:例如,自古以来,大学是城市中不受警察直接管辖的空间。
在此意义上,1970年代以来大学的变化是过去八百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根本断裂——各地表现得并不一样,但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正如Gayatri Spivak在占领华尔街时的一次演讲中所评论的,哪怕在20年以前,当说起“大学”,基本上人们指的是教员(faculty);现在,当说起“大学”,人们指的是行政(administration)。大学在众人眼里不再是中世纪的法人(corporations),而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企业(corporations),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成立的官僚机构,尽管现在讨论的“利润”概念更为广泛。它们不再将追求知识和理解本身视为有价值。因此我觉得真的可以说,大学,在它这个词原初的意义上,已经死了。[3]
但是,“大学死了”还伴随着一个奇特的双重运动。学者们要花越来越少的时间做学术,越来越多的时间进行各种管理工作——即使他们的行政自主权已经被剥夺;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国家官僚主义和市场逻辑噩梦般的结合。但同时,几乎所有参与某类自主文化生产、且其传统运作游离在资本主义逻辑之外的人,都开始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有画家、雕刻家、诗人,甚至调查记者。最终,市场化也伴随着公然用暴力排除异见的政策——同样的,是美国在近几年带了头,但是这一模式已被广泛模仿——哪怕对于最轻微的反对迹象,武警都会配备诸如泰瑟枪、胡椒喷雾等酷刑设备,甚至还会部署反恐特警队。
我们或许要问问自己,学术界是如何将这样的事接受为简单、毋庸置疑的现实。仅仅几个月前[4],一场反对伦敦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学生运动卷土重来,迅即受到暴力镇压;我曾亲眼目睹年轻学者的牙齿被打飞、被拳打脚踢、鲜血就洒在参议院前的街上,这就是非暴力静坐得到的回应——接下来的事同样令人愤怒,诸如伦敦大学学生会选举出的主席被禁止参与校园政治活动,就因为校园游行没有征询警方许可——但是大多数所谓“激进”的教师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别说发起什么大规模的抗议了。在2011年末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自由派阶层对暴力镇压的态度是相似的冷漠。这种冷漠是有原因的。在普遍的程序主义风气中,人们几乎不可能把被合法授权的行动视作暴力行动,哪怕它包括打飞和平抗议者的牙齿;同样的,任何法外程序都很难反转为其他行动,哪怕其行动并没有伤害任何人。结果就是,我们社会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甚至影响了那些自认为是甘地的人的情感——实际上,很可能有人会说,主要就是影响甘地们。
我不想说得太悲观。考虑到镇压水平和这种冷漠,那些学生运动的出现就已经鼓舞人心。这种运动比我们想象中更能决定未来的方向。毕竟,有太多理由相信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经济模式——已经陷入终极绝境。面对2008年经济崩溃的影响以及正统市场理论随之失去合法性,英国精英的首要政治举措之一,是全方位打击大学系统的自主权,要求其更彻底地向市场逻辑屈服;这一事实显示出,这一政治阶级至少明确意识到潜在的意识形态威胁可能来自哪里。无疑这会花点时间,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尤其重视要赢得意识形态博弈——可以说是以损害资本主义自身的长期经济活力为代价[5]——但是很清楚,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另类社会价值的守卫者,这让它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扮演了有独特潜力的角色。
最后的这些话是有意为之。在我看来,资本主义这一最后的、金融化的阶段是其终结阶段。资本主义唯一真正赢了的是意识形态之争。该系统似乎已经奄奄一息,从任何标准来看都在迅速通往死胡同:无论是在增长、可持续性、技术发展,还是政治想象力方面,这还没算上生态灭绝的可能。你可能会说“资本主义”一词具有欺骗性——就像许多不然会被视为资本主义拥趸的人类学家习惯做的那样(例如Chris Gregory在本卷所描述的文化经济学家们);或如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学者,他们更喜欢谈论,在由多元的、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所组织成的世界经济中,资本的统治作用。关于后者的立场有很多值得讨论的。但在目前的历史关头,因为其论点而默认现有系统将长存不朽,是不明智的。至少对我而言,这不太是关于资本主义(至少是以历史所认可的形式)是否还能持续50年的问题,而是关于接下来会不会变得更糟的问题。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再把关于什么是更好可能性的思考都视为禁忌了。
人类学和1980年代批判的失败之处Anthropology and the Failure of the 1980s Critique
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头二十年里,这个词几乎从未在学院里被使用;新的制度只因被当作是令人晕眩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新时代的到来而被讨论——回想起来,当时只有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话语和精神在媒体上被精确呈现。几乎当时所有新兴的理论焦点(身份、创意消费、流动和景观等等)其实都是某种新自由主义宇宙观的缩影。[6] 更有甚者,后结构主义理论——尤其在(主宰了许多看似相左的学科的)所谓“庸俗福柯主义”之中被奉为神明——将职业管理阶层的独特阶级经验作为普遍真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网络和编造网络的世界(a world of networks and networking),身处其中,权力的博弈创造了社会现实,所有的真理主张都仅仅是战略,而武力胁迫机制似乎无关紧要(即使它们越来越无所不在),因为所有真正的行动都被假定为是发生在自我规训技术、展演形式、以及无数分散的去中心的作用力中。要描述学术生活、或者一般的职业生活,这种描述还算准确。但这不是、也从来不曾是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它没有被当作一种阶级经验,而被当作一个普遍真理(实际上是唯一的普遍真理,因为其他真理都被否定了),这确实表明,忽略旧有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多么错误的趋势。[7]
那么,人类学和这些都有什么关系呢?在1980年代,它起先的确朝着与大多数学科相反的方向发展,当时“后现代主义”徘徊在(往坏了说是)无用、虚假的激进主义和一种自以为是的、激烈去政治化的世纪末的绝望之中。在美国人类学,“后现代主义”这个词真正起了作用,但绝非去政治化。反身性思考的倡导者(exponents of the reflexive moment)提议在各个层面上剖析和挑战人类学实践的政治含义,甚至不排除抛弃整个人类学事业的可能性,因为它已因其殖民主义帮手的历史而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教学,后现代的挑战改变了人类学。所有的导论或学科史课程,都必须对人类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仪式性的谴责,上溯维多利亚时期,下至至少1950年代(甚至更近)。这恰好掉进了激进主义的陷阱。这个学科的存在本身被质疑。但是那些批判从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激进。首先,它最主要的实际效果之一是削弱了人类学的政治潜力(因为人类学能够传达社会可能性),它给了任何人类学门外汉——那些被人类学所记录的关于政治、经济或家庭生活的无穷多样性吓退的人——两三行方便的标语,让他们认为,所有形式的人类学知识,从根本上来看都是非法的。这对不想承认自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人来说无疑是很方便的,也不用让自己陷入学习非欧洲世界观的麻烦。但是此刻,它对人类学家参与关于人类可能性的全球对话的能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尤其,(也许有人会这么说),此刻正是我们最被需要的时刻。
其次,这种形式的批判主要针对殖民主义及其遗产,而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针对那些不与殖民主义直接相关的统治的经济结构、企业和金融权力、官僚制和国家压迫结构。请记住,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南方国家施加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时期,但如果阅读写于当时的许多“激进”人类学作品,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有人也许会反对说,重述学科与殖民主义纠缠的历史,难道不是至少让现在的人类学家比1960年代那些相对自满的人类学家更能觉察到这种危险吗?实际上,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2001年和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中重新出现了彻头彻尾的殖民拓张,并且人类学家也被招募参加,但美国人类学学会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无法达到自己在1960年代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水平,也没能明确声明反对与军队或中央情报局进行人类学合作 (Zehfuss 2012)。[8]
因此,我觉得可以说,哪怕按照它自己的判断标准,后现代时刻(postmodern moment)也被证明是一场彻底的、巨大的政治失败。仪式性地谴责人类学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事业,其最终效果仿佛就是要说服其从业者,人类学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了。实际上,我要更进一步分析。在更深层次上,我认为这些自我谴责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微妙的占有;毕竟,将积累的知识看作是从根本上被污染的、当成你自己的肮脏的小秘密,仍然是将其视为你自己的肮脏的小秘密。再加上,拒绝“高理论”(high theory)(认为它多少内在是帝国主义的),这成了学科自我封闭的完美姿态,所有派系都对抓紧一小块知识领域(通常从地理上定义)最感兴趣,以此为基础来发展自己越来越行政导向的职业生涯。[9] 与此同时,这一语境中产生的反身冲动(reflexive impulse)只会成为一种布尔乔亚式的自我文学建构;这至少与当时开始的该学科的过度职业化是相连续的。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反身性(refexivity)的一些关键工作,尤其是以贝弗利·斯凯格(Beverley Skeggs,2002)为代表的女权主义传统,她本人借鉴了玛丽莲·斯特拉瑟(Marilyn Strathern,1987,1991)关于反身性作为一种展演形式(reflexivity as a form of performance)的观察。我认为斯凯格切中要害。众所周知,自我道德叙事的忏悔模式有着悠久的基督教历史,但她指出,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讲述自己故事的整个传统沿着阶级界线分叉。
正如社会历史学家早已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背景的人很少写自传。用文学技巧自我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精英们玩的游戏。这似乎总是如此。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处于“强迫性自述”(“coerced self-narration”)境地,他们不得不讲自己的罪恶、苦难、罪行、救赎和改造,这些都是为了达成管理阶层眼中“值得帮助的穷人”(deserving poor)。精英们自述的故事,最终都是他们自身权力的展现与反思;其他人则被迫讲述自己的苦难和毅力。当人类学家来思考这段历史,很难不立即想到以下两者的差异:(a)随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学院过度职业化而产生的那种反身性展演(performance of reflexivity),以及(b)同时期流行的关于“抵抗”(“resistance”)和“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研究——虽然开始得稍晚一些,但在时间上却有很大重叠。两者几乎是处于不可思议的平行。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2013)最近认为,“苦难的主体”(“suffering subject”)已经取代了野蛮人(savage)成为人类学主要研究对象——这也许夸张了,但一定程度上是事实——并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我认为同样适用于大多数“抵抗”研究):大多数此类叙述尤其欠缺在,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被要求共情的那些感受在生活中是重要的、有价值的。
这一段让我颇为惊讶:
“作为Biehl、Daniel以及其他研究苦难的人类学家的读者,我们认识到共同的人性将我们和受难的他人联系在一起。我们也意识到人类能多么严重地伤害彼此,有时我们会洞察到我们如何与这种伤害共谋。这些教训或许会促成改变,而这很明显是苦难人类学的希望……这样的人类学肯定能为处理我们时代的重大文化问题进行重要工作。”
(ROBBINS 2013: 456)
罗宾斯显然是在尽力展示大度——这并不是批评他(大部分我都同意),但是,在阅读时我仍然不禁要问:“是的,但是‘重要的工作’是给谁的?到底是谁在看这些书?这里的‘我们’是谁?”诚然,有些难得的作品赢得了人类学家以外的读者——比如南希·谢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的《没有哭泣的死亡》(Death without weeping 1992),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布置给学生去读的书,作为专业培训的一部分让他们进入学术或行政职业生涯。(这是有道理的。毕竟,真正经历着惊人苦难和抵抗的人很少需要别人来提醒他们,苦难和抵抗是真实的、是怎么样的。)人们只能问:如果这会“促成改变”,那么我们在谈论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我们期望谁带来这种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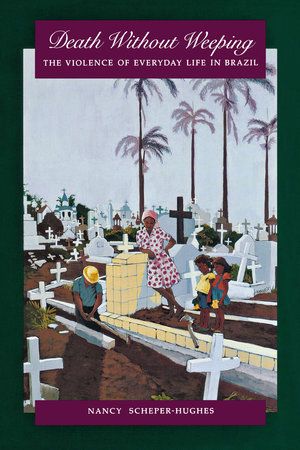
另一方面,通过写作进行自我创造(self-creation)——更不用说那种沉思于自己权力和特权细节的癖好了——是一种典型的产出职业管理精英的阶级环境。假如这种反思是以典型的美国清教形式进行,那也一样,也就是上述精英们去比谁更有道德优越性、比谁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本质缺陷。正如Skeggs(2002)所强调的,这里的真正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10]:一个人是真的在实践反身性(doing reflexivity),不断地重新审视我们研究过程中暗含的权力动态,并将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积极地与我们的共事者互动、并对其负责;还是仅仅表现反身性(being reflexive),来满足过度职业化所要求的自我展演。就像玛丽莲·史翠顿(Marilyn Strathern)定期提醒我们(1991 etc)的那样,以下两者是相互连续的:要求个体不断进行自我反省(individual self-examination);80年代到90年代间,大学里开始的“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中,要求不断进行集体性的自我考评(collective self-assessment )。我想再进一步。我认为反身时刻(reflexive moment)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权威形式的转折点。冒着有点脸谱化的危险,让我速写两个不同的学术权威范式。一方面,我们有父权式的教授,这个人物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占主导地位。他是一个绝对自信(absolute self-assurance)的人物,无论他是学究式的还是顽皮的,他都至少是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使得他的生活之所以能如此的特权和剥削形式,由于制度结构保证了他几乎完美的生活,他得以保持内心平静。这很讽刺,但是,任何在学术界待了很久的人仍然会遇到符合此描述的人,而且至今依然有少数人(如果数量已经急剧减少了的话)这样生活,并且处于权威的位置。不管怎样,这样的人不再被生产出来。毕竟,正是他们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校园动乱里被严重挑战。在新自由主义的大学,这样的挑战——加之自1980年代以来学术生活的剧烈市场化——最终产出了另一种非常不同的权威人物。让我们想象他也是白人男性,因为白人男性仍然最有可能赢得学术竞争,但他并没有父权老教授的自信,而是一方面对自己的特权进行不间断的、令人紧张的自我反省,另一方面决心以各种方式利用自己的所有优势——包括上述特权,好在日益不稳定的学术环境中获胜;这种学术环境要求不断的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营销。不难看出来,在人类学中(长期作为不切实际的和古怪的人们所偏爱的庇护所),反身性时刻为这种畸形人物的诞生提供了土壤。[11]
预兆式人类学 Prefigurative Anthropology
有人可能会辩称,出现这样的人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的学院也发生了其他变化:不管是学生出身、资金、学术界外工作机会、学术劳动的临时工化,还是学术出版的组织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即使现在有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或埃文思-普里查德那样的著作,他们也永远找不到一家出版商(或许在学院外还有可能)。
我不想在这里赘述这些。但我确实觉得至少有必要指出来,因为我们倾向于把理论写得像是在某种自主泡沫中被调和而成的。实际上,人类学里几乎所有主要的理论趋势,都只能在那个它们自己倾向于抹除的语境中理解。我已经举了我称之为“庸俗福柯主义”的例子,它将职业管理工作中的主体经验,发展为人类社会普遍原则的基础,同时还否认了资本主义或直接身体暴力威胁的核心重要性——而当时直接的身体暴力威胁正成为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方式。但是,相同的抹杀行为,也可以在那些高声号称与之相对立的方法里被观察到。比如说,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学者,坚称他们正在“做的事”是挖掘那些被理论家们简单假定为是“社会的”(“the social”)联系。但是实际上,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做的是将政治——不仅是政治而且是学术政治——翻译为现实的构成原则(the very constitutive principle of reality)。或想想“本体论转向”,它使得人们甚至无法讨论哲学家过去所说的本体论一词,正如曾经的相对主义人类学也使得人们无法讨论哲学家过去所说的人类学。
如何突围而出?如果问题在于,在特定的制度语境下专门和特定类型的人讨论,会不可避免地再生产这类人和语境的情感和思维习惯(而且是以抽象和假设的形式),那么很明显,要换个语境换个人讨论——而且不能以田野工作的封闭形式,因为其意义只能在别的地方体现。我自己的方法是参与社会运动。这经常被误解。我发现自己经常被批评为“愤怒”的人:坚持要求其他人类学家走出象牙塔、都成为社会运动者,而甚至无法认识到知识和理解本身的价值。实际上我所相信的恰恰相反。诚然,我是认为那些智识上认可社会运动的学者,至少应该注意到几条街外的学生正因为参与社会运动而被打掉牙齿,但是实际上,我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就是所有以学术为职业的人都号称自己是活动家。
也许我从激进的社会运动中——尤其是那些从无政府主义、反独裁传统和激进女权主义中生成的运动——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是预兆(prefiguration)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点——你可以在1900年左右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呼吁“从旧的躯壳中建立新的社会”(“build a new society in the shell of the old”)中看到这一点——但它在古典先锋主义的崩溃中获得了新的力量:斯多葛式的、毫无幽默感的革命观念遭到广泛抗拒——那种革命者的纯粹性的判断标准是,多大程度上能因献身事业而放弃所有享乐;这被视为是理性的、有计划的对权力的追求。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样的人物永远无法制定出任何人真的想生存其中的社会秩序。相反,预兆式政治意味着,尽可能使一个人的手段与一个人的目的相同,创建出的社会关系和决策过程要尽可能接近于我们想要的那种社会里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陈述过的,这是一种反抗的坚持(defiant insistence),坚持要表现得像是已经获得自由(Graeber 2004, 2013)。这种反抗的乌托邦主义(defiant utopianism)——以及拒绝由职业管理精英和他们的程序主义伦理所主导的制度结构运作——越来越成为民主社会运动的基本原则,不管是在突尼斯、埃及、希腊、西班牙、占领华尔街、加拿大的“不再无作为”(Idle No More),还是近期在土耳其、波斯尼亚或巴西爆发的运动。实际上,它无处不在。这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民主运动意味着什么”在观念上的真实转变。

将这种预兆式原则应用于学术实践意味着什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知识和理解的热情要让步于社会运动的战略命令。它反而会挑战现有的观点,即两者(学术与运动)终究是分裂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2010年的运动中,每一次学生占领运动都会先宣言,教育不是一种经济产品,而是价值本身。但这也不只是一种政治产物。对我而言,预兆式的方法主要意味着,放弃过度职业化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那种紧张兮兮的防备;以及向我们自己承认,引导我们来到这一工作的主要是一种乐趣,和观念们打交道本身就是愉悦的;以及,在职业化过程中我们被默认接受的那个交易——我们必须仪式性地牺牲学术生活中所有最能让我们快乐的事,来换取获得一点点生活保障的机会——其本身是暴力且不必要的。回想起来,很难不注意那个轻松自信的父权老教授的吸引力(而且这是一个非精英阶层背景的人的看法,他本人任何情况下都没机会成为那种老教授)。毕竟,归根结底,权利和特权的问题,不在于有人拥有了它,而在于其他人无法拥有。任何人类学家,只要直接经历过一个哪怕只是勉强够得上平等的社会,都能证明:一般而言,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不是表现得像我们所以为的工人或农民那样,而是表现得像贵族。你可以管这个叫思想实践里的乌托邦时刻(the utopian moment in intellectual practice)。但不管你叫它什么,对我来说,任何真正有效的改革实践中都必须含有自信和愉悦的感受,并且要能通向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自信和愉悦的新世界。
译注:原文中的class在本篇中多被翻译为“阶层”,如核心概念“职业管理阶层”等。但是在一些固定用法中保留了“阶级”的翻译,如“中产阶级”等;另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相关,如“统治阶级”等。
尾注:
[1] Michael Albert和Robin Hahnel (1979),在同一卷中,提议另一术语“协调阶层”(coordinator class),Albert已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使用该词,但其实是艾伦瑞克(Enrenreich)的使用让其流行。鉴于我会聚焦于大学,我曾想结合教授和行政人员,称其为“professional-administrative classes”,但最后决定还是不创造新的用法了。不管怎样,我对这个术语的用法是特殊的:我并没有完全采用这些作者的用法,而是将其作为某种阶级构成过程里的替代性术语,这一过程始于企业官僚(corporate bureaucracies)下层和职业管理阶层上层的情感(sensibilities)趋同化,本书出版时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全面展开。我会在一本关于官僚制的新书中描述这个过程及其更宏观的含义。
[2] 这无疑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理想型:工人和管理者的利益在终极上相同,就像Keynes (1936: 345)所说的“房贷者的安乐死”。不能对它浪漫化。它或许是塑造战后福利国家的条件,但是其最极端的历史表现是法西斯主义。
[3] Ginsburg (2011)有对此现象的敏锐观察,尽管可能是保守的。关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化,Schmidt (2001)的文章是最好的评论。
[4] 本论文基于2014年1月的演讲;该事件发生于2013年10月。
[5] 我在别处有更为详细的论证:相对简短的是Graeber (2013)。
[6] 更详细的讨论见Current Anthropology special issue “The new keywords” with articles by Leve, Gershon, Rockefeller, and myself: Current Anthropology 52 (4) (August 2011).
[7] Fred Pfeil (1990)首先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例子,包括我所说的“庸俗福柯主义”,是职业管理阶层的阶层情感(class sensibility);但是在1/4个世纪之后,他认为这使该阶层发起了反对资本主义霸权的全面挑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究竟怎么样。
[8] 他们最终在2007年时这样做了,在美国第一次入侵阿富汗的六年之后。相反,美国心理学学会当时立即禁止成员与军队或智囊合作。
[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激进主义”被重新定义为降低自己的野心,因此常常导致人类学沦为类似于区域研究,而这种人类学在历史上恰恰是被如国务院或情报机构的政府部门所鼓励的。
[10] 所有这些似乎都具有讽刺意味,当然在许多方面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思想史往往会冲洗任何历史时期中荒谬的过剩部分,这种过剩的部分很少见诸纸端。马库斯、克利福德、泰勒等人的实际作品,从未像常见的学术挪用那么粗糙。(比如臭名昭著的问题“我怎么能认识他者?”无休止地遍布于研讨会和学生的课间讨论。但据我所知它从未在当时人类学文章中出现过。)但是,作为民族志工作者,我们当然知道这样的行话和标语再重要不过了。与庸俗的福柯主义一样,他们创造了一个智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学科的过度职业化不仅可以避免激怒别人,而且甚至看起来在政治上也有进步。
[11] 很明显,其他学科不是这样发展的,尽管最终会造成类似的影响。
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链接。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读书会第30期 |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