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食粮|马来印尼的三张脸
前段时间做了一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民间故事绘本,在和营销老师讨论营销方向时,他认为直接推故事本身,最好不要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典民间故事”大写出来,因为“很少读者(家长)对‘弱势国家’的文化感兴趣,尤其是传统文化”“毕竟连我们编辑恐怕也说不清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什么样”。于是我成功陷入做书的“困境”:一方面我觉得确实如此,另一方面我觉得不该如此。
巧的是,在此前后我还读了两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主题的书,分别是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儿童文学作品。再加上这本涉及马来、印尼地区文化传统的绘本,我想,可否勾勒出一点这个极近又极远的地区的面貌呢?

《雨》
“自异乡归来的说故事者”
听说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很久了,很不好意思地才开始看第一本黄锦树。黄锦树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赴台湾留学后定居。这自异乡归来的说故事者,“他的故事有大森林的雨声,猿猴的戾叫,犀鸟拍打羽翅的扑扑响”。
开篇的短诗像是古老的预言,昭示了往后会发生的、往后所发生的:“水泥地板返潮,滑溜地/倒映出你的乡愁/像一尾/涸泽之鱼/书页吸饱了水,肿胀/草种子在字里行间发芽”。
15个湿热多雨的短篇,组成了马来半岛深深的胶林;15个回忆中的故事,组成了难以穿越的梦境。这其中还有8篇以“《雨》作品x号”为名,同一个家族的故事在雨林里反复上演,断裂折射,最终失落。那个叫“辛”的男孩见到火一样的老虎,那个叫“辛”的男孩窒息在母亲与邻居浑浊的情欲中,那个叫“辛”的男孩在幼时便去世了又不断被梦见,那个叫“辛”的男孩走过被日军屠杀过的村子,那个叫“辛”的男孩在外公浅褐色的瞳仁深处见到了一尾鱼形舟。密密匝匝湿湿漉漉的雨落在主题作品里,也落在整部作品里,变幻诡秘的故事彼此相连又并不相通。如果把倒数第三篇《后死》的情节挪入雨的主题作品中来似乎也成立——那个叫“辛”的男孩“看到那个你也在看着一个瓶子里头的你看着另一个你看着另一个瓶子里头的你看着那无限缩小的你看着——而耳畔只剩下雨声。这世界所有的雨声。有的梦变成一朵朵云。有的云变成了梦。”
这种南国气息浓郁的文字冲击着我们这些处在某个中心的读者,我们为它的陌生而着迷,但对南洋华裔历史一无所知。我们也试图从中寻找熟悉的线索,忽而联想起聊斋,肉身白骨竟无差异,过去今日终为一体(《归来》一篇恰引用《聊斋志异·白莲教》),忽而联想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里也有浸泡着整个世界的雨水与轮回的家族,铁锈生花的奇迹和冉冉上升的死亡,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于是有人讨论,这本书去掉了地域特性还留下什么。我觉得这种讨论没有必要:它天然生长在那片雨林里,拔除不掉。雨笼罩着他们,也笼罩着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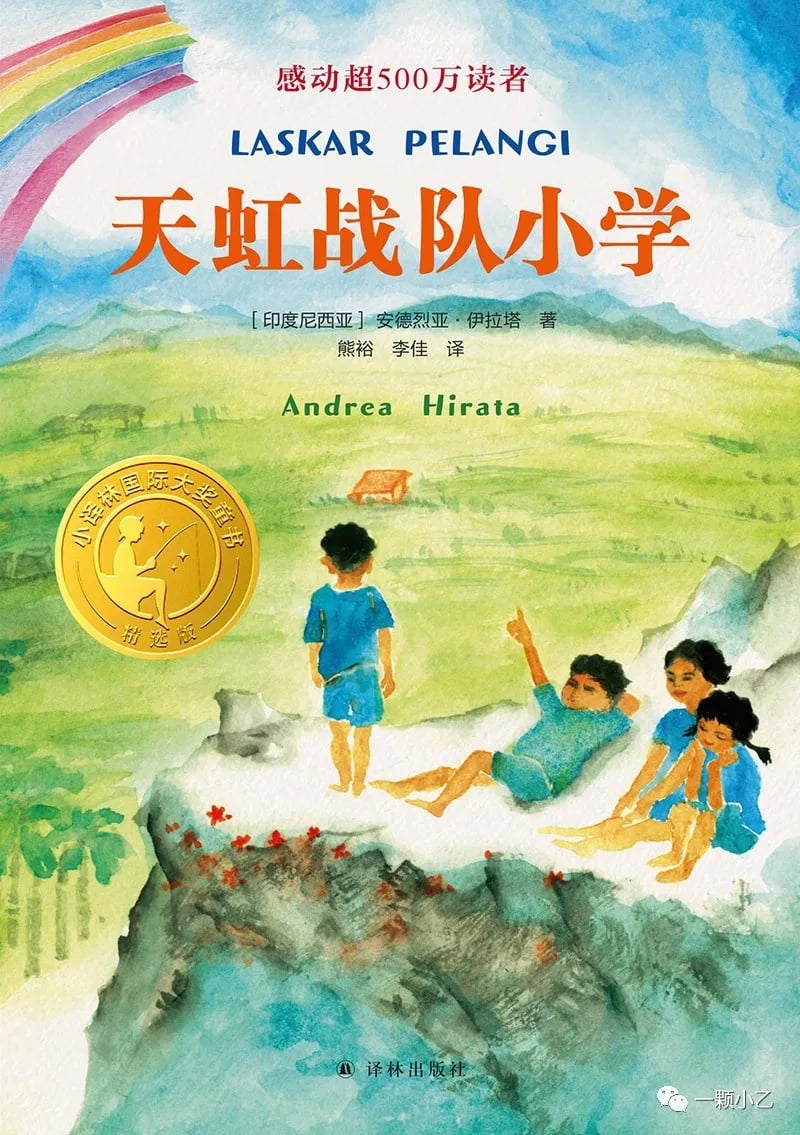
《天虹战队小学》
“保卫一座漏雨的课堂”
本书的封底这样介绍道:“十个来自贫困家庭的‘问题’学生,两位坚守初心的乡村教师,一所破洞比砖瓦还多的学校,这就是‘天虹战队小学’。”正如你所想象的,这是一个印尼乡村小学故事,这里有贫穷但好学的学生,奉献自己的老师。本书灵感来自作者安德烈亚·伊拉塔的亲身经历:他童年的老师婉拒贵族学校聘请,坚持下乡教书。而这部儿童文学作品就是他自幼年起便许愿要送给老师的礼物。
在看之前,我以为这故事略显俗套,却没有意识到它从儿童文学角度让我看见印度尼西亚的面貌。是的,我们听说过,看到过,但从没看见。殖民的历史、贫富差距巨大的阶层、多元民族的汇聚、热带雨林岛国的生活,这一切和孩子们的求学成长过程息息相关。
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印尼的勿里洞岛,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地下埋藏着大量的锡。然而这笔财富却让当地人陷入贫穷乃至危难。勿里洞岛是印尼最先被荷兰人占领的地方之一,“整整七代人都一直处在被剥削的状态”。后来,荷兰人走了,日本人来了,“那些刺刀不离手的士兵简直把咱们的世界变成了地狱”,“我父亲”说道。等到殖民者都走了,印尼政府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接管了岛上的国营锡矿公司。这座公司就是盘踞在岛上的巨型血汗机器,在这里,最高等级由主管人员占据,他们住在带花园的大房子里,而最低等级由“我们的父辈们”组成,他们做搬运管子、筛锡等重活。
勿里洞岛上也汇聚了多元民族。有当地的马来人,他们住在马来群岛,信仰伊斯兰教;有华人,他们大部分是客家人,最早是被荷兰人带到这里来当锡矿劳工的;有萨旺人,他们有深皮肤、窄额头,属于当地极少的澳大利亚人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个岛上不同民族的孩子们组成“天虹战队”(因为他们总是喜欢爬到木羊齿树上看彩虹),由哈凡大叔和穆斯老师带领,保卫着他们漏雨的课堂:一面是难以为继的家庭支持,一面是文教部门官员的检查,最后还有来自国营锡矿公司的收购土地。
尽管我没有介绍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日常,以及他们对现状的反击,但书中的描写其实非常有趣。更让人意难平的是,最后“我们”成功保卫了小学,但人生故事却并没有出现童话式的反转,学校里被称为“天才学生”的林唐在父亲去世后决定退学并成为苦力司机,贫穷困住了大多数人。我也知道,正因为大多数人难以实现梦想,这本书对求知的描写就显得更有意义。

《神圣的香蕉叶》
“蒙娜丽莎芭蕉叶”
有一天我和Y老师聊起带儿歌的童年游戏。我说,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拉起手作拱门状让别人通过,喊着“城门城门几丈高”。他说,小时候流行的是“蒙娜丽莎芭蕉叶”,在念到“蒙娜”“丽莎”和“芭蕉叶”时要做出不同的动作。接着我们都笑出来,城门的童谣显然和南京的建造息息相关,而芭蕉叶这样的特色物种自然也离不开广东的土地。
之所以说到这件事,是因为前段时间做了一本名为《神圣的香蕉叶》的绘本,内容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民间传说。有老师说从书名里感受不到异域特色,我想,是他没有察觉到香蕉叶这一南国元素。在《天虹战队小学》里就有一段描写:(穆斯老师)“用一片香蕉叶当雨伞,在雨中一路小跑,穿过校园,跑一阵就在我们校园北边的那一圈菩提树下停一停”。
说回绘本内容,书中的主角鼠鹿(又名鼷鹿)是一种和野兔差不多大的鹿,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可以见到。有趣的是在《天虹战队小学》里也可以读到,如“我们的祖先用鼷鹿、藤果、槟榔果和树脂在巴洛海湾跟萨旺女人换盐”,又如文教部门的官员质问穆斯老师:“你的这些孩子就跟捕鼷鹿的猎人似的,哪里像学生!”也由此,在马来、印尼地区形成了以鼠鹿为主角的大量民间故事。在故事里,鼠鹿体型小但聪明,经常与猛兽斗智斗勇。鼠鹿狡猾聪明的形象属于民间故事里常见的一类tricker形象,像动物故事中的列那狐、希腊传说中的赫尔墨斯,都是这类典型的骗子,或称恶作剧者。而本书讲述的就是鼠鹿掉进丛林的深洞里,通过编造预言来哄骗其他大型动物,并最终成功逃脱险境的故事。
在印度尼西亚,鼠鹿的故事常常用皮影戏或木偶戏的形式来讲述,这两种形式统称“哇扬戏”。每一场鼠鹿故事哇扬戏里都有很多角色,表演要持续几个小时,讲述鼠鹿捉弄其他动物或被捉弄的故事。同样,在《天虹战队小学》里我也发现了这个词:“(店员)在手肘往下一点的地方紧紧地箍着一个铝手镯,就像哇扬戏中那些粗暴无礼的大个子常戴的一样。”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刚刚了解某一种文化,又立刻在另一处得到佐证。
这本《神圣的香蕉叶》除了故事来自马来、印尼民间传说,插画也既有特色,采用的是印度奥里萨邦的帕达契特拉布画艺术。不过和本篇主题关系不大,就不进一步介绍了。
最后是一个彩蛋。在写作过程中,我忽然发现自己对马来、印尼文化最早的认识来自民歌。小时候家里有一张收录了世界民歌的VCD,父亲经常唱的《美丽的梭罗河》《哎哟妈妈》《星星索》等,都是经典马来、印尼民歌,我甚至也全都会唱。这里面传播度最广的应该是《美丽的梭罗河》,黄秋生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有一种独特的风情,与你分享。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