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第6期Corona读书会 / 2020年3月22日
书单 / https://www.douban.com/note/750963811/
主讲 / 晓宇、叶葳
主持 / 毓坤
书记 / 晓清、契约
编写 / 叶葳、晓宇
导言
在新冠疫情的发展中,动物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
新冠病毒肺炎首先是一种“人畜共患病”(zoonosis),即指病毒会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在科研领域,人畜共患病是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EIDs)防治的重要研究对象。疫情期间,学界和舆论也一直关注相关问题,诸如: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于哪种动物?受到何种人畜关系影响?
另一方面,疫情防控导致人类活动减少、活动范围及影响缩小,动物的活动空间则相应扩增、可见度提升。国内新闻中出现过不少类似报道,如四川国道上发现大熊猫、浙江发现了新物种等;英文社交网络上“Earth is healing”(地球在疗愈)成为流行话语。
新冠疫情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非人类共生关系的契机。

近十年,“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来自地理学的概念在人类学研究中流行起来。“人类世”意指在工业化、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性环境危机(如气候变化等);人类成为影响地球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有必要命名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世”,epoch)。人类学学者讨论人类世,要求正视人类所导致的全球危机,并重新审视人与其他生物或自然环境等的关系。这一思考线索也与近二十年人类学界内兴起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方法相合:多物种民族志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要求理解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其中“人”不仅是被一系列“非人”所包围,更被“非人”所构成。
半年前的这次读书会上,我们从关于人畜共患病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出发,谈到理解人与动物关系的诸多视角、以及病毒概念所带来的种种思考。在开放讨论环节,大家进一步探讨了人类学中的“本体论转向”、民族志写作对“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应等。本篇节选部分讲稿与讨论笔记。
人畜关系与防疫
关注新兴传染病(EIDs)相关研究的学者也一直在进行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反思。比如体质人类学家Muehlenbein (2016) 认为应该通过积极地改变人类行为模式来防患人畜共患病,如确保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不被人类活动影响、改变一些地区的兽肉(bushmeet)饮食习惯等。
但是究竟该如何界定人类和动物的关系是否合理、融洽?又应该怎样积极介入和改变?这些问题指涉复杂的动态过程——人畜关系并不是真空的,对它的认知与评判也始终与各种社会关系、文化背景、政经体系相交织。
在疫情中,“野味”饮食习惯往往被认为是破坏人畜“正常”关系的典型。然而,官方未曾对“野味”下过明确定义,野生和野味的概念在行政上是模糊的。
在“界面文化”对保护生物学学者王放的访谈(2020)中,他尤其谈到所谓“喜食野味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当代迷思。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历史悠久的野味偏好,是直到近几十年来,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及运输网络的成熟,野生动物才被大规模、大范围商用。人类学家詹梅(2005)在一篇有关非典的论文中也写到,西方媒体话语通过区分能吃/不能吃野味而构建出两种身体:吃野味的“中国身体”被描述和想象成是传统的、东方的、异域的,对立于另一种现代的、西方的、普世的身体。在非典疫情后期反复时,曾出现过(不必要地)针对果子狸的大规模扑杀——事实上这正是顺应了这种关于食欲与身体的异域想象,将疫情简单定罪于一种“不文明的”“非现代的”人畜接触。

印度尼西亚关于禽流感的防控也有类似的例子(Lowe 2010)。在印尼,散养家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国际组织认定这就是阻碍禽流感疫情防控的首要障碍。但当他们将防控措施聚焦于对普通农户的教育时,却忽略了鸡肉工业生产中潜在的巨大危险。人类学家Celia Lowe(2010)把印尼禽流感疫情比作“多物种云”(Multispecies Clouds),描述的正是不同生物集中搅和在不确定的变化状态。
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和传播与人畜关系有关,防疫也必须引入动物的视角。医学人类学家Frédéric Keck(2020)区分了两种应对传染病的方法:畜牧式(pastoral)和狩猎式(hunting)。公共健康领域,依赖对潜在威胁的监视和控制,以隔绝的方式保护健康群体,是畜牧思维。生物学家和野保领域,模拟和跟踪病毒在物种间的变异和流动,是狩猎思维。采用狩猎思维的微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往往需要从动物的视角来理解社会,他们反对简单的扑杀防疫的措施,倾向于将相关动物视为共同抗疫的“哨兵”。

作为动物的人
从人类学本体论进入公共健康的讨论,可注意到人和动物之间的相互转换,人可以被当作是动物,动物可能是人,他们都可能是被保护或是被牺牲的对象。以动物的主体性来说,人在吃它时,它是被动的消费品,在传播病毒时它又成了主动的威胁,在消灭病毒时它成了被捕杀或是遗弃的消极对象。
人也可能变为动物或是亚人类(subhumans)。病人,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在这次疫情中面临着被归为亚人而被差异处理的风险。人体作为商品被运输和交换的走私和人口贩卖行业,也常有动物化的语言特征。熟悉的中文语境里,有蛇头(人贩子)和人蛇(偷渡者)。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它们对应的词是coyote(豺狼)和pollos(鸡)。在伊朗,偷渡者则是gosfand(羊)。语言中人的动物化,暗示着人可以被当作动物来流动和处置,人-他人的关系也转变成人-动物的关系。
针对病人和感染物种的措施,不限于防疫和流行病的场合。畜牧式和狩猎式的思维可见于对社会产生威胁或是“污染”的对象,口头上说的害群之马和不洁之物。比如,应对恐怖分子/极端势力/难民流民时,就像政府在防疫时应对疑似感染者一样,同样有隔离和追踪的举措之分:是将他们隔离于“健康人群”之外,还是追踪他们在社会里的行为。
欧洲政府应对民粹运动和政党时,就分为两个政策方向:1)法律手段禁止和政治孤立,2)允许参与议会合作以“去极端化”。在比利时,主流政党达成孤立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的联盟,并通过一系列的反歧视立法限制其活动。在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的议会参与没有被围堵,主流政党通过有限的合作,来软化它反体制的立场。
病毒政治
如今,我们对疫情的理解和管控紧紧围绕“病毒”这一科学概念,“病毒”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涵需要被进一步反思。科学上一般认为病毒是一种“类生物”(quasi-species),没有细胞外增殖的能力;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传统生物科学中难以被分类。Lowe(2010)就谈到H5N1禽流感病毒的不确定性;它具有一种时而可见、时而不可见的“多物种性质”,穿越弥漫于鸟、家禽、猪、猫、狗、人等生物载体上。新冠病毒同样有“时隐时现”的特点。
比如,当美国加州确诊了两例不明原因的新冠患者之后,所有人立即注意到疫情的严重性。这是因为这个确诊传达出的信息是美国本地的社群传染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事实上,是患者的确诊使得病毒可见,因为可见的患者暴露出了不可见的社群传染过程——并且这个不可见的过程正是病毒威力强大、令人恐惧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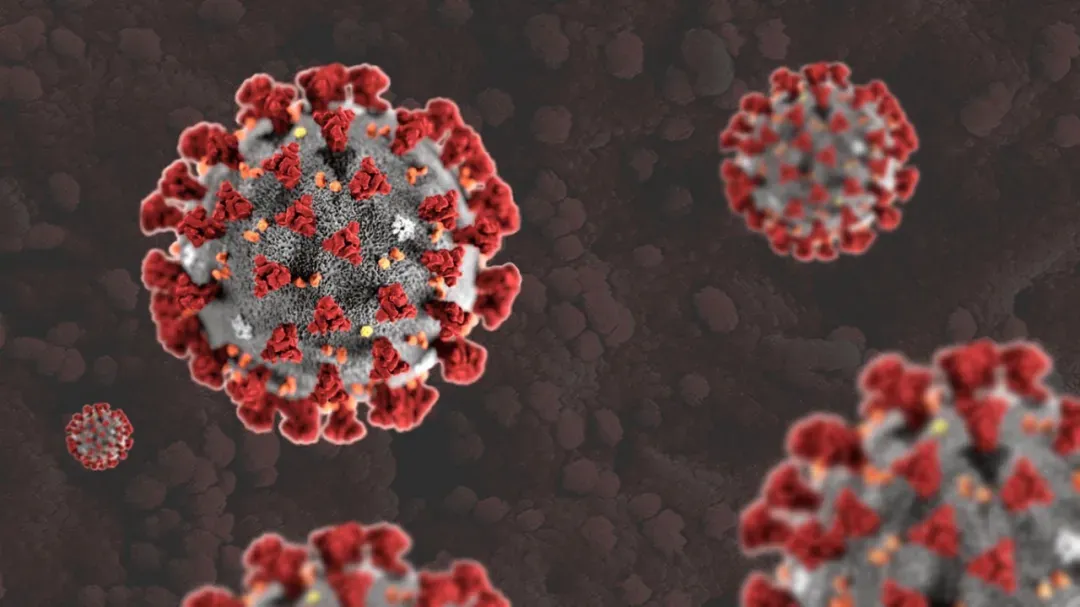
另一方面,病毒本身肉眼不可见,但是它使得我们以往忽略的许多关系和联系得以现形,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真实可见。之前一些时事政治的讨论,似乎往往只关乎远离于我们个体生活的一个地区、一类民族、一种性别,甚至只是一个人、一桩案件、一段剖白。新冠则是这样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它不仅仅关于一个地方、一些人、一段时间,它总是并且必须总是关于所有地方、所有时刻、所有人(和非人)。这是因为,病毒虽然不可见,病毒传播却可能对每处地方、每个人的生活造成实在的影响。人们曾经犹豫的、冷漠的那些“大”和“远”的问题,病毒简单粗暴地把它们推向每个人的面前: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为什么要关心全球变暖?为什么要呼吁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些问题可能不会达成简单的共识,但是在因为病毒而被迫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生活和生存所在的网络与关系清晰地浮现出来,社会里平时不可见的权力运行和结构暴力变得可见。
当下我们似乎看到了大家更积极的思考与发声,这是由“非人”(不可见的病毒)所推动的。甚至,我们作为网络公民在介入或讨论的时候,也与病毒有某种相似性。我们想要尽可能地传达信息、介入行动,但是有时又需要让自己“不可见”——因为一旦“可见”了、肉身化了,就有被消灭、“被”不可见的危险。但我们又不希望自己是完全不存在的、消声的。所以像病毒一样时隐时现,保持流动性、保护幽灵性(spectrality),也许正是当下生活必要的策略与技术,也是未来力量的可能来源。(“幽灵性”参见德里达在Spectres of Marx一书的相关讨论)
病毒及疫情激发了我们恐惧、愤怒、焦虑等等情感,似乎引发了某种公共发言与参与的热情。我们意识到情感本身对于行动和思想的重要性。比如阿甘本在Remnants of Auschwitz中谈到的“羞耻”(shame),是人之所以能够不忘记、不离开,以见证者(witness)的身份存活、发声、行动的基础。
当然,人人主体间的情感与伦理可能对动物无效。Donna Haraway曾引用德里达的演讲《因为我是动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讨论相关问题。德里达提出,只有暴力和杀戮是人与非人生物都能共同理解和感受的。因为我们作为动物,都能感受到痛苦(suffering)。共同的对痛苦的理解和避忌,成为多物种伦理可能的出发点之一。
我们探讨这些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共通共情,不仅是为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成为”(becoming)的可能性,也是为了思考我们对历史与未来的切入,“成为”时间性的连结点。
讨论节选
当代人类学里经常说的本体论转向究竟是什么?
– 这个概念和南美人类学家讨论人和动物之间的转换有关。比如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2014)认为我们在谈论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时,我们想象的是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Culture)里面,但是会不会有可能大家本身的这个“本体”(Ontology)就是不一样的——不把我的存在定义为一个社会人、文化人,而是将之理解为处在一个跟动物非常密切的、能够转换的关系里面。所以针对“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他们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就是说我们可能都处在不同的自然(nature)里面。当然本体论转向不仅讨论人与动物,也讨论包括AI技术、机器人等等。(xiaoyu)
– 在Cannibal Metaphysics(2014)里,Viveiros de Castro还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故事作为说明:殖民时期,当西班牙人抓住原住民,他们讨论的是原住民是否有灵魂,来看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北美原住民在遭遇殖民者时却是相反的思路,他们讨论的是西班牙人是否有身体——所以他们淹死了西班牙人,来看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是不是有一样的身体,还是只是有灵魂?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所谓“本体论转向”的讨论:多元文化主义是说,我们的物质性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对事情的看法不同,社会化的方式不同;但多元自然主义就说我们共享同样的灵魂,我们主体的视角是一样的,但身体不同。(wei)
– 这个新的理论转向并不局限于某些人,除了Viveiros de Castro和Philippe Descola之外,还有STS,尤其女性主义STS如Donna Haraway, Karen Barad等人。除此之外可以追溯到比如像六十年代,符号学家们有大量关于信息论等三论的讨论,也一直在强调如何去人类中心;又如研究环境的学者,也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回应表述/表征危机的问题。究竟如何能把这些彻底的、非人的他者,不只以观看者、书写者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想让ta们自己发声,这就得走向所谓的本体论转向了。2010-12年,是在人类学内部及与其他学科相关议题共同形成了一个讨论场域。如果比较狭义地溯源,会追到像我们说的这个南美传统。本体论转向另一重要理论资源是法国哲学家Quentin Meillassoux的作品After Finitude,切入点是康德和休谟的认识论立场,这是哲学史上经典问题的现代演绎。但对社科取向的研究而言,问题是接下来so what,可以用这个视角看到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另一方面,在人类学内部了,本体论一词并不新鲜。五六十年代就有很多研究用这个词,许多研究也和现在这一转向下的民族志很像。所以即使在学科内部如果光谈学理,即使能做一些区分和推进,但过于陷入内部讨论也没太多意义。回到当下, 本体论视角是否能帮助我们捕捉一些武汉当下的情形?能不能多结合当下的形势进行一些讨论吧?(yukun)
民族志写作如何回应“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要求?“非人”的视角是可能的吗?
– 究竟有没有办法从动物的视角写作民族志?我很怀疑。比如我的研究对象是婴幼儿,但像学步儿童、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患儿等等,我无法对他们进行访谈。究竟如何理解他们的视角?有的做法是让他们画画,再从其中解读意味,但最后还是用成人的视角去解读,很难说真正凸现儿童视角。(linliang)
– 生物符号学和语言人类学的可贵在于强调交流。同一个情景下,我们都面对同样的弗雷格意义上的reference,但每个语言的sense是不一样的。背后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意义问题,在同一context之下,你的视角随着你的语言被决定而被决定。比如Kohn(2013)在How Forests Think描写的当地土著,与动物之间有相当多的交流和默契:比如狗会做梦,似乎还是特殊文化中解梦的传统,但对动物有特殊的敏感性;比如美洲豹有灵魂,可以解读他们在森林中留下的痕迹。Kohn特别强调生命符号学(biosemiotics)作为工具,强调跟自然相关的语言而不是人类中心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好的行为学研究,比如灵长类民族志,也和人类学想达成的深描异曲同工。举个例子,人类学家Bateson有个概念叫meta-communication,此概念的提出并不基于人类社会,而是通过观察一个水獭咬另一个水獭,什么时候是真咬,什么时候是游戏性的假咬。交流的层面之上,起作用的是引导交流的线索,一些行为上的细微差异会暗示这是否是游戏。(yukun)
– 我从文本上没有看到特别令人信服的,text-based本身就很“人”,但我看过一个动物园的案例:把摄像头放到玻璃窗那边用猩猩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看到的就是人们用不同的语言在讨论。除了英语之外你其他都听不懂,但接近于你是一个动物在体会人类的观看。视觉、嗅觉、听觉可以作为切入点。(xiaoyu)
– 如果我们考虑到残障研究中对于模拟残障体验(disability simulation)的批判,我觉得用摄像头和vr再现动物经验的方式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生产性。残障模拟的一种典型方式是黑暗餐厅去模拟盲人的“失明”体验,它呈现的是一个短暂的片段化的体验,且这种体验是个人的、孤立的,抹去了残障人士日常生活中不断经历的结构性的暴力。片段只可以帮我们建立临时脆弱的共情。这种模拟体验可以作为一种证据,但手段本身不是目的。(zihao)
– 在很多场景里,我们已经把其他人、残疾人作为某种“亚人”(subhuman)来看待。一个典型视角可能就是是残疾人群体没有被当做一个完整的人,比如我们要尽量给他们装义肢、做医学矫正,让他们更像一个“正常”人,而不是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其本身的生活状态。所以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议题: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什么是人?(xiaoyu)
– 我们人类学说要站在其他物种的视角理解世界,这是不是一种人类学的自大?我们真的有能力这样做吗?可能只是共情的角度,试图理解ta们,没法说完全站在他们的角度。(maya)
– 人类学家的介入,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能还是人类。比较说服我的一本方法论的书是Decolonizing Extinction(Juno Salazar Parreñas 2018),从婆罗洲的猩猩保护去说,讲到人和猩猩、细菌等不同生物之间共存的实验。她觉得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要从四个尺度去理解:首先是此时此刻的那种亲密性的互动(intimate interaction),这一秒钟的四目相对;其次是“几十年”(decades)有一定的历史维度;第三是“世纪”(century),对“灭绝”(extinction)的理解混杂了殖民时期宗主国对臣民的想象;最后是“人类世”,即数百万年来地质的尺度、地球的角度。我想这种时间尺度上面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帮我们理清该怎么思考任何动物之间的种种关系,每个时间尺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研究。当然这和呈现动物的视角本身没有关系,而更多的还是说回到人和动物如何共生。(zihao)
情感、政治、学术
–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于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我想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武汉,我会写议论性的文章,像现在很多学者写的那样,比如不能把战争作为抗疫隐喻等等。但我如今身在武汉。我发现,作为学者的反思,往往体现在把理性推到前端、冷静地反思当下,让情绪不可见,把情绪隐藏在概念里,变成一种抽象概念讨论的东西。我现在比较批判这样的反思。我觉得一旦把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去除,我们可能就把最有力量、或者那种最基础性的东西也剔除出去了。像江山娇那件事,之后会有很多反思的文章出来,但它上线时后面跟的那种情绪化的留言,比如“我们是你的公民而不是你的粉丝”,它所激起的反思性的东西,应该大于概念化的讨论,要看到情绪化本身的力量。情感研究是现在政治学界很流行的话题,也是对我们所处状态的反思。(xiaoyu)
– 赞同。我也补充一个小故事。前不久和一位同事谈到一则疫情新闻,对方说“you must be excited”,我非常震惊,但是很快意识到是因为那则新闻的内容和我的研究有些联系。但我当时感觉很糟糕。这个可能跟学界的文化有关系。比如大家经常会用“interesting”去评论一个研究,这个“interesting”有时就会变成一种学术活动的系统性冷漠。比如说,你家邻居失踪了你不可能用有趣去评价,但如果一位学者研究印第安女性的失踪率就很有可能会收到interesting这样的评语。interesting,是跟道德和情感没有关系的一种冷静态度,之所以能够冷静,因为它针对的是抽象之后的事物。我们一直在说怎么反思体制、挑战权力关系,其实需要情绪的力量,需要把被抽象之前的情绪和情感重新带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讨论hauntology是有主动的行动的意义(wei)
本期阅读材料
Keck, Frédéric. Introduction. Avian Reservoirs: Virus Hunters and Birdwatchers in Chinese Sentinel Post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0.
Lowe, Celia. “Viral clouds: becoming H5N1 in Indones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 no. 4 (2010): 625-649.
Muehlenbein, Michael P. “Disease and human/animal interaction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5 (2016): 395-416
Zhan, Mei. “Civet cats, fried grasshoppers, and David Beckham’s pajamas: Unruly bodies after SA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7, no. 1 (2005): 31-42.
林子人(采写),保护生物学学者王放:只是禁食野生动物,长远的生态安全就还不乐观,界面文化
其他参考文献
Agamben, Giorgio.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Zone books, 1999.
Derrida, Jacques. Specters of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Derrida, Jacques, and David Wills.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 Critical inquiry 28, no. 2 (2002): 369-418.
Haraway, Donna J. When Species Meet. Vol. 3. U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Keck, Frédéric. “Avian preparedness: simulations of bird diseases and reverse scenarios of extinction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4, no. 2 (2018): 330-347.
Keck, Frédéric, and Christos Lynteris. “Zoonosi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ine Anthropology Theory (2018).
Kohn, Eduardo.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arreñas, Juno Salazar. Decolonizing Extinction: The work of care in orangutan rehabilit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 Cannibal metaphysics. Trans. Peter Skafish. Minneapolis: Univocal (2014)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