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娟 与香港书

在常坛咖啡里,李宇娟一直翻动菜单,最后没有找到自己的心头好,便干脆叫了一杯热水,并自嘲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这个细节,你记得写下来啊」她说。
对上一次见到李宇娟,正好是一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以记者身份前往香港,为接下来的报道做准备,没想到疫情突然爆发,香港随即「封关」。高铁停运后,两地的来往只剩下深圳湾口岸。
接下来便是「港区国安法」、「制裁」、「宣誓」.........2019年至今,这座城市跌入回归23年来以来最激烈的漩涡中。
中港矛盾,是其中一个历久不衰的议题。在香港,当地人习惯将南下的大陆移民称为「新香港人」。目前移民香港的途径不少,除了单程证和优才计划外,内地学生在香港读书、留港工作七年后,可以选择办理香港身份证,成为「新香港人」。
李宇娟是以后一种方式留在了香港。从2014年夏天赴浸会大学入读传理系算起,2021年将是她在香港的第七个年头,这意味着她即将有资格去选择,让自己是否成为一名香港人。
在访谈中,李宇娟不自觉地谈到一点,即她认为香港人是一个悲哀的「民族」,我随即提醒她,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触犯相关法律——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能对香港这个话题保留一些幽默感。
浅浅的深圳河,曾经将两个地区划分成两个世界。
如今,这两个世界的界线日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大湾区」。
一堵「新柏林墙」,在2019年那个夏天悄然筑起。
Part One
小时候父母对我的管教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我不知道跟现在的小朋友比,补习是不是已经成为常态,反正我那时候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要补习,很少娱乐项目,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较惨的那一类吧。
在幼儿园中班到小学二年级这段时间里,我住在一个幼儿园副主任的家里,从周日晚上到第二周星期六早上这段时间,我都会住在那里,实际上在家里的时间只有周六下午和周日的白天。
这个副主任对我很好,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在那里寄养了一段时间后,从三年级开始我的周一到周五开始去另外一个幼儿园老师的家里做功课,周六回家,然后周日再去补习,每周循环如此。
简单来说就是我没有什么娱乐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所在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我爸爸那一代人会信奉「知识就是力量」,不断强迫我去念书学习,从我小时候他就很会跟我的老师打好关系,例如会请老师吃饭、给老师送礼物等等。
因为小时候我就住在老师家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很害怕见到老师,有问题也不敢问老师。在我看来,老师并不是「人」。可能是因为我爸会很关心我的学习情况,经常跟老师有联系,所以如果老师一看到我,他们就会跟我讲分数讲成绩,会跟我说「你做得还不够」。
我记得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负责寄养我的幼儿园老师带着我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刚好碰到了我当时的数学老师,那时候老师怕我饿,还给我买了一个菠萝包。我咬着菠萝包吃,然后数学老师用俯视的眼神(因为小时候长得矮)望着我,跟我说「你(数学成绩)还是不行啊」,让我觉得很害怕。
从此以后,我对老师的害怕进一步加深,直到后来初中和高中的老师,虽然他们还是很关心我,但我会不自觉地跟他们保持距离。
高一的班主任是一位教英语的男老师,我那一届是他第一次带高一班,当时他已经很厉害,教高三的时候已经带出一个英语状元,也是他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抱歉我有点想哭......我是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帮助我认识了自己的性格——他说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我和他的交流也很少。
为什么我会这么感触,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他对我这么好,但我一直没有去探望他。有一次我回到广州,在公园前那个地铁站里遇到他,当时我觉得有个男人一直看着我,但我却跑开了,因为我很怕老师嘛,虽然他对我很好但我还是觉得很害怕。
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直到现在我还依然很想念他。如果他不是跟我说我是外冷内热,我都不会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以前我脾气很暴躁,有一点点不喜欢我就会吵,例如我爸有时候会带我参加一些饭局,我也会「扭计」不给他面子,当面跟他吵。
从小到大我都是以学习为主,没有私人时间,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样的,也不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小时候我不想住在老师家里,但我爸会逼我去补习,逼我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于是我的脾气会很大,但无论我怎么发脾气,我都知道我要听他说的话。有一年的十一黄金周,我不想去补习所以假装肚子痛,一直躲在厕所里不愿意出来,但我爸把我从八楼拖到楼下,然后送我去上课。
我爸从来没有打过我,也会很耐心地跟我讲道理,但他没有办法让我喜欢上学习,所以我对学习一直都很反感,直到上大学才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因为很多人都说只要过了高考,上大学就会变得很轻松。在大学期间,我对学习还是认真的,只是没有百分百认真,而且国贸这个专业也不是我兴趣,所以我也会逃课去实习。

Part Two
我对大学的记忆真的很短,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也不清楚大学是怎么一回事。以前高中的时候我真的会非常认真地读书,老爸说什么就做什么,连选学校填志愿都是他替我安排好的,我甚至不知道国贸是怎样的一个专业,但他说这个专业好,那我就去读咯,读完四年发现原来也就这样而已。
我不知道其他父母对大学有没有研究,反正我爸对这些是非常有研究的,他为了给我铺路,从初中开始每年都会收集那本《高考报考指南》,他也认识很多教育局里的人,很清楚每个志愿的大概情况如何,每年也帮不少人报考学校,所以当时我的分数不够一本线,但广中医又是一本学校,他就决定帮我报广中医。
陆:上大学算不算是你第一次掌握自主权?你可以远离你的家庭,去做一些喜欢的事?
李:我不觉得我自己远离了家庭,因为从小我就住在老师的家里,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远离了家,所以我的性格也相对独立一些。
不过上大学后,我爸对我的管控确实少了一些,有时候他也会让我自己做决定,但也仅限于学习方面,在其他事情上他对我依然管得很细很多,例如经常催我剪指甲,收衣服等等。
陆:你一直在说你爸,但好像没有谈到你妈妈。
李:因为她是听我爸的,她比较像是师奶角色,虽然不是全职家庭主妇,不过平时没有什么主见,基本上都是跟随我爸的意见。
我对大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和记忆,感觉那四年很快就过去了,其实那时候我可以用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例如学车。大二的时候我曾经报过班,当时笔试也考过了,但是到了夏天我觉得太热,学车这件事就半途而废了,浪费了三千多块钱。
但我在想,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高考结束后就应该去报个班考车牌呢?有时候我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抱怨过多。
其实我发现自己越长大,越容易把自己藏起来。最近有个很好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我好像有些事情不想讲,然后我想了想,感觉她说的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还是其他人的故事比较精彩,我会在旁边一直听他们讲。
陆:其实我觉得大家并不是那么想象中的那么没故事。
李:那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没有故事的。大学的时候我的生活很规律,甚至想不起一件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大三的时候做过几份实习,有一次还参加了公司的年会,我才知道原来要负责这么多东西。当时公司年会在琶洲的一家酒店举行,广州区的总经理要上台致辞,我就负责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准备PPT和演讲稿等等,其实跟我现在做的事情差不多。

大学里有一件比较后悔的事情,就是没去看流星雨,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件事,直到最近一两年有人跟我说起我才知道,但我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1]。
另一个是没去看张敬轩的演唱会,虽然说读书的时候没有什么钱,但当时的演唱会门票也就两百多块钱,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买。
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但很小的事,是谭慧英。我记得是有一次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聊天的时候她说到她也在学车,然后我们就一直聊啊聊,她突然说我以后不如去考研或者毕业后做一些事情,具体是什么我不太记得,我就回复她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好,那时候她就看着我,问我是不是有点自卑。
我跟她说:你说对,我确实是有点自卑,但我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想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信心不足的人,以前经常被同学嘲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校园欺凌」,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碰到这种情况。
我一出生就很胖,小时候又长得很男生(男仔头),甚至去女厕的时候,会被阿姨说「你干嘛要进来啊」。那时候还是小学,我留的是短头发,剪一次头发只要5块钱,再加上长得胖,小学同学给我起花名,一开始是叫我「woman pig」,母猪,后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woman pig」的谐音「内分泌」,但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反击。
上了初中,也有一些同学会说一些很伤人自尊心的话,例如「你长得那么奇怪,你不怕以后没有人要你吗」,而且这句话还是我初一入学的第一天,一个男生跟我说的,如果你有看综艺的话,你可能还认识他,这个男生现在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还有一些粉丝。
有一些话,说的人可能是无心的,但对于我这个一直被欺凌的人来说,这些伤害是会累积起来的。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徐佩仪在北京路逛街,不知道为什么跟一个男生四目相投,那个男生当时和他的女朋友一起,我看到他用非常嫌弃的眼神望着我,于是我立马将转移眼神。这件事之后,我都尽量避免跟其他人有眼神交流,避免我的心灵再受创。
大学的时候有个师姐跟我说过,她认为我像是一只刺猬,说我很多时候都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让人接近自己。我觉得她说这话还挺对的,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老师家里,所以自小就很独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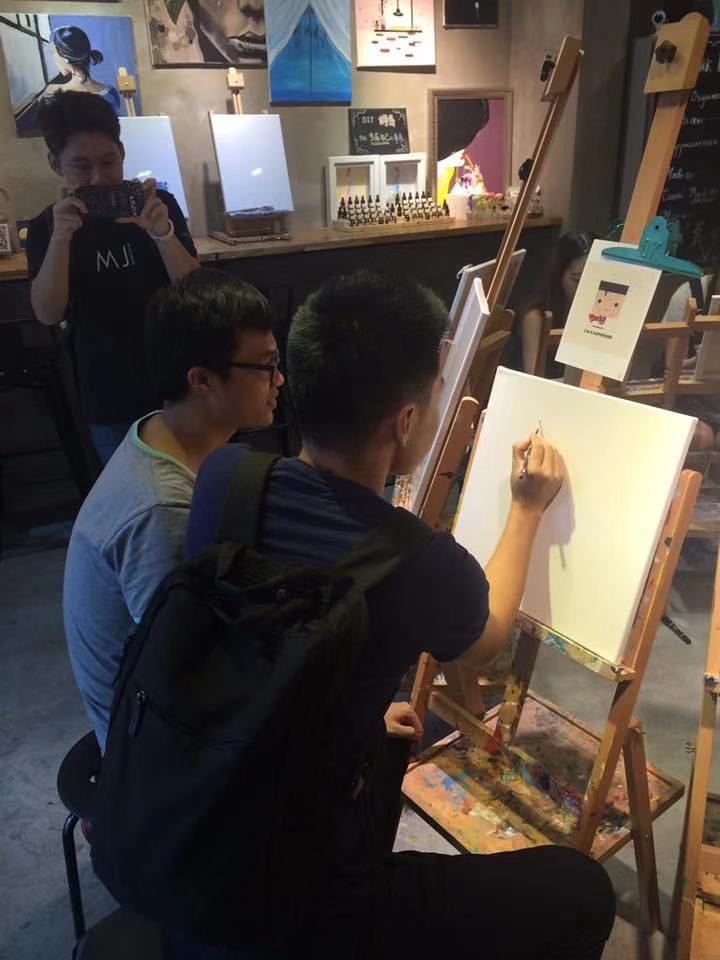
Part Three
陆:必答题,列举三个你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不限性别和学院班级。
李:现在还有联系的,就是你和马文生,还有布茵。欧阳天卉也有一些联系,但她和布茵比较熟。我发现我从小到大跟男生更要好,不是说没有女性朋友,但很多都是随着时间渐行渐远,就是你想联系她,但她已经不想理你了。
在香港念研究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来自广东省的同学,我们当时一起做项目、一起去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爬山,但后来我说不如去哪里哪里的时候,他们就说不去啦,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去,没有叫上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他们不想跟我一起玩,那我也不好意思打扰,这样做太尴尬了。
最近因为我回到广州,有一个跟我同届但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同学突然联系我,说不如见个面,她刚刚生了小孩,然后还跟我讲了很多其他同学的近况,像谁谁谁生小孩了,谁谁谁已经结婚了,但这些事情其实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怎么看朋友圈。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双向的,如果别人不愿意主动跟你分享,那我也没有兴趣主动去了解。
去香港念研究生,也是我爸的决定。从高中开始我就向往到国外念书,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去美国,可能是崇尚外国的自由吧,我也不知道,也有点想逃避家里的管教吧,想离家里远一些。不过我爸觉得应该选一个离家近一些的(香港),他说美国有很多野鸡大学(陆:那你可以选正牌的),对,但是他出钱,所以这事他说了算。
但传理系是我自己选的专业。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这个专业,只是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对这个专业确实感兴趣,然后我在浸会大学的官网上看到其他专业好像没意思,而传理系跟实习内容还挺相关的。
陆:浸大的传理系排名亚洲第一,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你。
李:但这个专业已经没有原来好了,我进去以后发现原来很多同学的英语很差,我们一起做项目的时候我就留意到,他们的英语写得这么差但居然还能考进来,因为我备考前启德的老师跟我说这个学校和专业对英语的要求很高,专业英语要7.5分以上,但我入学后发现有些人只有6.5分也考进来了,所以我入学的时候,这个专业的水平已经降低了很多,学生的素质也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高,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太羡慕。
我有个朋友今年也在浸大传理系毕业,但刚出来也是做一些工资很低的工作,他在TVB写稿,不是做主播,主要负责做一些资料整理的工作,白班夜班轮着来,而且还经常被上司骂,所以我觉得不用去羡慕那张文凭。
在浸大这一年其实是很开心的。很肤浅的说,我是一个很短视的人,在香港,周末不用开车也不用坐很远的车才能去爬山、到海边沙滩,那一年我就像一个游客,到处去打卡,有很多的娱乐活动。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读书结束之后会不会留在香港,就是以游客心态去玩,真的玩得很开心,很自由。家里父母对我的控制也少了,不过如果我一个月都没有回一次家的话,他们就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不过我不可以说我父母怎么样,他们也是很尽责的父母,就是管教上相对严厉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留在香港的原因吧,因为我不想回来被他们管。当初我选择留下来,其实也是想试一下自己可不可以在香港生存,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才是想逃离家庭。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其实也是有惰性的,如果现在这个年纪回广州,一定会被父母催婚,我爸不是那种很唠叨(日哦夜哦)的人,但他总是见缝插针地提起这个话题,最近我回来广州他提得特别多,就是想教育一下我,跟我讲道理。
2015年毕业我开始在香港做公关,但是在乙方公司。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这份工作,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找跟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且我大学的时候实习也是公关,但是在甲方公司里。在乙方里,主要负责写新闻稿啦,翻译啦,还有打电话给记者,后来就不打电话了,发短信就行。
其实我最讨厌就是打电话,感觉就像是做销售,当早上我把新闻稿发到记者的邮箱后,下午开始就要给电话薄上的记者们打电话,差不多每家报纸选一个版面,然后再选一个记者去沟通,提醒他们去看邮箱的新闻稿;隔一两天再打过去,再问问他们有没有看新闻稿,有些可能还是没看,那我会说再给他们发一次,有些如果已经看了,就要问他对这个新闻感不感兴趣。
陆:如果我作为记者,我觉得这套模式还挺烦的,在内地应该行不通(唔work)。
李:这一套模式是我刚入行,一个比我年纪大一点的上司教我的,他经历过上一个年代,所以直接将这一模式套在我身上。在这份工作三年时间里,我不觉得我和某个记者特别熟,工作关系比较简单,如果他不出这个稿件的话那就拜拜,如果他出的话那下次有类似的新闻稿我会继续找他,但从来没有养成私下约出来吃饭的习惯。
头三年的工作经常给记者打电话,我自己都觉得很烦,很惨,如果记者感兴趣的话,那我们会安排采访,我会负责跟受访者,例如总经理、CEO等等做一个简报(Briefing Book),告诉他们这个记者是来自哪家报社、记者是怎样的人,他们大概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还会就这些问题准备一些答案。
我是很讨厌做Briefing Book的,因为要花很长时间做,而且CEO未必有时间去看。再说,如果这些问题我都能回答,那为什么要CEO出来答,让我来做CEO不好吗?这样子太假了。
有一些公司跟我们是签一年或者半年的长合同,我们会承诺每个月都保证出采访出新闻,这种情况就非常麻烦,我们会负责一些科技公司,例如做云端、智能手环、U盘等等,还有一些做开源服务的企业。有些偏B端的企业不会经常有新的东西出来,记者就很难做采访了,但我们合同规定要每个月都有新闻产出,这对我们的要求就真的很高了。
其实香港记者写东西都很浅,就算有本地的科技媒体,他们也不会写得特别深入,科技记者需要写的领域非常多,可能除了C端还要写B端。
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在造假,记者的问题由我来回答,我都知道怎么答的话,那企业CEO还要来干嘛?
陆:在国内,很多企业的CEO都是把采访直接交给公关来处理,他本人可能连看都不会看。
李:这个就取决于CEO自己怎么看了。香港的科技公司比较小型,记者不一定会发他们的新闻,而且如果没有新产品出来,每家报社每个记者来采访问的问题都是重复又重复,真的很无聊。
这一份工作持续三年后我换到第二份工作,一直做到现在,工作内容偏市场营销多一些,主要是负责做社交媒体运营。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我觉得现在不用再去求人,其实也是写一些文章和做社交媒体内容,这些在上一份工作里也有做过。

Part Four
直到最近见回我的研究生同学,我才意识到原来今年是我在香港的第七年。我刚刚也说过,我是一个很短视的人,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想好,到底是继续留在香港,还是要回广州。
这次回来,我爸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一些话,他说我要想想以后,到底要在哪里继续发展。他也说道爸妈年纪大了,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尽照顾父母的责任,现在他也有一些病痛,然后说我不可能在广州买房子然后去上海工作吧,让我想好未来的发展规划。
我自己觉得人是流动的,我不想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上。如果我决定在某个地方发展,然后在那里买房,那是不是要做一辈子楼奴?这样我觉得有点不甘心。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直在香港,但我想试试去外国,美国应该不会了,新加坡或者欧洲吧,但我觉得很难。
陆:虽然香港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没有好到哪里去。
马文生:我同事去新加坡旅游,都说新加坡挺好的。
陆&李:去旅游,和去当地工作,是两回事啦。
陆:我觉得起码你在香港工作,文化体系与内地还比较接近一些,这也是你作为新香港人的一些优势吧。
李:说实话,其实我不想做香港人,因为我想保留内地的身份。我一直不觉得香港有多好,这么多年来,香港好的地方在于买东西很方便,不用扣税,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就是爬山,可以看很多的演唱会,出国也很方便,而且离家稍微远一些,父母的管制也少一些。
陆:你那些来自内地的同学朋友,他们最后怎么选择?
李:他们就是一直熬到了今年,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然后辞了香港的工作,回到内地重新发展。其实我以前做项目认识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回来了。
陆:分享一下你在香港生活这些年的见闻?
李:其实没有太多可以说的,但我有些后悔2014年雨伞[2]没有去看看,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当时有很多人参加游行,但我没有去看看。
陆:香港这些年一直都有很多游行的说。
李:但那一次是有雨伞的,壮观很多。其实那时候我有些置身事外,不太关心这些事,因为在自小以来的教育都没有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这些事情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点像是个外人。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经过弥敦道,那条路上有一些黄色的雨伞,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用绳子把照片挂起来,我当时就去看了一下。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们到底想要抗争些什么东西。
陆:你再继续说下去,我的公众号应该发不出来了,不过你可以继续说(笑)。
李:(笑)我觉得我不是后悔没有参加,而是后悔那时候没有去体验一下,见证一下。跟2019年的修例风波相比,2014年的程度没有那么激烈,那一次雨伞就像是把种子埋了下去,然后经过五年时间爆发出来。
陆:我突然想起那张很经典的图,黎先生说,我的诉求就是想上班(笑)[3]。

李:对,香港人真的很喜欢上班,不管是打工仔还是当老板的。打工仔很害怕上班会迟到,会被老板骂,所以他们不会搞罢工,就算是八号风球也要坚持上班。
陆:有李氏力场[4],不怕啦(笑)。
李:对,还有有李氏力场。坦白说,其实我觉得香港人是一个悲哀的民族。
陆:我把你这句话登出来的话,我的公众号应该会被封,因为香港人并不是一个民族,这话已经触犯港区国安法(笑)。
李:我明白我明白(笑)。很多人觉得日本的职场现状很惨,实际上香港的也一样很惨,工作氛围非常的压抑,幸好我遇到的上司人比较好,我算是那种做事情比较认真的人,也经常加班OT,他们都会叫我下班回家,但工作时间真的很长。正常时间都是八九点才下班,如果能七点下班走人就已经非常开心了,当然我也试过带电脑回家继续加班,但公司其实都不会给我们算加班费。
研究生同学毕业后,有一个去了香港商报做记者,有一个去了甲方企业做公关,有一个继续读书没有工作,现在已经是少奶奶。刚刚还说到一个最近生小孩的,她之前一直在香港某个很小的电视台做主播,回到内地后,她的家公家婆帮她在番禺电视台找了一份工作。
其实去香港念研究生的,99%学生都是内地人,我只有在工作的时候会遇到香港人,但工作认识的始终不是朋友,同事是很难变成朋友的,但也要看是怎样的人。
在香港比较难忘的事情,大概是去看演唱会吧,像张敬轩的;每年也会去一两次旅游(陆:那你在香港的工资应该算不错?)那是因为我没有给家用。其实在香港,多少工资都可以生存下来,像我刚入行的时候,工资水平也不高,但我依然可以熬过去。
陆:之前看新闻说,有线新闻港闻组的记者,一个月工资才一万四港元。
李:真的很低,做传媒和公关其实工资水平是一样的,这个数字放在香港真的很低,我刚入行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但如果是做金融的话能去到三万,做老师即使是刚毕业的也能拿到两万多,我们这个工资在香港是真的低。我们有时候在街上看到有茶餐厅招洗碗工,开的工资跟我们其实没差太多。
陆:你觉得在香港,拿多少工资才能生存下来?
李:看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你可以不去演唱会,可以不去外面吃饭,可以什么都不做,那也能生存下来。其实我们也不会自己做饭,因为上班已经很累,在香港满大街都是餐厅,你完全不需要自己下厨。在内地,我们的文化是过节一定要在家自己做饭,但香港人是喜欢到外面吃团圆饭,像中秋节、春节就要订位。
Part Five
陆:疫情对你们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李:没有太大影响,其实我习惯了独处,和香港的朋友也不会经常见面,偶尔才会见一下吧。
陆: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去爬山?
李:自己一个人爬山有点危险,而且我也很久没有去爬山了。
陆:我以为你会去捕获发哥[5]。
李:我也不是喜欢追发哥的人(笑)。我经常自己去旅行,但旅行的目的地通常是有当地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见一下,没有时间就算了。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是没问题的,但现在想想有些后怕,我自己一个人居然还可以去旅游?如果我在当地被人打劫,或者水土不服怎么办?幸好没有发生什么事。
陆:Facebook有提醒我,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去了一趟香港,当时你还请了我吃饭。
李:对!我记得我们点了三个意粉,但最后都吃不完。当时你还说打算来香港,幸好最后没有来。

陆:国安法出台后,我来香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李: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在香港是挺孤单的。事实上,只要是离开家,自己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都会觉得孤单。但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孤单的感觉,因为我从小就住在老师家里,已经跳过了这个程序。
陆:我在北京做北漂那四年,虽然也认识一些朋友,但始终会觉得,这个城市不是我的家。
李:就是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还在香港?因为我不想被父母管着。我爸问我以后在哪发展,但我不想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如果回到内地的话,我不一定会选广州,可能是上海,之后再看看怎样。但以后可能我会屈服于家里人对我的期望,可能要我回广州照顾他们,甚至也可能假结婚。
陆:谈谈你的感情生活吧。
李: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真的没有。
陆:听说班上某位男同学一直很迷恋你。
李:那也已经是陈年旧事了,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吧。
陆:有没有想补充的地方?
李: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如果要给过去十年做总结的话,我觉得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这样说,但很多时候要做的计划我最后没做到。
我自己一直没有什么目标,以前我爸会给我安排好一切,我会很自觉很认真读书,否则我爸会批评我;去了香港之后就没有人给我安排,也没有人提醒我,我自己也没有自主性。
陆:感觉你所处的家庭有点父权社会。
李:绝对是父权,不是有点,你不知道我爸是那种年龄和性别歧视很严重的人,他会在家里骂我妈煮饭不好吃,但又一定要她煮。我觉得我本身不是很重视家庭观念的人,但我爸会逼我这样做。
陆:过去这一年半里,香港的事对你有没有影响?
李:没有什么影响,不是说我离这些事比较远,而是我一直都比较偏向于支持香港人,我觉得他们这一段时间挺惨的,但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看待吧。
我对那些歧视新香港人的事早就免疫了,我姑妈很早就嫁到香港去,她自己以前也是内地人,但现在也经常歧视内地人,所以对这种冷言冷语,我已经听过非常多了。如果香港人骂内地来的留学生,我觉得就让他们说吧,反正我觉得无所谓,我也不是香港人,我觉得自己一直是中国人。
陆:但你刚刚说到,香港人是一个民族(笑)。
李:我说错了我说错了(笑),可能是因为这两年的事情,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和本土身份的意识。其实有一些内地学生在香港很爱国,他们两边的新闻都看,但偏向于看爱国的。我的大部分研究生同学还是受内地的教育影响比较深,以致于他们接受不了香港的文化,一毕业就离开了。有一些广东省的同学,可能跟香港接触多一些,相对同化一些,接受的程度会高一些。

注释:
[1] 流星雨时间为为2012年10月8日。
[2] 雨伞革命,又称雨伞运动或占领行动,是指于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真普选XXX的公民抗命XXXX运动。(维基百科)
[3] 截图来自有线新闻采访。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市民黎先生表示他的诉求就是上班,成为全民焦点。
[4] 李氏力场(英语:Li's Field/Li's Force Field)是一个广泛于香港流传的恶搞文化,源于香港市民不满热带气旋吹袭香港时,香港天文台没有发出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致大批市民在暴风下仍不能停工、停课。部分市民讽刺天文台和李嘉诚为首的商界官商勾结,以免股市停市和大多数行业停工而使商界利润减少,后来演变为讥讽李嘉诚设立了能阻挡、甚至控制热带气旋的移动路径及速度的「李氏力场」,避免因停工、停市而招致经济损失。(维基百科)
[5] 周润发近年热衷爬山,在香港多条爬山热门路线里,不时有市民遇见发哥爬山,后来网民并将此称之为「野生捕获发哥」。
采访手记:精神香港人对话新香港人
跟李宇娟做这次采访,刷新了这个访谈计划的一些新记录。
她是第一个要求我不做摄影的受访者。按照以往的规矩,我会为每一个受访者拍一辑照片,尽管某些受(luo)访(ying)者(ming)一直认为我拍得不够好看。
她也是第一个要求不作任何核查的受访者。每一次在文章正式发布前,我都会将稿件所有内容交给受访者予以审核,并允许他们对稿件进行修改,不过李宇娟希望不经她审核而直接出稿,原因是她也想知道在我的整理下,这篇稿件会如何呈现她所描述的内容——她只想当一名普通的读者观众。
最重要的是,李宇娟是第一个在访谈过程中流泪的受访者。在谈到她的高中英语老师时,她突然潸然泪下,当时我有些措手不及,急忙找服务员要了一张纸巾。
事后她还问我,她的反应这么大,有没有吓到我。我说当然没有,但很感慨会有这么一些瞬间,让这种对话不仅仅是朋友间的普通交流,而且是深入对方世界的一次碰触。
因为谈话的内容有些过火,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将所有的内容呈现,但你大概能从我们的谈话内容,猜测出我们想要表达些什么。
我一直自认为是精神香港人,即不是香港人却非常热爱香港这个地方。所以在过去这些年里,我时不时就会到香港,去拜访这座以自由、司法独立、尊重人权而闻名的城市,也见证着它如何走向衰落。
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百度百科上,修例风波这一词条的开始时间为2019年6月,但并没有写上结束的时间——这是不是也在暗喻,尽管当下的香港已经再无反对的声音,但这场风波其实并未结束。
非常期待疫情结束后,能有机会再到这座城市,去看看天星码头和序言书室,感受它仅存的温度。
(原标题:《李宇娟 与一个悲哀「民族」共存这七年》)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