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俄羅斯,烏克蘭文學一直以來理解到了什麽

尤伊列姆·布蘭克爾 撰文
柴春芽 翻譯
2月26日,火箭炮彈落如雹,砸向基輔,隨之便是俄羅斯軍隊即將入城。就在戰鬥的間歇裡,烏克蘭頗負盛名的文學批評家,塔瑪拉·妔朵娜娃(Tamara Hundorava),平靜地坐在筆記本電腦前,發表著國際在線演講:關於當代烏克蘭最為經典的世紀末頹廢派詩人和劇作家列霞·尤克拉茵卡(Lesya Ukrainka)。
尤克拉茵卡由於年輕時代寫下的那些愛國散文——每一個烏克蘭的小學生都會讀到——常常讓人輕視她的文學價值。然而,妔朵娜娃卻在講說,其實,尤克拉茵卡本來是一位集劇作家、女性主義者和反殖民主義者於一身的思想家。
結束演講之後,妔朵娜娃嘆了一口氣,接著說:
從未想過,我竟然會通過網絡在基輔對諸位發表演講,也從未 想過,我竟然會在走廊的地板上聽著可怕的爆炸聲入眠,然後又從爆炸聲裡醒來,看著孩子們在防爆掩體下而不是操場上玩耍。但我也被烏克蘭人的勇氣所鼓舞——所有的人,無不懷著必勝的信念和愛,去幫助我們的抵抗戰士。諸位知道嗎,普京發動的這場戰爭,把烏克蘭人塑造成了真正的烏克蘭人。
烏克蘭人經常會談到:我們必須成為烏克蘭人——經過幾個世紀的帝國壓迫之後,通過文化、語言和習俗的固守。但是,烏克蘭人視為一項偉業的這種自我形塑進程,卻被俄羅斯人不當一回事。俄羅斯人認為:烏克蘭成族建國,純屬一個歷史的意外。實際上,在烏拉迪米爾·普京命令坦克發動進攻之前,他就在電視上花了將近一個小時,試圖向俄羅斯人證明,烏克蘭什麽也不是,只是在「我們世襲的土地上」被西方操縱的一台「反俄」機器。
烏克蘭的民族身份之產生,並非一個偶然事件,也不是被西方製造出來的一個概念。幾個世紀以來,烏克蘭人都在極力反抗對他們文化的抹殺。19世紀初葉,俄羅斯的出版商接受的烏克蘭文學,只能是民族誌的、喜劇的和無關政治的作品(嚴肅文學必須得寫成俄文)。而在1863年和1876年,俄羅斯接連頒布法令,嚴厲禁止一切烏克蘭語的作品,與此同時,出版環境也變得一片肅殺。到了1930年代,斯大林處決了整整一代剛剛在十多年前重建了烏克蘭文學-文化的作家,故而,這股生機勃勃的先鋒之潮,遭到了殘忍地狙截。
烏克蘭文學,說起來,也是烏克蘭人面對傲慢的帝國奮而反抗的一幕往事。經常是,為了創造出一種文學生態,烏克蘭作家只能在俄羅斯帝國的禁令之下小心翼翼地寫作。有時候,他們通過俄語寫出作品,來表達烏克蘭人的心懷。有些作家則直接批評俄羅斯帝國主義——他們因此而遭難。另一些作家只是對那些視烏克蘭為草芥的倨傲行為予以簡單的諷刺。
以幽默捍衛烏克蘭身份的作家,最為著名的,便是尼克拉伊·高格爾(他有一個烏克蘭名字:米克拉·豪霍爾)。他因規避自己的身世而以俄羅斯人的身份聞名世界。可能是受到父親的鼓舞——他的父親用母語為烏克蘭中部的外省劇院寫作民間戲劇——高格爾早期的作品(發表在1830年代初葉),充滿了烏克蘭鄉村生活那種喧騰嬉鬧的氣氛和亮麗明快的色彩。但是,他用俄語寫作,面向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讀者。在他最受歡迎的作品裡,有一部,《聖誕前夕》,講的是一群哥薩克人去聖彼得堡拜見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故事。有一個喜劇橋段,人物的對話因為文化和語言的誤解而乖舛可笑,同時也閃爍著政治諷刺的意味:這幫哥薩克人詢問葉卡捷琳娜二世,為什麽要摧毀他們的自治領(這是發生在1775年的真實事件)。但是,就在女沙皇準備予以嚴肅回答的時候,故事情節一跳,重又安全地回歸到喜劇的氣氛當中。很多俄羅斯讀者在這個沖突裡看到的只是哥薩克人玩弄的一個笑話,可是,烏克蘭人一看就明白——這一幕來自哥薩克民間傳說中的場景,巧妙地揭露出那些不願抵抗奴役的烏克蘭騙子醜陋的嘴臉。
這種對帝國的不敬,乃是19世紀中晚期建立而成的烏克蘭文學普遍的基調。其代表作家,便是被譽為“烏克蘭民族詩人”的列霞·尤克拉茵卡和塔拉斯·什維申科(Taras Shevchenko)。這兩位作家的抗爭精神要遠遠高於假裝效忠俄羅斯的高格爾。什維申科出身農奴,所以他深知農民的生活絕不像高格爾的田園喜劇所表達的那般祥和。“你滿懷大笑,”他責備自己的這位同胞作家而在一首詩歌中如此寫道。“我卻必須慟哭。”什維申科抨擊俄羅斯帝國及其對少數族裔的壓迫是多麽地殘酷多麽地霸道。他的一首詩歌,《高加索》,如此寫道:“從摩爾多瓦到芬蘭/每一根舌頭保持著沈默。”正是因為這種立場,什維申科遭到逮捕,被迫服兵役,並且禁止他十年不得寫作。
列霞·尤克拉茵卡反抗帝國禁錮,通過一系列批評殖民主義的作品而逐漸形成自己的女性主義思想。她的文學創作,擺脫了地方主義的狹隘,以西班牙、特洛伊和巴比倫為背景,把歐洲和世界文化帶入到戲劇當中。有些烏克蘭的知識分子批評她忽視了烏克蘭最為迫切的主題。但是,實際上,她寫過一部關於烏克蘭歷史的詩劇:《貴婦人》,講述了一個發生在17世紀的故事。那是在哥薩克領袖鮑赫丹·凱末爾涅斯基為了讓烏克蘭脫離波蘭控製,而與莫斯科簽定了一份至關重要的聯盟協議之後。一位哥薩克婦女,奧科薩娜,同意嫁給一名在莫斯科法院工作的烏克蘭貴族,以此來紓解自己在“異邦之地”生活的恐懼。劇中,奧科薩娜說:“這是一塊讓人感到不再格外陌異的土地,不是嗎?/宗教儀式也是一樣的,而我/也已差不多明白了他們的語言。”
然而,奧科薩娜錯了。在莫斯科,她不準像別人那樣,跟人平等地說話;到了公共場合,她得蒙上臉;不能單獨外出。她是個外國人,這個身份讓她在人們眼裡成了怪異而又不可理喻的特質。就像妔朵娜娃在受困的基輔發表的演講中所說的那樣,奧科薩娜被當成了一個可觀看而不可聽聞的“物”,這就特別類似於列霞·尤克拉茵卡身處的那個時代,在俄羅斯帝國的文化想象裡,烏克蘭文化被縮減為一種色彩斑斕的小飾品。奧科薩娜非常抑郁,卻又無法返回故鄉,因為烏克蘭已經落入非常混亂的沖突:“烏克蘭人在莫斯科的皮靴之下翻滾在地,渾身鮮血/難道,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和平’?噢,烏克蘭,豈不已成廢墟?”
這部詩劇透露的訊息,顯然影射莫斯科對烏克蘭製造的悲劇,因而與俄羅斯帝國的官方歷史觀相抵觸,所以,既不能出版,也不能上演,直到帝國崩潰。同樣,蘇聯時代在編纂烏克蘭作品集時,這部詩劇仍然遭到刪除。
1991年,烏克蘭人終於贏得了獨立,列霞·尤克拉茵卡成為新一代作家和思想家的啟蒙者——這些人中,就包括塔瑪拉·妔朵娜娃。隨著世界潮流——譬如說: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漸成一股流入民主烏克蘭的涓涓小溪,烏克蘭本土的知識分子立刻就在列霞·尤克拉茵卡的身上辨認出:喔,原本她就具有這一切“新思想”。比方說,烏克蘭非常著名的小說家(也是列霞·尤克拉茵卡的傳記作者),奧科薩娜·贊布西柯(Oksana Zabuzhka),便在她寫於1996年、也是獨立後的烏克蘭最為暢銷的小說《實地考察烏克蘭人的性》裡,探索了這些主題。這部小說講述了烏克蘭剛剛獨立的那些日子裡,一個女詩人和一個男畫家喧囂般的浪漫愛情。
因為主人公,不僅在政治領域,也在私生活中,一心要維護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時也一心要拒斥俄羅斯同化,從而導致她獨斷地掌控伴侶的選擇和自己要生一個孩子的願望:
我們肯定能保護自己的孩子,難道不是嗎?然而,噢,主啊,我們這些毫不幸福的烏克蘭知識分子,到底有多少人,在歷史上一以貫之地予以頑強地捍衛——這人數極少,而且還一盤散沙瀕臨滅絕的族群,這即將從人類中被排除的族群。我們必須得像瘋子一樣不加節製地繁殖,繁殖,再繁殖。
然而,和《貴婦人》中一樣,女主人公總在渴望個人和民族的自由,卻又總是受到那些不能走出俄羅斯帝國陰影的男人一再的羈絆。在列霞·尤克拉茵卡的戲劇中,奧卡薩娜的丈夫是個奴顏婢膝的男人,動不動就用烏克蘭民歌和舞蹈討得沙皇歡心,而在奧科薩娜·贊布西柯的小說中,女主人公的丈夫,那個畫家,一直深藏著被統治民族卑微而又復雜的臣民心態。
在這些作品裡,女性角色往往具有強烈的烏克蘭身份認同,然而,與之相對的男性角色,卻總是顯出一種與俄羅斯帝國藕斷絲連的危險傾向。
在這次國際連線的網絡演講中,當塔瑪拉·妔朵娜娃談到列霞·尤克拉茵卡戲劇中命運悲慘的主人公奧科薩娜時,突然,她收斂了嚴肅公允的學術腔,語氣急切地把《貴婦人》所蘊含的那種至為關鍵的文化沖突,與當下的戰爭聯系在了一起。在《貴婦人》中,主人公奧科薩娜被俄羅斯人當作是一個無聲的“物自體”。
歷經好幾個世紀,俄羅斯都在拒絕體察和聆聽烏克蘭,都在拒絕承認烏克蘭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而普京的侵略。便是建基於這種歷史觀念之上。2月26日,基輔街頭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這種歷史-文化沖突最為暴烈的形式。然而,從列霞·尤克拉茵卡到奧科薩娜·贊布西柯,所有這些烏克蘭作家的作品,全都表明:暴力只會激發烏克蘭人去尋找更為有力、更有創意,也是更為桀驁的方式,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烏克蘭人。
(本文譯自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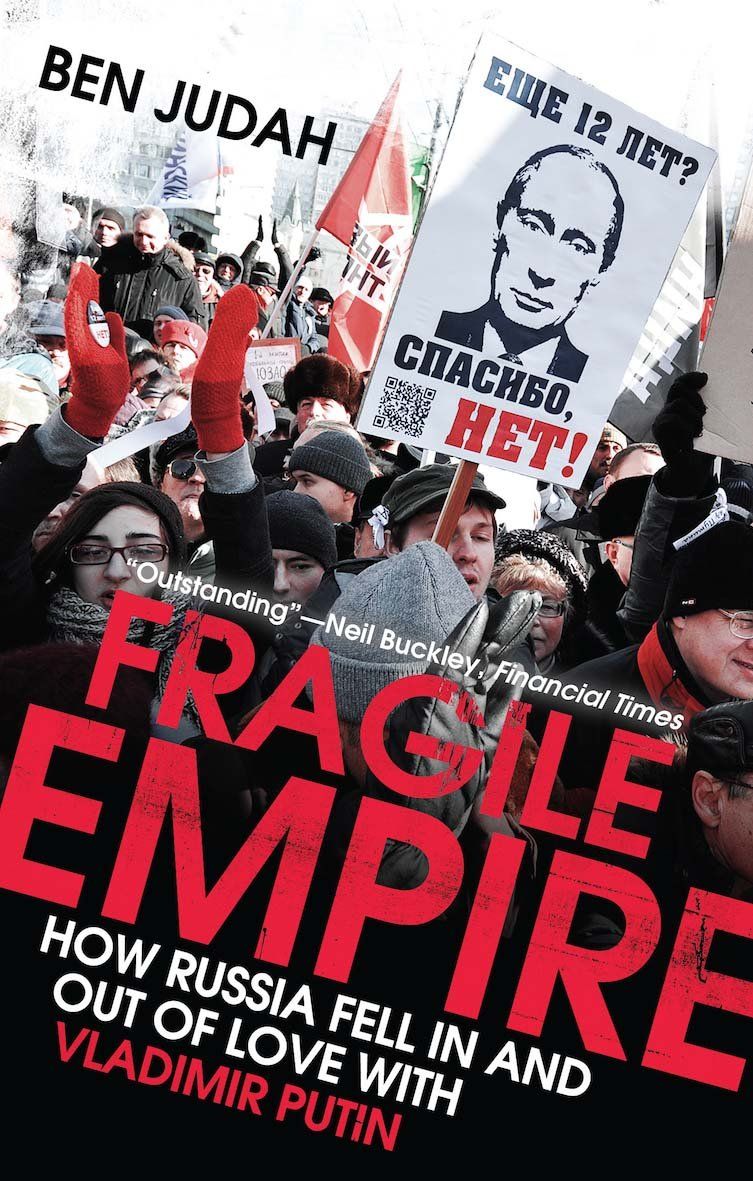
作者
尤伊列姆·布蘭克爾(Uilleam Blacker),倫敦大學學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東歐文化比較。
譯者
柴春芽,定住日本奈良,1975年出生於甘肅隴西一個偏遠農村,1999年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政治法律系;先後任《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和《中國新聞周刊》攝影記者以及鳳凰網主筆;曾在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已在臺灣和大陸出版文學著作十部,代表作有:《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你見過央金的翅膀嗎》、《創意寫作的七堂課》和《邊境線——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翻譯過博爾赫斯和德裡克・沃爾科特詩選以及《傑克・倫敦作品集》(四卷・待出版);導演獨立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和《異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