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 | 阿布 - 卢戈德 |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近些年来,性别议题在全球各地均得到广泛关注。就人类学视角而言,女权主义民族志的理论化、实践化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本文分享的是莉拉・阿布 - 卢戈德(Lila Abu-Lughod)于 1988 年 2 月 29 日在纽约科学院人类学部所作的演讲,具体探讨了在当时语境下,“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这个问题。虽然距离如今已有三十余载,但其中涉及的 “客观” 与 “主观” 二分法、民族志书写与理论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等议题,不仅在当时颇具争议,在全球联系日益加深、学科不断交叉、科技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更是值得继续探究。
阿布 - 卢戈德教授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她因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性别和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表达和媒体方面的工作而被广泛认可。1978 年至 1980 年代中期,阿布 - 卢戈德在埃及与来自 Awlad’Ali 部落的贝都因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半,为她的民族志《遮蔽的情感:贝都因社会中的荣誉和诗歌》(Veiled Sentiments)和《书写妇女的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奠定了基础。她曾在访谈中提到,“我最初选择与他们一起工作,是出于对沙漠生活的浪漫迷恋,但当我到了那里,一切都变了。我参与她们的世界,试图理解她们的世界,并且传达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世界,特别是通过她们的诗歌和故事。我与她们保持了近 30 年的联系,有种共同成长和变老的奇妙感觉。” 她还撰写或编辑了许多性别、媒体相关作品,包括《重塑女性:中东的女权主义和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自 9.11 事件和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来,阿布 - 卢戈德教授也一直致力于从民族志、性别、经济、政治等多重视角,打破对于阿拉伯社会的偏见,呈现这一地区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面貌。
原文作者 / 莉拉・阿布 - 卢戈德(Lila Abu-Lughod)
原文标题 / 《妇女与表演:女权主义理论杂志》(Women and Performa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Theory)
原文发布时间 / 1990 年
翻译 / 王玮祎
校对 / 王菁、马景超
编校 / 王菁
01. 讲故事,也讲理论
开始这个演讲时,我有些惴惴不安,因为我并不太习惯这类演讲。人类学家们更擅长用他们从田野带回来的故事来吸引观众。
就我自己而言,我一直得益于在埃及生活时,当时接待我的贝都因家庭给我的东西,包括凄美的诗、有趣的歌、离奇的民间轶事、关于爱情和婚姻考验的动人故事,以及那些关于死亡和失去的悲剧。就在你要打瞌睡,抓不住我论述的主线时,我就会用其中的一个故事把你拉回来。但讲故事不仅是为了这些,我常常通过这些材料来进行理论化的工作,并在谈话中保留这种理论与故事的互动性和民族志的优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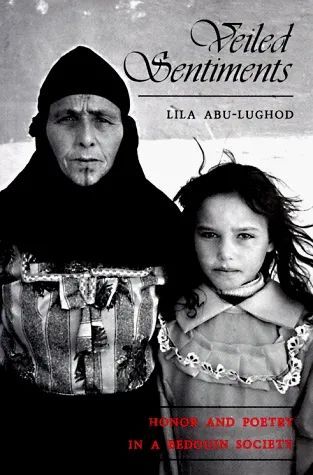
但是,在探讨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这一问题上,我没法提供一些故事来让你保持清醒。我会更多地去考虑一些理论问题,我现在正在写的书也是这些理论问题的一次实践。因此,研究的这一方面是没有故事和民族志的。
而这本书将充满叙述,就像我所居住的社区里一位老年女族长会说的那类故事。这位老族长向我生动讲述了 60 年前,在她还年轻时抵抗婚姻的三个事件 —— 她曾哭着并拒绝进食 12 天,曾在峡谷前长时间祈祷只希望神灵附体让她发疯,也曾用黑色颜料涂满全身,逃跑到她舅舅家,还把装满食物的碗扔出帐篷。
这本书也将涉及避孕和生育的故事。比如有一位妇女,她的大女儿自豪地说,正是因为她踩碎了七个白色蜗牛壳,蜗牛壳里装满了她母亲最后一个孩子的脐带血,她的母亲才终于不再怀孕(在生了 9 个孩子之后!)。她踩碎了这些蜗牛壳,便可以让母亲不再怀孕;而如果她把它们放在罐子里埋起来,用浸泡过它们的水让母亲洗澡,母亲便可以再次怀孕。
本书也会涵盖那些在狂热的掌声和庆祝的枪声中会唱的歌曲 —— 为了赞美在婚礼上展示的贞操布而唱的歌曲,这代表着女孩的荣誉,以及她父亲、新郎和他的家人及到场客人的荣誉。书中也有贝都因妇女对于婚礼的各个方面的详尽评述 —— 从谁来了,到如何安排用餐,以及新娘带了多少件衣服和多少黄金。这些故事展现了生活在这个电视、广播、学校和伊斯兰运动时代的人们身上所发生的复杂转变,包括贝都因未成年少女对埃及最新的广播肥皂剧《电脑新娘》的讨论。这部连续剧以大团圆结局告终,主人公使用了电脑婚介服务,在被迫尝试了三位不合适的新娘之后,终于成功地与他所爱的女人结婚。当时,我正和几个贝都因女孩坐在一起,边烤面包边听广播,烟刺痛我们的眼睛,风从沙漠中吹来,鸡群嘈杂地互相追逐,这几个女孩向我介绍了我错过的剧情。她们讲完后,怯生生地问我:“什么是电脑?”
这个讲座无法详述这类故事。当我们在讨论是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以及 “女权主义民族志可能会是什么样” 的问题时,我将不得不谈论诸如认识论和表征(representation)、人类学、女权主义、自我和他者等问题。我将不得不引用许多名字,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所以并非为所有人所熟知。你们需要靠自己保持清醒。
我想要论证,我们正处于女权主义和人类学发展的关键时刻,这将使女权主义民族志的发展更有可能,也更值得期待。为了论证这一点,首先,我将探讨在人类学和女权主义领域中对 “客观性”(objectivity)的批判 —— 这种态度也可能被援引来宣布 “女权主义” 和 “民族志” 无法共存。然后,我会讨论人类学的危机和女权主义的危机,正是这些危机使得女权主义民族志项目恰逢其时。
但是,首先要对术语进行定义。若问是否可以有一种专门的女性主义民族志,我们必须先了解民族志的定义。事情已经很复杂了,因为民族志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术语,它既指从事人类学研究,又指这种研究的书面成果,现在,这种文本或民族志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半文学体裁。我暂且搁置女权主义的定义,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都对它有一个粗略的概念,也因为女权主义这个术语太有争议,若要定义它就会立刻陷入麻烦。
我们问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就是在问女权主义对人类学的研究和描述其他文化社群生活的写作会带来什么改变。考虑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客观性问题。若客观性是人类学研究和写作追求的理想,那么主张一种女权主义民族志就是在主张一种有偏见的、有兴趣偏向的、片面的、且因此有缺陷的研究项目。客观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问题,而且人类学对它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会先谈谈人类学领域的 “客观性” 问题,然后再概述女权主义理论家在思考客观性方面的突破。对她们而言,认识论一直是大量理论研究的显要关注点,她们在客观性的大本营 —— 科学本身 —— 中试图应对了这个问题。
02. 反思及文本人类学
不知为何,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前景似乎并不像女性主义政治学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想法那样令人震惊。没有多少人会对此发出惊呼。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有着悠久的文化相对主义传统和关于多重真理的概念,而这也意味着人类学中已经隐含了对客观性学说哲学基础的批判。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人们对客观性的可能性提出了更明确的质疑。这与其说是来自知识社会学,不如说是来自阐释人类学,而知识社会学在其他领域中对知识的客观性的颠覆更为有力。在阐释人类学中,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了 “文化作为文本” 的隐喻及其著名的推论,即人类学 “不是一门寻找规律的经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找意义的阐释科学”。【1】这为当下流行的、人类学对客观性批判两个最重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个是对田野察过程中反思性的关注,另一个则是对书面表达中的文学性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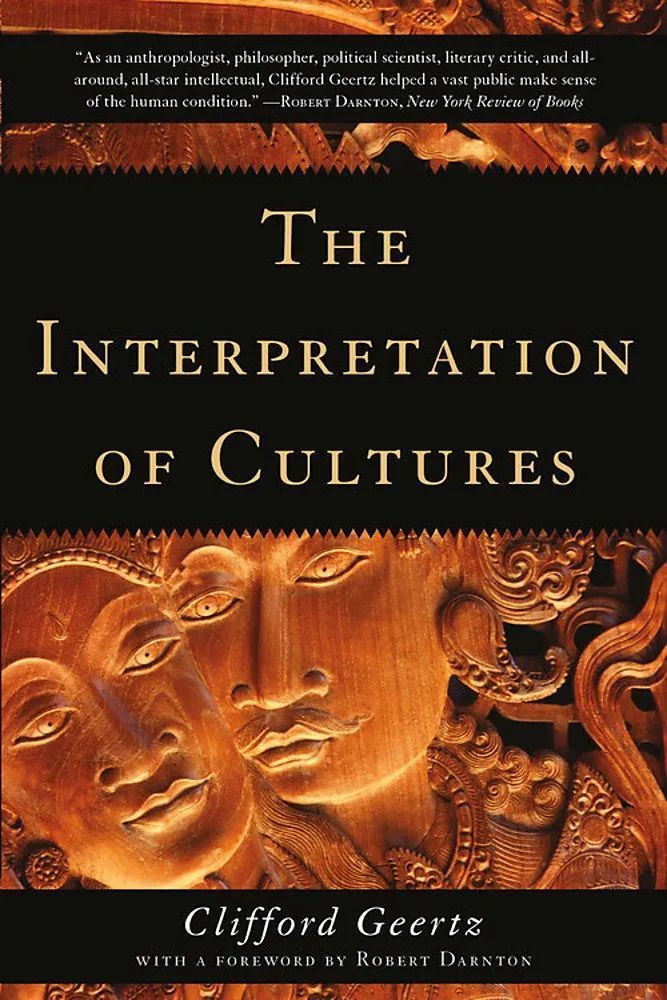
以反思人类学为评测标准的那些作品,关注的是在田野中得到的所谓 “事实” 如何通过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人类学家与特定个体的私人互动构建而成。这类研究的主要人物有温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 Crapanzano)、让 - 保罗・杜蒙特(Jean-Paul Dumont)、凯文・德怀尔(Kevin Dwyer)、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和保罗・里斯曼(Paul Riesman)。尽管方式不同,这些学者都把田野调查的相遇看作主体间生产出 “事实” 的所在之处。【2】作为人类学家,如果我们是通过情感上极为复杂、交流上十分模糊的社会相遇来获得相关的田野知识的,那么必然不存在什么客观性,人类学也不应该被比作科学。
第二波对客观性的批评风潮角度稍有不同。格尔茨的出现还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学家实际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写作。从民族志写作的文学传统来看,一些人类学家指出,现实主义和体现客观性的透明化语言被用来维护了经典民族志中叙述者及人类学家的权威。在此,人类学叙述的构建方式至关重要,并且这些构建方式和民族志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以及不平等的关系紧密相关。【3】
克利福德在《写文化》的导言里写道,也许作者本人意识和控制之外的因素,才真正塑造了民族志写作和描述的种种方式。他写道:“民族志写作至少由六种方式所决定:
(1)语境上(它取材与充满意义的社会环境,并创造有意义的社会环境);
(2)修辞上(它使用有表现力的常规手法,也被后者使用);
(3)体制上(写作既处在特定的传统、学科和观众读者之中,又对立于所有这些因素);
(4)一般意义上(民族志通常区别于小说或游记);
(5)政治上(表述文化现实的权威的分配并不平等,有时也有冲突);
(6)历史上(上述所有常规和限制都在变化之中)。”
这显然是在说,所有民族志都是情境性的,没有一个是对现实简单客观的表述。【4】如克利福德所说,这些决定性因素” 支配了内在一致的民族志虚构的撰写”,然而绝大多因素还未被系统地探讨过。【5】大多数的自我意识是关于文学传统的(以上第二点和第四点),并导致了一些关于(文学)形式的有趣实验。另一个流行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对话体(dialogical)或多声部(polyvocal)的民族志。这种民族志旨在文本层面上去殖民化,清楚地体现出叙述者 / 人类学家的声音只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并使研究对象的声音也能被听到。
在这种对作为文本的民族志的批判中,认识论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的问题)和我们如何表述的问题被迅速地混为一谈,某种程度上回避了人类学最核心的基本政治问题 —— 来自西方的认识者和表述者,以及非西方的被认识者和被表述者。这是一个有关自我和他者、主体和客体的问题,我之后将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它与性别和女权主义民族志也息息相关。
03. 女权主义理论和 “客观性” 问题
另一方面,对于女权主义理论家而言,性别、方法、理论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跨学科研究的主题。持续至今的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指出,对许多现有理论和知识的非难,往往说的是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客观或不够客观。
学者们指出,在对社会和文化生产的研究中,女性是如何被忽视的,他们也指出,通过提出或回避某些特定问题,以致于忽视了性别或女性的存在。在科学研究中,那些支持性别差异和女性劣势论的流行假设的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并被指责为 “坏的科学”。在多数研究领域中,记录下因男性中心主义而扭曲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对它们进行纠正的相关研究也同样重要。【6】
学者们批评现有的学术是带有偏见的,而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目标是完善记录,并通过纳入女性的生活、经验、文学和艺术等,使理论更客观、更完整,并且更有普遍性。在这种表述中,对客观性的追求仍然是毋庸置疑的,而其反面则被认为是偏见或偏袒。【7】
第二波女权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她们对客观性进行了多方位批判,也同时批判了 “客观” 与 “主观” 二分法,而客观性这一概念的意义正是通过该二分法而来。由此,女权主义者开始将辩论的重点从传统的担忧,即 “客观性的局限”(多少带有一种将客观性作为理想的传统科学假设),转向了对客观性概念本身的地位和价值更彻底的质疑。
在这一思潮中,由于在社会科学领域,将客观性作为一种理想或是切实可行的可能性始终具有争议,因此第二波女权主义中最猛烈和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并非来自社会科学,而是来自自然科学的哲学或历史。之所以如此强而有力,是因为科学似乎是客观性理想最坚不可摧的地方,而且对认识主体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分也是最明确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指出,科学所谓的客观性不仅是性别化的二元论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权力的模式。一些观点认为客观性的概念应该被废除,另一些则认为这一概念应被重塑。
我来举个例子让大家体会一下。伊芙琳・福克斯・凯勒 (Evelyn Fox Keller)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客观性的定义来自于它与主观性构成了一组概念。而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二元论与性别的二元论是相互呼应的,也就是说客观性与男性气质相关联。【8】一系列被认为是阳刚的特征,正是因为和 “感性” 对立才成立,就像精神相对于身体,疏离和非个人的相对于个人兴趣和参与 —— 这种关联性使得科学的威望与男性气质的主导地位互相都得到了增强。【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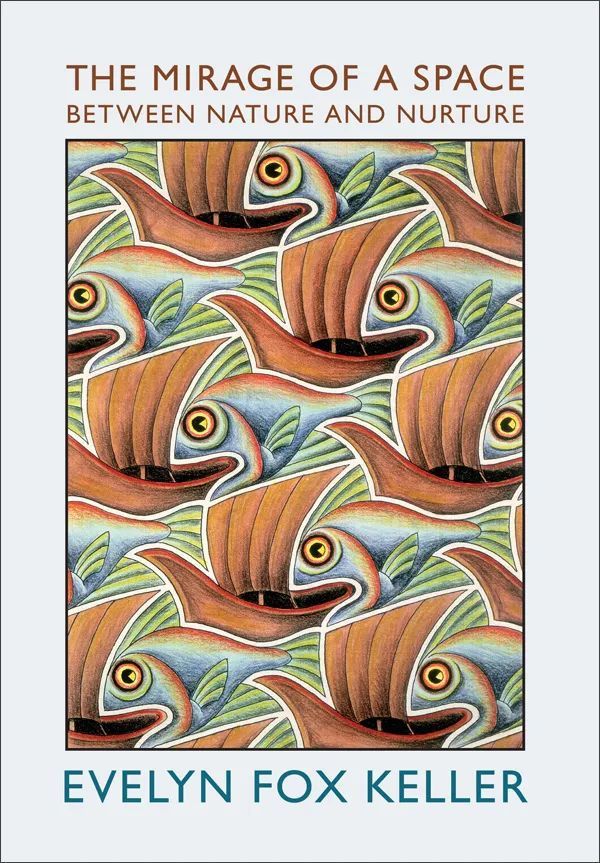
凯勒还提出,她所说的科学中的客观主义意识形态,是通过一种自我选择的方式进行自我再生产的。她认为,科学吸引了那些共有特定价值观的人,或至少其自我形象与这些价值观一致的人 —— 主要是男性。此外,她还提出了一个更偏向推测性的心理动力学论点,即一些人的婴幼儿经验使他们觉得科学事业所承诺的疏离感和边界的清晰感对他们来说十分舒适 —— 同样,大多数是男人。
她的论点还有很多。然而,在我们这次讲座中,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文化解释是多么具有说服力。只要想想科学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两个轴心 —— 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 你就会得到像主观 / 客观、有偏见 / 无偏见、个人 / 非个人、被认同 / 被疏远、局部 / 普遍、特殊 / 一般、有意思 / 无价值、情感 / 理性等等这样的对立。这些都与 “女性气质 / 男性气质” 有关。然后,我们就能得到作为一种主体 / 客体关系意义上 “科学 / 自然”、甚至是 “人 / 自然” 的关系,毕竟这其中的 “自然” 总是与女性相关。
凯勒希望能保留 “客观主义”(objectivism)与真正的 “客观性”(objectivity)之间的区分。她认为,客观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对科学实践的描述。然而,从凯瑟琳・麦金侬 (Catharine A. MacKinnon)到多萝西・史密斯 (Dorothy Smith),这些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不会接受这种区分。
麦金侬是最激进且饱受争议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她的理论涉及了客观性如何在像我们这样的、在根源上是以性不平等为结构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她认为,客观性主要是男性权力的一种策略,而不仅仅是一个通过与男性气质相关联而被赋予文化意义的概念。她提出,“女权主义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主观的、片面的或不确定的,而是认为这是对过去说法中所谓的一般性、无私性和普遍性的批判…… 女权主义不仅挑战了男性气质中倾斜的天平,而且进一步质疑了普遍性要求本身。女权主义揭示出无视角性(aperspectivity)是男性霸权的一种策略。”【10】她认为,男性总是占主导地位,从他们的角度、尤其是物化女性的角度创造世界,然后采取了某一种认识论的立场,也就是客观性,以符合他们所创造的世界。
麦金侬经常因为她指责男性理论家的全面化倾向而受到指责,她在关于 “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男人的性统治” 上,表现出的普遍主义和非历史性的论点必须谨慎看待。然而,她对客观性和统治相联的直觉,在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的工作中得到了更细致详尽的支持,史密斯论证了客观性、社会学话语、男性和统治机构之间的亲和性和关联度。通过把分析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学科和社会领域中,史密斯把她的论点建立在了具体的细节上。她认为,社会学的议程和领域都是 “建立在男人的工作世界和关系上的,他们的经验和利益在参与这个社会的统治机器的过程中产生。社会学的公认领域 —— 组织理论、政治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精神疾病社会学、偏差等等 —— 都是从专业、管理和行政结构的角度以及从他们的观念出发来定义的。”【11】她接着指出,社会学的理想视角 —— 科学的、客观的、阿基米德式的 —— 与社会学家参与统治机器有关。她写道,“社会学的独有特征是通过悬置认识者实际的、特定的位置,从而来反思社会、反思社会关系、反思人,这种学科倾向必须结合学科自身所处的地位来理解…… 这是一种局部的视角,起源于社会中占一种特殊的位置的人。”【12】这个视角来自上层和占统治地位之人,至少在现代西方社会,这种地位主要被男性占据。
麦金侬补充道,这种视角不仅仅是对男性作为支配者、统治者或管理者经验上的反映,而且就是他们统治的有效工具。她指出,“如果两性确不平等,而视角仅参与到了其中一种情况,那么就不存在所谓无性别的现实或无性别的视角。而且,这一切都是相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性 —— 无定位的、普遍的立场 —— 无论是声称的还是所追求的,都是对性别不平等的存在或不平等程度的否认,且沉默地参与了主导观点构建现实的过程。”【13】
由此,女权主义学者对客观性批判主要有两类回应方式。一些人谴责了客观性概念,并探索女权主义是否可能创造出一种替代性方案。这些当中的许多人承认了主客二元论中先前被贬低的主观性的价值,提倡建立一种新的主客关系 —— 强调关系而非距离,平等而非支配,依存而非疏离或无关利益关系。
另一些人或许太过清楚这种态度只是将等级制度头尾倒置,其背后仍然保留了性别二元论。换句话说,以上仅仅是一种对传统上女性气质的重估,没有去挑战使等级制度存在的二元论。因此,后者强调批判中暗含的另一个意义,这些学者的观点建立在倾向性(partiality)的基础上,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有倾向性的,都是某种视角的具象。他们希望重新认识并定义客观性,使之恰恰意味着 “情境观点”(situated view)。他们会认为,没有什么研究是不置于某种情境之中的。女性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具有特权的,因为就像任何庶民观点一样,我们无法假装它是一个没有来源的观点。
作者注释

阿布 - 卢戈德教授对本文的介绍:
这是我于 1988 年 2 月 29 日在纽约科学院人类学部所作的演讲,内容略有修改。演讲是学者们经常进行的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尽管有缺点,我仍决定将这篇演讲原样保留。自从发表了这篇演讲,我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关于女权主义者们和 halfies 的共同点,和她们对于人类学有何启示,我在《反 “文化” 的书写》(Writing Against Culture)一文中进行了更多讨论,收录于 Richard Fox 编辑的《介入:当下人类学》(Interventions: Anthropology of the Present;校注 —— 此书后来出版时题为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我感谢 NEH(国家人文基金会) 的研究经费,使我能够于 1987-88 学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研究,也包括为这次演讲所做得准备。我受益于性别研讨会的讨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我也感谢 Cathy Lutz 的评论,以及 Connie Sutton 和 Susan Slyomovics 鼓励我将这篇演讲以更永久的方式发表出来。
译者介绍
王玮祎,古镇人,在日本读人类学,爱好小鸟和野生三色堇
校者介绍
马景超,哲学系博士在读,现居美国费城
王菁,喜欢没有(以及看起来没有)脊椎的海洋生物,人类学视角的跨学科研究和公共对话
本译文受作者本人授权,若要转载,请在本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
Posted in 世界人类学 , 中东 , 公共人类学 , 性别 , 编译
最新文章(持续更新)
193. 家务、猎巫、女性与关怀空间 |《卡利班与女巫》试读
194. 小镇做题之后?| 弗雷勒的地平线(V)
195. 纪念贝尔・胡克斯 | “那个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人”
196.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1 年 11-12 月
198. 爪夷文:马来西亚现代性之症
199. 教与学|访谈张巧运:做人类学老师,在没有人类学的地方
200.阿布 - 卢戈德 |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