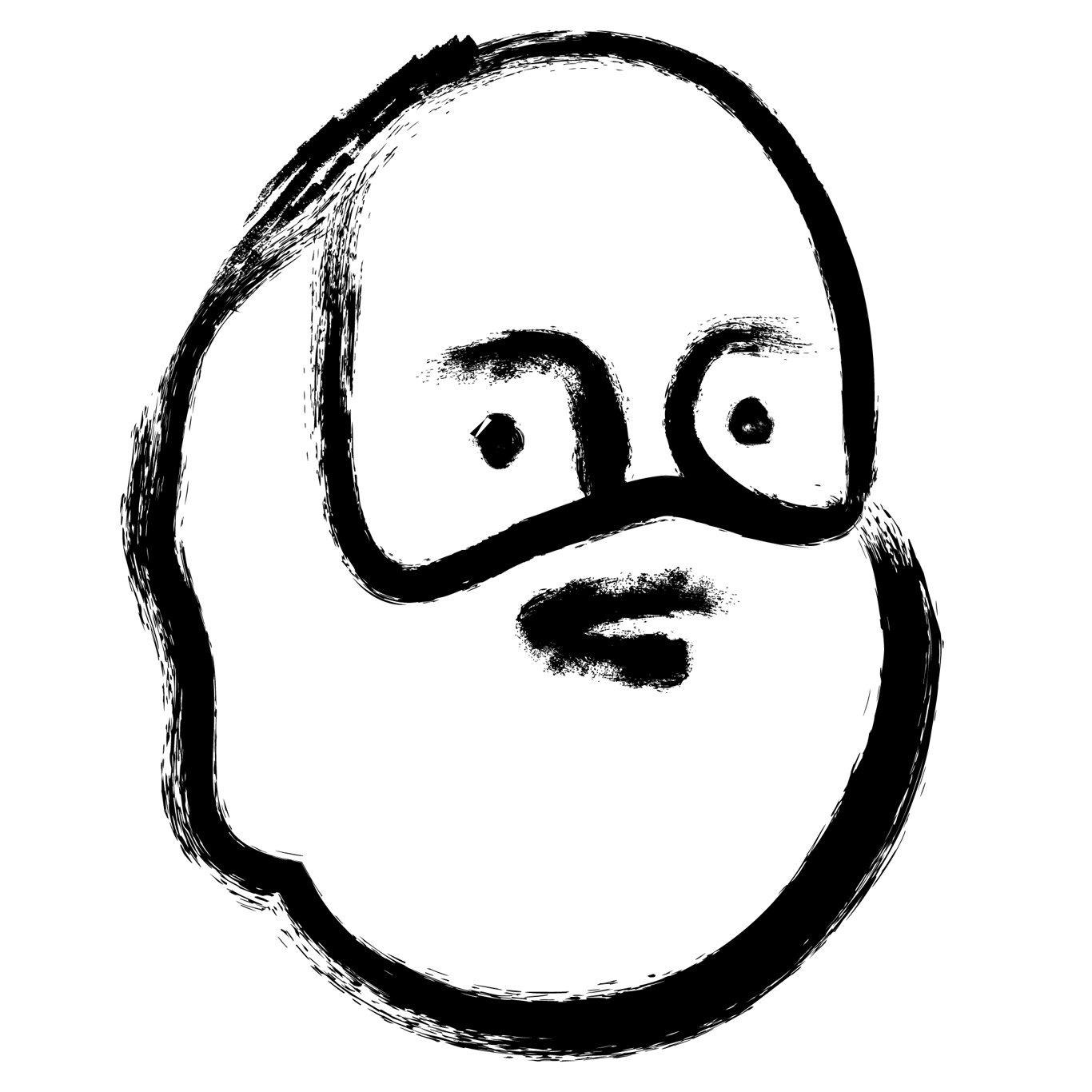敘事與人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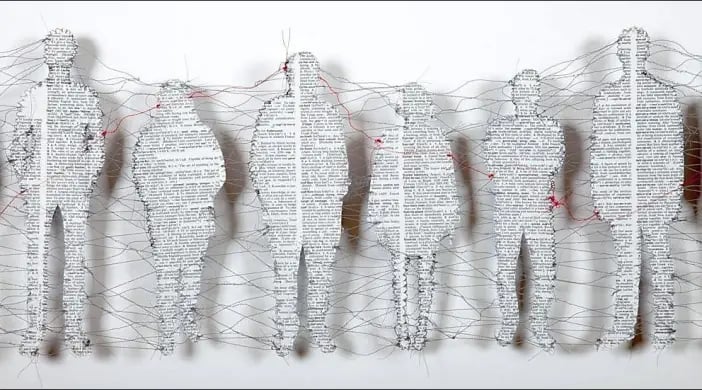
作者︰李四
難度︰★★★☆☆
於沙特(Sartre)的著作《嘔吐》(La Nausée),主角 Roquentin 有這樣的一段說話︰
「一個人永遠是講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別人的故事之中,通過故事來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努力像他講的那樣去生活。」[1]
這段說話指出了一個頗為普遍的現象︰我們都傾向用故事來理解自己的人生。我們思考自己的人生時,並不會鉅細無遺地將所有事件羅列出來。相反,我們會將自己的生命片段組織成故事。我們會把自己視為故事的主角,並根據自己構想的情節去行動。我們也會根據自己的故事為他人安排角色,視他們為朋友、敵人或者於背景中經過的路人甲。我們甚至會用某些文學類型去總結某人的一生,說他的人生是一齣悲劇或喜劇。
人生即故事
Alasdair MacIntyre 認為,這種理解人生的方式並不是出於偶然。我們之所以會用故事去理解人生,是因為我們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個「活的故事」。他說︰「我們首先活出一個故事,然後才將這個故事講出來」[2]。換言之,我們的人生其實是「最原初的故事」,講述自己的人生,只是將這個事先存在的故事用語言表達出來。然而,即使我們從來沒有講述它,它依然是一個故事。
說人生是一個故事,MacIntyre 的意思是指我們的生命片段並不是單純的先後次序關係。相反,人生的過去、現在、將來會連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就是他所謂的故事。
我們的生命之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因為人類是能夠自己訂立目的、並採取行動的「能動者」(agent)。我們不僅僅存在於時間「之中」,還能夠「使用」時間。我們採取一個行動時,其實是將我們的生命片段結合在一起,使其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
我現在的處境(例如作為一個哲學系的學生),是由之前選擇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我在這一刻選擇的行動(例如報讀研究院),又會影響到我的將來。因此我的過去、現在、未來不僅僅是先後次序的關係,它們還具有「目的上」和「因果上」的連結。由此可見,人生片段是環環相扣的。每一個個別的片段,都是構成生命整體的其中一個部分,只要其中一個片段改變了(例如當初沒有選擇讀哲學),我就會擁有不一樣的人生(故事)。根據 MacIntyre 的講法,人生就像一齣持續上演的連續劇,只要我們活着,故事就會繼續發展。而我們既是這個故事的主角,亦是這個故事的作者。
我們是自己的人生故事的主角,因為我們是這個故事的中心。在我的人生電影中,鏡頭永遠是第一身的「Point of View Shot」。萬事萬物都圍繞着我發生,所有我遇到的人都是故事中的角色。我的人生經歷就是故事的內容。我的出生是故事的開始,而死亡則是故事的終結。
但我們同時也是這個故事的作者 [3],因為故事的劇情由我們自己的行動決定。小說作家用語言去敘事,但其實所有人都會用行動去「書寫」自己的人生故事。當我們在人生的分岔路口猶豫不決,其實和一個小說作家為着劇情應該如何發展而感到煩惱沒有分別。我們每一個行動都是劇情的推進,而採取的行動將會決定我們的人生最後會發展成喜劇、悲劇、抑或是可笑的鬧劇。在這觀點下,人生就像一件自我創造的藝術品︰我們既是這件藝術品的作者,又是這件藝術品本身。
總括而言,MacIntyre 認為人生本來就是一個故事,因此用敘事去描述、理解、或思考人生是最自然、最適合,亦是最能夠把握人生本來面目的方式。[4]
人生非故事
雖然很多學者都贊成我們有着將人生理解為故事的傾向,然而他們不少卻對這種理解方式抱以懷疑的態度。他們不但認為敘事不能夠準確反映人生,有些更認為用這種方式來理解人生是「危險的」。[5]
和 MacIntyre 相反,Louis Mink 認為人生和故事完全是兩回事,他說︰「故事不是活出來而是講出來的。」[6] 他認為故事於本質上是人為的藝術品,它唯有在敘述的時候才存在;沒有敘述,就沒有故事。換言之,根本就沒有所謂未被講述的、原初的「人生故事」。
故事是人為的創作,在一個故事中,所有事件都經過作者的篩選與安排,每一件事都有被講述的理由與目的,事件和事件之間總是有某種聯繫。然而,真實的人生卻充滿着偶然和不相干的事件。我們的人生片段是零碎的,片段與片段之間並沒有情節上的連結。在故事中,偶遇總會帶來進一步的發展、意外總是後續的舖排、角色總是有登場的理由;真實的人生卻充滿着無疾而終的偶遇、單純的意外、可有可無的人物。
因此,真實的人生根本就沒有敘事結構。故事是講出來而不是活出來的。我們首先活出我們的人生,然後才回過頭來,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我們的生命片段中尋找材料去組織故事。敘事結構是我們在講述(或回想)人生的時候才賦予在它們身上的。我們所講(或想)的人生故事,就像一本自傳(autobiography)── 這本自傳是建基於真實人生的文學創作,卻不是人生本身。
Peter Lamarque 同意 Mink 的講法,認為人生本身並不是故事。他進一步指出,用故事來理解人生,其實是將不適合的框架強加於我們的生命之上。這樣做會使我們得出扭曲的人生圖像,令我們以一個錯誤的態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因此用敘事方式理解人生不單是錯誤,而且更是有害。[7]
如果我們將人生「閱讀」成一個故事,我們很容易就會從一個讀者的角度看待自己,嘗試將生命中發生的事件理解成情節的安排。這個傾向是危險的,因為它會驅使我們向生命提出不恰當的問題,繼而尋找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答案。這樣會使我們變得不容易接受生命中發生的意外。
當不幸的事情發生(例如親人突然離世),我們會問「為什麼」,並希望找到一個「理由」作為答案。我們就像一個文學系的學生那樣分析故事的情節,嘗試從中解讀出隱藏的意義。然而,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真實的人生總是充滿着偶然事件。Peter Goldie 說︰「人生的簡單事實就是『stuff happens』。」[8] 事情僅僅發生,沒有理由可言。在文學評論的角度,我們可以問作者「為什麼」安排某件事發生,但在真實的人生,事件只是發生,根本就沒有「為什麼」。
如果我們執著於尋求一個答案,我們很容易就會將事件「過度詮釋」︰強行為無意義的事件賦予意義。這個情況在教徒中最為明顯。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容易就會將生命中發生的事件視為上帝(宇宙的「作者」)的安排,無論是幸運或苦難,總是有發生的理由。因此 Lamarque 認為,將人生視為故事,會鼓勵某種迷信(他稱之為神秘主義),令我們曲解事實。[9]
另一個更糟的情況是,我們於情感上不能夠接受某些事件的發生。我們覺得自己的人生(故事)毀壞了,就像一本寫錯了而又不能修改的小說一樣。我們不知道如何可以再延續這個已經「寫錯了」的故事。於是我們被困在一個半途而廢的故事中,就像一個被作者放棄了的角色,停留在錯誤的關節,看不見未來。
因此將人生視為故事,既是錯誤,又是危險。即使我們擁有自我敘述的自然傾向,我們也應該要認清事實,將人生和故事嚴格區分。當我們能夠認清人生和故事的分別,明白到生命無常的真相,就會更容易接受生命中的偶然事件。
人生如故事
以上談及了兩種相反的立場︰一種認為「人生即故事」,而敘事是理解人生最好的方法;另一種認為「人生非故事」,用敘事來理解人生不單錯誤,而且有害。我的立場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我贊成人生和故事有着重要的分別,亦贊成用敘事來理解人生會有潛在危險。然而,我卻認為敘事於我們的生命具有不可取替的重要功能,我們應該將人生「當作」(as)故事來理解 ── 縱使它本身並不是故事。因此,我的立場可以概括為「人生如故事」。
我將會寫一系列的文章仔細探討敘事和人生的關係,現在先簡單的說明當中的基本方向,作為這篇「引言」的結尾。
我認為自我敘述的目的不是要客觀地描述人生事件,而是要「解釋」(interpret)這些事件,為這些事件賦予意義。正如 Paul Ricoeur 所講,假如沒有經過敘述,人類的生命僅僅是一個生物性現象。[10] 換句話說,敘事是將作為生物的「人類(human being)」轉化成「人(person)」的活動,而人類和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僅僅活在物理世界,後者則活在經過解釋、擁有意義的文化世界。Ricoeur 引用歌德(Goethe)的講法,指出大自然能夠製造生命,但這些生命是無意義的;藝術只能夠製造出死物,但這些死物卻擁有意義。敘事,作為一種藝術,就是將無意義的東西帶到意義領域的方法。[11] 因此當我們用敘事來解釋自己的生命,其實是嘗試將自己的生命轉化成一個具有意義的人生。
建基於這種對敘事的理解,Ricoeur 重新解釋蘇格拉底的名言︰如果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那麼,一個經過反省的人生,就是一個經過敘述的人生。[12]
注腳:
[1] 沙特。《嘔吐》。桂裕芳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頁 76-77。
[2] 這一句是「Stories are lived before they are told」的意譯,見 MacIntyre, Alasdair.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3rd ed.).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 212.
[3] 更準確地說,MacIntyre 認為我們只是自己的人生故事的「其中一個」作者,因為我們的人生故事會被其他人的行動影響。見 MacIntyre, Alasdair.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3rd ed.).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 213, 215.
[4] 同上 p. 212.
[5] 事實上,說出文章開首那段說話的 Roquentin 自己就反對用故事來理解人生。
[6] Mink, Louis.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1, No. 3.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57.
[7] Laramque, Paul.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Literary and Real-Life Narratives”, in Daniel Hutto (ed.) Narrative and Understanding Pers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9.
[8] Goldie, Peter. “Life, fiction, and narrative”, in Noel Carroll & John Gibson (eds.) Narrative, Emotion, and Insight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
[9] Laramque, Paul.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Literary and Real-Life Narratives”, in Daniel Hutto (ed.) Narrative and Understanding Pers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31.
[10] Ricoeur, Paul. “Narrative Identity”, in Davi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Edited b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27-28.
[11]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a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p. 80.
[12] Ricoeur, Paul. “Narrative Identity”, in Davi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