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 邂逅 “灵”:与海豚的眼神交汇
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 “多物种民族志” 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 “它们” 栏目)。
然而,人类学视角并非唯一路径。文学、宗教、艺术、科学等不同学科均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 - 非人类的关系。本文作者陈济舟便揉杂了宗教和哲学的视角,用文学的笔触,书写与 “灵” 邂逅的体验。如其所述,“所有的到来和离开,震撼与失落,获得与抛弃,都在我与它的一眼之间。万物的颜色都一时鲜亮起来,直至它离去,遂又归于沉寂。” 虽然其后对于 “灵” 的论证逃不开与西方哲学源流的对话,但济舟却在搜寻过程中,回溯汉语源流(甲骨、简帛和金文),从中发掘关于灵的 “最原初的” 书写,以及背后不断变化的涵义。
此外,本文也是结绳志 “写作” 栏目的尝试之一,旨在投入这种听与说、读与写的辩证,在文(text)与质(texture)之间找到不同实践主体和表达方式之间的合作、断裂与平衡(欢迎读完此篇后移步阅读《在世界环境日演练它们的诗歌》)。
作者 / 陈济舟(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博士候选人)
编辑 / 王菁
原文链接 / https://tyingknots.net/2021/06/ling/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 年 6 月 16 日
01.
那是 2018 年的五月末,我从耶路撒冷乘车一路向南,沿着死海西岸,来到以色列这座最南的海滨小城:埃拉特(Eilat)。小城坐落于红海阿卡巴湾之北,对岸是约旦,驱车南下,只需十五分钟,就已是埃及国境。
边城的阳光明媚得不真实,那光海里似乎暗藏了某种可将整个世界洗白的力量。我站在海边,遥望对岸约旦王国的一带远山。看见云在那寸草不生的荒山上投下自己的影子,而山对此却并不眷恋,任由它们来去,就觉得心中升起一丝莫名的悲凉。远方云影的暗反衬着近处海湾里的白帆,帆与船身一样洁白,散发着生命的光,折射入湛蓝的海水之中。

看到这些,我便迫切地期望着,自己也可以将生命中那些不堪的往事,都统统抛掷到这片蔚蓝的海水里。
我来到埃拉特,并非为了学术上的田野调查,而只是单纯地想要潜入红海,进入它的身体里。我固执且没有丝毫科学依据地认为,对于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水,不管它们是属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或者其它,在它们的水体里都带有一些远古且永恒的记忆。这些记忆里承载着关于人类、物种和这个星球的故事,当人潜入水的深处,当迟来八分二十秒的天光(太阳与我的距离),照亮这方 2000 万年的水(红海的年纪),以及水里这个在更新世才作为 “智人” 出现的 “自己”,我才能够在有意或无意间,获得一些远古的讯息,一些关于 “灵” 的消息。
02.
我的工作是在北美学术界研究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而当我的一位导师起初向我介绍 “环境人文” 这门学科的时候,我对它保持着一种嗤之以鼻的不屑态度。我曾自以为是地暗忖,这种和生态以及环境相关的学科,无非就是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再激进些的人,也无非是一面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面大谈素食主义,为猫狗平权,还一面开着烧油的私家车或坐着头等舱,全世界到处跑,留下一大串碳足迹。
我抱着这样半信半疑的态度,阅读了大量关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环境历史和动物研究等范畴的书籍,虽然在知识层面,已经能够理解并肯定这些学科的价值和必要性。但若扪心自问,对于一个在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能从情感上对环境产生任何的共鸣。
我想要寻找的是一种近乎超绝的感知,一丝心神上的灵明,因为只有那些最最虚无缥缈的东西,才能将我从现实的苦闷中解脱出来,找到一点内心的释怀。
只怪这个世界,早已真实得狭小。

学术知识的增长和生命经验的匮乏,如同两片地球板块的分离,在我内心深处日渐拉扯出一条狭长的深渊,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直到很后来,当我开始把这些知识和自己在世界各地潜水时的所见所感联系在一起时,我才为这些书本上的东西,找到了它们在我浅薄生命中的一种微若却深沉的回响。
那是一种不间断地沉吟,来自我内心的深渊之中,却如海豚的哨声,有一种无远弗届的通达。那是海和这颗星球的叙事和意识,零碎而不成体系,也不屑被人类这种生物所理解。我只能无限地向往且向它靠近,但它注定存在于我这种生命体的感知能力之外,它近乎是另一个维度的了。
这些知识和讯息,以物质的形式,与水中的我产生某种不自知的交换。那是一种在细胞和浮游生物、骨骼和珊瑚之间的对话和聆听。这些非人的言语在不断地提醒着水中的人,我依旧只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偶然,如同这里已逝的和未来的千千万万个偶然。然而,正因为这些偶然,我才发现,自己不用在静夜的时候,再去一个人承受生命的孤单。
考前的月亮与六便士.
次日,海水、沙漠和港城,依旧如昨日一般在我的梦中苏醒。红海的阳光仍然炽热,漂白了一些记忆,又驱散了一些阴影。我和导潜决定前往以色列和埃及边境上的一片海滩,从那里入水,然后沿着海底逆流北上。因为在那里有一间水族馆,馆里放养着四只半野生的海豚。白天海洋馆会开启水底闸门,让这些海豚自由来去,晚上,则会在海豚归馆之后,关闭闸门,让它们有得安眠。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在水下遇见它们。
此片海域并没有什么丰富的珊瑚礁和鱼群,海床上都是白色的细软的白沙,但是水底海流强烈,我不断努力地踢腿方可北溯。十五分钟后,我的体力越发不支,却突然发现在海床上出现了一圈用石子排列出来的人工地界。
我匍匐在这海底的疆界之外,发现除了石子,还有很多人造珊瑚礁结构,上面附着着各类自生的和移植过来的小珊瑚。因为知识的匮乏,我无法辨析这些珊瑚的种类,但它们都是极小且零星地生长在这些人工结构载体上,还未成势。但从这个圆圈来看,似乎是想在几十年后,在这里长成一个半径约莫十几米的珊瑚礁带。
我用海水清洗了一下起雾的目镜,再用鼻腔喷气,将水体排出,这才发现抬头不远处,有一个看似闸门的物体,想必那便是海豚的家门了。导潜用手示意让我耐心等待。又过了十几分钟,身边依然不见海豚的踪迹,而我瓶中的空气已所剩不多,于是心中的期望变为失望,我们不得不返程。
紧贴海床,我们顺着海流南下。在漂移的过程中,我的思绪又飞向了别处。我想不管是观鸟人、野外摄影师,还是像我这样水底观光潜客,与野生动物邂逅之前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这种不一定有结果的等待上的。而在我的生命里,我不曾记得我真的等待过什么。大部分的教育,都在告诉我一件事,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就要努力去争取。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定律在人的社会里是正确且可行的。但是当人一旦离开了陆地和空气,来到了海里的世界,便突然变得十分被动起来。我可以通过知识的获取,而知道在海底的哪些地方大概会有哪些地貌和鱼群,但这都是一种大概,而非一定。而当人生没有了可以预料的可能性,就突然很难再去判别一个人的得失……
想到这里,从我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细而清晰的哨音,如电台调频,紧跟着是一些脉冲式的嘀嗒。我用力转过身来,半躺着仰望四五米外水的反面,在海里的天空下,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只正在飞翔的巨大的海豚,它也恰好俯瞰着水底的我。
那一刻的天光,从八分二十秒之前的太阳射入这一汪海水,在海豚浅灰色的身体背后,铺排开一张粼粼的天幕。如某种圣灵的降临,亦或是一种拨云见日的天启,它兀自地闪现在这个与我交汇的刹那。

虽然我知道海豚是一种喜人的生物,可当我在光影和海水的移动中,看见它那流线型的身躯,和那健硕的肌肉群在身体侧面所留下的几道长长的凹槽。我心中起初的惊奇竟迅速地被一股恐惧所覆盖。可爱,绝对不是那一刻我对这只海豚的感受。
我,身负气瓶,寸步难行,它,无拘无束,来去自如。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大力,原荒而不羁。它对我的凝视,没有狗的忠贞、猫的冷漠、豹的凶心和兔的胆怯,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巡视。在那一眼之中,它变得无比的宏大,如同海洋和天空本身,而我在那一刻,自动地蜷缩成一个自卫式胚胎的姿态,退回一种原初的无能为力中。
那凝视,仅有几秒,此后那只海豚并没有像我所期望的那样,潜到我的身边。只是匆匆一眼,它便迅速地离我而去,消失在一片苍蓝之中。到来,相遇,以及离开,都是它的选择,而我的存在,在这短暂的邂逅里,竟然变得如此的微不足道,如此的苍白无力。人们总是说动物是有灵性的,但我却相信,我看到的是比灵更远古更亲密的一种存在。
04.
这件事发生已有三年了。这三年里,我继续着自己的生态研究,却在冥冥之中,愈发对 “灵” 这个概念产生了兴趣。
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德国宗教学家奥托(Rudolf Otto, 1869-1937)在 1917 年出版的一本著名的神学著作《论神圣》(Das Heilige),其中谈到了当人面临 “神圣”(holy)的时候,所产出的一种复杂的经历,这种经历实际上是对 “灵”(numen,numinous)的感知。虽然宗教学研究者中有人将 numinous 翻译为 “圣秘”,然而我却更希望用中文中已经存在的词汇 “灵” 来与 numinous 展开对话。
然而,奥托并没有中规中矩地列举出什么是降 “灵” 的时刻,反而极有针对性地在第三章开头直言不讳的说到:“首先,我们要吁请读者全神贯注于一种被深刻感受为宗教经验的瞬间,尽量勿用别的意识形式来描述这种经验。谁不能做到这一点,谁在他的经验中对这样的瞬间一无所知,谁就不要继续往下阅读。” 这诚然已经是一种意会后才能言传的论述方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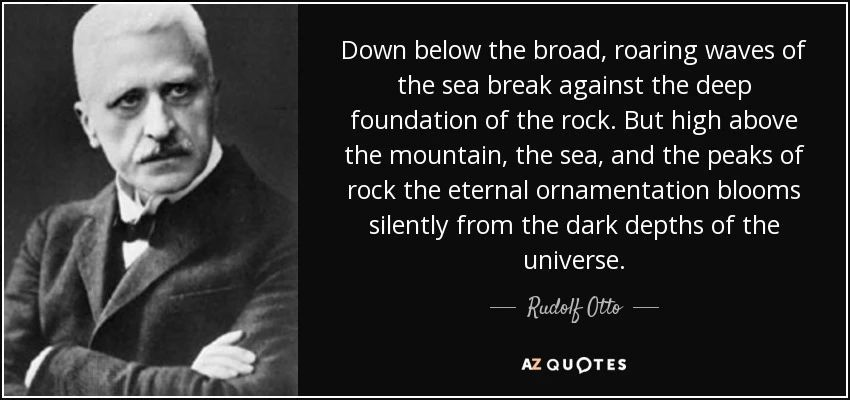
再细分出来,奥托认为 “灵” 是一种复杂的感情结构,他用拉丁文的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nsicans,即 “让人敬畏且渴望的神秘”,来解释这种感情。对于奥托,这 “神秘” 中,有一个人无法解释的 “绝对的他者”;这 “敬畏” 里,有一种让人颤栗且自觉渺小无助的力量;而这 “渴望” 后面,是一种 “超大全能” 的所在,让人祈求获得怜悯。而对于 “令人畏惧的神秘” 奥托的描述是这样的:
令人畏惧的神秘,对它的感受,有如微波徐来,心中充盈着一种深深的敬仰的宁敬心情。它继而转化为一种为稳定与持久的心态,不断轻轻振颤和回荡,直到最后寂然逝去心灵又回到世俗的,非宗教的例行状态,它能伴随着撞击而与惊厥从灵魂深处突爆发出来,或者变成最奇特的激动,变成如醉如痴的狂乱,变成惊喜,变成迷狂。

虽然在我与那只海豚邂逅之时,确实产生了一种类似奥托所诠释的情感,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要从它那里获得任何的怜悯,也并不觉得它的出现,是指射了这个物种背后所代表的某个造物主,或人格神,我也绝对不想在任何所谓的 “宗教” 中获得救赎。我只是觉得,所有的到来和离开,震撼与失落,获得与抛弃,都在我与它的一眼之间。万物的颜色都一时鲜亮起来,直至它离去,遂又归于沉寂。
此前在很多关于人和动物的小说之中,我发现了很多类似的际遇,很多都是和眼神的交汇有关。好比小说家红柯(1962-2018)在 1997 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美丽奴羊》中就讲到一位杀羊无数的屠夫最后竟然被草原上一只美丽奴羊的回眸一眼所击败,身体里发生一种响彻天地的巨响,最后 “他栽倒时手和膝盖着地,刀子扎进沙土,连柄都进去了。” 又或者小说家次仁罗布的短篇《放生羊》中也谈到在羊的眼神中所看到的羊的灵性。亦或是美国小说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描述的他看到狼在濒死是眼中消散的光芒。

虽然,这些类似的经验,使我一直关注人和动物的眼神交汇,但直到看见那只海豚的一刹那,我才明白,原来眼神的交汇,并非一定要是我的瞳孔看见它的瞳孔。因为在当时的距离下,我并没有清楚的看到它那原本就和我一样小的眼睛,但在那一瞬间,我们两 “面” 相对,作为人的我和作为海豚的它,都应该 “看” 到了一些什么,从而感觉到了什么。虽然我不能妄自推断海豚的感受,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明,在那一刻,我的心,确实是被某种不可言喻的力量,深深地击中了。
虽然西方神学对 “圣”“灵” 等相关意义的思考从奥托,还能追溯到荣格和韦伯等等鸿儒,但当我回溯中国的文字,试图从甲骨、简帛和金文中找到 “最原初的” 关于灵的书写时,我发现了更多变幻莫测的意义。
现在繁体汉字中的 “靈”,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一个更为古老的霝字,在甲骨上就已经出现,虽然字源学家们对它的理解不同,但我认为大家都承认这个 “霝” 代表落雨;下半部是个 “巫”,巫史祝卜的 “巫”,可以理解为一种远古的萨满文化。两个部分合在一起,“靈” 就是通过某种萨满文化而祈雨的仪式和过程。但我们不妨将这种意义更扩大一些,将其定义为对于某种降临的承受和感知。

“靈” 字的出现,多见于春秋时期的金文,但极有意思之处在于,这个字的上半部都保持不变,但是关于 “巫” 的下半部,却有诸多不同的呈现方式,甚至是替换和改变。好比黄子鼎上是 “靈”,秦公镈上是,叔夷钟上是和等等。实际上,和 “鬼” 或者 “神” 相比,“靈” 字下半部分的变体和变形多达几十种。但在这么多变的呈现形式之中,我发现,虽然雨的降临来自一个广义范围上的 “上苍”(天),但是字体的下半部分,实则表现了一种祈求和盼望的能动性。人因为有了这样的等待和期盼,才能感知灵的到来。在这些千变万化的靈字中,而我最喜欢的是秦公镈上的,因为下面无它,单是一颗 “心”,却应了一句老话,心诚则灵。

05.
当我在三年后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新英格兰五月已近尾声,我也要收拾起在这片我无法付出任何感情的土地上的生活。这三年来,我时常想起我与那只海豚的邂逅,它那巨大的身体和飞翔在水的反面的姿态,总时常提醒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没有人类的自洽所在。这种独立于人的存在,总能让我在动乱、愤慨和不已的悲伤中找到一丝慰藉。
我必须坦诚地交代,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环境主义者,因为我仍然拥有烧油的私家车,乘坐飞机,且不完全素食,但这并不妨碍我,通过那只海豚和阅读,找到一种自己能够接受的了解生态和其它物种的方法。
那红海里的邂逅给与了我什么,我至今仍词不达意。但我相信,在我匍匐在海床上,静静等待却又失落之后,在转身的惊喜和敬畏之时,在那只海豚与我穿透海流和光影的面面相视之间,我邂逅了 “灵”。
关于作者
陈济舟,1988 年生于四川成都。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哈佛大学区域研究(东亚)硕士。著有小说集《永发街事》。曾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联合早报》金奖。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博士候选人。关于 “灵” 的详细分析,请见笔者 2021 年下半年将在美国期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发表的论文 “The Feeling of Ling (the Numinous): Human-Animal Relations in Three Stories from Sinophone Literature”。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 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 读书会第 23 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 读书会第 6 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 “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 “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 年 9-10 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 读书会第 30 期 | 把 XX 作为 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 Corona 读书会第 7 期 | 全球公卫中的跨国人道主义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 年夏季
- Corona 读书会第 28 期 | 大坝与水利政治
- 特朗普人类学(一):手、谎言、# 魔法抵抗
- Graeber 丨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 黑色海娜:对苯二胺、孔雀与不存在的身体
- Corona 读书会第 32 期 | 松茸的时日
- 编辑手记 | 《末日松茸》: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
- 影视造梦:横店 “路人甲” 们的生活群像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 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 “小丑”
- 哀恸的哲学:“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 年 11-12 月
- 从丁真到拉姆:直播时代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
-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基督教,和圣诞节
- 结绳志的二零二零
- “两头婚” 的实景与幻象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哥伦比亚 2019 年的抗争行动:不期而遇如何构建共同未来的想象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20 年智利抗争:与废墟同在
- 在炉边和在狩猎的女人们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坚持与归属:重思印度新德里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运动的起落
- 无母体的子宫,无身体的器官
- 为什么疫苗是一个社会问题?
- 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对话 Rachel Murphy
- 东北 | 东北完了吗?否思通化的 “官本位文化”
- 与系统周旋:关于骑手劳动过程的田野观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①
- 被绕开的劳动法:外卖平台发展史与骑手劳动关系的变迁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②
- 平台内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③
- 春节特刊・乐 | 为何春晚不再欢乐 ——Fun 的社会性
- 春节特刊・情 | 三代女性的离散与游牧
- 春节特刊・婚 | 先恋爱,后结婚?
- 春节特刊・牛 | 牛的人类学
- 人口贩卖:历史延续与全球难题 | 一份书单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厄瓜多尔的社会运动:从 2019 年十月抗争到新冠疫情
- 世界母语日与母语政治的变迁
- “无障碍” 之障 | 实时字幕、聋听空间与沟通劳动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1 年 1-2 月
- 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 聚焦乌俄 | 最不幸的一代
- 乌克兰书单:超越霸权之眼的民族志视角
- 国际 HPV 知晓日 | 一则关于 HPV 的故事
- 三八节快乐 | 听她们说
- 它们 | 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
- HAU:民族志理论的回归?
- 树 | 它们孤独地生长,悲惨地死去
- 系统人会梦见行动与价值吗?
- 红毛猩猩 | 如何评价 “不止人类” 的照护
- 红色圣女米歇尔与巴黎公社的太平洋原住民遗产
- 大灭绝时期,什么样的命才是命
- 排华与反穆:种族主义的跨国交织
- 李晋:利奥塔之死
- 在工业区与盆栽相依为命
- 照料濒死的河道
- 寇大夫的诊所
- 悼念 | 马歇尔・萨林斯与保罗・拉比诺
- 下一次还将是烈火:反思明尼苏达警察执法暴力的再起
- 为社会而艺术? 社会介入式艺术与人类学的一次圆桌式偶遇
- 与深圳握手: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的艺术实践
- 反高校性骚扰:如何将 “网络风暴” 变为 “制度性防范”?
- 实验艺术,也是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实验 —— 评《实验北京: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全球化》
- 阿兰达蒂・罗伊:作为 “危机制造机” 的政府正将印度拖入地狱
- 打字、身体与性别:从 “打字女孩” 到 “技术直男”
- 迪士尼乐园:没有蜘蛛侠的墓碑,没有入场券的童年
- 动物保护:本体论层面上的「意索政治」
- 爆炸的预燃与回声:黎巴嫩十月十七日革命及其余波
- 五一 国际 劳动 人类学
- 民族视阈:本真性的想象,多样性的局限
- 生病的茶园
- 书单:群众科学到国士无双
- 达尔维什:我们也爱生命
- 在世界环境日演练它们的诗歌
- 高考备考与人生治理(上)
- 高考备考与人生治理(下)
- 高考制度、中国家长与命运的竞赛
- 自由的塞内加尔,非洲的音乐与政治
- 邂逅 “灵”:与海豚的眼神交汇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