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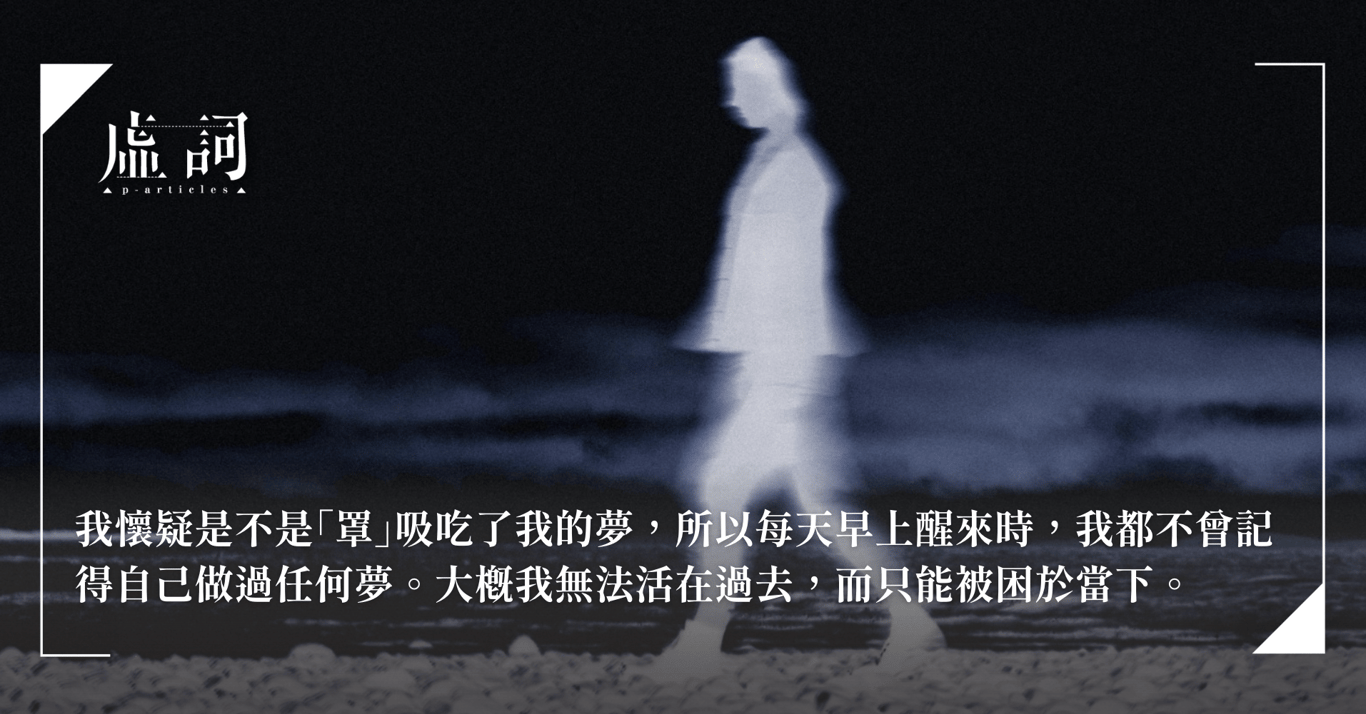
文|周丹楓
回到過去的唯一方法是做夢,而非搭電車,所以他們拆掉路軌,把鐵鑄造成我頭上的「罩」,借此來每晚查看我說過的話,去過的「地方」。
我懷疑是不是「罩」吸吃了我的夢,所以每天早上醒來時,我都不曾記得自己做過任何夢。大概我無法活在過去,而只能被困於當下。我時常去觸摸那些古老的東西——百年樹林砍成的桌子、鑲嵌著繪畫大航海時代風暴的畫框、穿越過整個大平洋的行李箱、爺爺用過的煙斗。我想從中汲取關於「過去」的知識,但我並不想真的夢見它。
在每夜被荒涼景色辛勤洗刷過的街上,人們碰面時,都會交換昨晚自己夢見的事情,若有誰夢見了過去,大家都會請他喝一杯酒,向他好好道別,因為到了晚上,他就會被「捕夢者」帶走,從此消失。
每一份細小的回憶,都是不可或缺的零件,「過去」是唯一能抵抗「它們」的武器。
我的母親前天消失了,她留下了她獨門的甜甜圈——我最喜愛的食物——食譜,以及家中所有的鑰匙,這樣我便可以一直流連於家中,試著對應每一個插入口的形狀,而忘記外面的世界。可是笨手笨腳的我,儘管用上精確到微克的重量計,卻仍然無法還原母親的味道。忘記的人沒有夢。
我問街上那些假裝匆忙的人,如何前往那間母親工作過的甜甜圈店,他們說沿着從前的軌道,一直走到盡頭。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半途折返。在與「它們」越來越激烈的戰爭中,白晝的時間越來越短,夜——夢的勞役愈來愈長,即使你根本沒有回到過去的能力。從前每當我質疑自己的時候,母親都會說:「很多人都不會記得自己做過的夢,所以你無法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回到過去。」
母親幾乎記得每一個自己做過的夢。她常常夢見自己在灰暗的地方踽踽獨行,有時她會夢見一些神奇數字,有時有人會告訴她某些不可告的秘密。她知道總有一天,她也會夢見過去,所以她總是告訴我,我要學會自己做飯。為甚麼人要肚餓,為甚麼我們要進食,增加自己的體重,將自己更忠誠地貼在地面上,我不敢繼續想像。
「它們」說要改造我們的身體,以適應宇宙無限黑暗的環境。我怕我晚上夢見自己漂起,浮到半空——反地心引力是叛人類罪行。
我開始在像貧窮一樣愈來愈巨大的商場裡與其他同樣失去家人的少年們聚在一起,交換各自的鎖匙,每一晚睡在陌生的床上,試圖做既不涉及過去,亦與現在無關的夢。每天,我在不同的廚房裡翻看母親的食譜,餓的時候,我會抬頭望向天空,橋像網一樣相互交纏,在上面高速行駛,是我的夢想,但那比「捕夢」更難。人一旦丟失了習以為常的生活,就會變得焦躁,像找不到自己洞穴的兔子,紅色的眼睛像傍晚高速公路上的車尾燈,暴露在不安的城市之中。睡眠不再是避難所,人再也無法逃亡。
每天,我都比前一天更餓。當我沿着路軌行走時,我就會想像曾經乘客們的樣子,他們是否將我一樣戰戰兢兢地擔憂著「它們」的奴役,或者,夢的捕捉?我記得在母親去參與「戰鬥」的一個月前,她的牙縫開始變大,蛇一樣反覆扭動的舌頭扯出的是我漸漸聽不懂的語言,舌頭後面的深淵是吞食了星光的顏色。
某天,我在一個陌生客廳的牆上看見一幅全家福,相中左邊冷漠微笑的中年女人像極了我的母親,但另外兩個人卻面目模糊,像只活在夢中的人,也許你能猜到他的身份,卻無法描述與細看。在這個客廳的另一面牆上,是一幅用釘標記了著名旅遊景點的世界地圖。有時,我不敢揭開窗簾,我怕窗簾的後面的並不是窗,而是「楚門的世界」。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一到傍晚時分,成千上萬細小的翅膀就會掠過趕着回家睡覺的行人頭上,很多人裹緊風衣,如孤獨的島嶼在風暴中承受海浪一樣那樣安靜。生活在安靜裡的我,如同大多數人一樣,太了解昆蟲來自哪裡,它們從生到死的過程,就像我們不了解「過去」一樣。在被我母親那樣沉默的蒼老雙手日益滋養的摩天大廈前,我看見一隻昆蟲快要撞到堅不可摧的玻璃,我第一時間想到的並不是開門,而是鎖緊它。
但蝸牛總是能夠瓹進室內,在牆上畫出一條條明亮又濕潤的路線,他們背負着的螺旋似乎有一種魔力,讓重量無論如何都不至於剝落。我開始着迷於這種向心的形狀,不知不覺間,在一個又一個陌生,蜂巢一樣的房間裡我也能完成那些困難的瑜伽動作。我更好地入睡,甚至漸漸開始記得每晚做過的夢,於是,我開始忘記自己的母親。
在夢裡面,我總是身穿一件相同的外套,有時,我穿越森林,遇見恐龍,有時,我來到就讀過六年的中學,反覆攀爬數之不盡的樓梯,有時,我打門雪櫃,發現裡面一無所有。對於恐龍,我並不害怕,讓我恐懼的是樓梯與一無所有,因為它們曾實實在在我的生活之中出現過。
「時間」潛入我的夢,像無端的河流,莫名流過幽暗的地面,彷彿只為輕輕曲折水草一般的人。我不清楚精密如電視機的「罩」是否能捕捉到純粹的時間,我聽說「捕夢」其實是源自「它們」的技術。但只要我醒過來,螢幕總是在重覆播放「它們」對人類的殘酷暴行。「復仇」是我們的本能,「懦弱」同樣。
渴望甜的飢餓身體越來越笨拙,就像反覆摺疊過的城市一樣。我想不起過去的味道,當我一再沿着鐵軌前行,沉重如氣球的頭使我一再跌倒——這裡面到底裝載著什麼,像水一樣,當你要一步一步往前時,它就會向另一個方向搖擺,將生命拉扯成力學的一部分。力學,在它永恆黑暗的巨大尺度裡,每一顆星對自身都無能為力,它們只是燃燒。
所有地方都像石頭一樣變得相似,我徘徊過的房間都在打結、收縮,尚未消失人的都在變得更加透明,取代因為酷熱而躲進室內的晝,保衛還沒未被夢到的地方。我開始一再想起那隻撞上玻璃的飛蛾,它仍然在下墜。
城市中心廣場那個母親囈語般的巨大嘴巴日益擘大,彷彿黑色的眼睛與夜相互凝視。向著軌道的更深處走去,想像曾經熱徹召喚我的叮一聲,那些被她發出的「過去進行式」語言勾掉的夢想從「它們」的上方俯瞰時,也是某一個人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