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沖繩.虛實之旅】面對沖繩,解構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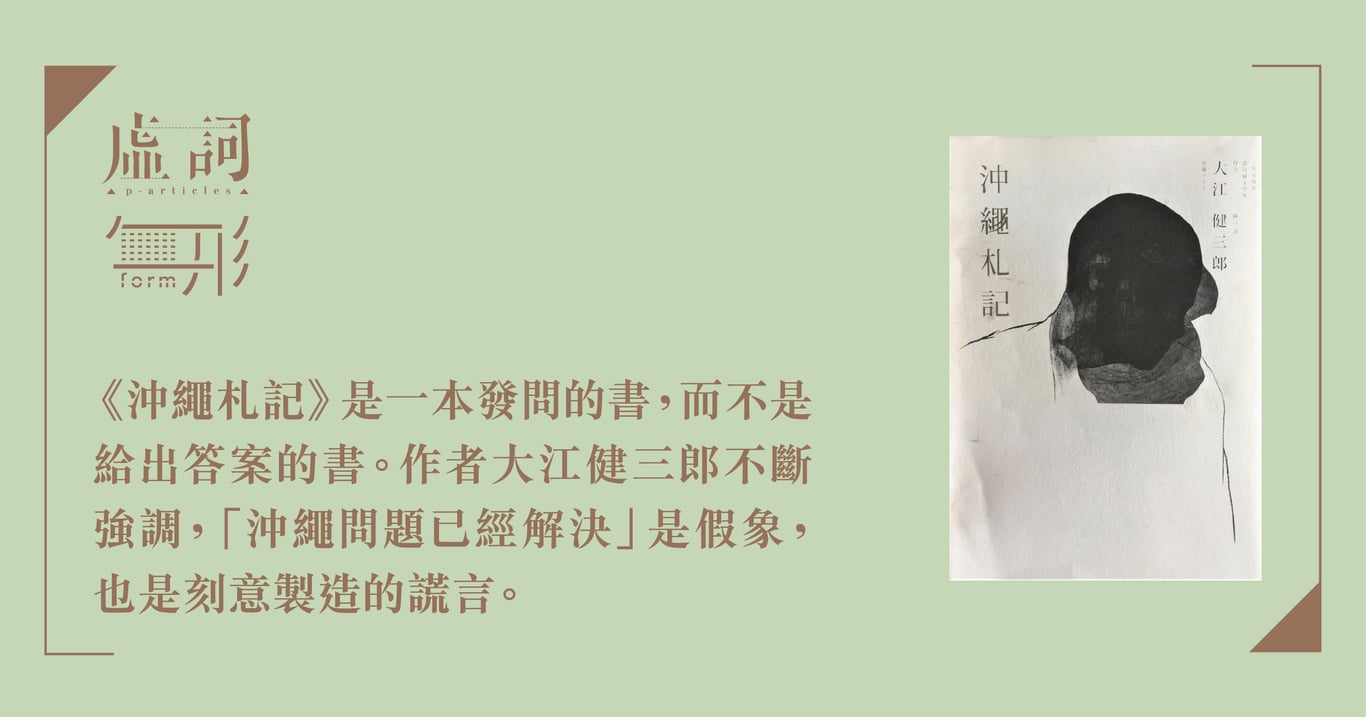
文|董啟章
《沖繩札記》是一本發問的書,而不是給出答案的書。作者大江健三郎不斷強調,「沖繩問題已經解決」是假象,也是刻意製造的謊言。在書中文章發表的一九六九至七零年如是,甚至在今日,可能也依然如是——如果沖繩問題沒有以沖繩人的意願和尊嚴為依歸去處理的話。
先說後來的事。在《沖繩札記》(1970)出版之後的三十五年,即二零零五年,二戰末期沖繩戰役中的座間味島日軍駐守指揮官梅澤裕,以及渡嘉敷島日軍駐守指揮官赤松嘉次之弟赤松秀一,在日本右翼勢力的鼓動和支持下,向大阪地方法院對大江健三郎與岩波書店提出妨害名譽訴訟,要求停止出版《沖繩札記》並且登報道歉。二零零八年,一審宣判原告敗訴;同年十月,大阪高等法院駁回原告上訴;二零一一年,最高法院再次駁回原告上訴。期間原告承認,根本沒有仔細讀過《沖繩札記》的事實。
提告人所謂的名譽受損,基於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中談及在沖繩戰役期間,日軍為了保存充足糧食,減少負擔,而勒令沖繩民眾集體自殺,以表對天皇的效忠。這是大江從一九六五年至七零年間多次到訪沖繩,從親身經歷者及當地歷史學者的研究資料中知道的史實。不過,大江沒有在文中寫明涉事軍官的姓名,所以並不構成名譽損害問題。但縱使在法庭上勝訴,文部省照樣藉著教科書審查制度,敦促出版社刪去「命令」和「強制」沖繩民眾自殺的字眼,從而使責任模糊化。沖繩問題至今並未解決,這是今天《沖繩札記》依然具有閱讀價值的原因。
沖繩古稱琉球王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曾經受明朝冊封。十七世紀初被日本南部的薩摩藩入侵和控制,但表面上依然維持獨立國家的模樣。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於一八七二年設琉球藩王,正式把琉球收編到體制內。一八七九年全國實施「廢藩置縣」,琉球王被迫遜位,琉球國改稱「沖繩縣」,完成所謂的「琉球處分」。一九四五年,日軍於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沖繩成為了阻止美軍進佔日本本土的最後防線。戰役中超過十萬沖繩人死亡,當中包括士兵、民眾和被勒令自殺者。戰後沖繩被美軍佔領和管轄,沖繩人淪為二等居民,為美軍基地提供勞動力,飽受剝削和屈辱。美軍對沖繩環境的破壞,核武及化武的危害,促使沖繩人多次反抗。
可是,一九七二年的「沖繩返還」,即美國正式把沖繩的主權及管轄權交還給日本,並沒有解決問題。沖繩依然是日本政府在國際博奕上的棋子,其中沖繩「帶核回歸」(即連同美軍留下的核武回歸給日本)的妄想雖然沒有實現,但美軍基地的持續存在,以及以沖繩為對抗中國的橋頭堡的思維,並沒有改變。沖繩一日被迫扮演這個角色,便沒法逃離一旦開戰即會成為敵方導彈攻擊的對象,以至全島毀滅的結果。問題是:為甚麼沖繩要一再為日本付出這樣的代價?一再為日本的利益而「被犧牲」(被自殺)?
上面的問題不容易解答,因為沖繩與日本之間,或者沖繩人和日本人之間,在歷史的糾結中,存在著複雜難解的關係。《沖繩札記》就是在這個糾結中,所寫出的沉痛反思。我們絕不能以為,這是一本對沖繩人表示同情、支持,或者為被壓迫的沖繩人發聲的書,因為大江深明自己就是壓迫者當中的一分子,與壓迫者血脈相連。他在道德上無法置身事外。他甚至感到,連代表日本人的所作所為,對沖繩人作出懺悔和贖罪,也是不道德的。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卸下道德包袱,只是自欺欺人,亦是對沖繩人再次的侮辱。站在無可開脫的日本本土人的角度,他的書寫注定不能被沖繩人所接受。沖繩人的「拒絕」具有道德上的絕對性,但這個「拒絕」也是作為一個道德的人所必須面對的。這就是《沖繩札記》所立足的、處於「不可能」和「必須」之間的出發點。
一九六五年,拿著美國發出的證件,第一次到訪美軍佔領下的沖繩,大江健三郎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我為甚麼要去沖繩?」但是,當他直接面對長久承受剝削的痛苦、壓抑內心的憤怒、眼神充滿尖銳的批判的沖繩人,他聽到的是不留情面的質問:「你為甚麼要來沖繩?」為此,他感到深深的羞恥,每每抬不起頭來。但他沒有逃避,而是忍受著羞恥,認真而虛心地探究「沖繩人是甚麼」,以及「沖繩的民眾意識」或「沖繩人的意識結構」的問題。
大江的做法並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他反對由歷史偏見累積而來的刻板印象,也拒絕講述煽情的沖繩殘酷物語。大江試圖從歷史資料中尋找沖繩抗爭精神的形象。由明治時期主張琉球獨立,因反對「廢藩置縣」而在中國自刎而死的林世功(琉球名為名城里之子親雲上),到在日本大學專攻農科,回到沖繩爭取民權,與知縣長期對立,最後被迫瘋的謝花昇。但更為鮮活和難忘的,是眼前親見的談話對象,包括:在少年時期曾參與沖繩戰役,戰後從事學術工作的沖繩知識分子;投身沖繩回歸運動,畢生在日本本土奔走,最後橫死於東京的古堅宗憲;畢業於琉球大學,曾組織學生運動的詩人兼記者新川明氏;或者從事教師工作,同時參與劇場創作和社會運動的戰後新一代。
在這些具體的人身上,大江見證到當代沖繩人的多種面貌。他多次強調沖繩的「多樣性」,以抗拒日本人對沖繩簡化印象——無論是效忠天皇、熱愛「祖國」的臣民,還是貧窮、教養低下,具有犯罪和精神病傾向的異類。在面對沖繩人的同時,大江發現他要面對的其實是身為日本人的自己。所以《沖繩札記》的重要叩問反而是:「日本人是甚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而對「沖繩的民眾意識」或「沖繩人的意識結構」的探究,亦同時是對「日本的民眾意識」或「日本人的意識結構」的探究。自我與他者形成鏡像,互相映照。
這樣的對照帶來的是對日本和日本人的嚴厲批判。當日本人批評琉球人依附明朝或清朝所代表的「中華思想」,大江卻指出,「日本所擁有的,無非是日本中心的『中華思想』的感覺。」而當日本人批評沖繩人意識中的「事大主義」和「自卑」,大江卻指出,遵從「事大主義」而又同時感到「自卑」的,其實是日本人。日本人對自己的問題視而不見,但卻誇口大談「沖繩問題」。所謂日本「本土」一詞其實是一種扭曲。在與「沖繩」對稱時,因為無法稱之為「日本」,又不欲稱之為「內地」,而出現了「本土」的說法。但經過大江的解構,他認為「本土實際上並不存在」。那個「本土」其實是個空洞的、站不穩的東西,並不是日本人以為的居於中心的自己。沖繩的存在意義,就是對這個虛構的「中心」或「本土」作出不斷的批判和抵抗。
在《沖繩札記》中,因為面對「他者」的挑戰而照見自身問題的大江,發現了多重的倒置。這對大江作為小說家的思維產生深遠的影響。他甚至大膽地提出了「日本屬於沖繩」這樣聽來匪夷所思的觀點。大江沒有清晰說明「日本屬於沖繩」是甚麼意思,但把常見的「沖繩屬於日本」的觀點倒轉過來,便可以猜知,這是一個主客關係的對換。真正的「沖繩返還」不是把沖繩及其人民像物件似的由美國手上歸還給日本,也不是甚麼「回歸祖國」,而是從此以後,日本要以沖繩為定義。所謂「日本」,是「有作為主體的沖繩參與在內的日本」,也即是「屬於沖繩的日本」。假使沖繩的權利沒有得到充分尊重,沖繩人民沒法充分參與日本的國政,而繼續被歧視、排除和壓抑,「沖繩返還」就沒有真正地實現。
在大江眼中,「日本屬於沖繩」的積極意義,是「現在在沖繩被發現的、被承認的、依據經驗不斷地強化的、持續不斷的新亞洲中對日本的展望」。他認為戰後沖繩培養出的新人,能夠「用從束縛中解放出來的視野」,「憑藉自由而豐富的想像力,去理解沖繩、日本、亞洲和世界。」這就是具國際主義意識,而不是狹隘民族主義激情的「新沖繩人」和「新亞洲人」。而大江所自問的「能不能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也在此得到肯定。這一點給我們重大的啟示。所謂的歸屬問題,不是中心和邊緣、中央和地方、多數與少數、強者與弱者的關係。能秉持獨立精神、具有豐富道德想像力的一方,才具有所歸所屬的力量。若不,就只不過是強權和惡霸。這也是我們今天還要讀《沖繩札記》的理由。
董啟章
1967 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事寫作及兼職教學。1994 年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同時獲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雙身》獲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獲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出版後,榮獲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2009 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藝術家獎(文學藝術)」。《物種源治.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榮獲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及第四屆香港書獎。2014 年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近期著作包括《心》、《神》、《愛妻》、《命子》和《後人間喜劇》。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