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部電影不能罵這世界真操蛋?——評《大象席地而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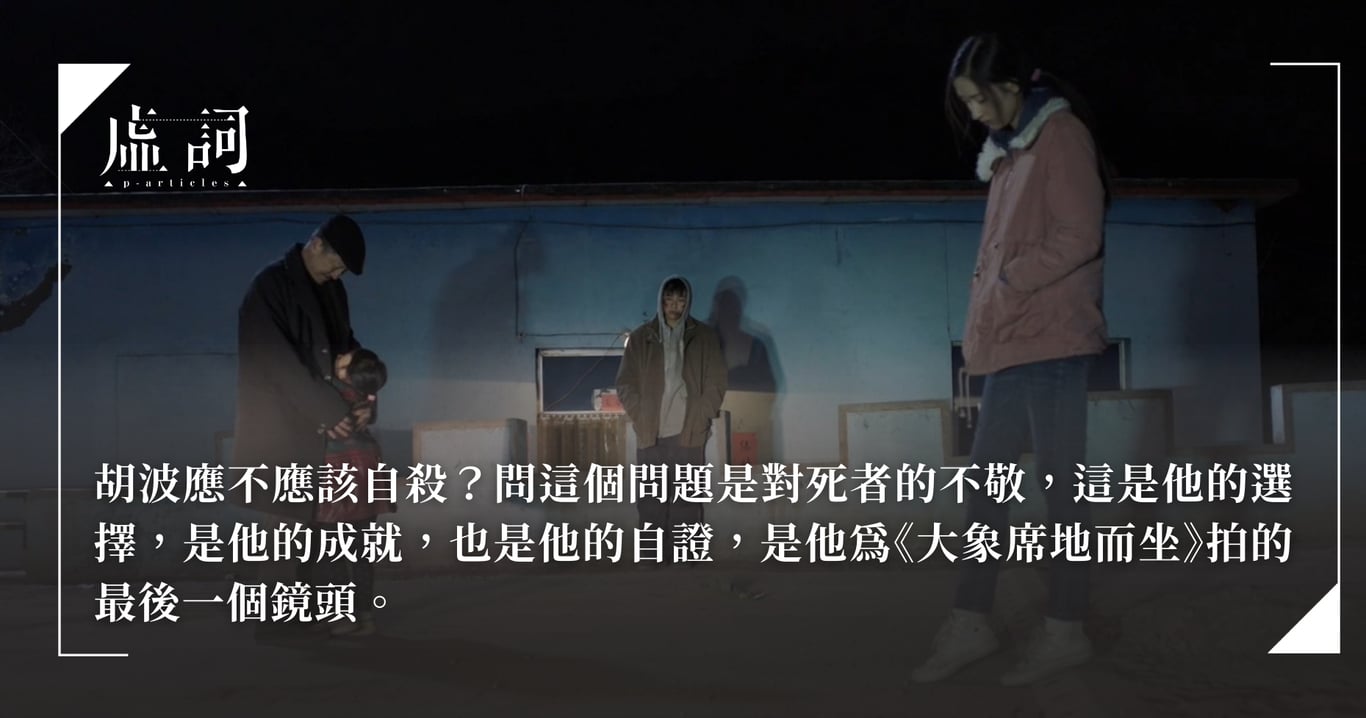
文|廖偉棠
看近四小時的導演版《大象席地而坐》,我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裏如坐針氈,不是因為又累又餓,而是因為絕望,電影裏每一個人的絕望都讓我感同身受,甚至那隻沒有出場的滿洲里的大象,我感覺我就是它,因為腳傷而席地而坐,忍受針扎也不願再往別處挪動。
曾經,我們都相信「生活在別處」,都曾經嚮往過電影裏的「滿洲里」這麼一個名字飽含時空差異性的陌生地方,《大象席地而坐》裏的主要角色分別飾演了導演胡波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除了童年,所有人其實都知道去滿洲里也是一種逃避,都知道去了滿洲里也依然是這個邪惡的世界,老年人老金更是直率地說出了這一大家心照不宣的絕望。但少年韋布跟他說:還是去看看吧。
這場長途汽車站的戲很重要,是導演的最後一次攤牌,雖然攤得有點露骨。胡波體內的各種矛盾在爭執、撕裂,電影裏他以大家坐上了去瀋陽的長途汽車、深夜換乘了滿洲里的車、夜半停車聽見了大象叫聲這一連串的不停歇無對白的長鏡頭作結,修補了,或者說按捺下了這矛盾。現實中,他放棄了修補,電影尚未上映,胡波已經在去年10月12日上吊自殺。
汽車站售票處那裏,當少女黃玲對女童說不要哭了的時候,女童反問:「為什麼不哭?」——那時我看到這個沒什麼戲份的女童,才是心底最深處的胡波。
所以王小帥對胡波說不要浮泛地罵這世界操蛋的時候(原話是:「你以為別人是傻逼看不出來你要表達的東西?衝着空氣罵這個世界多少操蛋這種笑掉大牙的表達?」),胡遷用整部拒絕刪剪的電影回答:為什麼不罵?!
安東尼奧尼的《扎布利斯基角》罵這世界操蛋,用了反覆循環的爆破把象徵西方現代文明的所有物質炸個稀爛;寺山修司《拋掉書本上街去》罵這世界操蛋,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罵這世界操蛋,因為少年們珍惜的一切都輕易地被成人世界毀滅。
那些不罵這世界操蛋的電影,都不是少年拍的。而胡波的稀罕之處,在於他始終惦記着這種少年心氣,像是《麥田捕手》裏霍爾頓的責任,那怕被人視為憤世嫉俗。雖然他同時承認,這種心氣已經一點用都沒有了,在那個萬物苟且的河北小城。
很多人用萬能青年旅店《殺死那個石家莊人》裏那句「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來形容《大象席地而坐》,其實並不準確,後者的大廈崩塌之後並沒有前者歌詞裏的風起雲涌,這個世界沒有一點改變。
原定叫《金羊毛》的電影的一張概念海報上,寫着這麼一句話:「每個人都失去了他最重要的東西。」一片血紅中直視前方的少年,像極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海報的設計。老金失去了他的狗,副主任失去了他的蘿莉,于城失去了他追慕的女人和唯一的朋友,黃玲失去了擺脫家庭的唯一稻草,韋布失去了一切。但是那又怎麼樣呢?他們必須重建這個「最重要的東西」,但卻找了最虛無縹緲的「滿洲里的大象」成為他們的臨時信仰。
惹怒王小帥的,也許是這種強大的虛無、強大的無力感,而不是憤怒與片長。胡波不屬於60後、70後這兩代強悍掙扎的中國藝術家,甚至不屬於他本應該屬於的長袖善舞的80後,他的電影倒是更接近90後、接近日本的廢世代或者坂口安吾、太宰治那種「無賴」作家,然而他本人兼有着片中老金那種拒絕妥協的倔,因此才會徹底和這個世界切結、撕裂。
黃玲砸向與她「師生戀」的副主任的那一根棒球棍、老金捅向流氓的一根桌球棍,與少年韋布一直裝在書包裏壓根不敢拿出來的擀面棍形成強烈反差。前兩者與它們的使用者本來是格格不入的,後者卻聲稱是來自「我爸審訊犯人」的秘技真傳,它們的效用恰恰表明了胡波渴望一次爆發一次叛逆,他本來可以用電影做到的,最後卻只能用自己的死去完成。
《大象席地而坐》裏面的兩個自殺,是胡波的一次自我彩排。這兩個自殺,如果在社會人、在中年人眼中看來,都是不應該發生的:于城的朋友因為撞破于城與自己愛人偷情而自殺,當下大多數觀衆都會想「跳樓的不應該是于城嗎?」——這時電影不過剛剛開始,相信看了三小時後,觀衆們就理解了他的自殺,因此也理解了第二個:韋布的同學在開槍擊傷于城,獲得了平生從未獲得過的「他人的恐懼」之後,毅然自殺。
沒有自殺是矯情的,兩次自殺,一次因為自我欺騙被自己撞穿,一次因為自我欺騙被自己成全。胡波應不應該自殺?問這個問題是對死者的不敬,這是他的選擇,是他的成就,也是他的自證,是他為《大象席地而坐》拍的最後一個鏡頭。因為這一抹死亡的底色,我們才得以尊敬《大象席地而坐》裏那些被專業人士詬病的「任性」。
是的,這部電影並不粗糙,只是「任性」。尤其那些過於貼近的特寫和跟拍鏡頭、無論何時都全開光圈保持狹窄景深的鏡頭,一度讓我胃部一陣陣痙攣。這種不適感經過三個多小時之後變成了一種依賴,我反而渴望再度體驗,希望永遠跟隨這幾個和油滑社會格格不入的「廢物」在這個缺乏景深的世界中游蕩下去,不要終結,也不要知道導演本人已經終結。
有那麼一刻,我以為黃玲走出副主任家外那條無遮攔的空中走道時,她也會跳下去。但是她沒有。其實她也是胡波的一個選項,但是他沒有。
他只留下了一部好電影,說「好」也許有點輕,事實上這是一部胡波的血氣盡含其中的電影,此後,它將代替胡波活下去,繼續罵這操蛋的世界。
(寫於2018年4月6日)
(轉載自廖偉棠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