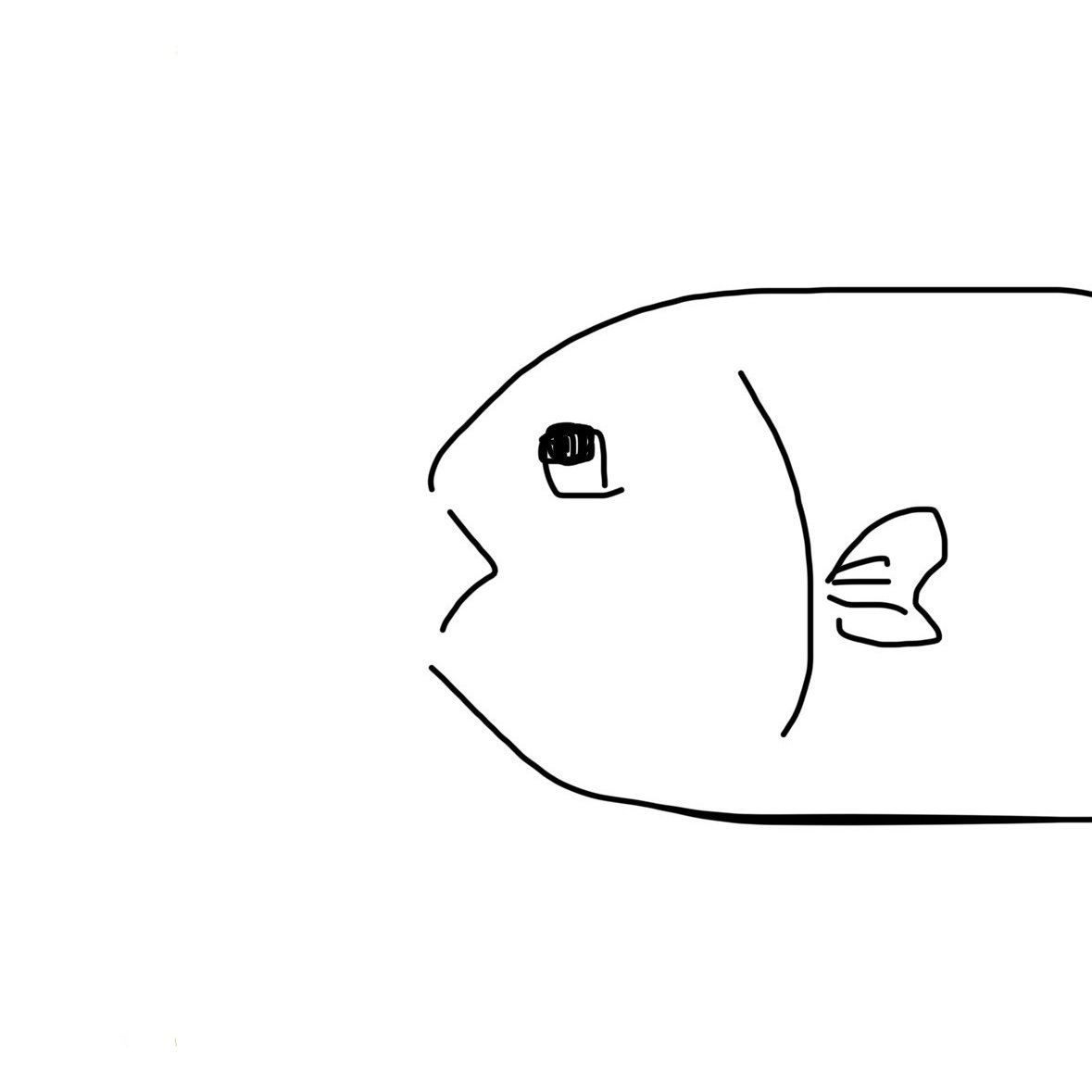七日书第五天 - 走出那个房间
寫寫你最難以下嚥的一餐飯。
Trigger warning:
存在详细的性侵描写
我和L相识是在一场集会上。我们办这场街头集会,为的是收集明信片,写给被捕的人,声援支持他们。涉谷车站口人来人往,没有什么人知道谁被抓了,也没有什么人关心谁被抓了,几乎没有人来写。我和L一起站在受付的地方,守着一堆空白明信片和笔,还有一个喷了红漆充当邮筒的纸箱,百无聊赖。我们开始聊天闲谈,站在那里聊了一下午。收摊时,L加了我的line好友,把他的住址发给我:“有空来我家玩。”
我和L相遇则是更早的另一场集会。我看到他衣着考究,胸口别了一小簇花,在演讲台附近维持秩序。自己也上去讲,慷慨激昂地带着人喊口号,嘴长得很大,光头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格外醒目。
L是社群里行为比较激进的,“支黑”那一个派别的核心人物。彼时,社群中的女权主义者和支黑之间多有矛盾,支黑的惯用语常常带有厌女色彩,饱受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社群逐渐从分化走向分裂,我站在靠中间的位置,感到担忧和悲伤。我在和L相识时刻意地恭维了他,接近他,希望我作为核心的女权主义者,和核心的支黑有良好的私人关系的话,能一定程度地维持着这个社群。
我和L后来又见了一次面,在他家,他的室友也在,他过去留宿的朋友也在。我错过了终电,只能在他家过夜。客厅被他的另两个朋友占了,我能睡的地方只剩他的睡房。在酒精的微醺下,我聊了很多我的过往,和一些深入的话题。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令我们的氛围变得很暧昧。我们开始互相爱抚,小声地发出冒着傻气的咯咯笑。
我度过了不算差的一个晚上。
但第二个晚上很差。那是个带有腥味的晚上。
L在第一次见面后约我下个星期的周二吃晚饭。我一周里有几天要打工,但周二恰巧不用上班,所以我就答应了。
直到赴约当天我才发现那天是情人节。
事情不是很对。但爽约的话可能会让我前功尽弃。万一我跟他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差了的话,社群会变成什么样?我不敢想。即便是结束,我也需要一个体面的结束。
那是一场,还没去就已经希望它结束的约定。
我的不情愿让我迟到了。本来约定在电车站见面后一起走过去,我来不及了,我们就在店的附近碰面。L和我见面后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硬纸袋,一看就知道是礼品。他笑眯眯地把这个纸袋递给我:“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我感到一丝丝的厌烦,甚至是厌恶。若有若无的腥味从袋子里散发出来,但我想这应该是我的错觉,毕竟这样精致的小袋子里不可能放了一叠鱼干。我礼貌地婉拒:“我不收别人的礼物。”他皱皱鼻子,笑容不减:“你就收下吧,我特意挑的。”我没办法,只好道明原因:“我对礼物特别挑剔。我不喜欢不实用的东西,可是对实用的东西也会很严格。所以别人送我的礼物一般会惨遭吃灰的结局,我都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礼物只会成为我的负担。”他笑笑:“这是润唇膏,你肯定用得上的。”我如获大赦地赶紧说:“我不用润唇膏。我甚至不护肤,连大宝都懒得涂。”他向侧面小小地横跨半步,挡在我身前:“你用一用嘛。你的嘴唇太干了,都起皮了。就当是为了我。”他自以为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我。
无名的腥味在空气中炸开。我想转身就走。
但不行。我还要体面。我不能搞坏和他的关系。
但他这话我实在没法接,所以只能接下他递过来的纸袋,心情复杂地跟在他身后,开始盘算我到底该怎么抽身。大概只能快点吃完快点走了。
他预定的餐厅是有名的法餐。侍者的站姿和他的西服一样笔挺,脊背有一种高傲的弓的弧度。侍者接过我和他的大衣,寄存了那个小袋子——谢天谢地,腥味可以离我远一点了——我和他走进去,他看上去好幼稚,就像小孩子在扮家家酒一样。
落座后,他开始跟我聊这家店。这家店的历史,主厨是谁,米其林星星是什么时候获得的,评价有多好。索然无味的话题。我一向不喜欢太主流的事物,所以也对主流的评判标准嗤之以鼻。名声是负担,金钱则是粪土,将这称为艺术家的矜傲也可以,但我实在是难以认同这些虚无的东西。我并非没有吃过米其林三星的餐厅,那次经历更加让我确信,我跟这种地方确实八字不合。我喜爱的是自我的,超出框架的探索,这和争取众人喜爱和赞赏的路线完全不合。我一边抿着餐前酒,一边眺望着厨房,心里暗暗读秒。就像我小时候被我妈逼着去做治疗近视的疗程一样,百无聊赖地通过读秒来消遣,顺便计算自己还需要忍耐多久。
菜色其实还不错,也有几个还不错的。但他一直在旁卖弄,听得我不胜其烦,料理的美味程度也不断削减。他一会儿跟我聊食材的原产地,一会儿喊来侍者,询问跟他关系匪浅的厨师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上班。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想赶紧吃饱肚子走人。
煎熬的一餐总算吃完了。我想要体面,所以也不能直接表露出自己的不耐烦。我只能得体地微笑,快速吃完,并表示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当我说出“我要回家了”的时候,我脸上的表情可能过于希望四溢。幸好他没察觉到这一点,但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这或许其实是一种不幸。
L表示要送我到电车站。我应允:他的请求很绅士,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披上大衣,走出餐厅。风很大,吹开我大衣的衣摆,冷风从我的袖口往里灌,令我后悔我没穿一件可以束住袖口的衣服。这件大衣是90%的纯羊毛料,厚重又温暖,长至脚踝,良好的收腰与下摆放量让它有优雅的剪裁,能衬得人身材挺拔,很适合搭配复古的衬衫与长裙。它应当是很能对抗冷风的,因为它厚实的质地让冷风无法穿透。然而一旦它被吹开,就没有任何用了。我瑟缩地拢好下摆,有点狼狈地按着它,抬脚迈步往前走。
L故技重施。他伸出了他的前臂,拦在我面前。他惯用这个绅士的手势来向我示意方位,我不曾想过这个手势还会挡在我的回家路上。或许这也是一种“示意方位”,他在绅士地向我示意:别往前走了。别回家。
我只能停下脚步。用询问的眼神望向他。我觉得有些尴尬,但他毫不受影响,仍是笑眯眯的:“天气太冷了,距离太远,打车回去吧。”
我说我家太远了,打车回家太贵,我支付不起。那股腥臭又冒了出来。
他笑容不减:“那就打车到电车站吧。让我送你去电车站,好不好?”
别无选择。他的理由还是听起来很正当。他只是送我到电车站,而去电车站的车费并不贵,无论是我还是他都付得起,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人情。
我沉默地跟在他身边,走向taxi站。我用力裹紧身上的大衣。可笑,就像它能成为什么盔甲,来保护我一样。从什么手里保护我?又怎么能够保护我?明明它连冷风都扛不住,轻易就被吹开了。
走到taxi站,自动门缓缓打开,他又伸出前臂,示意我上车。我突然很恍惚,这或许并不是什么绅士,或者这只是包着绅士外皮的要求。这是一个“引导”的动作,不出格,很有礼貌,我没有拒绝的空间,就像人很难当面拒绝一个可怜地笑着的人的请求一样。
我保持着沉默,躬身上车。他很快便也坐进来,并向司机报了一个地址。
——完了。那是他家的地址。
我刚刚一直处于被动的躲避状态。这个信号则让我进入了战备状态。我的脊背绷紧,耳膜鼓动,背上渗出冷汗。他不打算带我去电车站,他想把我带回他家。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想回家。我能跳车吗?他挡在车门开启的那一侧,我的逃生路线上又有他。不行,不行,不行……太不给面子了,太难堪了。我要怎么样才能体面地回家?车里延续着沉默,我的大脑飞速运转,试图找到一个脱身之道。沉默让飞驰的出租车脱离了这个世界,出租车离电车站越来越远,让我离家、离常轨、离我的期望越来越远。我的世界失控了。它被绑在这辆车上,以第三宇宙速度,用脱离太阳系的势头,被抛出了地球。
他察觉到我的僵硬。他突然把手覆在了我的手上。他轻轻抚摸我的手。我的头皮炸开。漂浮的腥臭味也在这时炸开了。他还是维持着人畜无害的灿烂笑容:“刚刚餐前餐后喝的酒让你都上脸了。上我家喝杯茶歇一歇吧。”他顿了一下,又说,“我室友今晚不回家。”
喝杯茶。
国家的“那些部门”的人也喜欢找人喝茶。这些人怎么都喜欢把喝茶当借口?我是爱喝茶的人,茶是无罪的,我要代表茶提出抗议。抗议。我又抗议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抗议。他想把我带回家,我不同意,但我也没抗议。我没法抗议。明明我在社群里是一个风格硬朗,说话直接的女权主义者,我看到性别不友好言论就一定会反驳和抗议,我这样一个强硬的女的——我怎么会如此懦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对他的厌恶和回避,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明明上次去他家吃火锅的时候,一切都好。
我的思绪就这样飘回了几天前。那是一个周末。社群的人开例行的迎新会。开迎新会的前一个晚上我刚在群里因为一个厌女玩笑而跟人吵了架,所以我就不太想去,我感觉太尴尬了,我像一个过于敏感的女疯子。最后是我的伴侣说服了我:你露个面还可以证明你是个好人,你连面都不露的话他们只能认识到群组里跟人吵架的你。
于是我最终还是去了。姗姗来迟,且非常不自在,坐下没多久,我就跑去抽烟。抽烟的房间是这个大房间中的一个小房间,由大块的玻璃隔开,内外都一览无余,又相对比较独立,所以我很喜欢站在门口附近,一边抽一边听。房间里已经有一个男生在抽烟,坐下来,我和他打了个招呼,闲聊了两句。L很快就注意到吸烟室的动向,走了进来。他站在我的左后方,用他的右手,揽在了我的肩膀上。他把我整个人都圈了进去。
我觉得不舒服。距离太近了,小小的房间里,气氛突然变得怪异起来。其他人都还看着呢。我把他的手拍开:“拿开你的狗爪子。”我其实想发火,但想到前一天晚上刚发过火,我今天是为了体现我是个正常人才来的,我不能把事情闹得又僵又难看。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比较婉转但又能表达拒绝的语句。
他嬉笑着放开我。他放开我,房间里的氛围缓解了一点,但又走向了另一种奇怪的方向。我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奇怪,其他人看我的眼神变得有点暧昧。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不想的,还没到这一步,不要这样想。我只是不想像个敏感的疯婆子。我是不是做错了?可是,得体、恰当、不凶、不会被这样误解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什么?
不管怎么样,这个房间是呆不下去了。正好抽得差不多了,我收拾起烟和打火机,逃一样地离开了这个房间。L尾随着我离开,他又一次从左后方靠近我,把他的右手搭到了我的右腰上。
我整个人都炸毛了。当然是在心里。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发火的样子。我要体面。我不能发火。我忘了我是怎么对应的,可能把自己的腰扭了扭,把他的手晃掉了吧。
走出去之后,他向我招手,要我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我之前坐的位置离我太远,房间挤挤的,我需要麻烦很多人才能坐回去。我半放弃地坐在了他身边。反正会议快结束了,没关系,再多忍耐一下下就好。
思绪还是很混乱。他为什么要把手三番五次地放在我身上?我怎么拍掉一次之后,他还敢把手放到我的腰上?是不是我有不恰当的举动才让他误会?我确实不算讨厌他,但我现在觉得他好恶心,然而如果他不是故意的,不应该怪他,那是不是该怪我?我哪些地方做错了?该怪我没有好好拒绝他,或者是我没有守身如玉吗?我是不是该严辞拒绝的?但那样的话会不会有其他人说我太过认真而且太凶?我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该招惹他?可是社群该怎么办?是不是我接近他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结局?为什么我预测不到呢?我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我该拿他怎么办?我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祸根早在几天前就埋下了。几天前的沉默造就了这辆车里的沉默。我觉得我在被牵着往他想走的方向走,我像踩在一个楼梯上,而楼梯的台阶在往下掉。一步错,步步错,如果我把他的手拍开的时候选取的措辞能更正确,我是不是就不至于掉入这样的局面,事情或许就不会变成这样。
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没得出结论,车就到了。
车停了下来,他下车了,又伸出他的前臂,引导我下车。
我放弃了。我四下环顾,他住在一个附近没什么生活设施的地方,楼下是一大片公园,我甚至没办法以去便利店为借口开溜。
他用眼神催促我。
无路可逃。我好想回家。鼻腔里是一直洋溢的淡淡腥臭。我想离开。
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思考怎么办。思考了也没用,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顺从地被他带上电梯,带上楼。他打开房门,又说了一遍:“我室友今晚不回家。”
太可怕了。完了。我真的没救了。他不疾不徐地脱大衣,挂好它,又把手伸向我,示意我把我的大衣脱下来。我的最后一层,不堪大用的盔甲。我一脸麻木地脱下。大脑一片混沌。之前发生过的事都突然蒸发,又从云雾化为具像的棉花,充塞住我的皮层沟壑。乱糟糟地堵住我的思考回路。脑子里同时有一千件事在回放,又有一百件事在反复轮回,即便我调出了这么多参考资料,我还是找不到体面地逃脱的方法。
我把包放在地上。脱下鞋子,踩在他家的地板上。他正在他的房间门口向我招手,又用前臂指引我走进去。这让我对今晚接下来会发生的事的猜测变得更有实感,我突然下定了决心。
既然插入是无可避免的,那么我只要让他满意就可以了。我偷偷瞥了一眼表,距离最终电车还有20分钟左右。他好像想跟我多多缠绵和交叠,慢慢地说一些悱恻的情话,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只有20分钟。
我主动把他的裤子脱了下来,进展太快,他甚至有点慌乱。我把他的生殖器纳入口腔,让它润湿,轻柔地吮吸,用舌尖去挑逗前端,又收张口腔,模拟出一种脉动。他硬得很快,但射得不快,没时间了,我焦急起来。我开始把舌头探入他的阴毛中,舔他的阴囊,手上不疾不徐地刺激着他的冠状沟,再用嘴吮一下。他架不住这般攻势,闷哼一声射出来了。我吐掉满口的白浊。麻利地走掉,拿上大衣,拎起门口地面上的包,换鞋——这是我渴望并在脑中演练了一晚上的事:离开。演练次数太多,实际操作的时候就能做得行云流水。他没预料到事情会是这样,他扶着他的裤子,又挡在我面前,想拦住我。我彻底失去了耐心,将他推开。逃命一样地走了。连大衣都顾不得穿上。
我奔跑着赶上了最后一班电车,到新宿换乘。一手大衣一手书包,瑟瑟发抖的我,看上去可能很张皇。电车里弥漫着终班电车特有的气味:被人的体温挥发的酒精,晒干了的兴奋,淡淡不语的疲惫。但我口腔里是又腥又涩的气味。跑出来时来不及漱口,这是他的精液的味道。和他对话时的那股无名的腥味可能总算有了答案:那是欲望的味道。那是来自他的“我想要”的味道。他的欲望仿佛仍具备实体,阻塞了我的喉咙,我总觉得有一些部分粘在了食道上。我垂头欲呕,却呕不出来。抬起身来,却泪流满面。
车到新宿,我的意识已然混沌。我不知道该怎么界定这个晚上发生的,一切。强奸……奸这个字仿佛像在说“奸情”,一种耻辱,我鼻腔里残留的肮脏更是一种佐证。我失魂落魄地走向回家的那班换乘的车,却怔怔地眺望着它,不愿上车。
我没办法回家。没办法用这个样子面对我的伴侣。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形容我遭遇了什么。
车走了。我回不了家了。列车员说电车站要关了,叫我出站。我像游魂一样走出电车站,眼前是不眠的歌舞伎町。
又是一股欲望的味道。
我跪倒在街边,终于吐了出来。
我到底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回不了家,在深夜的歌舞伎町街头,呕吐。我的眼泪和呕吐物一样都像解除了禁锢一般,滚滚地从我身体里涌出。我前所未有地希望这些事没发生过,希望我真的是喜欢他的,我和他真的是两情相悦的,我真的在同他调情。但我的胃,我的诚实的,不老实的胃,用一股又一股的呕吐提醒我:不是的。我不情愿。我不要。我想要回家。放我回家。
即便身上沾着呕吐物,坐在夜里的歌舞伎町街头,仍然会有男人带着蠢蠢欲动的神情走向我。为什么他们总能理直气壮地认为别人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不理解。我是不是只能是那个满足他们的容器?那我希望我不曾出生。
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没出生过,那就好了。请把我还给我来的地方。如果结局注定是这里,那我打从开头便不愿来到这里。我蜷缩起来。坠下去。世界缓缓地坍缩。掩在我身上。开始做社运后找到同伴的欣喜。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的雀跃。互相之间的信赖。都像融化的糖,覆住了我,结成一层壳。壳上散发着一股腥味。
写在后面:
写到最后其实已经写不下去了,这不是一篇完成了的作品,但我没办法继续写了。写小说需要一定的抽离,但我抽离不了。麻痹感顺着肢体末梢往上爬。腥臭味又出现了,我又想吐。我写的东西其实也和“难以下咽的一顿饭”关联不大:虽然我会约炮,也会把对方称为“小饼干”,但我没吃过这么令人作呕的饼干。
根据真实经历改写。愿意信哪些,那就信哪些。
后来我发现,此人被我冷落后马上转向其他女生,向其他女生出手。我无法忍受,便检举了此事。
检举带来了一地鸡毛。社群分裂。一部分人信我,另一部分人信他。他早在我检举之前,便跟许多人说我是他的前女友,说我把他当人肉按摩棒,说我始乱终弃,把他用完就扔。我说他是强奸,纯属我先勾引后诬告。信他的说法的人仍然不在少数。他也从未向我道过歉,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强迫的成分。
即便是社群内的女生,也会对我说,觉得我是很强势也很坚强的人,似乎不应当遭遇这样的事。也有人对我说,觉得我拍开他的手时所说的话太暧昧了,令他误会成调情。
我也以自己为耻。不够坚强、不够清醒、不够聪明的我。懦弱、绥靖、妥协、退让、服从的我。为了面子的我。想要体面的我。看上去强势的人,就永远不会受害吗?拒绝的悲鸣,就无人能知晓吗?
我明明不想要任何人社死,我只想要我的哭声被人听见。
可能这就是惩罚和报应吧:我一心想要一个体面的离开,最终却落得了狼狈的结局。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是不是从第一次就该发飙,从一开始就不该接近他,还是说我就不该做社运,或者是,我不该出生呢。
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
此事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我仍然没有走出那个房间。它的片段在我的梦里,在街角的法餐厅里,在歌舞伎町的灯火里。
我被追猎得筋疲力尽。一种熟悉的厌倦。我停下脚来。不想再逃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想要这一切停止。我想要离开。我想要走出那个房间。
但我的世界由那个房间的嵌套组成,房门后是另一个同样的房间。
所以,给我最后一击吧。让我真正地,离开这个世界吧。
请不要再来了。请让我,走出去吧。
谢谢你来看我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