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可meta:从形而上学到人文学界的“元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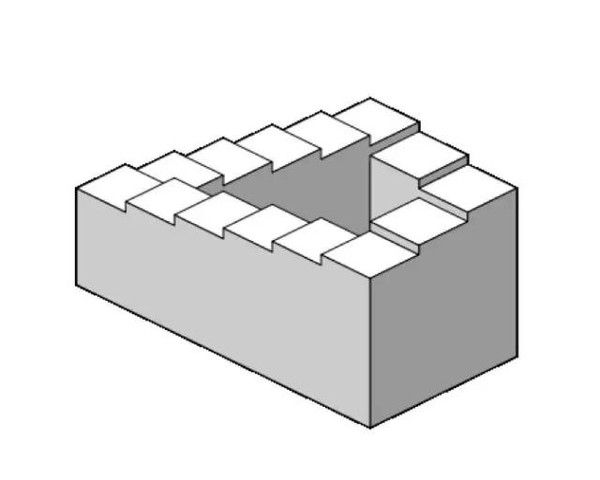
去年我在《关于自由的自由:从NBA自由门看自由的边界》一文中提出了meta-freedom(元自由,即关于自由的自由)这一概念,有些读者认为这种抽象思维偏数学,未必适用于人文学科。其实不然,数学中固然有类似的概念,但它真正大放异彩的却是人文学界,后者充斥着缀以meta的术语,如meta-narrative(元叙述)、meta-language(元语言)、meta-history(此“元史学”与蒙古人无关)等等。倘若逐个查阅其定义,不仅会陷入学科术语的泥沼,而且难以窥见全豹。所以本文从meta的起源与历史沿革讲起,谈谈怎么翻译与理解meta。这个题目比较生涩,但我对语言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历史实在很着迷,只能尽量将它讲的生动有趣一些,希望对同样感兴趣的诸君有所裨益。
meta有两种主流译法,大陆译为“元”,台湾译为“后设”,有趣的是这两种译法,其实对应了meta的两层意涵:自涉性(self-referential)与超越性(transcending)。而meta之所以从希腊文μετά(之后)延伸出两重含义,则与meta最早的复合词metaphysics(形而上学)密不可分。岔开来提一句,其实“形而上学”这个翻译就很值得玩味,属于一种直译化的意译。说是直译,因为“形”与“上”恰好对应了physics(自然之知识)与meta(之上)。说是意译,则因为它又典出《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如同佛教初入中国时,教众以中土思想相比拟的所谓“格义”之法。如此看来“形而上学”可谓妙手天成的佳译。和佛教比较成功的直译如涅槃、菩萨等一样,“形而上学”也完全被内化到现代汉语之中,以至于听起来不那么“直”了。(不少人表示形而上学熟是熟,但还是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这是因为这个词毕竟还是直译,就像菩提是什么大部分人也说不上来)
回到metaphysics这个词来,Metaphysics是亚里士多德讨论形而上学的著作,不过他自己却并不认识metaphysics这个词,也并未将之编纂成集。(Metaphysics是后人对亚里士多德十四部著作的统称)亚里士多德将这一部分内容归为四类: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第一科学(First Science),智慧(Wisdom)与技术(Technology)。百年后希腊学者将之整理成册,统一命名为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ὰ(物理学之后的内容),意在提醒当时的学子,必须先学习亚里士多德Physics(物理学)一书中的内容,才能学习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ὰ,也就是英文中的Metaphysics。
如此看来,meta在Metaphysics中的意涵非常朴素,就是希腊文原意(之后)。台湾译法“后设”从形式上更接近一些。但这不足以解释meta-history,meta-logic这些术语的意涵,它们可并不是什么历史学或逻辑学的进阶课程,更别说还有meta-joke这些戏谑的概念。这其间的演变,就涉及自然语言的演化了。
自从Metaphysics(《形而上学》)从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书变为哲学研究的一大范畴,人们对于meta的理解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形而上学这门学问其性质的影响。尤其是世殊时异,拘于信息传播、书籍收藏的限制,到了中世纪了解metaphysics得名由来的古人少之又少(现代人反而能借由翻阅专业研究快速了解)。于是当时出现了错误的拉丁文注解,将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ὰ注解为“超越于自然学的科学”,这显然是误会了这部文集的本意,倒是暗合了网民津津乐道的“科学尽头是玄学”这一朴素信念。
不过从长时间跨度来看,使用语言的人可能会犯错,语言本身却无所谓对错,其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代代人的使用习惯所层累而成的现象。因此有趣的是,meta本被用来修饰Metaphysics这本书,后来却反过来被metaphysics这门学问重新定义了其内涵。不得不说,这倒有几分禅宗所谓“曾见郭象注庄子,却是庄子注郭象”的味道。
既然metaphysics是超越自然学的科学,meta自然就具有了一种超越性,这也是台湾译法“后设”所力图表现的。“后设”不仅保留了meta“在……之后”的含义,也突出其设置于原范畴之外的超越性内涵。不止于此,自然学本身也属于科学范畴,而metaphysics既然是超越自然学的科学,(即超越科学的科学),其中便内嵌了一种自涉性质。事实上,这种自涉性反而成为了如今meta一词的主要用法,如我前述的meta-freedom(关于自由的自由),meta-joke(关于笑话的笑话),就属于这一范畴。就自涉性而言,“元”这一大陆译法较“后设”为佳。
虽然我一开始玩笑地提到meta-history(元史学)与蒙古的元史无关,其实他们还是有相当微妙的联系。元朝的国号,取的是《易》中“大哉乾元”之意。忽必烈说:
昔为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元的本意就是大到极致,因此蒙古人用以表现帝国之恢弘。还好忽必烈认为“大不足以尽之”,不然中国史就得多一个大朝。
言归正传,把meta译为“元”,那么“元”的这种“大之极也”可以描绘出meta这一概念其外延之广。从自涉性的角度,meta是对原概念的进一步抽象,如数学中的抽象代数,可视为对于代数之代数。初等代数中的加减乘除全部都需要重新定义,在更高的抽象层面,初等代数沦为抽象层面的一个特例,其最基本的规律也不复成立,如a+b不一定等于b+a。用非数学的例子的话,美国历史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借由meta-history(元史学)的概念,表达与研究人们书写历史的基本模式,将之分为多种子类。虽然海登怀特的书远比一般历史著作抽象,但同时他的涵盖范围也广得多(基本上任何历史书都可以借由他的理论分析,而不拘于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一言以蔽之,对一个概念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会极大地拓展其原本的外延(当然形式上也会变得更加艰涩)。meta这种“大之极也”的外延,正符合“元”的本意。同时“元”也有基本、本质的含义,也符合自涉性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由metaphysics而衍生出的自涉性与超越性,是在英文中已经发生的现象,大陆与台湾只不过在翻译时各侧重了其中一点。反过来说,要捕捉meta的本意,需要将“元”与“后设”两种译法结合起来。一般来说,人们通过梳理原文来讨论翻译的好坏,本文借由翻译来重塑对原文的理解,这也算是一种meta。
讲了这些可能有些枯燥,我个人的研究与笑话相关,就举一个meta-joke的例子放松一下:
一只鸭子,一个牛仔和一个gay一同进了一间酒吧。酒保见三人落座,走了过来。但始终没人开口说话,酒保在一旁等着,也不说话,场面极度尴尬。
过了十分钟,酒保实在忍不住了,怒斥道:
“你们他妈的是不是走错笑话了?!”
这是我给老美讲的压箱底笑话,其笑点本身就基于美式笑话这个整体(所以是一则关于笑话的笑话)。鸭子、牛仔和gay都是美式笑话的常客(但很少同时出现),酒吧又是美式笑话的常见场景。当鸭子牛仔gay这笑话三巨头同时出现在酒吧,美国人会期待究竟有什么爆梗出现,“谁都不说话”这个情节更是吊足了胃口,最后答案揭晓,他妈的这几位高深莫测不说话只是因为走错笑话片场了。但我给华人讲的时候反响比较一般,因为缺乏相应的背景经验。
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meta-joke,虽然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
为什么每个笑话的主人公都是小明?
因为笑点低的人看到小明就开始笑了呀。
笑话本质上是一种叙述。但上述笑话跳脱出讲故事的语境,点出了故事外的“笑点低”观众的存在,从而利用听笑话的人对于“小明”这一笑话知识的敏感,引发笑点,这也是meta-joke。当然这则笑话美国人肯定听不懂了,不过我也听过一个结构是非常类似的英文段子,是一个哲学教授讲的:
Today I am ganna teach you how to tell a joke. First, if you have an animal in your joke…make it a duck!
我五年前听的时候一头雾水,身边的美国学生则笑的乐不可支。现在想来,合着美国的duck就是中国的小明啊,笑坛巨子。
如果对戏剧理论有所了解的读者,可能会察觉到,这种meta-joke的形式经常出现在舞台互动之中。简单地说就比如德云社的相声讲到一半忽然抛梗给观众,或者《武林外传》中的角色多次与镜头互动:

从理论层面来讲,这就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Eugen Bertholt Friedrich Brecht)所强调的间离(alienation)手法,即刻意打断观众于戏剧舞台中的沉浸感,营造一种陌生化的互动效果。与之相对应的是斯坦尼拉夫斯基的经典学派,即要求演员“忘我式”的演出,以营造充分的沉浸感。所以《喜剧之王》中周星驰才捧着他的《论演员的自我修养》这么着迷。(国内还强调以梅兰芳为代表的第三体系,非但不是沉浸式,也并非在沉浸与互动之间切换,而是完全非沉浸式的表演,京剧演员都充分意识到舞台的存在并无意于消除与观众的这一“隔阂”,因此又将三大体系统称为梅斯布)
间离效果冀图观众充分意识到舞台的存在,在沉浸与疏离之间获得独特的观影体验,这一思路与文本创作中的“意识流”不谋而合。例如,皮兰德娄在其经典意识流剧作《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中,直接把抽象意义的“角色”作为自己剧本的角色,可谓是关于角色、舞台、与戏剧的一次meta三重奏。
上述元笑话、间离、与意识流语境下的meta,主要体现了自涉性,即关于X的X。但需要指出的是,“关于X的X”这种通俗表述具有歧义,我们来看一道思考题:
如果meta是关于X的X,那么同样是关于历史的历史研究,meta-history(元史学)与historiography(史学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不仅有,而且很大。其原因在于“关于”这个词本身具有模糊性。史学史是关于前人编写历史的历史,自身也是一种历史。元史学则是关于前人编写历史的理论,自身并非历史。前一种“关于”是内容上的亲近性,后一种“关于”则是形式逻辑上的关联性。因此只用自涉性来理解meta是不够的,相对来说,史学史一词代表了纯粹的自涉性(关于历史的历史);meta-history则不仅具有自涉性,也具有“后设”所提示的超越性(它不再是历史,而是一门理论)。这再次体现出“元”与“后设”这两种翻译(其实相当于两种注解)对于我们理解meta不可或缺。
总的来说,如今meta这一词缀在学术讨论中,其含义兼具自涉性(元)与超越性(后设)而更偏前者一些。当然也有反例,如meta-economics就不是“关于经济学的经济学”,而更像是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学。如前所述,语言的含义总是流变的,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没有对错之分,每一个词都是一个理论,也是一段历史。
meta是一种思维,具备了这种思维看世界就像多了一层滤镜,万物皆可meta,乐在其中矣。
网上的段子说:
一个经常放鸽子的人这次居然没有鸽,这也是一种鸽。
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元鸽”。
本文选题比较艰涩,能看到这里不容易。探究语言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历史脉络,是我个人的一大兴趣,所以下面整理了我在matters上发的关于语言文字的几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