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鱼:献给所有爱做白日梦的人
端午假期,《热带鱼》(1995)修复版将会在北京重映。这则消息与我没什么关系,它是大银幕时代的语言。人们需要去电影院里看电影,或是在意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才会有意提起。
我大多数电影是在逼仄昏暗的高中教室里看的,课桌上垒着高高一摞书,只露出一双眼睛,可以看到讲台、黑板和老师。低头的时候,就是手掌宽的屏幕,里面放是枝裕和、北野武、欧容、韦斯·安德森,还有一些被提过名字的青春片,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段日子看电影的感觉,而忘记了电影本身。
直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电影院,而将所有感情和期望都寄托于家里的小屏幕。《热带鱼》也是这么看完的。
这部电影诞生于90年代,让人难免产生一种浪漫联想:真是智力活跃的90年代。
这个词是我从张爱玲那里重新发掘得来的,第一眼就觉得恰如其分。今天人们都说什么“繁荣”、“黄金年代”、“不可再现”,有一种自我陶醉在里面,对于介绍和理解实际情况并没有什么帮助。
《热带鱼》的主人公是一位即将参加联考的中学男生阿强,平平无奇,爱做白日梦。喜欢上同校与自己一起搭公车的短发女生,写了一封信,迟迟未送出。他在信里表达了要与女孩共乘潜水艇游海底的幻想,始终没能让女孩知道。但因卷入一起绑架案,这个美梦却实现了。
阿强多么想逃避联考,多么想让海底飞出热带鱼的梦成真啊。但是他逃不了,他必须参加,学校、老师、家长都只关心这件事。也许他送出那封信,会得到他的梦中女孩答复:对不起,我想我们应该先努力准备联考。
距离联考还有短短一个月,他的模考成绩一塌糊涂。父亲来参加家长会,好像特地穿了一双新鞋,不太合脚,中途掉了一只,又急忙跑回来捡起,穿好。等面对老师时,更难为情了。回家后,阿强身上关于联考的压力又增加一重。
这都是顺理成章的,只有绑匪不是,和以往做的白日梦一样,突然就出现了。竟然有人绑架我,带我去做我喜欢的事。被打晕时,出现了海底鱼群散开的画面,这预示着阿强已经进入了海里,进入自己的白日梦。
白日梦就是没什么道理的。凶悍一点的绑匪也出车祸死了,留下那个喂人质吃饭还要耐心吹一下的阿庆。他开车带两个孩子回老家,一边掩人耳目,这毕竟还是一场绑架。大夏天,三人吃同一根冰棍,眼睛直勾勾地,要将整个冰棍勾去了。绑匪阿庆也不过是个没长大的小孩。
电视新闻里说,阿强多么可怜,就快要联考了,还被绑架。联考似乎比生命重要。阿强眼神迷茫,可能还在做一个没有联考的梦,但同时又不太确定。绑匪阿庆却慌了,他找来妹妹阿娟的课本,给阿强复习用。
这个糊里糊涂的绑匪,从这里开始回到了秩序的边缘。阿娟的故事被揭开,造成其悲剧的是另一种顺理成章。而绑匪阿庆也有了顺理成章的身份,他是阿娟的哥哥,是践踏梦的人,就像阿强世界里的学校、老师和家长。

阿娟的故事为这个白日梦带来了实感,她曾经做过另一种梦,与阿强完全相反的梦。如今,这个女孩真的不再做梦了吗?可是她找到了不可能出现在这片海的热带鱼。阿娟和阿强两人互相映照,或沉重或轻盈的梦,一体两面,展现不同的命运。
电台里经常读的那些听众写来的故事,是他人所做的白日梦,但此刻却成为阿强的冒险。

他一直讲的那个故事:海底的热带鱼吃了九千九百个孩子的梦,然后长出翅膀飞出大海。在被带到海上逃避追捕的那天,清晨看日出,飞出的不是大鱼,而是直升飞机,就预示着这个梦将要结束,只能到这里了。
结尾被绑架的另一个孩子写信到电台,讲出了热带鱼的故事。白日梦与现实世界似乎就此连通了,众人期盼的那条热带鱼终于飞出大海,穿过城市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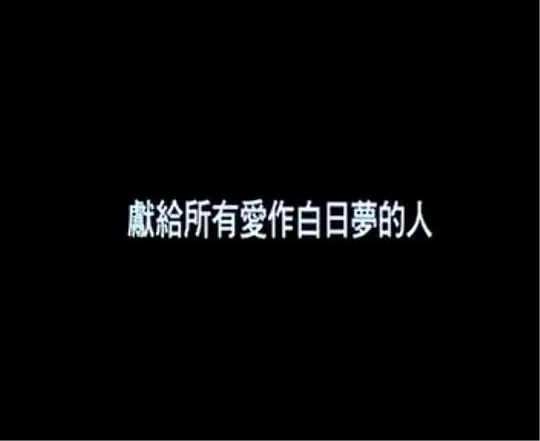
“献给所有爱做白日梦的人”,这是影片末尾的字幕。直到2002年,台湾联考取消。很难说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既然联考最终都能取消,还有什么白日梦是不可实现的呢。我们都没有见过,既不能断定是真的,自然也不能断定有假。
我没有在昏暗的高中教室看过这部电影,但当时一定做过这样的白日梦:如果我被绑架,就不必参加高考了。出车祸不行,生病不行,只要人还在,只要还有意识,只要能写字——也许不需要能写字,能口述就还能参加高考。今年还看到新闻说,感染了新冠病毒的高中生也顺利参加了高考。在人生前十八年里,竟然就有一件事,逃也逃不掉。
写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是要“安利”这部电影,还是教所有人做白日梦,但无论是哪一个,都是让人短暂逃避的好方法。
祝你观影愉快,祝你做梦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