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雾的早晨

上学很波折,毕业也很晚,一直觉得没接触过什么太复杂的社会,遇到的人,遇到的事,大多都是善良友好。但做过一些离奇的人生选择,也借此心安理得地允许自己和身边人多多少少有一些时差和疏离,习惯自己是和主流不大一样的人,不敢太享受自由。平常和人离得远,关注的议题和时代离得也远,在大部分时候保持不体面的怪诞或沉默,甚至要刻意地试图「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因此也被人质疑、批评、或「看穿」。那是一个让我舒服的常态,是更漫长的青春期,我也因此承载了一点关注,受到一点喜欢,并且借此把自己推得离常态更远,把自己保护得更严密。
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有运气的成分,有时代的印记,总之,我被造就成了一个充满善意的过路人。很难融入大的团队,对完全商业社会疑虑重重,谨慎地做一些自己完全可控的事情,对客观的标准和市场的走向、需求视而不见,或有时假装视而不见,并艰难地、如履薄冰地达到某种自洽和平衡。
在生活里,在与人的情感中,我也是一个下意识退后的姿态,只是被社会化得太好,第一反应还是要礼貌、热情、好奇、和善,但脚步在迈出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后撤的姿态。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理想状态,是退居某种隐喻意义上的田园,我对自己的期望仍是在不被打扰的寂静处走得更深,而不是在喧嚣凶猛的地方走得更远。
虽然听起来也许稍显消极,但我并不因此斥责或质疑自我——我仍然更偏向于凭借文学性、诗意的瞬间决定人生走向,而不是被某种或某些固有的社会身份定义。我仍然爱虚构多于非虚构。我仍然总是在退后的时候感到无限的平静。我仍然试图最大化保有自我,哪怕它有时候代价巨大。只是,和过去那个熟悉的自己比起来,最近的我可能没那么在意「自洽」这件事了。
我很喜欢思考「做自己」这个概念,它被过度的商业化,以至于最早被提出时的本意已经模糊,但有趣的是,在每个不同的层面去注视它,都有完全不同甚至迥然相反的解读。现在的我,想给它的一个新的、我所认同的方向——「做自己」有一种解读角度,是”be less self-conscious.“
「自我意识」在英文的语境里,有时会有一种偏负面的意向——自我意识如果过剩,是会捆绑和束缚人的,很多时候,它是社会观念潜入到脑中,指向人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责备。它的危险之处在于人们常常把它内化得过于彻底,以至于我们甚至看不出它有时并不完全来自「自我」,而是来自「他人」的视角,从而成为一种障碍,让人画地为牢。如果不好理解,每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脑中会出现的「这样是不是不大好」的声音,大多并不来自第一人称的自我,而是想象中的他者。它当然会引导人做出理智成熟、更被想象中的观众所认可的选择,但自我意识一旦过剩,人也会变得思虑过度、害羞扭捏。
类似波伏娃说女性是第二性,就是形容她们总在想象被第一性观看,是为「他者」服务的,社会观念削弱了她们的主体性。时代发展到现在,关注与名气更易得,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矛盾了,而是每个生活在社会景观里、同时又想活出自我的人都在挣扎的一个母题。
如果我把自我比喻为表演者,把外界的他者比喻为观众,把在社会视线中的一切行动比喻为表演。我总想象过去那个努力保持自洽平静的自我,是在仅仅为那些爱我、在意我的观众表演——这已经是克服了「我在为所有人表演」的心态,但还是不够。它仍然满足的是他人的期待,哪怕这个他人的目光是善意的、温和的、值得驻足的、对人的发展有益处的。在想象有人注目的环境中,自我仍然是向内收缩的,叙事仍然是试图要朝向一个公认的好的标准发展的,形象仍然是完整的、它仍是一个安全、自洽、收敛形态的自我。
那么理想状态是什么呢——我试着去想象它。恶意或者善意,被爱或者不爱,都不重要。去做舞台上的表演者,光打下来的时候四周是黑的,最好没有观众,哪怕有也是暗掉的、不被注意的,或是像博尔赫斯所说,「有五百个同时代的个人这件事并不重要,因为我不是对某种多头的怪我讲话。不,我是对这些个人的每一位讲话,因为如果我是当这五百人发言的话,我们其实是两个人:他和我。」——个体是唯一真实的。被内化的、想象中的群体的意识、观众的朝向、社会的目光,都是假的。舞台上允许快乐,允许冲突,允许痛苦,允许媚俗,允许失败,允许美丽,允许丑陋,允许意气风发,允许愚蠢至极。
让社会笼罩我却不奴役我,让时代流过我却不渗透我,让观众看见我却不塑造我,我是展开的,也是坚固的。「自我」的舞台在观众席消失之后,才亮起来。祝我获得不看观众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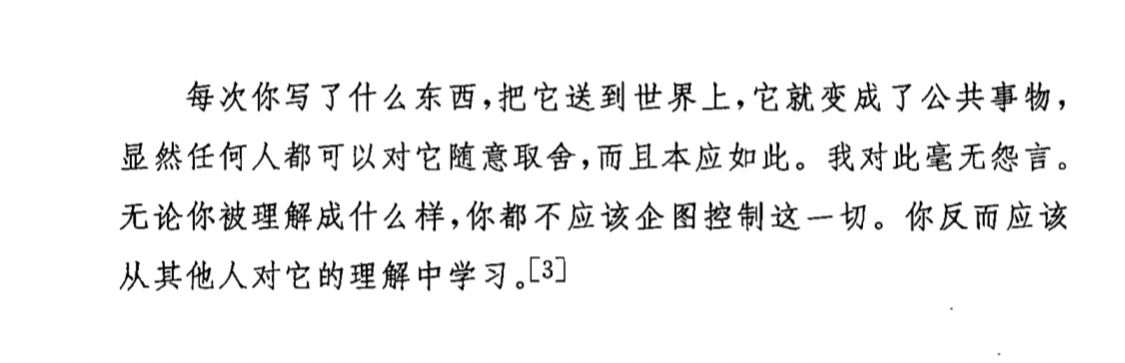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