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革命的局限性:斯里兰卡起义的经验教训

革命需要信徒。怀疑革命的胜利就是已经背叛了革命。正是通过逻辑和胆识,人们发起了革命并拯救了它们。如果你缺乏这些品质,你的敌人就会胜过你;你的敌人只会在你的弱点中看到一种东西 — — 他们自己的力量的尺度。他们的勇气将与你的胆怯成正比。
——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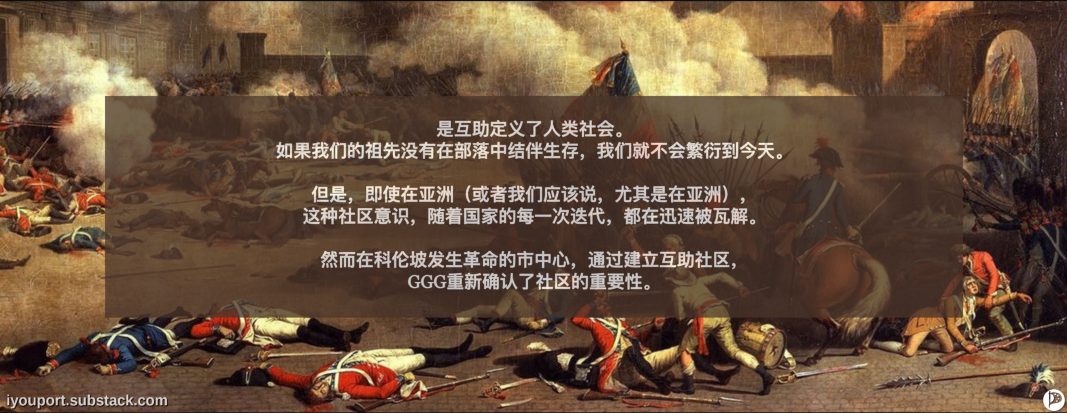
社会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连串的斗争遇到并克服了它们的限制。随着战术、口号和组织形式迅速传播到不同的国家,这些序列往往会以一连串浪潮的形式展开。这些浪潮往往发生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时候,这在世界不同地区创造了一系列类似的条件。

首先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如下。
1、
一旦起义开始,任何选举都只会赋予旧政权以合法性,将其包裹在革命的合法性之中。7月20日议会对拉尼尔的选举为这一普遍规则提供了一个典范级的案例。没有理由相信所谓的大选能有任何不同。
2、
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军事上,打败武装部队是可能的。但对于我们这个世纪来说,需要重新思考其可能性的条件。
当武装部队被叫到街上,但拒绝向人群开火时,革命的局面就会出现。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最初的起义中袖手旁观的武装力量后来又重新出现,成为革命命运的最终仲裁者,确保了旧政权和后来者之间的连续性。
3、
斗争在其将无产阶级的不同片段编织在一起的能力中找到力量。起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整个国家,来自各行各业和社区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参与方式。这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建立在种族和宗教分离基础上的、被几十年内战蹂躏的社会中尤为重要。
然而,存在于社会其他部分的分离往往会在斗争中重新出现,特别是在其早期成功之后。这一直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革命似乎无法克服的局限。
4、
反乌托邦的斗争倾向于采用对腐败的批判,作为一种自发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日益由专制强人主导的世界里,这有某种意义,特别是在斯里兰卡。
但同时,对腐败的批评歪曲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中的实际作用,因为它假定国家可以找到摆脱当前危机的方法,只要它愿意,它可以选择避免实施紧缩政策。这种混乱也是为什么反紧缩斗争往往导致重新洗牌而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原因。
政权倒台后,人们面临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逻辑仍然存在。革命带来的政府往往发现自己实施的紧缩措施与最初引发抗议活动的措施极为相似。
起义要想更进一步,就必须面对国家在与全球市场的关系中断时如何吃饭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毕竟,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并存在于其中,无产者才能够进行自我再生产。这正是限制所在,也是今天的斗争所要质疑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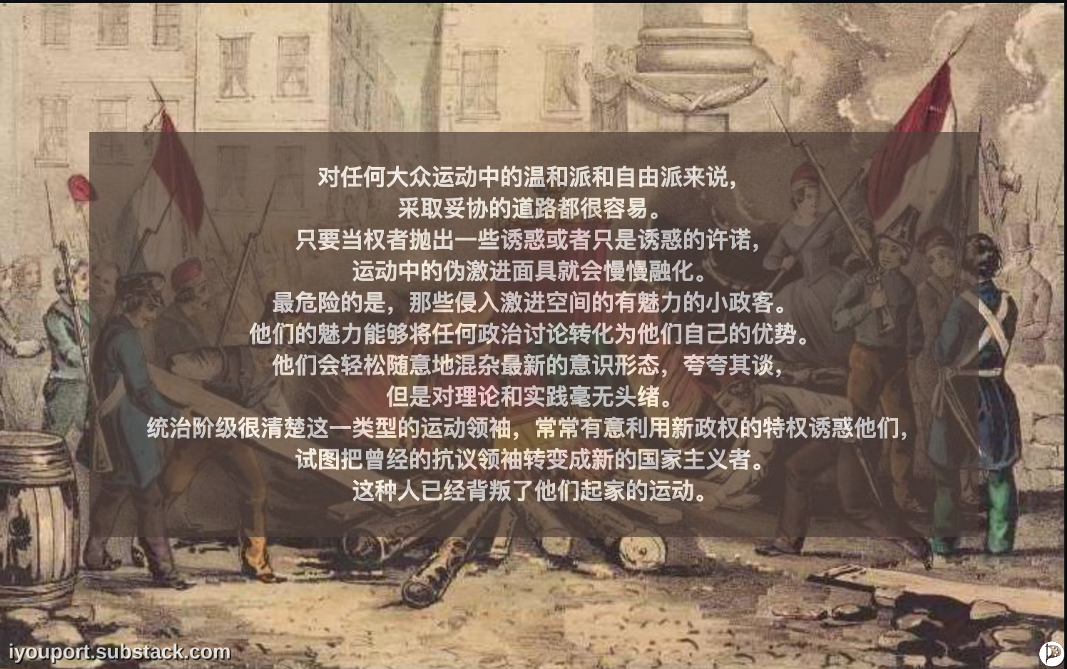
5、
起义往往是由某一社会群体的斗争引发的。然而,随着斗争的地理中心的转移,阶级构成也往往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抗议活动向大城市转移,城市中产阶级最初成为重心。例如,斯里兰卡的起义首先从农村腹地的农民抗议开始,然后转移到科伦坡周围的郊区,再到首都的中心。在那里,城市中产阶级最初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占领行动中。随着抗议和占领的势头更加猛烈,科伦坡随后被来自城市和国家各地的蜂拥而至的无产者占领,最明显的是在7月9日。在到达首都后,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到整个国家,甚至在首都保持一定的向心力。这种地理上的集中会使少数民族人口的参与更难以得到保证,比如集中在国家北部和东部的泰米尔人。
同时,斗争的地理环境与权力的地理环境并没有整齐划一。斯里兰卡的一些革命者认为,下一阶段的斗争将需要将科伦坡作为中心,并将活动分布在全国。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 夺取并掌握权力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因此,未来的反叛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地图?通过占领权力大厅,革命者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夺取了权力;但国家仍然在他们的背后继续运作。这也许是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不足以使革命不可逆转。对某些人来说,权力存在于基础设施中,即 “构成社会真正权力的有形组织”;但是,什么是基础设施,占领和重新利用而不是直接阻止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崩溃和潜在灾难的情况下?
6、
起义之后,往往会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因为被斗争浪潮塑造的激进分子会找到彼此,并制定出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的方法。
斯里兰卡可以借鉴全球其他地方最近十年的实验。也许最有力的是苏丹的经验。在2013年的起义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抵抗委员会,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为下一波斗争做准备。具体来说,这意味着:维护邻里社会中心;建设基础设施和储备他们认为必要的材料;发展全市和全国性的同志和同情者网络;并通过协调运动来测试这些网络的能力。当革命真的到来时,在2018年底,这些团体能够充当强化的载体。在巴希尔总统被迫下台后,抵抗委员会也能够将革命维持到下一个阶段。
这一连串的斗争也产生了不值得效仿的实验。群众运动之后往往会推动形成能够参加选举的政党,例如在希腊或西班牙。他们早期的成功往往掩盖了某种陷阱。当危机深重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和资本想把治理的重任推给运动。危机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运动要负责管理危机。而一旦运动掌权,它很快就会失去信誉。有时,左翼甚至能够推动改革或紧缩政策,而另一个 “政府” 则无法做到。在这个循环中,革命者发现了足以干预斗争的形式,但不是夺取权力。
7、
今天的革命努力是在孤立中开始的,被抛弃在镇压之下,因为支持它们不符合任何现有力量的利益。
革命斗争的零星爆发被一个国际镇压组织所抵制,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分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实际的革命国际主义组织来支持这场运动。
然而,只有通过这一连串斗争的深化,以及在可能从中产生的力量系统中,一种实际的国际主义,一种能够打破革命努力的孤立性的国际主义,才有可能成为可能。
8、
革命总是能找到适合其内容和情况的形式。Galle Face 公社就是一个新轮廓。公社为社会革命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公社可以从运动关心和复制自己的实践中看到;从它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分离的努力中看到;从它扩大的趋势中看到。斗争每前进一步,占领运动就会扩大一步:占领者的营地越来越多,新的营地不断涌现,新的建筑继续被占领。一些抗议者抱怨说,抗议活动被媒体定性为海滩派对了。但公社的宣言总是以节庆为标志的。
占领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空间和背景,让他们可以找到彼此,组织起来,并采取主动。它们为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使其能够自我繁殖;在冷清时期处理水;并随着潮水上升,吸收更激烈的动乱时刻的势头。守住这些空间可能总是比夺回它们更容易。闪电很少会出现两次。埃及和苏丹的革命者们在艰难的道路上学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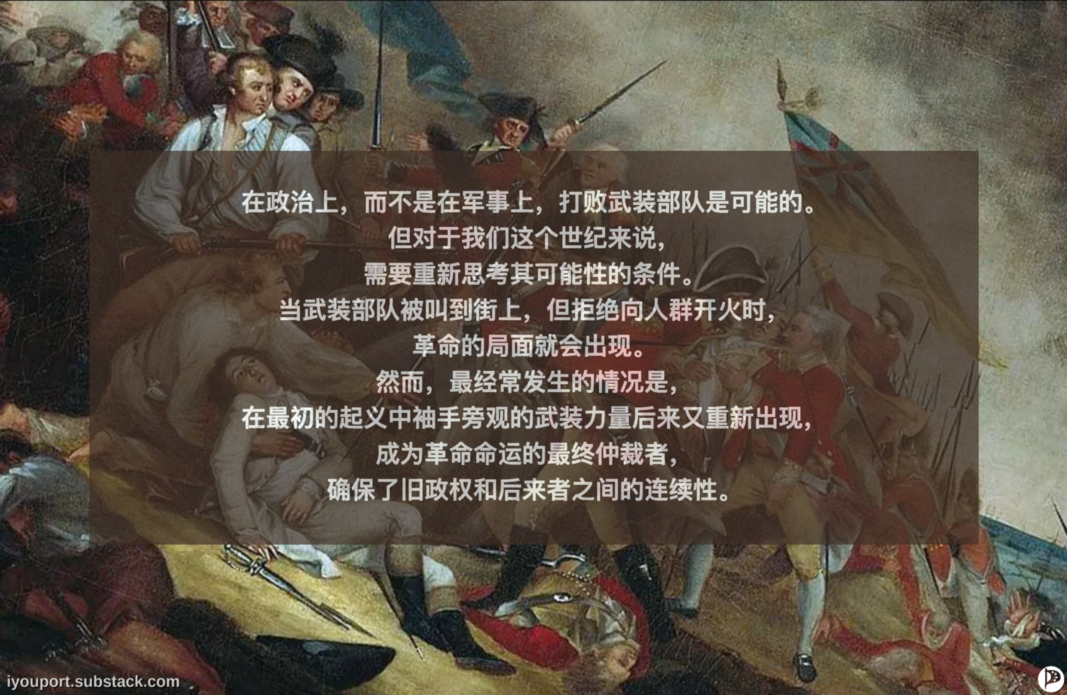
本文作者,这位参加了推翻总统加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 抗议运动的斯里兰卡无政府主义者,身处这个运动的核心 — — 占领行动,即 Gota Go Gama (“ Gota Go Go Home”)。Gama(加马),是僧伽罗语 “村庄” 的意思,在泰米尔语里是 Gramam,在这次抗议和占领行动中是呼吁总统 “回老家”。从4月9日开始,抗议者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中心海边公园 (Oceanside Park) 的 Galle Face 建立了一个永久占领点。7月9日,一群兴奋的抗议者冲进了总统宫殿、总统秘书处和总理的住所,拉贾帕克萨总统被迫逃离。

他们接管了整个村庄
“这似乎就是一生,或者至少一个主要时代,一个永远不会再现的高峰。 Gota Go Gama 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也许这意味着什么。从长远来看,也许又不会有什么 …… 但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言语、音乐或记忆的表达能触动那种感觉,那种能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活在那个时间、活在世界的那个角落里的感觉。不管这意味着什么…
“每个小时、每个方向都被疯狂所占据。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擦出火花。有一种奇妙的普遍感觉,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的,我们正在取得胜利……
“我认为这就是抓手 — — 一种对那些陈腐和邪恶战无不胜的感觉。这不是任何卑鄙或者军事意义上的,我们不需要那个。我们就是拥有优势的能量。战斗毫无意义,无论发生在我们这边还是他们那边。我们充满锐气,站立在高大美丽的波峰之上 ……
“因此,现在只要你在 Galle Face 那条陡峭的山丘上抬起头来,向西看,就可以看到那个高水位的标志 — — 波浪最终破裂并回滚的地方。”
— — Gatherer S. Thompson



那是斯里兰卡的伍德斯托克、喀琅施塔得,都与占领华尔街合而为一。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始于四月。在无尽的雨水和泥泞中,我们高喊,发出一千倍的声音,“Gota Go Home!”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1953年哈塔尔(总罢工)的辉煌时代。那是斯里兰卡的停滞时期,几乎每个人都在罢工。婴儿潮的一代回忆说,“人们走出家门,在铁轨上煮饭。这个国家就像一个鬼城。”
然后,就是血腥八十年代后期的辛酸回忆。当美国在为 “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 开辟通路、并且鼓励 “随便说” 的时候,斯里兰卡还沉浸在由酷刑室传出的尖叫声和那些在燃烧轮胎上的破碎肢体构成的小夜曲中。
但是三十年后,发生了截然不同的事,这是与1990年代以来那个贪婪政府相比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Gota(前总统 Gotabaya Rajapaksa)向人民许诺了一个美妙的愿景,但人们得到的只是长时间停电和通货膨胀的煎熬。自由市场无法解决这个烂摊子;而他在对我们所有人明抢豪夺,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人们的排队往往延伸数英里之长。当中产阶级(即 那些平时冷漠的阶级)都走上了街头加入抗议时,真正的麻烦就来了。当抗议者进入 Mirihana(总统居住的市郊)范围,朝着他的老巢发出嘘声,一切就都爆发了。斯里兰卡全国人民都在观看,所有人都黏在电视机上。当人们看到警方设置的路障被抗议者充满胜利的力量推翻时,笑容慢慢荡漾在所有人的脸上。
那是绵羊变成狮子的时刻。接下来的日子里,兔子们游行到这个叫 Galle Face 的草地,向空中挥舞拳头,彰显决心:除非 Gota 滚蛋否则他们绝不离开。



无领导的抵抗
GGG(Gota Go Gama)是斯里兰卡第一个真正的无领导运动。
“好吧,兄弟,这里没有人负责。 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在负责。 你,我和那边的那些家伙”,有人在 Galle Face 说。
(Anarchos 是希腊语,意为 “没有统治者或领导人”)
但这并没有阻止警察逮捕他们认为是 “领导人” 的任何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生在 Galle Face 的运动其无领导的优势让当局颇为沮丧,统治者一直在企图从某个 “策划革命的帐篷” 里揪出一个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
在GGG的头几天,我们记得卧底警察和政治间谍们到处询问 “谁是领导者”。 政府疯狂搜寻,企图像砍下蛇头一般斩首这场运动。
但是,就像罗波那一样(Ravanan,传说中的十头魔王),阿拉加拉亚也是多头的(Aragalaya,僧伽罗语 “斗争” 的意思)。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知道,火已经被点燃了……


守望相助
是互助定义了人类社会。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在部落中结伴生存,我们就不会繁衍到今天。
但是,即使在亚洲(或者我们应该说,尤其是在亚洲),这种社区意识,随着国家的每一次迭代,都在迅速被瓦解。
然而在科伦坡发生革命的市中心,通过建立互助社区,GGG重新确认了社区的重要性。
这里有一个厨房、一家医院、一个游击花园、分配站、图书馆、电影院和一所学校,还有两辆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的卡车用作发电站!有人贡献食物、衣服、帐篷和书籍,另一些人虽然无法亲自参与建造和维护占领村(Gama),但是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这个抗议点被称为 Adarasha Gammanaya,就是 “模范村”。
斯里兰卡政府以前曾经试图创建这样的模范村,例如受到以色列的基布兹启发的 Gammudawa Project (上进村项目,“Rising Villages”)。政府尝试过建立乡村自治和自力更生的模式,但那只是为了提高统治政权的形象,他们很少真正是为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注: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种常见的集体社区体制,传统上以务农为主,现在则历经转型,兼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但是,现在被全世界谈论的是我们的小 Gama!而且,GGG的人们聚在一起,不是以爆炸性的方式运作。没有任何人拥有特权,大家各得其所。 “这里是按需分配,也按能力进行分配。”



要知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彼此
长期以来,斯里兰卡一直为教派暴力所困。与暴力有关的偏执和种族主义根源可以追溯到独立之前。政客们利用种族差异和冲突分裂人民,这手相当有效。这些斯里兰卡的冲突历史,值得大书特书,仅仅一本杂志是不够的,需要的是一整个图书馆。
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斯里兰卡的诸多权力部门及其支持者们都以为我们这个团结互助的 GGG 运动会在一周内崩溃,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为此弹冠相庆,但是,他们都错了。
相反,他们看到我们的 LGBTQ 的同志们为穆斯林提供了iftar晚餐(在斋月期间日落之后吃的饭菜);牧师、僧侣、修女和伊玛目们,携起手来结成人墙,保护抗议的学生们免遭警棍的殴打;僧伽罗人在纪念1983年种族暴动和战争的最后阶段(斯里兰卡内战)中丧生的泰米尔人 ……
还有阶级的和谐。
参加聚会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是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夜晚,星空下从印度洋吹来的微风,提醒着我们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尽管有分歧,但我们互相拥抱。我们知道,五个手指需要紧紧相握并举起,以反抗压迫我们的人。




行动带来信心
我们是 Galle Face 的高卢人,一个野蛮人的部落冲向防暴警察的罗马盾牌。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催泪瓦斯。警察抛掷的CS气罐成为人们的收藏品。激进学生都是从街头战斗中的新手锻炼出来的。
如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那么被催泪瓦斯伤害的眼睛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们愤怒的闸门。
团结和互助如柱石一般支撑了占领村的直接行动,尤其是在总统府秘书处前的主要路障 “零门”,高声抗议连续24小时地进行。
随之,整个港口城市的墙壁都被涂鸦所覆盖,黑色横幅悬挂在灯柱上,许多小贩和小业主为每天涌入的抗议者开门营业。
借助支持网络,GGG在斯里兰卡许多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帮助教育人民。
当5月9日政府力量袭击占领者时,人民并没有旁观,他们急速增援,进入贝拉湖区域。
在这个饱含种族暴力和大屠杀创伤的国家,当5月9日晚间人们烧毁了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客们的房屋时,政治叙事翻转了。
而斯里兰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直接行动,毫无疑问,发生在7月9日的总统宫殿、总统秘书处和缅栀屋(斯里兰卡总理的官邸)。抗议者冲向这些奢靡建筑中的豪华游泳池,成群的人们涌向科伦坡,在这些过去对平民来说远不可及的奢侈品中欢跳。
GGG运动,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重新打造了受苦受难的人民的脊梁。对一群长期被军阀、专制者、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所征服的人群来说,这是胜利的日子。



我们走过的错路
占领这三座国家建筑物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政府豢养的媒体和宣传员并没有停止工作,他们继续挑拨族群矛盾,努力传播 “有少数族群秘密资助抗议者” 的谣言。
议会迅速选出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接替 Gota 总统的职位,试图拯救政府。拉尼尔是斯里兰卡的弗兰克·安德伍德(Frank Underwood)(美剧《纸牌屋》的主人公),曾是1980年代后期斯里兰卡的皮诺切特风格政府的左右手。他在斯里兰卡臭名昭著,其政治名声最初从一个凶残的集中营传出,这个集中营叫做 Batalanda。
拉尼尔最著名的是作为一个狡猾的政治掮客。奇怪的是,当占领者决定在7月22日移交这些总统建筑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被新的总统任命所打动。如同所有胜利的革命,GGG运动在胜利面前难免陷入了自满。我们没有看到斯里兰卡深层政府的黑手,正在悄悄毁损我们站立的地面。
对任何大众运动中的温和派和自由派来说,采取妥协的道路都很容易。只要当权者抛出一些诱惑或者只是诱惑的许诺,运动中的伪激进面具就会慢慢融化。最危险的是,那些侵入激进空间的有魅力的小政客。他们的魅力能够将任何政治讨论转化为他们自己的优势。他们会轻松随意地混杂最新的意识形态,夸夸其谈,但是对理论和实践毫无头绪。
统治阶级很清楚这一类型的运动领袖,常常有意利用新政权的特权诱惑他们,试图把曾经的抗议领袖转变成新的国家主义者。这种人已经背叛了他们起家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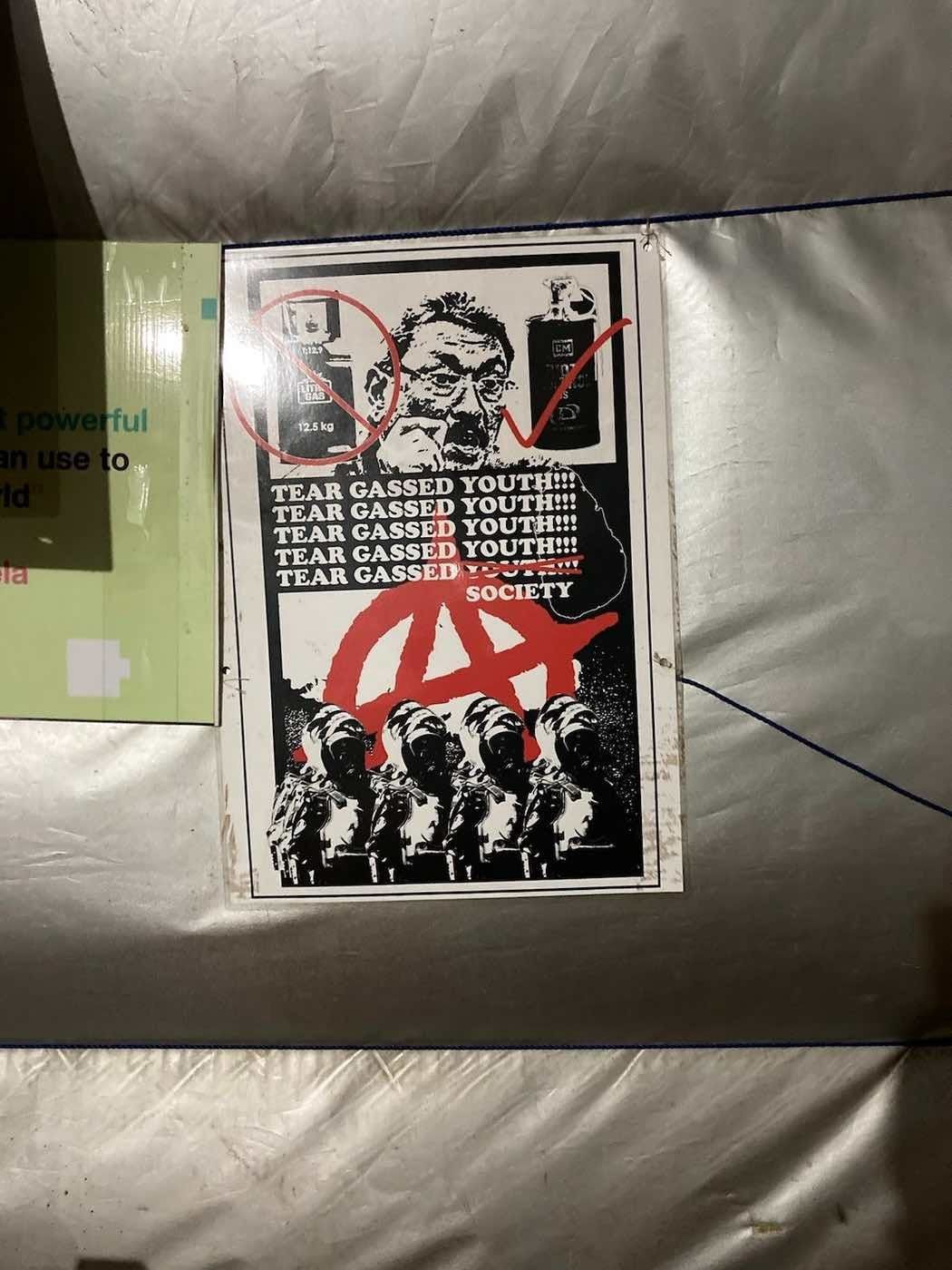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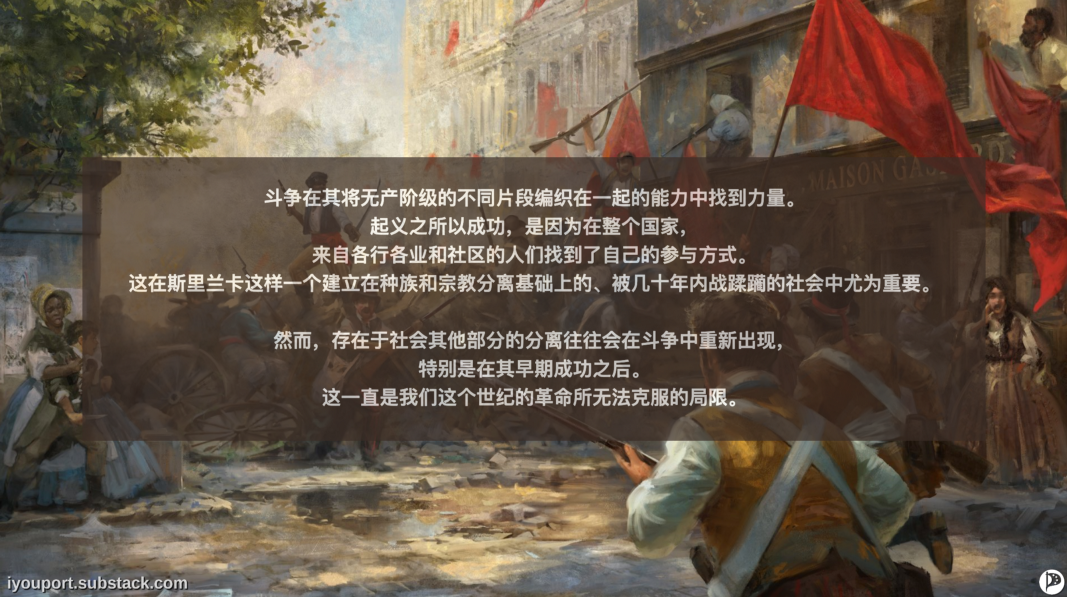
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的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团队来了又走,他们承诺的大规模救助对当前人民准备采取紧缩措施的计划来说,无疑是极其讽刺的。
加油站的漫长队列仍然是常见的。一条面包的价格升至350卢比,大多数工薪穷人都负担不起。
随着国家宣布进入非常状态,斯里兰卡的武装力量正心怀叵测地大规模逮捕抗议者。人们因刷啤酒杯、拥有旗帜和其他平凡的东西而被捕。如同地狱一般,甚至拥抱总统宫殿支柱的那个人也被捕了!
7月22日的残酷镇压一周后,GGG运动被清除了。许多抗议者被警察用铁棍和电缆残酷地殴打。帐篷和其他占领设施被捣毁。当人们开始在占领村旁边的海滩上清洗受害者尸体时,人民的恐惧增加了。头条新闻里充满了枪击事件,警察称之为 “帮派暴力”。
为了进一步强化侮辱,政府宣布抗议者需要对 Galle Face 的绿地造成的 “损害” 赔偿500万卢比(约合 13,800 美元)。
9月2日晚上,正在东南亚旅行、试图在第三国家寻求庇护的 Gota 总统,飞回了斯里兰卡,很快被一群政治奴隶在一队吉普车队的护送下前往南方拉贾帕克萨(Rajapaksa)的老家。有传言说,他可能会试图重新爬回议会,就任总理一职。
斗争(Aragalaya)正在退缩,但我们不会安静地走入良夜。我们已经学到许多,准备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创造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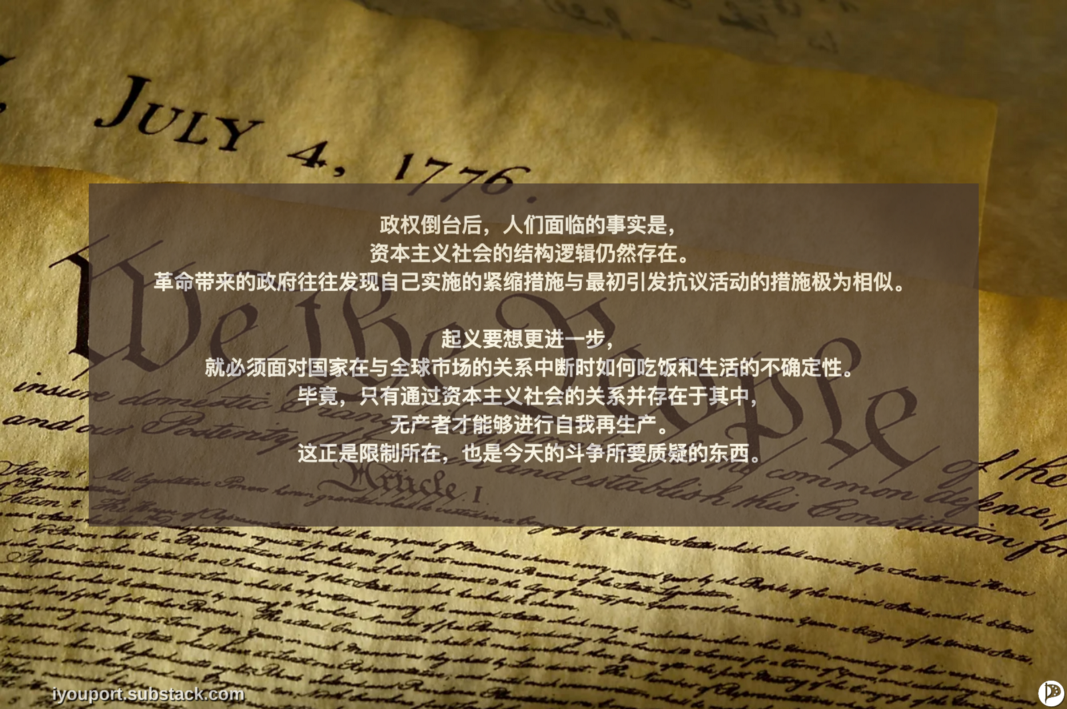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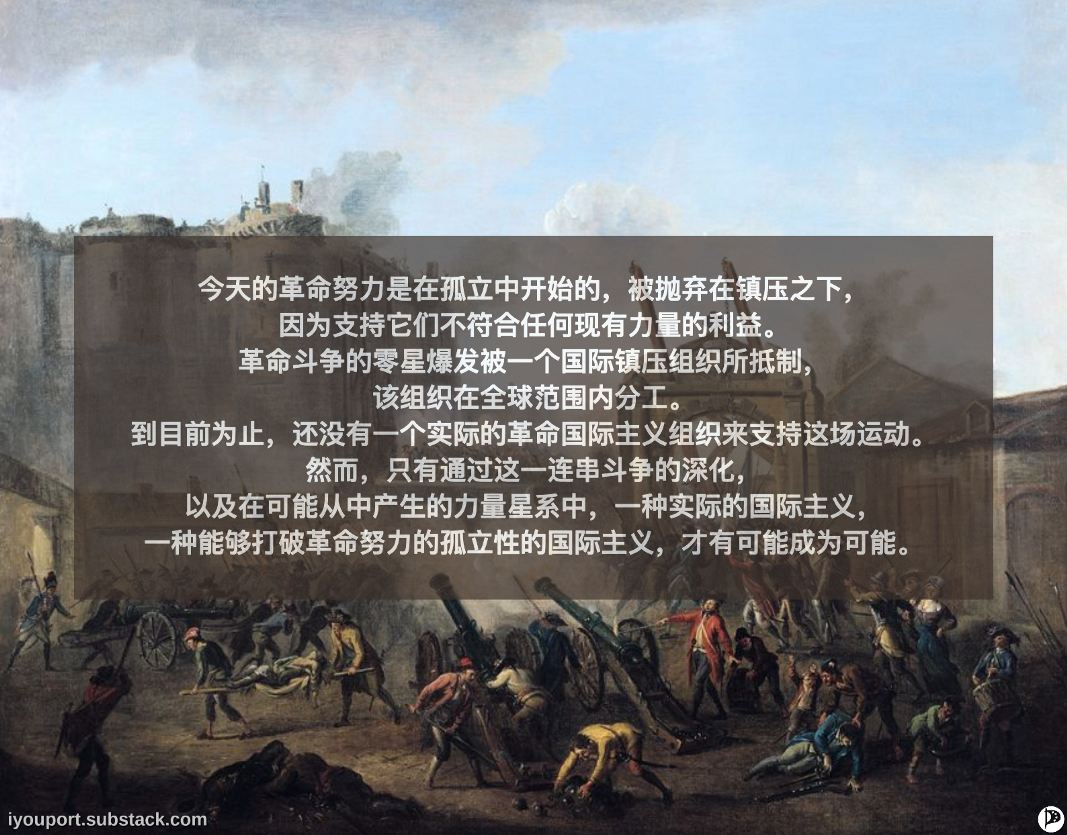
⭕️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