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年少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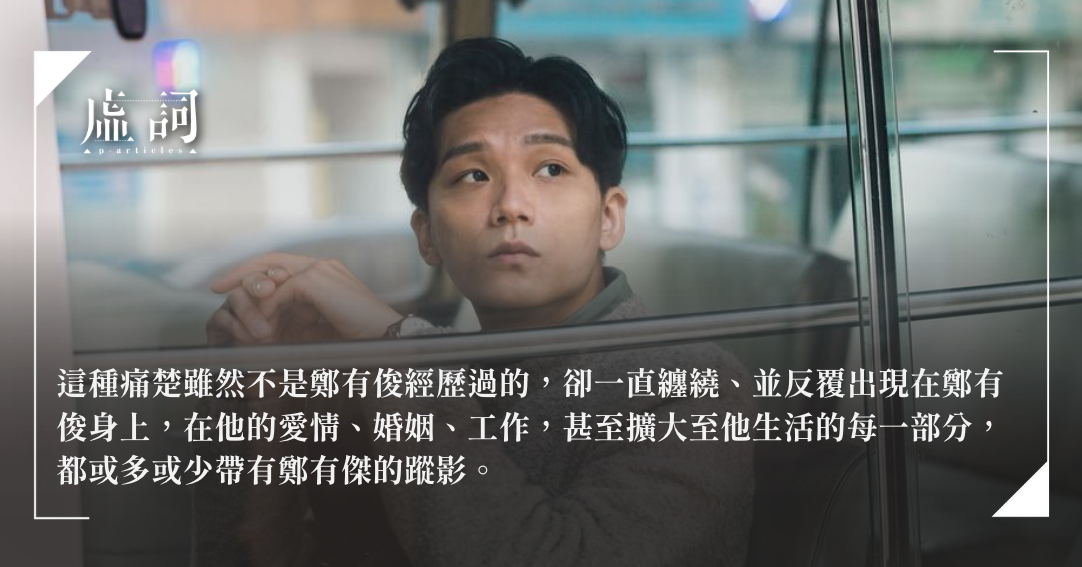
文|葉嘉詠
《年少日記》榮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和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可見這部電影既得到業界的認同,也能打動大眾的心靈。不少影評已指出這部電影的原生家庭問題、學童的心理健康和學習壓力等,本文則集中討論電影中的日記和配音兩個細節,突顯文字與聲音與角色設定的關係。
鄭有俊是一位中文老師,他對文字與聲音應該比較敏感,前者是他的專業知識,後者是他的職業需要,看來很符合人物設定。此外,導演有意選取鄭有傑的日記和他為公仔的配音這兩個細節,一方面將兩者貫穿整部電影,令電影的結構更加緊密,另一方面試圖透過鄭有俊和鄭有傑的距離感,表現兄弟間既疏離又親密的關係。
1.日記作為承擔痛苦的形式
《年少日記》已有「日記」二字,可見「日記」在電影中佔有不可取代的位置。鄭有俊沒有寫日記,但《年少日記》的轉捩點是鄭有俊重閱哥哥鄭有傑的日記,由此揭開他心理變化和內心傷痛的根源,也令情節產生一百八十度轉變,將電影推向高潮。
歷來以「日記」為題的文學作品不少,例如《安妮日記》曝露納粹黨迫害安妮及其家人的情形;中國自五四以來,魯迅〈狂人日記〉批判中國封建文化的吃人禮教、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描寫莎菲敢於提出女子的愛情慾求。概述而言,日記寫的都是私隱,很個人的,強調個人主觀感受和情感,而日記體作品包含打破現狀,揭示更深層次的個人、家庭與社會的矛盾,並有助讀者思考現實與理想的差異。故此,「日記」是一種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結合,並不是其他文類所能達至的獨特載體。
以上提到的文學作品雖然是具有虛構成分的小說,但《年少日記》與其相同的是,兩者都是以「公開」形式坦露日記主角的現實痛苦和心靈創傷,讓讀者和觀眾一直身在其中、感受其中。鄭有傑原本希望透過寫日記提升成績,希望入讀香港大學,希望讓父母高興,這是多麼正面又積極的行為。不過,由他開始寫下的第一句:「你好,日記。」只是短短四字,導演已故意將「日記」與「孤獨」連繫起來,並重新定義後者:「孤獨」的人並不只是單身、孤兒等我們常見的意思,反而擁有家人但仍只能對死物說話的人,才是真正孤獨的人。所謂的「視而不見」,我們怎能不為此而悲傷呢?
更甚的是,當觀眾投入在第一人稱「日記」主角鄭有傑的故事時,導演便打破這種慣性思維,捨棄一般直接的敘述,改為以既遠且近的弟弟鄭有俊視角,帶領觀眾一同觀看日記主角的內心世界。鄭有俊是閱讀這本日記的讀者,也是承擔傷痛的人,而且是承擔雙重份量的傷痛的人。故此,這種痛楚雖然不是鄭有俊經歷過的,卻一直纏繞、並反覆出現在鄭有俊身上,在他的愛情、婚姻、工作,甚至擴大至他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帶有鄭有傑的蹤影。由此帶出的問題是:旁觀他人痛苦的有俊是否比直接發洩負面情緒的有傑,少些悲傷和壓抑?
2.從配音到聲音
除了寫日記,鄭有傑另一個宣洩情緒的重要方法便是為公仔配音。因為沒有人願意聆聽鄭有傑的心聲,所以他只能幻想公仔是自己的朋友,只能把所思所想都寄託在公仔身上。其實,他與鄭有俊住在同一房間,後者又怎會不知道他的心事,但作為弟弟,鄭有俊一是假裝聽不到,一是以眼訓為由拒絕了解哥哥的內心世界。
導演將配音這種形式,表現得如此沉重又現實,令人深思自己曾否做過鄭有俊。幸好電影並不是一直如此悲情,林雪兒為河馬公仔配音便可愛得多了。當鄭有俊偷聽到林雪兒為公仔配音,自然想起有同樣愛好的哥哥。相似的行為成為了鄭有俊重新發現人生意義的關鍵,林雪兒讓鄭有俊以為是鄭有傑的重疊影像,令鄭有俊稍為消減失去哥哥的痛楚,不過,導演沒有讓這種愉快的情緒延伸下去,林雪兒移民時只留下河馬公仔,聲音的遠離代表溫情的消逝,也暗示哥哥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
總括而言,導演在聲音方面的鋪排很好,從鄭有傑的男孩公仔到林雪兒的河馬公仔,從人類到動物,都在顯示鄭有俊的內疚與無奈。電影將聲音提升至另一層次,而且是備受重視的細節,絕沒因為配音的「配」而視之為配襯,這是導演和編劇的用心之處。
如果配音的「配」字只是配襯的意思,聲音便不及其他感官如視覺、觸覺等得到關注,但電影除了重視「配音」,也花了不少心思設計與聲音相關的場景,實在是神來之筆。例如鄭有俊與Vincent並坐球場的一幕,Vincent好串地說:「全校都知你離咗婚,你仲戴住隻戒指!」(大概意思)這兩句是多麼的刺耳,但由一直被鄭有俊誤解的Vincent之口說出來,恰好說中了他的心事。Vincent的說話可視之為「另類配音」,而且這樣的情節似曾相識,不就是他的哥哥希望與他聊天但他沒理會對方的情節嗎?簡直是「聽而不聞」的典型例子。
另一個例子比較有趣,既可視為「聽而不聞」的反證,也能突顯文字與聲音結合的重要。鄭有傑知道班長鎅手,便與社工、班長一同到山上大叫。這個場景原本頗突兀,鄭有俊連Vincent花名「蛋糕」的由來都不明所以,又怎能取得學生的信任!不過,他先又大聲又長氣地嗌「呀~」,便勝過長篇大論的道理了。因為他在代替他的哥哥大喊,喊出心中的想法,也為自己喊出傷痛,而不是用千言萬語、語重心長的語調糾正學生的「錯誤」。試問誰都不會願意在陌生人面前展露自己脆弱的一面,這一點正回應上文提到鄭有俊一直掩飾離婚的真相。故此,導演的安排是很人性的。最後班長和社工一同吶喊「呀~」,便相對地自然得多,這也成為電影中唯一能令人發笑的場景了。由此可見,文字的多寡與聲音的長短可以互相補足,說得多和聲音大不代表內容豐富和深入,相反,說話的對象才是重點,而關鍵就在是否抓緊時機和選取合適的表達方式了。
《年少日記》由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開始,上文未有提到遺書,因為遺書必需與「年少」合併討論才有意義。當鄭有俊希望查出誰寫遺書時,有一幕課室場景是很震撼的。鄭有俊站在課室面向學生,鏡頭不斷轉換到不同學生的臉容上,有的憂愁,有的面無表情,有的不知所措,同時由學生讀出遺書內容,看來每位學生都有自殺的可能!這些學生不是「少年」嗎?為何都不甚快樂呢?我們都留意到,電影名字是「年少」而非「少年」。「年少」的年齡範圍更大,指涉也更廣泛。十歲的鄭有傑可以是「年少」,忙著考DSE的學生可以是「年少」,鄭有傑也曾經「年少」,我們都可以是「年少」。我們都經歷過或旁觀過這些「年少」的痛苦與遺憾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