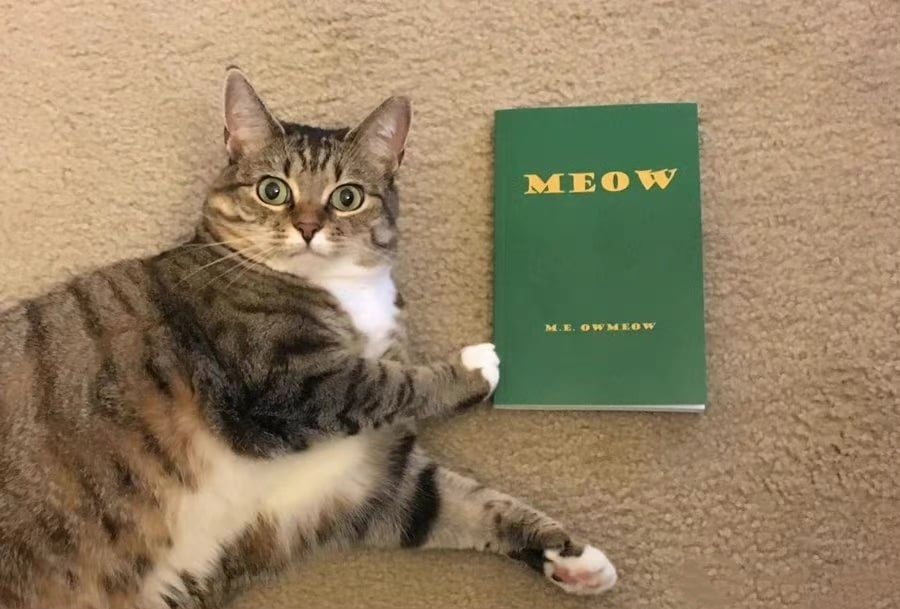【蜉蝣鎮回憶錄】藍知更鳥
*
蜉蝣鎮上的一位高中生於四年前4月27日夜晚離世。在長逝前,她昏睡了快三年。
據說在她離世消息傳出前的幾個小時,有人看見一只藍知更鳥從她書房窗戶飛出來。這裏從沒有這樣的小鳥,連藍色羽毛的鳥都從未有過,所以它在小鎮上,還是從小鎮人家裏頭飛出來,是很顯眼的。
這是建鎮歷史上的一起神秘事件,現在正以不同的版本在鎮上流傳著,今後可能還要再傳上好幾代。
那段時間我不在鎮上,她的死訊是她家人告知我的。我是她生前唯一聯系著的好友。直至今日我才搜集好現存的所有信息,理清這些年裏關於她的種種細節。將這些信息和我本就有的回憶整合成完整記憶,與古早年代拍攝一部奇想夢紀錄毫無二致。事實上,她的故事正是由夢境串連成,由她清醒時說過的話做旁白。多年以後回放它時,我的呼吸隨著熒幕失真的聲與色一起發抖,好像我也失了真。
這種夢境與記憶圖景的失真,容易讓人對已失去的抱有種哀傷與無力感。要我從永失友人的思緒中徹底走出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這樣勸我的人,還都把她的故事編得天花亂墜。這些流言總是夾雜著傳播者各自的目的,或是加上道德品行的框架以便警戒後世,或是附帶上詭異傳說的風味以便口口相傳。這裏我就不把這些傳言一一細說了。
出於這點,我決定寫下對這位好友的追憶,並把它放在小鎮回憶錄的首篇。這必然會打破我記敘的時間順序,不過在懷念之心和對真相與她名譽的維護面前,它顯得無關緊要。我給這篇擬題為《藍知更鳥》,因為這只藍色小鳥是她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角色,沒有之一。
我也不知道把這個故事說出來有多少人會願意摒棄那些離奇的傳言,用去娛樂化的態度來對待我這位認真活過的好友的真實經歷。不過我還是先不管這些,只盡力把我知道的詳盡寫下吧。
*
之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提及死者的姓名,是因為我不知道她叫什麽。除了給她起名的家人,誰也不知道她的真實名字,作為好友的我也不知道,不過這似乎並不影響日常交流,人們過去鮮有興趣提及起她,提及的時候也常常可以用「那個女孩」、「那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同學」替代。沒有名字就是她的名字。
在醒著的大多數時候,她就是個默默無聞的中學生——和這個鎮上其他大多數孩子一樣,她幾乎從未展現出對學業的熱情,更沒有少數學生的行善意識,我是說通過成績優異來給老師添獎金。一到那些無聊的課,她就開始假裝盯著黑板和書本,實際上蘑菇短發狗啃劉海遮擋下的棕眼睛總是失焦,神遊至某個未知奇境。其他時候她沈默寡言,除了和我,她從不會其他人分享關於自己的任何故事。當然,這也意味著她並不是那種愛四處惹事生非的人。這樣的小孩,不過是活在小鎮簡樸生活那幾條固定軌道其中一條。軌道裏除了頭尾,她這樣在中間的,在人們看來都差不多。
到這裏,你們可能會有疑問,那在學校的時候老師怎麽叫她呢?她不應該在書本和卷子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嗎?回答這兩個問題前,我想先打斷一下,因為我發現上一段最後一句的說法實在有失公允。我想大家應該明白一點,那就是雖然我們說班裏一個學生毫不起眼,但只要你細心觀察,每個孩子都或多或少地有著獨特的習性。
她把自己的真實姓名當作一個不可獲知的秘密,這就是獨屬她的習性。她確實寫了名字,但是自打第一天老師收集名冊要學生簽上大名,她就故意把名字寫得極度潦草,沒有一個人成功辨認出來過那些都是什麽字。碰巧的是,她進的每一個班裏只有她這樣一名學生,老師也都很不愛給自己添更多麻煩,索性從未因寫名字的事找過她,也很少讓她回答問題,只是每次分發東西時把她署名的放最後。同學都領完了自己的,剩下的自然就是她的。
從上學起,也就是在一個地方不得不用上自己名字的時候,情況就是如此了。人們也不是沒有問過她的家長她叫什麽名字,以及為什麽把名字寫成這樣,她的爸媽也不是沒因為這個事情和她有過爭吵,要她好好對待自己的名字。為了此事她小時候做過非常激烈的對抗,甚至不讓他們直呼她的名字,否則她會哭得讓人心摔成一攤稀碎。她的家人對她愛護有加,雖然沒有找原因,但最終也還是選擇尊重她執拗的個性,不求助什麽專業人士去「糾正」她,任由她把自己的名字寫得這樣無法辨認,改以她的小名稱呼她,也不把她的真名和任何一個人說。
我在初中的最後一年認識她,那時離她陷入昏睡還有一年多的時間。我們是在補習班相遇的。從那周開始,我調到了和她同一期的班。
這節課我遲到了,只好在擁擠的人群裏艱難又尷尬地尋找空位,然後我看到了她。她右邊坐著一個女孩兒,女孩兒右邊還有一長排陌生的臉,只有她左邊的位置是空著的,整個教室只有這麽一個空位。我走過去,她看我過來,就把凳子拉出來,拿出放在抽屜裏的書,示意我坐在這裏。我掃到一眼書的硬殼封面,那是一套百科全書裏的鳥類分冊。
這本書是我們友誼的開端。後來直到我們高中同班,她都隨身帶著它。一開始那本書還很新,到一年多以後她在學校的最後一段時間,書已經相當陳舊,兩面硬殼都有了折角,甚至快要整個脫離下來,裏頭的書頁只依靠幾根線和幹了的膠水可憐地吊著。
回到那天,我們這些補課的學生在一小時的課後精疲力竭,終於迎來了休息。老師剛走出教室去陽臺吸煙,她就立馬抽出那本書,翻到某一頁,然後照著書上的一行字用漂亮的意大利斜體抄在草稿紙上——「Sialia Sialis」(東方藍知更鳥)。
我全然被那漂亮的字怔住,以至於忘記了我其實不該長時間盯著別人的東西看,況且她和我並不熟。除了這兩個我看不懂的詞,草稿紙的其他數學公式和零零星星的單詞都很工整,與其說是草稿,不如說是種不經意的藝術,把不遠處她卷子上名字那欄潦草的字跡襯托得更加顯眼。
我那時就有一種感覺是,她不應該生活在小鎮的這個年代,再早一會她一定是個卓越的抄寫員。聽父母輩的人說早在幾十年前,書寫員就是一群字寫得相當好看的人,是那時發展落後的蜉蝣鎮上相當體面的又稀有的工作。那個時候,不識字的人要請他們這樣識字又書寫好看的人幫他們寫信寄給在外地的人,鎮上人開宴席也要找他們在那時還算昂貴的厚卡紙上寫請柬,還有些有點閑錢卻字寫得醜的學生,特地買來紙筆讓他們把自己的詩啊書稿啊抄在上面送給老師,朋友還有心愛的人,就算是非常用心又奢侈的禮物了。總之,書寫員是給文字與紙賦予紀念意義的工作,也因此受人尊敬。
直覺告訴我她本來也應該很適合這樣的工作。可現在呢,學校裏書寫竟成了有統一標準的量產物(比如你不能用意大利斜體書寫拉丁字母),學校外卻成了大多人最不在意的東西之一。
「嗨,你看我桌上的東西很久了。」她突然停下筆轉頭對我說話,擡起頭把厚厚的劉海撈到兩邊,露出那雙困倦的棕眼睛。你沒法從這張神情渙散的臉上讀出她有什麽表情,她說話語氣也幾乎毫無起伏。這時候你只能從社交裏的通常情形判斷出,被看的人至少是不悅的。
「啊,抱歉抱歉,原諒我的冒昧。我第一次來這個班上課,之前在另一個班。對不起,我不該隨意看的,但是你的字真的好漂亮啊。」
「真的嗎?謝謝你。看到也沒關系的,這上面也沒寫什麽見不得人的東西。對了,關於草稿紙上的字,你應該知道雙名法吧。Sialia Sialis......這是東方藍知更鳥的拉丁語學名,書上寫著呢。」說「藍知更鳥」時,她突然更激動、語速也加快了一些,又立即恢復一貫的冷淡。
說完她把書挪在我倆桌子的中間,翻開的那一頁正是藍知更鳥。這只鳥的藍色羽毛裹著它挺拔的胸前紅羽毛。這種高飽和的藍色經常受人喜愛,我也不例外。
「我很喜歡這種小鳥!這兒從來沒有這樣漂亮的小鳥啊。你看起來也很喜歡它們,是嗎?」
「是。它好像不在我們這裏,但我小時候看見過,我還想再看見它。」
「哇,你一定是去很遠的地方旅遊的時候看過吧,能親眼看到這樣美麗的生物是很幸福的事情!」
「不是,不是旅遊看見的,我很少出去旅遊。哦對了,你說你是新來的,那你以後每周都來這個班嗎?怎麽稱呼你呢?」
「對,以後都在這個班了。你叫我Y就行。不是旅遊看見的,那是在哪看見的呢?我很好奇,你可以和我講講嗎?啊還有,你叫什麽呀?」
「無可奉告。我不喜歡別人叫我名字。老師回來上課了,故事我們以後再說好嗎?」那時她轉過頭去,無表情卻放松的臉突然繃緊起來,好像在有意壓抑著什麽更激烈些的情緒,一直到下課都是如此。她把百科書最後裝進包裏,輕輕和我說:「我每節課都坐這個位置,以後我給你把這個位置留著可以嗎?那就這樣說吧,我們下次課見,拜拜。」說罷她把最後一條拉鏈拉上,就跑下樓騎自行車走了。
那時交朋友單純得多。你不用像現在這樣樹起道道門檻,比如要互相坦白心意到什麽程度,比如說話方式和節奏互相可接受,比如反復試探那個認識你的人和你的政見是否一致,等等等等。我和她,若按現在朋友的標準,那可真是幾乎一條都不符合。我似乎時不時不小心跨越她的界限,她好像也用冷淡的回話和拒絕透露姓名來給我的熱情與好奇潑冷水,潑完卻又主動回來繼續用冷淡的語氣說些什麽。但我們就這樣從一本書的藍色小鳥的名字開始,聊起了天,打了招呼,再約定下次繼續交談,這就算是朋友了。
我並不知道她在哪個學校,只能確定不在我那所初中。興許她是另一所的,不過這都不重要。我們就這麽認識了,並且清楚我們長期都頂多保持著一星期裏花數分鐘草草聊上幾句的關系,而這還得是在滿足我和她都繼續在那個班補課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接下來一整個星期,我都很期待再去那個補課班,因為她還沒和我講她小時候是怎麽不通過旅行親眼看見藍知更鳥的,以及為什麽偏偏是藍知更鳥,而不是其他這裏從未見過的小鳥呢?我的好奇心飽受折磨。哪怕那天只是隨口說說,下次再去她很可能已經忘記了她當時答應過我,只要我能記起來並且還好奇,我就一定要去追問。
*
第二個星期我坐到那個位置上時,她始終沒有出現。我的好奇仍然在,但是期待落空了。整個班沒有一人過問她沒來的原因,那位一到課間就跑出去抽煙的老師也對此只字不提,好像她之前從來不在這個班一樣。幾個星期下來,我也逐漸放下了這事,開始好好準備六月的升學考試。
再次碰到她就已經是同年高中開學了,如我前文提及,她和我被分進了同個班。由於我們倆身高差不多,老師安排她和我坐同一排,又讓我們做同桌。
「嗨!你是不是之前那個......」把我的東西都安頓到座位上以後,我先開口問她。
「是的!就是那個補課班對吧?我還欠你一個故事,關於我怎麽看到藍知更鳥的,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你還想聽嗎?」說到「藍知更鳥」時,她又像之前那樣提高了一些聲音,甚至還沖我笑。
「當然啊!下節課是體育課,快和我說快和我說!」我使勁朝她點頭,然後拉著她一起下樓去上體育課。
說是體育課,實際上是讓我們在學校裏四處遊玩的四十五分鐘。我和她坐在一個小亭子裏,趁這機會好好聊天。
「說那個故事前,我得先問你,你有過這樣的體驗嗎......就是一個朋友突然離開去了很遠的地方,但最近又通過某種方式聯系上了你。」她先開口問我。
「我經歷的都是小時候的事情了,我的那些朋友跟著家裏搬去了別的地方,沒有打招呼,也沒一個重新聯系上。噢,這麽說不對,我們過去是朋友,現在幸運地重聚了。這就是你說的體驗吧!」
她頓了一下,沒有回應我的回憶繼續說自己的事:「我小時候,大概是六歲還是七歲,總之那會馬上就要上小學了......等等,這是我第一次和人說這些,我覺得你是信得過的人。但是我還得確定一下,你不會因為我說的故事嘲笑我吧?」
「絕對不會。我才不是那種人呢。」
「好的,那我繼續。那會我做夢,碰見一只藍色小鳥。噢,快醒來時的夢總是會給人留下很清晰的印象,你不覺得嗎?夢裏的天半陰不晴的,但還是很適合在戶外玩。那只小鳥的藍色羽毛裹著紅棕色羽毛連到喉嚨的胸脯,可漂亮。你記得補課班那次嗎?那時候我剛買那套書,偶然看到書裏藍知更鳥的那一頁。我很確定夢裏那只就是東方藍知更鳥。我走近一些,它居然也不躲。一點也不像現實裏的鳥,不是不讓你靠近就是從樹上俯沖下來對著你的頭猛啄,還有些甚至對準你的鼻梁拉屎!這聽起來真像小學生的習作。」
「哦,百科書的那那頁我記得!你居然還能想起這麽早以前做過的夢!」
「嗯,我一直記得。我能記得很多往事的細節,這我不會騙你。」她拿起手裏的汽水喝了一口,接著剛才的故事說,「那只小鳥也在幾次試探以後靠近我,開始找我玩。它有時落在我手上,有時候又飛起來要我去追它......
「我好像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我看見它時,仿佛看見了我的整個生命,我陷入一種情緒中。那時候還小,我不知道怎麽描述。現在想來,那會兒好像是我已經有了種對命運的預感,我還無法用言辭說出時,惋惜和憂愁就先籠罩上了我。然而對於這些情緒,我又後知後覺,過了很久才能意識到它們。這話聽起來很傻,但實話說,我現在還是這麽想。夢就是這麽奇怪,無論它的情節多超乎常理,你還是會撥開這些表面,感受到情緒的沖擊。但凡你做了一個能記起來的夢,這多多少少躲不過。
「我和它又好像是認識很久的好友,過去現實生活裏從來沒有這樣的體驗。它似乎沒有住處,但只要它願意,我就把它帶到我家附近住下,雖然我不知道夢裏那個地方離我家多遠。你不知道它對我來說多重要。
「然後你知道嗎?突然它開始開口說話。它第一句就是問我的名字,我就和它老實說了。它聽完突然飛起來,一邊越飛越高,一邊回旋轉圈喊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但是夢裏我怎麽都長不高,六七歲的小孩能有多高呢?它喊我名字的聲音又吸引著我跟隨它,好像要我跟著它去哪兒一般。但是夢總是有你怎麽看也看不見的地方的,那就是它的盡頭。還有就是,現實中的各種因素也會換一個樣子成為你夢的一部分,現實的貓叫在夢裏可能是一場嬰兒啼哭,現實中你頭從枕頭上滾下在夢裏你被人從屋頂上推下。
「在我的夢裏突然有一陣驚雷。我馬上得回家了,它還在空中飛,喊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又有一道閃電撲棱了幾下,這會我再也看不見它了......
「我一直是個有點迷信的人,大多人所認為的平常小事,在我眼裏總會與好運或厄運掛鉤,雖然我其實明白這些想法特別荒謬。比如我一直想,或許我就不該和它說我的名字,不然它就不會因為喊我的名字忘記躲避雷電,又離我越來越遠,不是嗎?我絕不能說我的名字,哪怕改了名也如此,因為人們會用它呼喚我,還讓我想到夢裏那只走到盡頭消失了的藍知更鳥。」
她到此打住,眼淚已經在下眼睫毛根打轉,我把她拉進懷裏抱住她,她的身子好像因為我的擁抱而僵硬起來。可能她對擁抱感到不自在吧,我松開手臂。她離開懷抱以後緊接著站起來,我也跟著站起來。接下來十多分鐘,我們都陷入尷尬的沈默,期間甚至互相躲避對方目光。她繃緊著臉和我並肩漫無目的地走著,而我還在回味她講的故事。我似乎明白了她不允許別人叫她名字的原因,那只藍知更鳥對她來說,遠比我們想象的重要。好吧,我們現今人浮躁的心大概率是想象不到、理解不了她的心思的。好多人總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不要再想了。」可她還惦記著六歲的夢,甚至這麽多年來只把直呼她名字的殊榮留給了夢裏的另一個主角,這在那些人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
「你看,既然百科書上有寫這樣的小鳥分布在哪,那你也一定有機會在去那些地方旅遊的時候看見它們,不是嗎?」我先打破沈默。
「不,不一樣的,怎麽會一樣呢。」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你還會夢見那只藍知更鳥,畢竟你一直惦記著它。說不定再夢到,事情就不一樣了。」
「這就是我想接著說的。」她突然有點激動地抓起我的手,「過去幾個月裏我又看見了它。事情是,我搬進了新家,它在我回家的那條路上,我很確定那就是我小時候夢見的那只。但我不知道看見它時,我是醒著走在那條路上,還是在做夢,或者也可能是從夢裏飛了出來的。聽起來都有些離譜,所以我還不大確定。你沒有見過那段路,我沒法直接這樣和你描述我重新見到它的場景。這樣吧,什麽時候我帶你走一趟,在那條路上我和你說。這周五的放學可以嗎?」
我們就這樣約定了。離周五放學還有整整三天,我又開始害怕像上次補課那樣有新的意外,導致我不能繼續聽她講故事。想聽她說故事的私心讓我比以往更加關心她,同時也讓我非常小心,以免起了什麽摩擦或爭吵讓她改變主意不讓我跟著她去。我還嘗試讓她提前透露些,可她說好了在周五說,就是周五說,那個放學鈴響前,她都對藍知更鳥的事情只字不提。我們每天都坐在一起,看見她沈默保守秘密的樣子,我又一次陷入等待的焦急中。
那幾天裏她仍然像在補課班一樣,時不時在草稿紙一遍遍地、工工整整地寫「Sialia Sialis」,還在周四那天帶了彩鉛和紙照著照片畫藍知更鳥,畫完就剪下畫小鳥的那一塊遞給我:「你是我現實裏第一個願意聽我說這些的朋友,謝謝你,這張畫你一定要收下。」
直到現在這張畫還夾在我高中年代的日記本裏,我時常拿出那本本子,每次翻到夾了畫的那頁,都會想起她。在我記憶裏,她定格在那個剪蘑菇短發、眼神困倦又渙散的十五歲高中生形象。我最後一次看見她在學校時,她就是那樣,第二天她就再沒來學校了,身邊那張桌子一直空著到我高中畢業。
*
說回那個周五放學,後來終於安安穩穩地盼到了,我不用再小心翼翼。我用比平時快上數倍的速度收拾好包,然後就跟著她往那條路走。
路過一溜小商鋪,我們來到一個路口,兩邊分別堵著面墻,墻砌得很粗糙,墻頂一排磚頭都沒被漆覆蓋上。墻體有很多剮蹭的痕跡,牛皮癬小廣告一層疊一層——治梅毒的,賣鼠藥的,貸款的,維修電器的,等等,中間空白間隙還填滿了用藍色圓珠筆寫的人名和傷感句子。本來就窄的路口後還攔了兩個水泥樁子,這讓一輛摩托都難以從它們中間通過。走過墻和樁子,就是一個坑坑窪窪的下坡。說是說自行車可以通過,但這只適用於車技極佳的人,一般人準會頭朝地連摔帶滾地「騎」過這個下坡,這已經是最不嚴重的情況。
正是在這裏,她又遇見了那只藍知更鳥,不知道是在夢裏還是在現實中。這似乎是個無法蛻變為城市的地方,因為只要你不把這兒現有的元素全都清除,它根本就是一個易滋長各種閑花逸木的造夢之地。關鍵是人們不大樂意清除。
為什麽這麽說呢?傳說在這個地方,先前有位事業不得誌的詩人來這裏歇腳,剛安定下來,就愛上了這裏清甜迷醉的氣息,甚至表示他整個人都已經牢牢地和這裏的一切連成一體。漸漸地,他忘記過去的各種委屈,徹底放松繃著大半輩子需要和人應酬的神經。放松著放松著,他就躺在樹蔭底的草地上沈沈入睡,然後在夢裏吃飯,夢裏洗衣,夢裏作詩。後來人們發現他似乎在那兒睡了很多很多天了,就準備上前把他搖醒,發現他仍然腹部一起一伏地做呼吸,可半截身子已經和土融為一體,甚至還有什麽無名植物已開始在這人與土的融合體上紮根。好奇的人們被嚇了一跳,可還是壯膽子破了門,沖進他屋子裏看——真是家徒四壁啊,這裏頭值點錢的東西只有裏屋桌上一塊玉石,還有它壓著的詩稿。蒼白的稿紙已經起了黃斑,旁邊的墨早已幹透,擱在桌上羊毫筆的筆頭也被幹了的墨汁粘成了硬邦邦的一塊。人們看不懂紙上這些是什麽,只知道這是文化人光臨此地留下的紀念物,便滿懷崇敬地把它存在幹燥陰涼地供著。
直到後來,供奉它的地方連著書稿一起被斷斷續續燒了十多年的大火燒成灰燼。詩人的原跡沒了,只有零星幾首詩通過當時人的臨摹品保存了下來。可詩人卻一直在那樹底的土上睡覺,睡了好幾百年,早已全部變成了土人,再沒有人去挪動他。後來他頭頂那棵大樹死了,他身上和周邊又長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漂亮植物,這些植物又養活了一代又一代食草采花的動物,還有一代又一代食肉的和雜食的動物。人走過時,總感覺那條路過於夢幻,催人入眠,但他們一致認為這是詩人的靈感源泉,小鎮的文化聖地。
經過的那條下坡時候,我們也莫名有種困意。這就是詩人靠他長眠培育出的後世圖景,懶散卻生生不息。那時最熱的天已經過了,失去烈毒性子的夕陽掛在天上,用一束橙黃色的光線和路兩旁的樹影拉拉扯扯,來敷衍它值班的最後幾分鐘,伴隨人下班放學腳步組成的鼓點。透過樹垂下來的濃密枝條,有一個泛著水藻氣味的池塘。一只飛行技術奇差的麻雀在離水面不遠的低空上下顛簸著飛行,好像下一刻就要使不上勁,倒池子裏頭睡一覺。
她看到了那只麻雀,就馬上搖頭:「不是這只。今天藍知更鳥不在這裏,但幾個月之前確實在的,我可以很肯定地和你說。它是在這棵樹的這根樹枝上,我記得,那天它還記得我名字,又開始叫我名字,還是原來那個嗓音。我好久沒有聽到它叫我名字了。」
「那後來發生了什麽呢?」
「你看到我們剛剛路過的那堵墻了嗎?這次,我聽見它一遍遍地叫著我的名字。它又讓我追它,讓我沿著上坡方向,也就是那堵墻跑。它飛得很快,展開藍翅膀的那刻好像披著藍色外套迎著風跑的少女。然後它飛過那堵墻以後突然往下飛,可我在那時被這該死的石頭絆倒了,就沒追上它。」
「啊,好遺憾啊,它為什麽要這樣捉弄你呢?」
「你怎麽可以這麽說呢?它一定不是在捉弄我,怎麽可能?分明是我每次都差了那麽一點兒。」
「不過你這樣想:你又在家附近看見了它,說明它已經來找你了,它知道你住在這兒不是嗎?有了這次,一定會有下次的,你相信我,耐心等等,它還會來的。」
「我也是這麽想的,只能這麽想了。這算是安慰我自己吧。」
我們再往前走,已經走到了幾戶人家,這裏的人家幾十年來一直喜歡把竈子放露天來做飯。我們聞到了左邊那家家人做的魚湯香味。魚都是從後面那小池子裏撈上來的。
「你們剛剛在斜坡那兒找什麽呢?」做飯的老人放緩劃鏟子的速度,擡頭問我們。她聽到以後馬上低下頭。
「哦,一只小鳥。」我替她說了出來。說完,她擡起頭,來了說話的勇氣:「對對,一只鳥,是我之前在這裏看到過的,藍色羽毛的鳥,您有看見過嗎?」
「每天飛過這裏的鳥有很多,你們看,我這屋檐下還有個鳥窩呢。但你們說的藍色的小鳥......沒有見過,我在這裏呆了幾十年,從來都沒見過。」
*
看到了那條她必經的路,問了沿路的人家,我們繼續走,走到了她家樓下,我和她分別。回來時我還是走原來那條路,雖然路過時天更黑了,路上空氣帶給我奇怪的困意比先前還重,我還是硬著頭皮通過了,因為我只知道走那條路。後來她因為昏睡不醒沒再去學校,離開小鎮前,我抽空去了她家看望了幾次,也都經過這裏。或許其實是有別的路線的,但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自己去找別的。
那個周五的奇旅之後一段時間裏我們很少再提及那天的事情,我想那兩個夢已經夠折磨她了,再提及起來,她可能會更加難過。只等她來主動找我說。我們像其他學生那樣假裝無事發生地上學。她好像總是看起來很困倦,而且比之前第一次看到她要神情恍惚很多,甚至好幾次我找她借東西時,她手撐著,眼皮卻已經耷拉下來睡著了。她不像那會的我們一樣一夥人聚一起聊各處聽來的小道消息,或者商量下一次怎麽躲著老師們在教室裏打牌,她就坐在角落在草稿紙上寫寫畫畫。
她畫的藍知更鳥越來越多,手法也越來越嫻熟,比送給我的那張好看很多的有不少。每次一畫完,她就用熟悉的意大利斜體寫下「Sialia Sialis」,然後迅速把畫紙夾進那本百科書裏,生怕被其他人看見、過問。書被翻舊了很多,裏頭夾了各種各樣的資料,打印的,手抄的,從別的書上剪下來貼在一張紙上的,關於不同的藍知更鳥的特征,習性,疾病防治,等等,甚至還為了找到更多資料很努力地學外語。每次看到了新東西她還會馬上來和我分享。一個上課總是在神遊的中學生會在這上面如此投入,是那些認為她平平無奇的人怎麽也想象不到的。
終於在臨近第一個學期期末的時候,她終於和我更進了情況:「我好像還沒和你說,但我實在不能再把事情憋心裏了。從高中開學以來我看見了好多次那只小鳥,還是在我那天帶你去的那條路上碰到的,不知道是夢見的,還是現實中真有的,也好像是從夢裏跑出來的,聽上去都很離譜,所以我不清楚。它不像小時候那樣停在我手邊,每次都只是叫我的名字,然後讓我追它,這次又是飛過那面墻就不見了,那次又是我怎麽跑也跑不過去,再下次又是從斜坡旁邊樹林穿進去,在池塘上空飛,我沒有過去的路。」
「可它為什麽要這樣做呢?你一般在什麽時間碰到它呢?早上?中午?還是傍晚?」
「不知道,我要追不上了。真的好累,每次都差那一點點。我每天還要寫完這麽多作業,我哪有這麽多時間去找它!」說著說著,她趴在桌上開始抽泣,我不知道該怎麽安慰她,只好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慢慢地她雙肩就不抽動了——她又睡著了。
那段時間她路過那幾戶人家,老人們問她「小姑娘,你在那裏找什麽呢,這麽急呀?」
「一只藍色小鳥,你們記得嗎?我上次也說在這裏碰到過它,藍色的小鳥。」
「沒見過,其他鳥經常經過這裏,可藍色羽毛的鳥沒有。我們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了,從來沒見過。你什麽時候看見的呢?下次我們幫你留意一下。」
「我不知道是什麽時候,但是我昨天明明碰見了。」
這裏的幾戶老人出於善心幫她找了小段時間,什麽也沒看到,最後他們放棄了,再也沒問過她。她也再沒有主動問過他們什麽。
*
第一個學期之後迎來了二十多天的假期,一個月不到的分別以後回來,她似乎比之前更加恍惚。雖然其他人看來差不多,但我能發覺她的變化。興許就和第一個學期結束前她說的一樣,她看見藍知更鳥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已經到了分不清到底是在夢裏還是在現實的地步。她沒有和我說,我能猜到,但又不能完全肯定。到了第二個學期,她已經很少有稍微清醒的時候了,她百科書裏夾著的資料也沒再更新過,清醒的時候勉勉強強補一會作業。有時她確實睜著眼睛,但是叫她很久都不答應。還有次上著課她直接頭磕碰到桌上「嗙」地一聲響,我們都被這個聲音嚇壞了,以為她發了什麽疾病昏倒了。大家都不知道她叫什麽,老師只好叫我的名字,讓我看看這位同桌情況。她的呼吸很平緩,只是睡著了。
但是我們絕不可以怪她爸媽的失責。很多傳言確是這麽說,試圖讓人們指責他們,這讓他們的生活長期受到幹擾。事實上並非如此。他們其實知道她在學校的狀況,也找了各種辦法找到癥結給她治療,勸她先不要去學校了,在家休養一段時間。但每到白天鬧鈴響的那會,她又是一天裏為數不多時候清醒的,就執意要背著包去學校。有人猜測說她可能是染上了一種「睡病」。
她的情況在那個學期迅速惡化,這時高中第一年還沒有結束。到了那年三月的時候,她已經開始隔三差五地請假。聽說她請假經常是因為清晨四五點跑出家門,睜著眼,但誰叫她都聽不見。她在那條坡上磕磕絆絆地往坡頂的墻那兒跑,有時候甚至中途轉頭準備往旁邊池塘跳,萬幸被跟著她的爸媽攔下了。他們哭著問她怎麽變成了這樣,她只是不停地說:「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我追不上了。」問她在追什麽,她又是什麽都不肯說。
最後一次在學校看到她時已經是六月了。那天她出乎意料地清醒時間很長,因為我每次叫她,她都聽見了,而且馬上有回應。那天他還像我們第一次碰見和後來很多次那樣,她從抽屜拿出那本快掉硬殼封面的百科書,從書裏抽出一張畫,還是只藍知更鳥,這張畫的藍色顏料調得特別好看,你能看出是那種有光澤的藍色。」
「你在看我的畫嗎?」
「啊,對不起......」
「我們都這麽熟了,道什麽歉呀。這是昨天畫的。很奇怪,我這半年畫過很多張,有些還是在學校畫的,但是都不見了,不管啦。你喜歡這張嗎?」
「肯定啊,每張我都喜歡。」嘴上這樣回答她,心裏還是覺得很奇怪——她那半年有在學校畫過什麽畫嗎?
她說完笑了笑,在畫旁再一次簽上那串拉丁文。
「我已經跑了很久很久了,為什麽我每次都追不上它呢。」她邊寫字邊輕輕地說。
之後好幾天沒有看到她,我原本猜測她可能又夢遊了,以她的執意,過幾天還會回來的,況且馬上就要期末考試了。但是考完了她還是沒有出現。同學問我:「你知道你同桌怎麽了嗎?」我不知道。老師好像也不怎麽提及她的事情,頂多進班裏問一句:「那排的空位是誰啊?」說完沒多久,他們就似乎恍然大悟,點點頭,翻開書,繼續上課。
到了後來就是考完試我接到的電話,是她家裏打來的,說她從某天起就一直昏睡著,他們在她桌上找到了我的名字電話號碼,聽她提過我的名字,想來我應該是她在學校裏的朋友,讓我去看看她。
再次經過那條小路已經是盛夏,走到那段路竟然比其他地方涼快些。我下意識地看看下坡兩旁,有麻雀飛過,偶爾還有花頸子的斑鳩,哪有藍知更鳥的蹤跡呢,怎麽都不可能。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裏古代詩人的傳說,不然我會為這條路的涼快感到一些畏懼的。
我走到了她家,被領進了她的書房。書房裏的景象讓我震驚——她趴在桌上,就像之前在課上睡著那樣側臉貼著桌子,身上裹著一張毯子,還有——她右肩上站著的藍知更鳥,是她夢裏的那只,藍色的羽毛裹著胸脯上的紅色羽毛,紅色部分連到喉嚨。
「我們家怎麽會飛進來這樣一只小鳥呢,這裏從來沒有看見過。那天早上我們發現她趴在桌上,它就出現在這裏,一直站在她肩膀上。她桌上還有些資料跟筆記,上面寫的應該就是這種鳥,我們就按著她資料上寫的方式去餵養它,同時也給她些吃的。她嘴會動,吃一些,喝一些,但是怎麽都叫不醒,也不應話。我們還在聯系醫生,這小鎮連個能治療這個怪病的人都沒有。」
我親自和她的爸媽交談過,所以我能戳穿很多不實的傳言。他們並不是什麽都沒做,相反一直都在找能讓她醒來的人。無奈之下他們把她嗜睡,夢遊,還有那只莫名出現的藍知更鳥的事情都說了出來,結果這樣的人是一直沒有找到,倒是最後招來一大群記者。他們圍堵在她家樓下,想要進去一看究竟。她一下從平平無奇的高中生變成了小鎮上的名人。一家人都被這些事折磨得精疲力竭,出門常常被堵,找醫生這件事不得不暫停下來。每次出門都有人圍上去問他們她叫什麽名字,過去在學校在家裏生活的種種。甚至到了後來,還有些人在對面樓的樓梯間舉著望遠鏡,試圖窺視她書房,他們無奈只好把窗簾給拉上。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這些湊熱鬧的人已經在煩擾她家近半年。他們終於受不了,在那天下午人很少的時候把她房間的窗簾窗戶都拉開,準備給她和小鳥透透氣。誰知藍知更鳥就從窗戶飛了出去。據說看到的人都去追那只鳥,最後好一群人都抄起各路捕鳥工具,搶著去追它。
藍知更鳥飛著飛著,就消失在了眾人視野。小鳥飛走以後,房間裏的她呼吸越來越微弱,直至幾個小時以後徹底停了。而外面的人們則忙著去發布尋鳥啟示,當地野生動物協會的專家也紛紛開始關註尋鳥進展,於是就再沒有多少人去圍堵在這家人的樓梯口,只有私底下說說這幾年百傳不厭的各種流言。有一個版本的流言,甚至作為課文編進語文教材,和「貪泉」的故事放在一起對比著學,以告誡學生不要懶惰,不要貪婪。
*
前年秋天我抱病又回到小鎮休養,一整個秋冬,為了恢復狀態,我每天四處散步,但沒有一次往那條路走。好像藍知更鳥在那條路上留下了她的夢,那個夢一直神神秘秘地跟隨她,把她的夢與現實攪成了一團。在我對她的情況和那些夢略知一二以後,它也牽繞著我的心。好像我心裏的一部分也永遠分給了她和藍知更鳥,我時不時回想起,好像就發生在昨天,好像明天還會有新的事情發生,要讓我去期待期待。
那時我也是有打算回那條路看看的。可那年我被那場病折磨得幾乎不成人樣,實在無氣力回去,萬一走到那條坡的半腰,我累得再也無法從邁開腿,也睡倒在那裏該怎麽辦呢?
直到去年我恢復得差不多了,便打算再去看看她和藍知更鳥重逢的那條路,去調查清楚這個地方究竟有什麽詭異之處。附近人家的老人本來不樂意的,但在我一再央求下,他們最後還是你一言我一語地和我講了講這條路的傳說,也就是前文略有提及的古代詩人的故事。說完他們就都困兮兮地打了幾個呵欠,各自進門去了。
聽完那個故事,我再看了看後面那條坡附近的土,每次走到這裏的困意能夠解釋清楚了。我也在一股困意中隱隱有種分不清夢與現實界限的感覺,腦子被攪得一團亂。那個晴日下午,我在那條坡路上也有種預感,還沒能用語言表達出,就先被一種懷念擊中,而那種懷念在未來,似乎是無所依托的。
得知那個傳說之後不久,那片地方就被改造了。坡變得更長更平緩,那裏的植物全拔了,池塘的水也全抽幹了,變成了一片平地。人們在這上面澆上水泥,征用作停車場。
至此,我與她的記憶,也就是圍繞藍知更鳥展開的故事,就算走到了終點。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