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勳的文章說起,記消逝的80與90年代
來去上海駐點多年,連埋葬宋慶齡的萬國公墓都沒去過,6月卻在大太陽下千里迢迢(具體說是從上海住處花了近兩小時交通)來到這位於青浦區的「淀山湖歸園」,前稱華僑公墓。
手中拿著剛才向服務台詢問墓地位置的方位號碼,一個園區的工友好心想領我,卻怎麼也找不找。他問:「墓地大還是小?」「很大。」
一會兒後又問:「台灣的?」「是。從台灣回上海的上海人。」他立刻一副了然的表情,轉個身稍走幾步說:「是不是這個?」
一個石造的大圓盤以微微傾斜的角度靜靜躺在地面上,上面要仔細看才能看出刻字「卓鑫淼先生 1911-2006」。就是這個!一直以為是個高聳的立碑,難怪剛才都沒找著。墓區的工友說,說台灣人他就知道了,這墓碑製作當年也有他的一份勞力在裡頭。

2024年3月,蔣勳發表三篇紀念文章「慶弟—一個女射手的懷念」,懷念東華書局及馬可孛羅麵包店創辦人夫婦卓鑫淼與劉慶弟。蔣勳太會寫,把他擅長的紅樓夢解讀,繁華與虛無,人性中的善良與貪婪,社會階級等都揉雜在一起,甚至是海峽兩岸1980年代、1990年代的發展落差,也巧妙呈現出來。
陽光下得仔細辨清,卓鑫淼先生的墓碑上是這樣寫的:
「浙江寧波人,成長於上海,開創事業於台灣的出版家。他精緻、嚴謹的工作品質,怡然自得的專業態度,嘉惠海內外學子無數,影響社會深遠。
他博愛、自由的天性,樂善好施的心地,讓親人、朋友、同桌、讀者永遠懷念鑫淼先生與人分享知識和品味的君子風範。」
這碑文不走文言文風,簡單親切,不確定會不會是劉慶弟女士請蔣勳寫的。

蔣勳在三篇紀念文章中,寫下了這對有錢又大方的夫妻,如何抓住時機經營大學外文用書市場並致富,如何享受生活以及享受著款待親朋好友的快樂;他們不是勾心鬥角耍手段的商場梟雄,而是勤懇持守且具有文化關懷,卻也無法躲過身旁的各種惡意。
卓先生96歲時在上海連續四天的生日宴後,於下榻的希爾頓飯店跌倒並過世,結束他的快意人生。年紀小他許多的夫人,此後又生活了17年,劉慶弟2023年7月過世,享壽85歲。一生與人為善、慷慨捐輸的她,仍難免於鉅額財富帶來的麻煩,臨終前幾個月常活在自稱上海親戚者的恐嚇攪擾。
如果沒有生命末段受親戚要脅、被財產困擾的部分,劉慶弟的為人和生活讓我想到一本圖畫書的書名「一位溫柔善良有錢的太太和她的100隻狗」。好久以前讀的,書裡沒有壞人,甚至也沒有挫折、奮鬥、誤會冰釋等轉折,當時很懷疑:這樣也可以嗎?可以的,故事溫暖,令人嚮往。
但,現實不只有美善。就像北島的詩作「愛情故事」裡說的,「造福於戀人的陽光 也在勞動者的脊背上 鋪下漆黑而寂靜的夜晚 即使在約會的小路上 也會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時 降落的冰霜 這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 有我和你,還有很多人」。
學佛的蔣勳,旁觀那些圍繞在卓先生身邊的親友、甚至只是等著領小費的飯店服務員,總說有如「魚群爭食」;即使是卓先生告別式上的排著隊的人群,也讓他有「魚群爭食」之感。伴隨這份體悟也有反思,旁觀者的解讀是否又是某種道德高度下的評判?蔣勳很誠實的說,自己「修行不夠」,所以不喜歡看。
這個墓園早年應該是要有華僑身分或海外關係才能安葬在此,雖然也有一批看起來比較樸素簡單的低矮墓碑密集排列,但更多是占地較廣、有所設計的墓地,顯然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一處墓地用石板大器地刻寫出幾個大字:「我們只是暫時分別」。
豁達與不捨,放下與牽掛,不同的生命觀在墓園裡交會,無論你屬於哪一種,死亡都是必然要面對的此生終點。

看著蔣勳的文章,記憶裡各種不同時期的畫面都串連起來了。台北重慶南路的東華書局,上海新華路曾經的馬可孛羅麵包店,以及重建的八里雲門劇場外感謝名單,都有從前路過時我不知道的卓鑫淼夫婦的身影。
1980年代末,大姐考上北一女,家人從中壢北上逛逛的機會變多,我開始對博愛特區的一些地點有了印象。其中,姊姊帶著我們逛金橋書局、東華書局,那真是我心目中優雅大器的地方,一個絕對不同於中壢的城市。
心裡總覺得奇怪,書店裡沒太多顧客好像也經營得好好的。這家書店有很多蔣勳的書、畫和卡片(部分是來自蔣勳姊姊蔣安),也有一些其他書店少見的出版品,當時可能隱約已經猜到,東華並不真以經營實體書店為營利來源。也曾在二樓的馬可孛羅餐廳用餐,氣氛很好;在一個國中生的心中,餐廳上的白色桌巾、走動的侍者與那些晶瑩剔透的水杯,成了台北城讓人難以忘懷的一景。
1990年代的上海正要奮起直追,台資和港資企業開始湧進中國大陸,在餐飲等行業引領風騷。馬可孛羅麵包公司也在1994年進入上海,一樣結合當地文化出版界,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高水準的麵包。上海的西點麵包哪怕到了2010年代都還是普遍讓人覺得「貴又不好吃」,所以水準之上又價格合理的麵包特別讓人珍惜,馬可孛羅是其中之一。
2015年底,首次到上海展開輪調駐點生活。某次來到了知名的舊法租界新華路,歐洲風情的老房子,馬路上一整排的梧桐樹,很舒服的地方,顯然是在都市更新中特意被保留不任意開發改建之處。最特別的是,其中一間老房子就是馬可孛羅麵包店,「是東華書局的馬可孛羅嗎?」有點驚喜,只記得不算貴,店也不奢華,品質不錯。後來的我才知道,全盛時期的馬可孛羅,在上海有40幾家分店及專櫃。

再過了幾年,新華路上的馬可孛羅關了,當時也沒多追究,只當是商人純粹的盈虧考量,也許也是台資企業在中國發展的縮影。看了蔣勳的文章才明白,卓鑫淼夫婦沒有子女,過了80歲以後的劉慶弟,已經陸續把上海的事業結束,有些房產分給員工。
卓氏夫婦逐漸退出兩岸的經商舞台,雖然與經營者年邁又無繼承者有關,但時機上,確實也與中國經濟情勢的消長重疊。
1989年「六四」血腥鎮壓之後,各國對於中國的前景一度有疑慮,但中國以更開放的姿態迎接外資。於是,八零年代的「文化熱」消退了,九零年代人人談賺錢,那些因國企關停或私有化而被拋下的人們,也沒停留在感傷或不滿中太久,急忙跟上時代,做點什麼生意或打點什麼工。
2000年後的中國,因為加入WTO,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經濟成長突飛猛進。2014年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宣布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實質意涵是告別高成長。2022年底COVID-19管制放開至今,中國經濟更低迷。
此時,我站在寂靜的卓鑫淼先生墓前,懷想這對善心夫婦在兩岸都支持文化與教育事業(每年清明節,都有受贈捐款學校的學生代表來掃「卓爺爺」的墓),緬懷曾在台灣1980年代創造外文教科書榮景的東華書局,想像著那些在門口排隊的黑頭車及準備聆聽蔣勳講紅樓夢的貴婦們。墓園還是那個墓園,中國卻不是那個中國了。
蔣勳紀念劉慶弟女士文章: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8/7730939 reading.udn.com/read...、reading.udn.com/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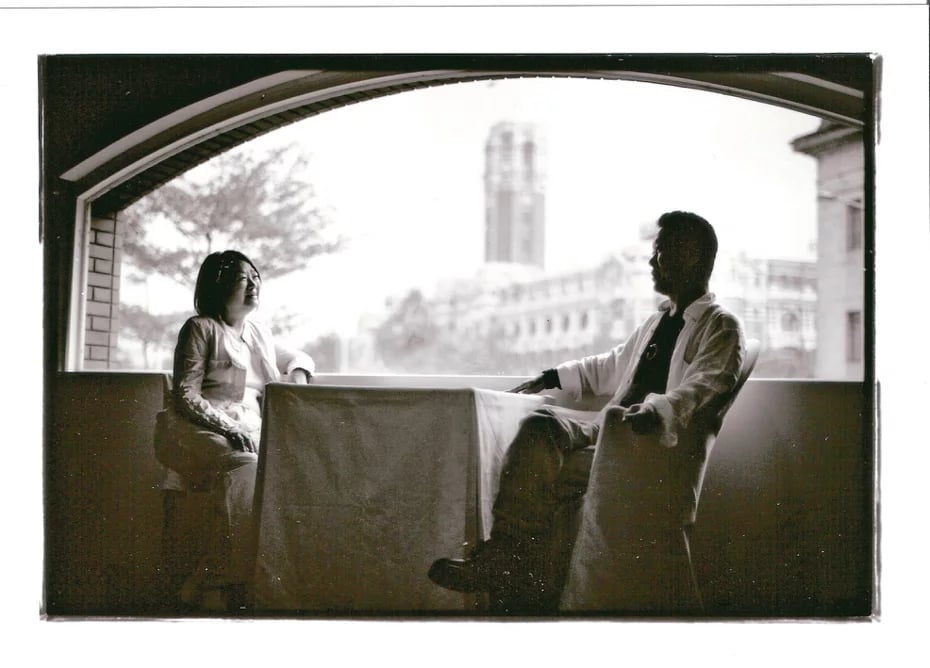
在中國,「八零年代」是一個標誌,直到今天仍經常出現在50、60歲知識界茶餘飯後的聊天裡。但其實緬懷的意義更多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質上的。
「其實誰想真的回去80年代過日子啊?」60多歲的老趙跟我說。即使到2000年代初期,整體來說中國仍然讓人覺得很落後,沒有人想再過同樣物質條件的生活。論開放,八零年代很多人的思維、爭辯還未擺脫過去的意識形態,只是當時沒有那麼厲害的科技監控,仍是傳統鄰里、工作單位相互監視的制約為主,「上面不是允許你隨意講話了,而是因為它有些地方管不了。」老趙又說。是的,即使到現在仍是如此。
但我們都知道,人們嚮往的「八零年代」精神,是從封閉走向開放,在價值上更體現個人為主體的自由,是允許對過去質疑和反思,是對於更開闊未來的盼望。它的魅力不在於現實所在的起點,關鍵是一切正在變化,並且是往好的方向變化。

就在拜訪卓先生墓不久前的4月27日,我來到上海松江新橋美術館,參加朋友們為文學批評家吳亮辦的展覽「漫長的瞬間」。
吳亮今年虛歲70,他在198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很知名,一支健筆帶動了外界對好幾位先鋒派年輕作家的關注,1990年代轉而關注藝術評論,2000年後又回到文學與文化評論。這些年代已經遠去,「漫長的瞬間」也宣告了吳亮對外界的告別。
他得了失智症,語言表達已經力不從心,愛他的朋友們為他舉辦了這樣一場展覽,內容有文壇作家與吳亮的書信往來,包括:莫言、殘雪、王朔等,以及吳亮自己的藝術收藏、朋友的作品等。當天還舉行了生日宴。

開幕式上,導演婁燁也來了,低調的他上前和吳亮握手,但沒有在大家面前發言。他穿著招牌的黑襯衫與黑褲,彷彿在這上海郊區和在法國坎城都沒有分別。吳亮的外甥告訴我,婁燁買下了吳亮小說「朝霞」的版權,這就是為什麼也邀請他來。那還真是令人期待呀。
婁燁的電影從2000年代開始在國際影展上展露頭角。然而,他的養分也是1980年代給的。1989年他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最廣為傳頌的作品「頤和園」描繪的就是1980年代的大學生,命運的轉折點則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在這場熱鬧的、與會者多為50歲到70歲江南藝文界人士的展覽開幕式裡,同時傳達了一個明顯的訊息:一個時代遠去,曾經的先鋒派文藝、曾經的蓬勃探索都已經遠去。
我看見吳亮的告別,也從蔣勳的筆下、上海郊區的墓園裡看見卓鑫淼與劉慶弟伉儷的告別。中國1980年代的一些種子在發芽、結果,但有些也在枯萎與凋零。1980、1990年代的過往,訴說了文學上曾經突破過往的先鋒精神、商場上曾經的冒險樂園、兩岸發展差異下的財富流動,這些對30歲以下的人來說,大概都很陌生了吧。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