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 HAU:民族志理论的回归?
2011年秋季,以毛利语“礼物之灵”为名的HAU人类学理论电子期刊开始了它的生命。面对大型出版社和期刊库的付费墙,HAU旗帜鲜明地强调开源(open access)和“著左权”(copy-left)的价值,所有出版材料完全面向公众,无需任何费用即可阅读、下载。两位创刊者,彼时在剑桥大学人类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乔瓦尼·达·高勒,和刚来到英国学界的大卫·格雷伯,共同在创刊卷首语中表达了他们眼中21世纪人类学的愿景:在一个不被商业公司捆绑的思考共同体中,重新挖掘人类学理论和行动的可能性。一时间,HAU激活了人类学学术网络跨越洲际和历史的再联结。大学纷纷加入期刊合作名单,论辩当下议题的同时,也重新挖掘人类学经典,整理20世纪前辈学者们的论文和未出版稿件。一份完全免费的期刊,仅仅几年一度成为人类学领域引用量第二高的存在。
然而,问题亦在以各种方式暴露:高质量的严格把控对应着紧张和高压的工作节奏。因为缺乏资金,所有编辑校对工作近乎都以志愿方式完成;参与劳动的通常是人类学在读学生或年轻博士后,他们怀抱着对开源模式的认同和对共同体的热诚付出大量时间,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达·高勒在一线经营HAU的数年里,格雷伯并没有全程参与。两人因为种种原因裂痕逐渐扩大,并最终在2018年的初夏彻底爆炸:格雷伯公开发表了一封道歉信,谴责达·高勒在职务之中欺凌、语言暴力学生编辑,并决定划清界限。与此同时,HAU也在7年开源免费的试验之后,被合并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变为混合半开放期刊。
HAU构成了电子时代人类学反思自身的一个重要注脚。它是一个失败吗?为什么一个坚持着平等、开源、反商业的愿景,在付诸实践时却恰恰变成了压榨劳动力的“旁氏骗局”?在最激烈的批判者眼中,HAU的实验失败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民族志理论复兴被视为“礼物”,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哲学;发现与传递“礼物”的人类学,则被想象成某种扁平的、独立于资本主义秩序的世外桃源。这种超然的愿景忽略了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唯民族志理论为中心的取向也会造成危险,可能导致进一步复制而非颠覆学术资本名利场。另一方面,HAU的发展与权威建立于大量初级学术劳工的无偿奉献,志愿工作成为其不稳定劳动环境的一部分。“开源”,不会自动履行平等与公正的承诺。
在公开道歉信中,格雷伯坚持强调开源著左权的梦想本身没有错,很多选择离开HAU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亦表达了他们对这份期刊愿景的认可。那么,是谁“谋杀”了HAU?本文译自为HAU创刊号卷首语的第一部分,是这个梦想最初表达自我的地方。虽然事后发生的一切走向我们已经知晓,但是请让我们借着这个愿景,带着对于劳动的尊重,带着对于学术阶序恶性循环的警惕,重新复盘开源知识与人类学共同体的可能性。
就拿民族志学者来说吧。她在马耶讷的博凯奇花了三十多个月研究巫术。“好兴奋,好刺激,好不同寻常!告诉我们所有关于女巫的事情吧”,当她回到城市的时候,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这样问起她。就像有人会说:给我们讲讲食人魔和狼的故事,讲讲小红帽的故事;吓唬我们,但同时要表明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或者告诉我们他们只是个轻信、落后和边缘化的农民;或者向我们证实有些人可以扭曲因果关系和道德律令,可以用魔法杀人而不受到惩罚;但记得要最后说明他们其实并不真的有如此这般的力量。
珍妮·费弗雷特-萨达,《致命的词语》 ([1977]1980)
我们或许可以说,美拉尼西亚关于人作为“分个体”的概念(M.Strathern)和洛克的占有性个体主义一样富有想象力;理解“印第安酋长制的哲学”(P. Clastres)和评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同样重要;毛利人的宇宙起源论和埃利亚学派的悖论和康德的二律背反同等重要(G. Schrempp);亚马逊的视角主义和理解莱布尼茨的体系一样是一个有趣的哲学挑战……事实上,如果问题是知晓什么是评价哲学的关键——即它创造新概念的能力,则人类学在不寻求取代哲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哲学工具,能够让哲学里沉闷的种族中心主义走廊得到通风,同时将我们从所谓的“哲学人类学”中解放出来。
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与》(2003)
翻译即叛逆。
意大利谚语
有些期刊根据其颜色定义,有些则是根据其名称。HAU的背景色黑绿相间,其下是画有衔尾蛇的旗帜。衔尾蛇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具有反身性的、能自我再造的头尾相连的蛇。至于期刊名——HAU则源于爱德华多·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在他对该杂志慷慨的背书中所说的“恰到好处的模棱两可”。既然马塞尔·莫斯把毛利人的hau一词解读为“礼物之灵”,那它必定是一切模棱两可的东西的精髓,一切不充分之物,也是一切陌生理念在翻译时具有无穷生产力和启发性的东西。

但要注意:当我们说“陌生”(alien)时我们是在说“陌生”理念,这些概念绝不仅仅来自奇异而浪漫之地;HAU无意将自己限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或亚马逊的雨林里:我们实际上认为“异域”(exotic)是民族志的保留地,但那是因为好的民族志让一切都具有异域性。HAU号召我们重新唤醒一切民族志见解的理论潜力,无论在哪里发挥作用,让它重新发挥其在创造新知识方面的主导作用。最重要的是,我们把民族志看作是对概念断裂的实用主义探询。借用阿登纳一句具有启发性的话来说(1987),“偏远地区”是HAU的兴趣所在,但HAU将其视为奇点或小型社会空间——不论是丛林或是城市,其中布满了“事件的丰富性”、概念的模糊性和社交上不同寻常的无聊。偏远地区不仅仅在等待陌生人-国王们(stranger-kings),它们同时充满了危险的陌生人-概念(stranger-concept),这些陌生人需要被邀请进来,作为尊贵的客人予以接待,才能被承认为亲属,最终甚至是祖先。
我们并没有在这里阐释什么特别新的东西。相反,将hau这个词作为我们事业的标志,我们将自己置于特定的人类学思潮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一思潮处理的正是这种概念的断裂,以及它们所引起的那些“猜测性的惊奇”或“积极的含糊其辞”。像HAU这样的概念,毕竟并不仅是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漂浮的能指”——能够包容任何意义和意义的缺失。它们是事件、不可分类的残余,通过将不同的文化形象和立场并置,重整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类别。正如玛丽莲·斯特拉森所说,这是一个过程,它经常“赋形于否定或反转我们熟悉的术语间的关系”、或如她所说的,“分岔”(bifurcation),人类学分析在那里被引向意外的方向。在民族志理论化过程中,分岔无处不在,在弄清楚我们所认为的自然与文化时、我们与他者、人与非人、固有与超越、宗教与经济、道德与物质之间的区别、矛盾与停滞的过程中。它们常常以挫折告终,与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帕洛玛尔》中帕洛玛尔先生试图分离和分析海洋中单一波浪时所遭受的挫折类似:他最终意识到,人们终究无法在心灵中同时保留那么多的视角。
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尝试给民族志理论下一个定义:它是陌生人-概念(stranger-concept)的转换,它并不意味着仅仅试图在两个实体之间建立意义的对应,或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构建异名同义的和谐,而是要制造一种断裂的同名异义性,破坏所有踏实的地方感,而要想修复这种破坏只能通过构想全新的世界观。这一意义上,民族志理论的运作方式无异于艰巨的翻译,相近于霍夫斯塔德所描述的把刘易斯·卡罗尔笔下Jabberwocky及其它的混合词从英语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时所面临的挑战。通过试图建立两个“无意义”词汇之间的等价关系,人们必然要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发明术语和概念,从旧的语言范畴中开辟新的联系。毋庸置疑,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与单纯的文化不可通约性的浪漫召唤大相径庭。乔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曾经注意到,从来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从田野点归来后宣称他或她什么都没弄懂。或者正如翁贝托·艾柯所指出的,人们不仅应只看到翻译在本体论上的局限,而应允许“几乎在说同一件事”也足以作为翻译,并且接受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无法比较,而意味着可比性会在翻译中逐渐生成。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同意,从田野现场(无论是西藏、马达加斯加还是伦敦的上流社会)中了解到的95%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很快就会具有直观的“意义”。至于剩下的5%,与其说其难以理解、完全陌生,不如说这是过剩的——至少就概念化所需的努力而言是如此。而对那些过剩的剩余物、那些当世界(愉悦而有效地)脱节时出现的奇迹和残余,HAU尤其希望能主持相关的“民族志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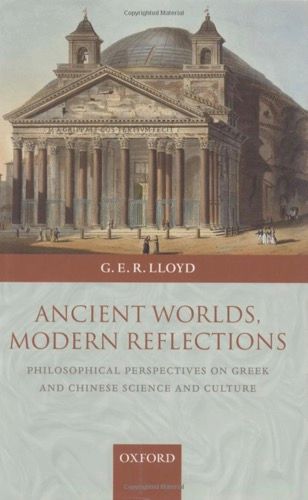
01.系谱
但是,我一直特别感谢我所理解的帕斯卡尔对“大多数人”和“民众的健全观点”的关注,这种关注毫无天真的民众主义痕迹;而且我感谢他总在寻找“作用因”的愿望,他的愿望与他的关注密不可分,他寻找表面上最不合逻辑或最微不足道的人类行为——比如“中日逐兔”——的存在原因,而不是像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一样,对此要么愤怒,要么嘲笑,这些人总是准备“扮演哲学家”,他们试图通过对常识观点的虚妄表示非同寻常的震惊而耸人听闻。
皮埃尔·布迪厄 著,刘晖 译,《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2页.
促成HAU成立的起因是在去年2月份乔瓦尼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学没有一个通用的、高质量的、开放获取的同行评议期刊,并以“著左权”(copy left)的解放来取代对“著作权”(copyright)的需求?诚然,确实有少数(大多数可耻地被忽视了)稀有的开放获取期刊的例子,这些期刊拥有享有盛誉的学术传统。但他们主要还是内部出版物、研究生阅读的基地,甚至还有一些是(如《亚洲民族学》、《低地南美洲人类学学会杂志》、《博物馆人类学评论》——该杂志的创立归功于杰森·贝尔德·杰克逊)出色但是区域性或专门学科的期刊。有些优秀的开放获取期刊但并不面向于英语读者(如《马纳:夏威夷学报》)。开放获取也有可能会被误解为作者一端“更容易发表”(和更少的质量把控),甚至(但愿别这样)“智力低门槛”。乔瓦尼认为现有机构没有真正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出版速度。年轻学者们被丰富简历的焦虑所困扰,为学术职位和奖学金的激烈竞争抓狂。然而,他们还是要等上两年才能将一篇文章投进高端期刊。想想在博士写作研讨会上、美国人类学会讨论会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的工作坊上,出现了多少各式各样的主意呀。由于担心自己的观点会在通往印刷文章或专著的漫长道路上被剽取,学者们总是犹豫是否要分享他们最好的想法。一个解决方案难道不是这样一本期刊,能让作者投稿后六个月内便能经过同行评议发表、并能将这些原创性的想法传递给尽可能多的读者吗?
Justin Shaffner很快就加入到了团队里,他带来了在出版社和期刊方面重要的编辑经验,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电子化创新,如《开放人类学合作组织》和《美拉尼西亚人》。接着是Morten Nielsen,他为杂志成立的最初步骤提供了帮助。然后是大卫·格雷伯——对他自己以神圣王权的奇特形式被安置在神秘的自由编辑的角色中而感到困惑;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成员是Stéphane Gros,他迅速成为杂志的骨干——实际上他是一个不屈不挠但温和的人物,在聚光灯外工作,以高级文员一般的效率处理稿件。如果您正好在阅读这篇文章,您要知道,Stéphane 大概在早餐时检查了三次,甚至即使在将稿件发给审稿人之后。这些“编辑助理”们很快就成为了HAU创立时的重要伙伴:Rachel Douglas-Jones(后来因其在市场推广和艺术方面无懈可击的领导才能而获“晋升”为副主编)、Mylene Hengen(我们慷慨的译者)、Harriet Boulding 和 Amiria Salmond(他们拥有完美的编辑能力)以及Philip Swift——我们编辑工作中的万事通。

在组织上,HAU的构想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本学科正在遭受商业出版的支配,在大多数学者都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工作时,无耻的订阅价格正在严重破坏对人类知识的追求。从智识的角度来讲,HAU的发展源于一种挫败感——挫败于这门学科独创见解的贫困——及由此而来的感触:人类学,至少就其与其它学术领域的关系而言正在进行智力自杀。比如:
- 1913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受弗雷泽(1906-1915)和罗伯逊([1889]1995)的作品启发,发表了名为“图腾与禁忌”的系列文章([1913]1952)。
- 1931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写了一系列哲思,被称为“谈弗雷泽的《金枝》”([1967]1993)。他在其中发展出了一套有关魔法的理论。这套理论其后引领他写成了《哲学研究》(1963)。
- 四十年代晚期,让-保罗·萨特决心写一部存在主义道德论理的作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为夸扣特尔人的散财宴[1]所困扰——他相信其一定指出了某种出路摆脱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之困局,虽然其在表面上貌似完美地呈现了黑格尔所描述的那种追求认可的挣扎(详见萨特[1983]1992:373-79)。
我们能够想象有人以类似的方式运用当代人类学的种种概念么?
实际上,在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夜的重要思想家中,很难找到哪一位不觉得需要了解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学概念。从民族志工作中直接提炼出来的概念——比如玛那、萨满信仰、图腾信仰、散财宴和禁忌这样的词——或是人类学分析所产生的概念——比如魔法思维、君权神授、亲属系统、礼物、牺牲式意识形态或创世神话——全部是最受热切争辩的学术话题,是所有人,包括哲学家们,都必须严肃对待的概念。
如今的情况则完全颠倒。人类学家不再从民族志中提炼他们所用的概念,而是主要参考欧洲哲学——我们用的术语都是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或者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而在人类学以外,没几个人在乎我们围绕这些概念进行的论述。因此,我们成为了一个狭隘的边缘学科。与此同时,从前的那些人类学争辩好像压根没有发生过一样。德勒兹派和思辨现实主义者们在写作中讨论本体论,和生命之模糊性(elusiveness)(详见Thacker2020),而其他的学科则颇为严肃地争辩这些学者的思考,谁也没有注意到丰富的讨论玛那的人类学文献。拉康派们热烈地辩驳着拓扑学,但没有任何人记得利奇(1961)甚至列维-斯特劳斯([1985]1988)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观点。[2]更奇怪的是,人类学家们经常参考福柯的生命权力,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前提,也即主权权力对于健康、生育力和人口昌盛的关心是某种现代性的剧变,与那之前的政治事件有根本区别,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学科中大量的有关“君权神授”的人类学文献,而这一概念所探讨的恰恰是主权权力对于健康、生育力和人口昌盛的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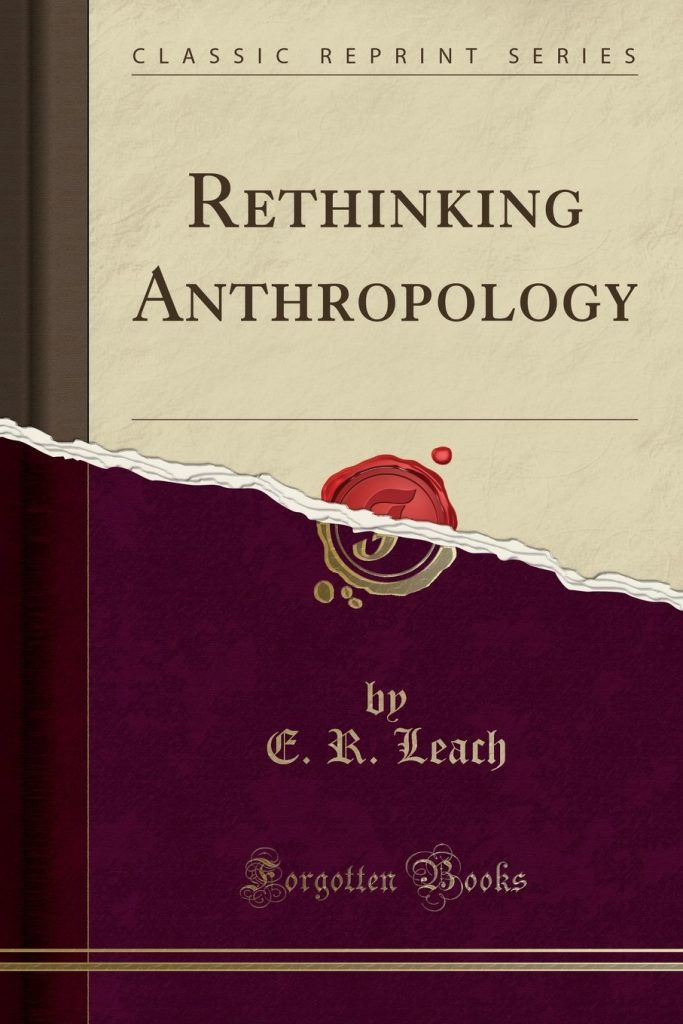
这是如何发生的?该怎么解释这无与伦比的信念的惨败?
原因这一可能仅仅是,人类学所面临的任务实在过于艰巨。不久以前,我们还可以写一部部讲述“爱”,“真相”,或“权威”的历史,从古希腊或古罗马讲起——或是从旧约开始——接下来仅仅考察欧洲资料即可。要是想拥抱世界性,就将“西方历史”与“东方哲学”中对这些概念的讨论作对比,也就是说,向在印度和中国被写下的思想传统致个敬。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就连马塞尔·莫斯这样的大家都只有有限的民族志案例可以参考,即使当他极力想做到全面。在过去还可以把案例按照进化论排先后顺序,也就可以挑出一两个案例来代表其他全体。因此,学者们也可以不假思索地引用人类学的成果。
如今这已不再可能。
可以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种颇为奇特的困境。北大西洋的强权已不如从前;即使是在旧帝国秩序的诸中心,社会也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在这样的世界里,维护以往纯粹欧美中心的知识体系显得愈加遥不可及。但与此同时,我们积攒的有关各个思想传统的知识实在过于庞大,叫人无法招架。这不仅限于我们更广泛地接触到了全世界的书面思想传统,从中世纪伊斯兰密契主义到非洲哲学。人类学已经揭示,从喀麦隆到温哥华岛、从也门到西藏有无穷无尽的一大批所谓物质哲学[3],这些哲学系统通常含有无比成熟的有关人性之困境、社会性与宇宙体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无法脱离各式各样的物质存在。这些哲学传统并不分高低。令人惊奇的事实在太多了。有谁能够掌控这么多知识?这不禁让人怀疑,其他学科的学者的反应是一种静默的、但非常真实的恐慌。要知道的太多了。但又不能干脆忽视其他这些传统:那样做难道不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就连从两者中选出一个都显得毫无根据——依据什么标准呢?要涵盖所有的又不可能。
在这种语境下,八十年代人类学的自我批判被用来服务了某种完全偏离其本意的目的。实际上,从其初始,人类学就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的战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对于外人来说,八十年代的自我批判则提供了一组便利的、简化的口号,以用来打发人类学知识——既然这些知识从根本上讲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主义的,那么它就不真的是知识。这样一来,那些想撰写爱、真相与权威的历史的人就又可以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写起,接下来也许再写写笛卡尔或者萨德侯爵,最后用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收尾,完全不提欧陆哲学传统以外有任何视角存在。很多时候——实际上,大多时候——这种仅仅专注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复兴是以批判(critique)的形式出现的——但这一批判必定限制于西方哲学内部,因为这些批判者同时相信,在当代大学接受训练的学者是无法跳出这个框架进行思考的。最后,就连人类学家也开始效仿这种做法,彻底放弃根据他们自己的民族志工作创造理论词汇,转而借用那些仅仅参照西方哲学传统的思想家所发展的词汇。最后,那些认同非西方传统的学者也默默接受了这一做法,部分是因为这一做法巩固权威的构架方式,因为它意味着,一旦其他的“文明”传统被承认,那些传统也会呈现出类似的源于书面、从上至下的结构,而非源于物质哲学、从下至上的结构。而人类学的研究方式通常会揭示后一种结构。
我们如此容易地变得愈加狭隘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学术人(Homo Academicus)在当代的根本性质。民族志理论正逐渐意识到内省的必要性,转而去做日常理论的民族志,去发现知识是如何在每一天的点滴互动中产生的:学生、教职人员、学术部门和资助机构之间的互动。很多人感到不满的是,人类学为了资助机构多变的口味而往不同方向碎片化——显然,这是HAU自创建以来收到极大支持的因素之一。民族志的深度逐渐被竞逐“月度最佳概念”的游戏所取代——令人害怕的(the uncanny),令人生厌的(the abject),情感(affect),生命政治(biopolitics)——每个概念都要没完没了地解读,并在博士写作研讨会上骄傲地展示,但只要从斯宾诺莎、海德格尔、罗蒂或巴塔耶的著作中重新挖掘出下一个词汇之后,这些词就可以抛弃了。反思马林诺夫斯基的《珊瑚园及其魔法》这样的作品的杰出之处和它们的魔法所在,绝对不像引用某个欧洲哲学家的某个不为人知的新术语那样“酷”,它可以生出有趣的新的光影游戏,投射到人们以为人类学家仍没走出的黑暗洞穴里。不然,人类学家们还细致地研究着他们手里的洛可可式民族志人像和各种原始用具呢。在这个世界里,除了比谁知道的名字多,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好像没有谁注意到,学者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以为回收大约1968年至1983年之间的法国理论家是件很时髦的事。但这正是我们称为“经典摇滚”的时期(也就是说,读着思想界的佛利伍麦克合唱团(Fleetwood Mac)和齐柏林飞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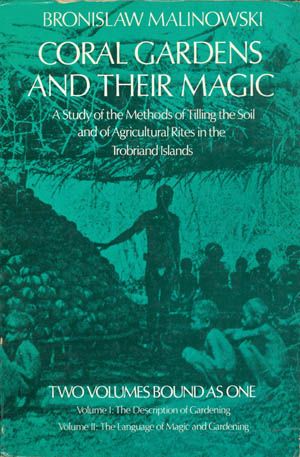
这一过程包含一种有趣的递归性(recursivity):作文中列出或讨论课中提到的学生名单如何影响教职人员后续的理解?互联网和数字革命已经完全改变了获取知识的过程——这一活动现在包括广泛访问博客、电子书、官方和盗版PDF的广泛普及和流通、以及像谷歌图书这样的搜索引擎。除少数例外,信息最丰富的人文博客均由欧陆哲学家经营,他们发展了许多出色的原创运动与思想潮流,几乎完全依赖数字工具和在线联络(比如说,“思辨现实主义”就通过博客、在线文章和开放获取资源实现了有效的传播)。
如今,人类学学生典型的研究姿态不是穿过图书馆过道以提取古旧的专著或选集,而是到谷歌上搜索某一话题,或去查看某本书的PDF是否已被上传到某个互联网存储库中[4]。学生和图书馆都缺乏购书的资金,这让问题更加复杂了。我们都喜欢我们的PDF集合,有各自最喜欢的博客,但是这些工具也有其缺点;他们有可能导致“快餐”理论,零碎阅读,组合微型摘录,或叫人急切地滚动网页以捕获上口的概念。任何判过本科生作文的人都知道,维基百科现今在有关仪式与宗教的作文中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在部分上(或全部?)取代了老一代更加可靠的著作,诸如莫里斯的《宗教人类学研究》(1987年),莱撒和沃格特(Lessa and Vogt)的《比较宗教学读本》(1979年),甚至各种美洲印第安人手册。
七十年代后期,翁贝托·埃考(Umberto Eco)在思考复印机在学术界所扮演的角色时发现了类似的过程,并警告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他所命名的“Xerox文明”以及复印机所提供的“思想辩护”。
Xerox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它时长会构成一种思想辩护:一个人离开图书馆时手里拿着一大摞复印件,确信自己永远也读不完手里的文件。最后他发现哪个也用不上,因为所有纸张都混在了一起,乱七八糟。尽管如此,他仍然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些书的内容。在Xerox文明之前,同一个人曾经在巨大的阅览室里手写卡片,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便沉淀在了他的记忆中。随Xerox引发的焦虑而来的是这样一个风险:在图书馆浪费整天的时间复印永远不会被读的书。
([1977] 2005:87,达·高勒的翻译)

埃考强调,堆积复印件会导致“累积之眩晕”,他的大多洞见也可以应用到如今大批唾手可得的PDF上。作为在线期刊的编辑们,大讲特讲数字人文的危害也许看上去很虚伪,但我们在此提出的建议实际是保持警觉——或更准确地说,是对生产与再生产学术知识的社会前提进行细致的调研。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学术界的Xerox文明出发,我们不妨将当前身处的情况视为“学术生活的Adobe化”,而我们将受益于研究PDF的社会生活的民族志。
我们质疑当代人类学对欧陆哲学的顺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哲学不感兴趣;正相反,我们希望发展出一种不同的与这一哲学传统的互动方式。因此,在我们期刊的首期中,我们特意决定不加编辑出版玛丽莲·斯特拉森于九十年代初期撰写的手稿。在其中,她对德里达、鲍德里亚和拉康进行的解读颇有趣味,并向我们展示除了对(通常是过时的)欧陆风格盲目崇拜以外还有其他思想资源。人类学家们不需要“应用”德里达派或德勒兹派的概念来展示我们的“他者”是如何在本体论视界思考(近来,所有原住民似乎都变成了德勒兹派),而是可以有批判性地探讨学术概念生产的可能性前提,避免(或者借助巴特比作业网(Bartleby)的帮助,决定他们只是“更不想”)通过调配哲学概念、术语和流行语以达到华丽的虚荣感。我们宁愿让蒙古学家们来展示“游牧机器”实际上和德勒兹和瓜塔里所以为的截然不同,而进一步追溯德勒兹和瓜塔里这样的哲学家如何从民族志的丰富概念中汲取灵感(还借鉴了从贝特森(Bateson)的《高原》到克拉斯特派(Clastrean)国家理论的各种思想资源)。用受帕斯卡(Pascal)启发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话来说,“真正的哲学轻视哲学”(2000:2)。相对于那些渴望“扮演哲学家”并掀起又一阵有关“异常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或国王的多个身体(the multiple bodies of the kind)(谢谢你,Andrew Shryock)的思想旋涡的人类学家,我们更感兴趣、更关心的是那些认识到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可类比之处、仔细考虑两者之间的不同何在、并同时有足够的勇气创造他们自己的概念库的人(我们要在这里感谢Martin Holbraad)。
人类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同样富有成果。从韦伯的《古犹太教》([1917]1952),到罗伯逊·史密斯的《闪米特人的宗教》([1889]1995年),再到鲍亚士的《钦西安神话》(Tsimshian mythology)([1916]1970年),社会理论家和人类学家们将历史数据作为“激进的他性”的例子以进行深刻的思索,挑战西方的,和/或“自然的”,“科学的”或现代的宇宙(cosmology)。最近的例子有Prytz-Johansen(1954)对毛利宗教本体论(religious ontologies)展开的宏大的民族历史研究,Tambiah(1977)对东南亚“银河政体”的分析,Burghart(1978)对尼泊尔的皇家礼物交换、种姓和禁欲等级制度的研究,Geertz(1981)对巴厘岛的内加拉系统的研究,以及Sahlins(1998)对西方宇宙论的人类学思考(我们在此要感谢Gregory Schrempp和Martin Mi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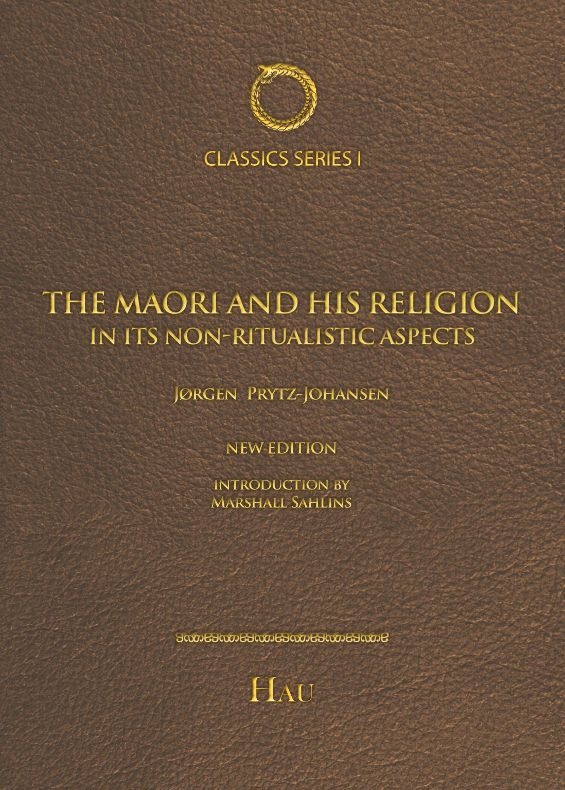
在就这些主题进行初步交谈之后,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我们很快意识到,返归民族志理论的愿望是存在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是至今还没有名字。致HAU成立之路包括几封发给资深学者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既热情洋溢,又带有绝望。我们需要积累声誉和学术玛那,才能有效地传达这一想法、散布我们的愿景。我们需要其帮助的学者在发文章、攀登期刊排名方面无利可图,他们必须有资本在未知领域冒险。我们的最初交流所引发的反响与热情很快蔓延开来。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立马做出了回应——读他的第一封回复引发了怎样一种情感啊——还有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爱德华多·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珍妮·法夫雷特·萨达(Jeanne Favret-Saada),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布鲁斯·卡普弗雷尔(Bruce Kapferer),莫里斯·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基思·哈特(Keith Hart)和其他很多人。这其中还包括广受尊敬、经验丰富的数字人类学领域的专家,他们有着无比的合作精神,例如Mike Wesch,Mark Turin,Chris Kelty和后来的Alex Golub(最后两位是受广泛阅读的人类学博客Savage Minds的创始人之二)。利奇、皮特-里弗斯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继承人慷慨地给予了许可重印被忽视的民族志理论经典。这不是蝴蝶效应,而是雪球效应。隆隆的声音确凿无疑,有什么就在地平线上滚动、增长。
十个月以后,我们还在陆续收到无与伦比的反馈。有人说,我们开始了一个运动。无论是否如此,我们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认可、收到的手稿的质量、以及以出色的作品或建议支持我们的愿景的作者们的热情和才华感到敬畏。我们还要感谢认识到这一世界性愿景之重要性的所有人:一个免费获取的非商业的人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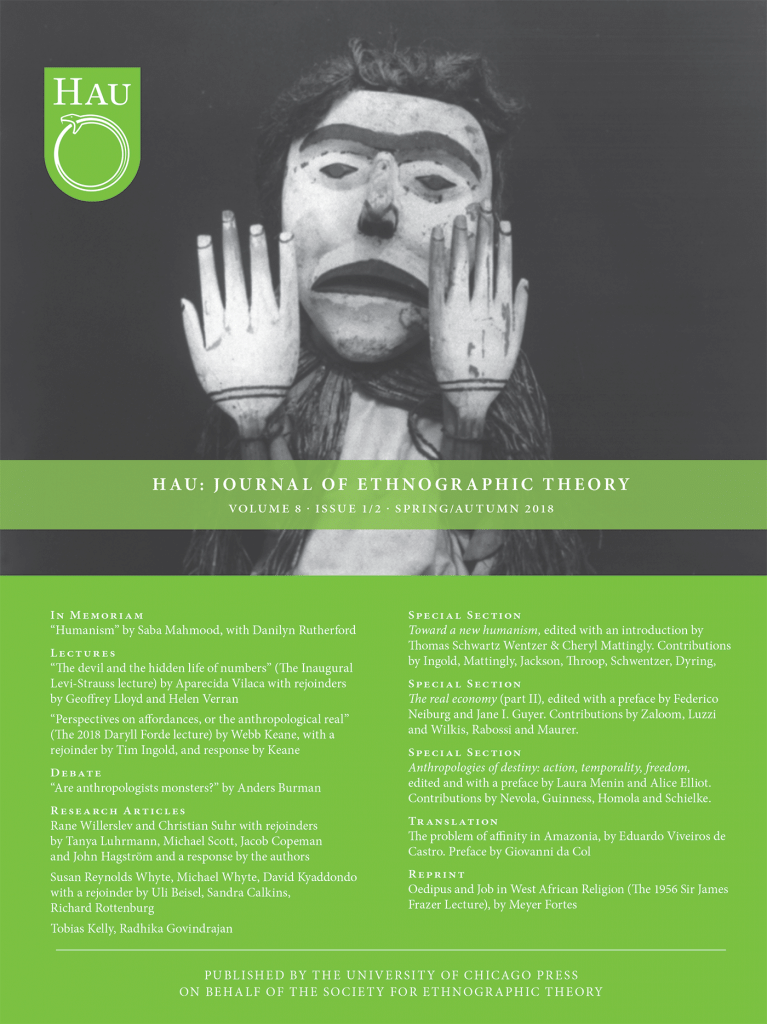
注释:
[1] 译者注:夸富宴或散财宴(potlatch)是流行于各北美原住民族群的一种赠礼仪式。
[2] 利奇受过数学和工程学训练,讨论了拓扑学和其他非欧几里德的社会模式;列维-斯特劳斯是最初引用克莱因瓶的学者之一。虽然当代拉康派们忽视了这一点,拉康本人是李维·斯特劳斯的热心读者。
[3]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物质哲学”并不限于没有书写传统的哲学,虽然大多“物质哲学”确实如此。我们要强调的是那种扎根于日常实践的哲学,区别于那些诞生在专门机构制度、由一些长期脱离日常生活以进行思考与学习的个人写成的、更加抽象的思想系统。
[4] 例如scribd、aaaaarg.org和library.nu这样的网站是谈话中经常提及的。
延伸文献:
Bruce Kapferer. The Hau complicity: An event in the crisis of anthropology. https://www.focaalblog.com/2018/07/09/bruce-kapferer-the-hau-complicity-an-event-in-the-crisis-of-anthropology/
Claire Lehmann. How David Graeber Cancelled a Colleague. https://quillette.com/2019/09/09/the-anarchist-and-the-anthropology-journal/
David Graeber. HAU Apology. https://davidgraeber.industries/2018/06/11/hau-apology/
Don Kalb. HAU not: For David Graeber and the anthropological precariate. http://www.focaalblog.com/2018/06/26/don-kalb-hau-not-for-david-graeber-and-the-anthropological-precariate/
Patrick Neveling. HAU and the latest stage of capitalism. https://www.focaalblog.com/2018/06/22/patrick-neveling-hau-and-the-latest-stage-of-capitalism/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读书会第30期 |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 Corona读书会第7期 | 全球公卫中的跨国人道主义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夏季
- Corona读书会第28期 | 大坝与水利政治
- 特朗普人类学(一):手、谎言、#魔法抵抗
- Graeber丨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 黑色海娜:对苯二胺、孔雀与不存在的身体
- Corona读书会第32期 | 松茸的时日
- 编辑手记 | 《末日松茸》: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
- 影视造梦:横店“路人甲”们的生活群像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小丑”
- 哀恸的哲学:“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11-12月
- 从丁真到拉姆:直播时代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
-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基督教,和圣诞节
- 结绳志的二零二零
- “两头婚”的实景与幻象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哥伦比亚2019年的抗争行动:不期而遇如何构建共同未来的想象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20年智利抗争:与废墟同在
- 在炉边和在狩猎的女人们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坚持与归属:重思印度新德里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运动的起落
- 无母体的子宫,无身体的器官
- 为什么疫苗是一个社会问题?
- 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对话Rachel Murphy
- 东北 | 东北完了吗?否思通化的“官本位文化”
- 与系统周旋:关于骑手劳动过程的田野观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①
- 被绕开的劳动法:外卖平台发展史与骑手劳动关系的变迁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②
- 平台内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③
- 春节特刊·乐 | 为何春晚不再欢乐——Fun的社会性
- 春节特刊·情 | 三代女性的离散与游牧
- 春节特刊·婚 | 先恋爱,后结婚?
- 春节特刊·牛 | 牛的人类学
- 人口贩卖:历史延续与全球难题 | 一份书单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厄瓜多尔的社会运动:从2019年十月抗争到新冠疫情
- 世界母语日与母语政治的变迁
- “无障碍”之障 | 实时字幕、聋听空间与沟通劳动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1年1-2月
- 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 聚焦乌俄 | 最不幸的一代
- 乌克兰书单:超越霸权之眼的民族志视角
- 国际HPV知晓日 | 一则关于HPV的故事
- 三八节快乐 | 听她们说
- 它们 | 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
- HAU:民族志理论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