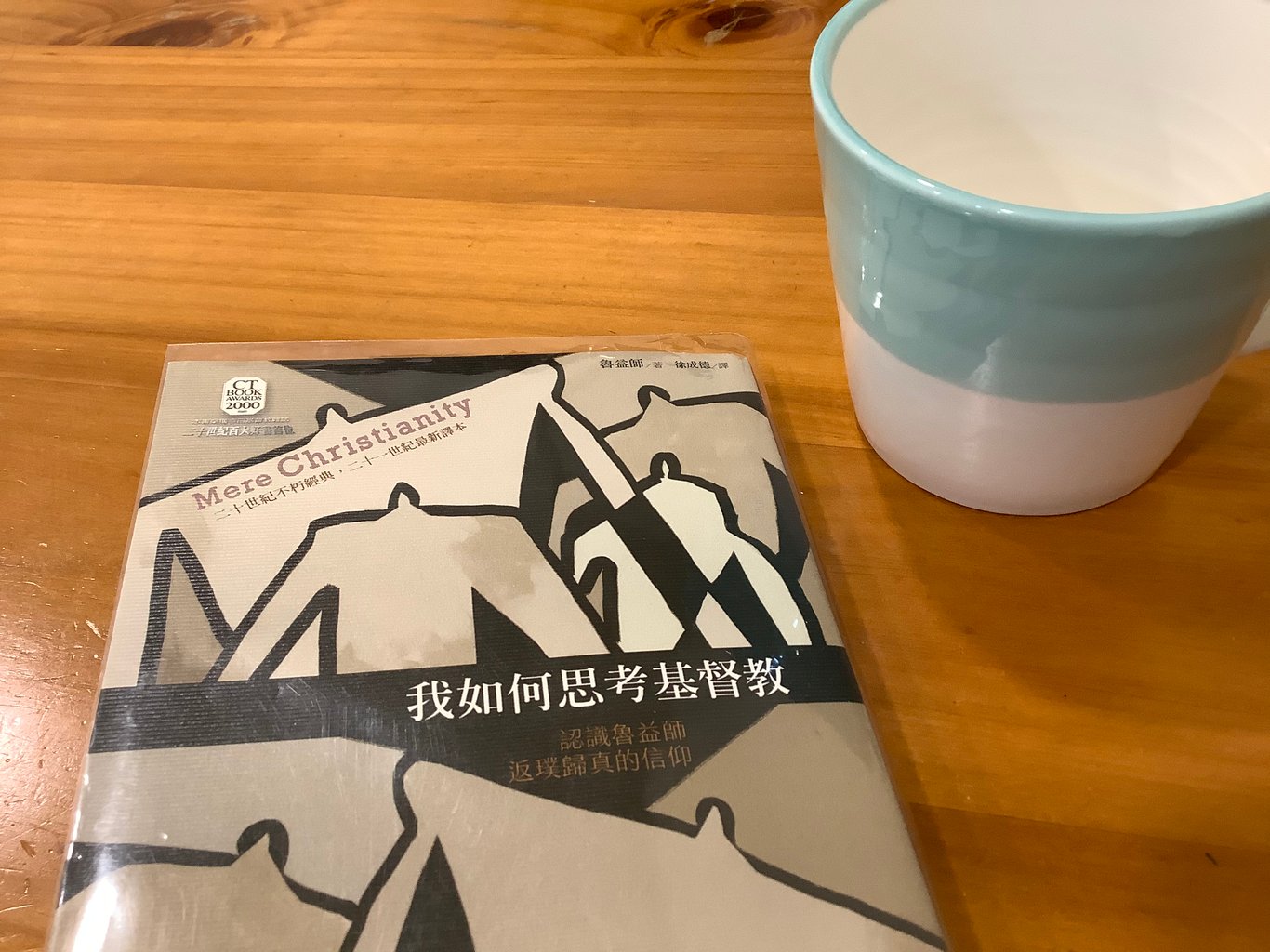荷風的東京散策記

永井荷風讓我想到鄧南光、翁鬧、李火增這些有錢人家的少爺,他們未曾為生活所苦,生活從來也不曾成為他們的目的,他們被奢侈養成了一種特質,那就是沈溺。沈溺於自己所喜好的事物,下定決心不為其他的事物而活。
這是嬌慣,是敗壞,但也是一種昇華。他們的感性和關注都再也無法正常,一般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自然脫落的那些事物,根深蒂固地在他們身上,你可以說他們就像彼得潘,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裡,再也無法長大。但是這樣的沈溺不知為何令人羨慕非常。
1879年出生的永井荷風,出生在江戶風情仍然濃厚的明治時代,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目睹著城市文明逐漸西化,經歷震災後街景的劇烈變遷,一樣又一樣美好的事物消逝,永不復返,喜愛散步閒晃的他用感受寫下紀錄這一切的文字。

頭帶西洋黑帽,手持黑傘,一身歐洲裝扮的荷風,熱切熱愛日本的歌舞伎和落語這些傳統戲劇文學,因為對他來說並不是傳統是好的,或西洋是好的,而是單純追求所有浪漫美好的事物。
父親是大實業家,永井荷風不需憂慮生計,雖然背負著父親出人頭地的期待,永井的心裡始終只有父親眼中那些無管緊要的風花雪月,對於同樣喜愛文學的父親來說,文學只是閒暇的調劑,與朋友交際的風流,但是對於永井荷風來說,文學就是他唯一能夠看見的一切。
父親逝世後,永井立刻辭去慶應大學的教職,從此過著無所事事、放蕩不羈的生活,1920年代時,興趣從藝伎轉移到銀座的咖啡館的女侍,獵豔的際遇寫成了名作「濹東綺譚」(濹指隅田川的舊稱墨田川)。
感覺永井荷風如果不會寫作,也不過就是沈溺於風化場所的廢柴一個。像這樣有才的廢柴,日本時代的台灣作家也有一個,那就是寫下「天亮前的愛情故事」的翁鬧。
翁鬧的小說描寫主角與咖啡館女給之間似真還假的戀情,在那個自由戀愛被認為敗德的年代,唯一接近自由戀愛的體驗就是與咖啡館女侍之間的曖昧關係。小說裡對比著咖啡館裡認識的女侍,和故鄉等待著自己的青梅竹馬。一邊是濃艷的,一邊是純情的,主角(自戀的?)在兩者之間猶豫不決。
當20出頭的台灣留學生翁鬧,流連於銀座咖啡店,擔心自己是不是太受歡迎時,永井荷風已經是將近五十歲的中年人,兩個人也許曾經在銀座飄落著飛雪的街頭擦肩而過,帶著同樣孤獨的身影,尋找著幻想中的溫柔鄉。

同時代的鄧南光,出身北埔富豪世家,從高中開始在東京讀了12年書,17到29歲這段青春歲月都在這個大都會度過。
鄧南光到銀座的金城商店補充底片和攝影設備時,是否也曾經看過永井荷風散步的身影呢?在他的鏡頭底下,保存了東京戰前最美好絢爛、歌舞昇平的那個年代。銀座的喫茶店、咖啡座、啤酒廳(ビアホール)、淺草的戲院、劇座⋯⋯在相機背後,按下快門所保留的瞬間,似乎也是鄧南光唯一看見的真實。

讀完法政大學的學位,回到台灣的鄧南光,有很好的學歷人脈可以進入文官系統,或是進入商業戰場,但他的選擇是開一間攝影館,一輩子安安穩穩的將他最喜歡的興趣當作職業。
你可以說這是富家少爺的奢侈、錢財堆積起來的浪漫,但它畢竟是確實的浪漫。我們一生總有什麼主題,使我們不致迷失。能夠尋找到這樣的主題,是幸福的。
在葉石濤的筆下,批評這些到東洋留學的富家子弟,有許多是在咖啡座和劇院「遊學」的,連課也沒去上。葉石濤雖然也是世家子弟,但在他那一代已經沒落了,不具有供他到日本讀書的財力。葉石濤批評這些能夠到日本讀書的有錢少爺,但他自己的作品裡其實也充滿了有錢少爺的浪漫意識,不管在哪裡都可以發展出一段曖昧的戀情,這是不是一種可以稱之為賈寶玉的浪漫病?
無論如何,還是很喜歡荷風筆下的風景。我也覺得不管什麼樣的名勝古跡,都比不上散步途中偶然發現的景物。到了東京,我也想要站在茗荷谷小徑過來的切支丹坂上,注視令荷風深深著迷過的風景,想像那個已經過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