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 迪士尼乐园:没有蜘蛛侠的墓碑,没有入场券的童年
五一长假,上海迪士尼跻身全国黄金周热门景区榜首,主题公园类景区也在前十名中占了六席。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迪士尼乐园如此吸引人?除了构造出来的“欢乐”,我们还能从主题乐园中看到什么?
在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 Walt Disney表示: “主题公园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的开始,它最终将在剧院、歌剧和电影之外,占有一席之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可否认的是,主题公园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形式,流通的资本、技术和游客使得迪士尼乐园迅速扩散至全球。而在中国,迪士尼乐园的前景更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与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想象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然而, 在看到迪士尼的勃勃野心和创意之际,我们也要看到迪士尼帝国背后的扩展逻辑。迪士尼构造的实体乐园和虚拟世界,成了哲学家 Jean Baudrillard 所说的「超现实」 或「过度真实」(hyperreal)最好的注脚。在 Baudrillard 看来,迪士尼乐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变得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人们被封闭的符号系统裹挟而不自知,也无法体察这个系统外的世界。
本文由T杂志首发于“假日线上特辑”,结绳志(ID:tying_knots)授权转载。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与主题乐园的情感纠葛,以及你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思。
原文作者 / 王菁
编辑 / 堵译丹
原文发布时间 / 2021年5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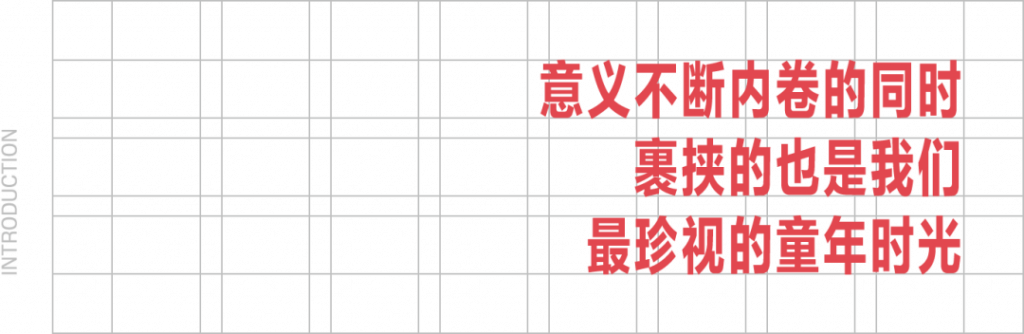
在 2017 年出品的电影《佛罗里达乐园》(The Florida Project)中,导演 Sean Baker 追随六岁女孩 Moonee 的视角,讲述了她与单身母亲 Halley 的故事。母女俩住在佛罗里达基西米市(Kissimmee)的一间破旧汽车旅店中,附近就是迪士尼乐园。
同一时空,两个世界: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米奇和伙伴们迎接四方来客,超级英雄轮番登场,在不同的区域满足孩子和成人的梦想;一个平淡乏味,失业母亲想法设法养活孩子,住在汽车旅馆的几个孩子则用自己的方式,在破旧旅店、停车场和废弃建筑之间,构筑想象王国。

1966 年,Walt Disney 在接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采访时表示,主题公园的最初灵感主要来源于他的两个女儿。作为父亲,他期望有这样一个地方,不仅能带着女儿享受周末时光,自己作为成年人,也能乐在其中。然而,这种乐趣在当时是深植于美国白人中上层阶级的一种对纯真童年的幻想。
这种看似「纯真」的快乐童年,深植于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阶级、性别和种族隐喻。一大片被圈起来的土地,定位往往在郊区,工作日期间,孩子多由全职在家的母亲照料起居,父亲若是能在周末陪孩子出门玩耍,那便是负责的好父亲典范。在乐园中,孩子可以亲身体验卡通人物的生活,而这些卡通角色多来自北欧或以安格鲁-撒克逊为主体的欧洲童话传统。家长 —— 尤其是能负担这笔开销的父亲 —— 则能暂时远离资本主义主导下的无聊生活,或在抹除了美洲原住民、非洲本地历史的模拟探险之旅中,寻求一点感官刺激和异域想象。
如果说电影《佛罗里达乐园》还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艺术加工,引发的是观众对主题公园背后社会问题的反思,那么现实中,迪士尼公司是否就如其所说,致力于保证童年的纯真快乐呢?
2018 年圣诞节前夕,一个名叫 Ollie Jones 的孩子因先天性基因型疾病过世,年仅四岁。由于孩子酷爱迪士尼公司旗下的漫威超级英雄,尤其是蜘蛛侠,他悲痛欲绝的父亲 Floyd Jones 写信至漫威和迪士尼公司,请求他们允许他为早逝的儿子建造一个刻有蜘蛛侠形象的墓碑。

面对 Floyd 的请求,迪士尼公司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童年需要远离死亡和与死亡相关的事物,从而确保迪士尼角色的「纯真」和「魔力」。
孩子的父亲深表不解:难道迪士尼的卡通形象和漫威的超级英雄不会死亡吗?在 Floyd 被拒绝后,英国国会议员 Helen Whately 为 Floyd 一家致信迪士尼公司,网友也发起请愿运动,收集了超过 12 万签名,希望迪士尼能满足孩子家庭最后的心愿。但是,这一切并未改变迪士尼公司的立场。最后,公司提出要送一张手绘的胶卷给 Floyd 一家,以示对这位小粉丝的哀悼。
这是一则现实版的主题乐园故事:以保护角色的「纯真」和「魔力」为名,真正体现的,是迪士尼对版权的吸血鬼式偏执。
这从迪士尼对其最经典形象米奇的漫长版权垄断之路就可见一斑。
1928 年,迪士尼出品的第一部米奇的有声动画片诞生了。这只老鼠身穿水手服,在威利号汽船上吹着口哨掌着舵,但好景不长,真正的船长坏皮特出现了,米奇被踹下了台阶。这部动画片在纽约殖民大戏院首映后,轰动了整个纽约,还在 1932 年获得了才启动五年的奥斯卡特别奖。之后,随着迪士尼主题公园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米奇的形象也从银幕转向了不同平台,成为迪士尼的经典代言。
在中国,米奇也被称为「米老鼠」,早已深入人心。1932 年,《良友》画报引荐米老鼠及相关动画产业,开启国内的米鼠之风。将近 80 年后,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以单体面积居全球迪士尼乐园之最为亮点之一,短期内成为了近几年周边地区最红火的度假地。

既然如此,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妨发问:在 2021 年的今天,若是有人在街头涂鸦、自制 T 恤衫,或是在艺术作品中加入米奇的形象,还算侵犯版权吗?从法律上来说,答案是肯定的。
在米奇版权即将过期的五年前,也就是 1998 年,美国国会在迪士尼公司的游说下,再次修改了版权法,将 1978 年 1 月 1 日当天或之后创作的作品版税,延长至在创作者寿命基础上再加 70 年,而公司名义下的作品版税也再次延长,可以是初次发表年份的 95 年之后,也可以是创作完成后的 120 年,以最早过期期限为准。这也就意味着,两年后的 2023 年,米奇的版权才会过期。同样的版权垄断,也由此延伸到了迪士尼旗下其他卡通人物和超级英雄形象。
既然如此,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妨发问:在 2021 年的今天,若是有人在街头涂鸦、自制 T 恤衫,或是在艺术作品中加入米奇的形象,还算侵犯版权吗?从法律上来说,答案是肯定的。

在米奇版权即将过期的五年前,也就是 1998 年,美国国会在迪士尼公司的游说下,再次修改了版权法,将 1978 年 1 月 1 日当天或之后创作的作品版税,延长至在创作者寿命基础上再加 70 年,而公司名义下的作品版税也再次延长,可以是初次发表年份的 95 年之后,也可以是创作完成后的 120 年,以最早过期期限为准。这也就意味着,两年后的 2023 年,米奇的版权才会过期。同样的版权垄断,也由此延伸到了迪士尼旗下其他卡通人物和超级英雄形象。
或许,大部分公司甚至许多消费者都会觉得,现代公司试图通过影响版权法,从而保障自己最大盈利,这无可厚非。姑且不论在知识开源、全球共享的当下,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版权垄断到底扼杀了多少充满创意的改编,也暂且不计这种版权垄断使迪士尼公司在全球扩展过程中,收获了多少巨额的版权红利。真正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宣称为儿童创造「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的迪士尼,恰恰以保护「纯真」和「魔力」为借口,吸食着垄断下的各种盈利。
回到《佛罗里达乐园》,在最后一幕中,Moonee 即将被社工送去新家庭寄养。她逃出了汽车旅店,向隔壁旅馆中唯一的小伙伴求助。两个小女孩手拉手,经过由三根钢丝卷成的米奇状地标,跑过 Halley 曾经贩卖廉价香水的停车场,穿过迪士尼神奇王国的大门,奔向正中心的城堡,消失在人群中。

电影终止在了这一幕,虚拟和现实通过影像剪辑,无缝衔接在了一起。某种意义上,我们作为迪士尼乐园的潜在游客,或许已经很难分辨哪个世界更加真实。迪士尼构造的实体乐园和虚拟世界,成了哲学家 Jean Baudrillard 所说的「超现实」 或「过度真实」(hyperreal)最好的注脚。在 Baudrillard 看来,迪士尼乐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变得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人们被封闭的符号系统裹挟而不自知,也无法体察这个系统外的世界。
在当今世界,迪士尼主题公园所象征的超现实世界并非孤例。意义不断内卷的同时,裹挟的也是我们最珍视的童年时光。迪士尼创造了一种单一的梦想童年,排除的是 Moonee 这样社会底层的孩子,也拒绝让挚爱蜘蛛侠的孩子拥有一块刻有蜘蛛侠的墓碑。
可是,我们难道不该问,孩子们到底去了哪里?什么样的孩子才有资格在迪士尼构筑的超现实世界?没有入场券的童年,又该何处安放?
Posted in 联结
独立网站:tyingknots.net
微信公众号ID:tying_knots
【倾情推荐】订阅 Newsletter
成为小结的微信好友:tyingknots2020
我们来信、投稿与合作的联系地址是:tyingknots2020@gmail.com

目次(持续更新)
- About us | 一起来结绳吧!
- 进口、洄游与误归:三文鱼的驯养经济与后新冠时代的多物种认识论
- 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 结绳系疫 | 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
- 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Corona读书会第23期 | 医疗基建 Medical Infrastructure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 Corona读书会第6期 | 动物、病毒与人类世
- 非男即女?:生物学家有话说
- Graeber | 中文里的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萨林斯悼念格雷伯
- David Graeber |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 Graeber+Piketty | 劫富:关于资本,债务和未来的交流
- David Graeber | 傻屌:解开“领带悖论”
- 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 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 国际聋人周的礼物:一份人类学书单
- 「修车大水,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自我去稳定化(self-precaritizing)的「三和大神」
- 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
- 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9-10月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上)
- 欧洲以东,亚洲以西:后冷战世界下的中亚(下)
- Corona读书会第30期 | 把XX作为XX:方法、地方与有机知识分子
- Graeber | 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少是已经发生的那部分)
- Graeber | 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
- 马克思、韦伯、格雷伯:学术与政治的三种面向
- Corona读书会第7期 | 全球公卫中的跨国人道主义 Transnational Humanitarianism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夏季
- Corona读书会第28期 | 大坝与水利政治
- 特朗普人类学(一):手、谎言、#魔法抵抗
- Graeber丨格雷伯与科层中国:从《规则的乌托邦》说起
- 黑色海娜:对苯二胺、孔雀与不存在的身体
- Corona读书会第32期 | 松茸的时日
- 编辑手记 | 《末日松茸》:一本没有参考文献的民族志
- 影视造梦:横店“路人甲”们的生活群像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小丑”
- 哀恸的哲学:“孩子带来了冰河时代的那种焦虑”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0年11-12月
- 从丁真到拉姆:直播时代的少数民族旅游开发
- 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基督教,和圣诞节
- 结绳志的二零二零
- “两头婚”的实景与幻象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哥伦比亚2019年的抗争行动:不期而遇如何构建共同未来的想象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2019-20年智利抗争:与废墟同在
- 在炉边和在狩猎的女人们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坚持与归属:重思印度新德里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运动的起落
- 无母体的子宫,无身体的器官
- 为什么疫苗是一个社会问题?
- 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对话Rachel Murphy
- 东北 | 东北完了吗?否思通化的“官本位文化”
- 与系统周旋:关于骑手劳动过程的田野观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①
- 被绕开的劳动法:外卖平台发展史与骑手劳动关系的变迁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②
- 平台内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③
- 春节特刊·乐 | 为何春晚不再欢乐——Fun的社会性
- 春节特刊·情 | 三代女性的离散与游牧
- 春节特刊·婚 | 先恋爱,后结婚?
- 春节特刊·牛 | 牛的人类学
- 人口贩卖:历史延续与全球难题 | 一份书单
- 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 | 厄瓜多尔的社会运动:从2019年十月抗争到新冠疫情
- 世界母语日与母语政治的变迁
- “无障碍”之障 | 实时字幕、聋听空间与沟通劳动
- 书讯 | 英文人类学新著 | 2021年1-2月
- 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 聚焦乌俄 | 最不幸的一代
- 乌克兰书单:超越霸权之眼的民族志视角
- 国际HPV知晓日 | 一则关于HPV的故事
- 三八节快乐 | 听她们说
- 它们 | 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
- HAU:民族志理论的回归?
- 树 | 它们孤独地生长,悲惨地死去
- 系统人会梦见行动与价值吗?
- 红毛猩猩 | 如何评价“不止人类”的照护
- 红色圣女米歇尔与巴黎公社的太平洋原住民遗产
- 大灭绝时期,什么样的命才是命
- 排华与反穆:种族主义的跨国交织
- 李晋:利奥塔之死
- 在工业区与盆栽相依为命
- 照料濒死的河道
- 寇大夫的诊所
- 悼念 | 马歇尔·萨林斯与保罗·拉比诺
- 下一次还将是烈火:反思明尼苏达警察执法暴力的再起
- 为社会而艺术? 社会介入式艺术与人类学的一次圆桌式偶遇
- 与深圳握手: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的艺术实践
- 反高校性骚扰:如何将“网络风暴”变为“制度性防范”?
- 实验艺术,也是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实验——评《实验北京: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全球化》
- 阿兰达蒂·罗伊:作为“危机制造机”的政府正将印度拖入地狱
- 打字、身体与性别:从“打字女孩”到“技术直男”
- 迪士尼乐园:没有蜘蛛侠的墓碑,没有入场券的童年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