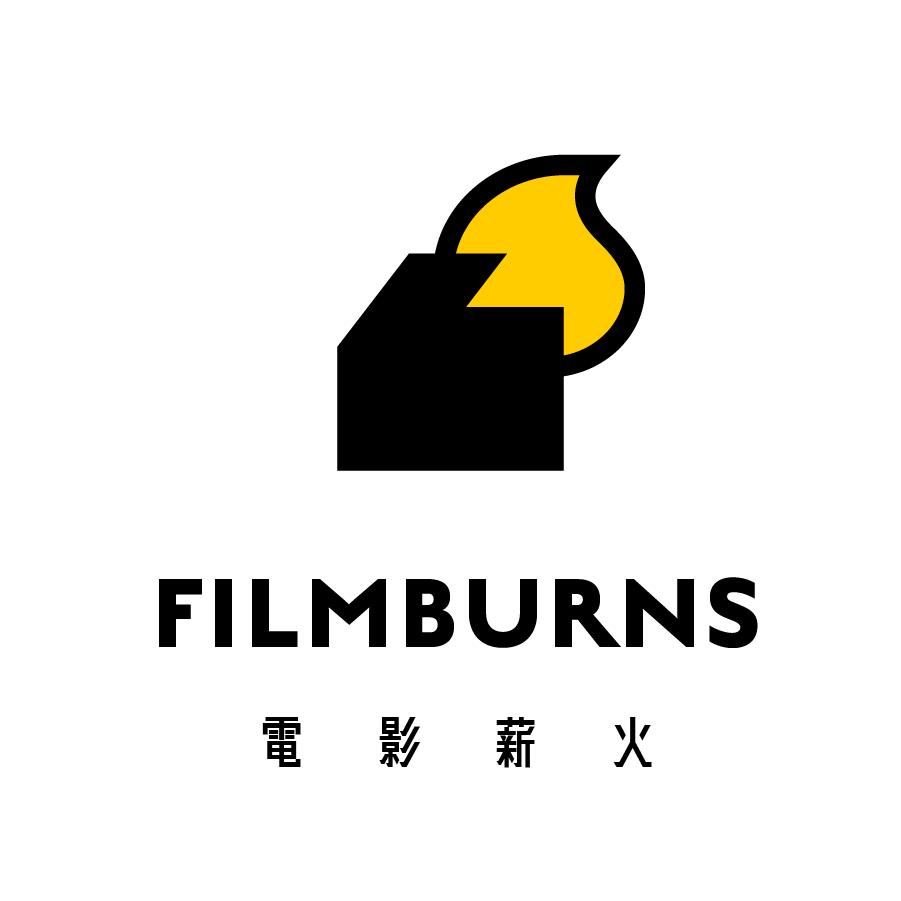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無邪之境》:邪惡之存在

文|劉境南
擅寫對話的濱口龍介,新作《無邪之境》與音樂家石橋英子合作,另闢新徑,以影像及音樂為主要敍事手段。電影回歸屬於影像的藝術,音樂不是作配,而是不可缺少的表達形式,如對白之於人物。電影開首,鏡頭仰望上空——陽光穿過枝椏、映出樹影,天裂之間有藍天與白雲。大提琴如樹木低鳴,風葉碰撞竊竊私語。因應仰視者快速移動,樹椏葉影忽明忽滅,天空的形狀不斷變化。正當觀眾開始沉醉其中,音樂戛然而止,畫面兀然跳轉,女孩花仰望著天空,不發一語。

這個不尋常的開場道明來意:這不是一部歌頌大自然寧謐優美的電影。這裡的大自然帶有距離感,清冷自持,情緒變化莫測,甚至隱含著危險。從飛掠的樹椏晴空、女孩的仰望,到後來父親巧出場劈柴盛水——這沒有對白的十分鐘之間,鏡頭角度與兀突的跳轉,都在發問一個問題:凝視者是誰?
電影很快就給出答案,從巧與陸山葵對視一幕,以及後來花與鹿對視一幕,都清楚告訴觀眾:那是大自然的活物之眼。至於音樂,就是大自然的語言。所以當濱口為人物寫對白,石橋英子則為大自然寫,縱然說話的方式不同,卻有著同等的份量。

然而當大自然加入了人,聲音也就嘈雜起來。以往濱口著力寫對話之無垠與必要,今次卻反過來,寫其限制與無能為力。乍看相反的取態,其實同樣在探討語言的曖昧與社會性。《無邪之境》的主要故事環繞豪華露營落戶郊區的爭議,而開宗明義地,第一場關鍵對話就是露營公司召開的居民大會。借角色之口,濱口再三表明這場對話只是資本的把戲,以搏取政府的疫情援助金,不志在以溝通解決問題。回到自己的舒適區,濱口展現出游刃有餘的場景掌控能力,短短廿分鐘,居民與資本的衝突、發展與保育的矛盾盡列無遺,並指出全片的核心:水向低流,上流有義務確保所作之事,不會為下流帶來災害,而發展的關鍵是平衡。

隨之引出另一場關鍵對話,兩個職員回去匯報居民的不滿後,受老闆指示,特意帶著酒拜訪巧,邀聘他擔任營地的夜間管理員,以解決夜晚沒看守的問題,順便拉攏一下居民。兩人驅車去巧的小屋途中,聊起對工作與生活現況的不滿,男職員表明嚮往郊區,甚至興起索性自己當管理員的念頭。這時觀眾才發現,原來在居民大會上為資本護航辯駁的他,也不是個壞人,而是個有追求的戇直傢伙。
那到底是甚麼讓他變成「壞人」呢?答案是社會這個場域。當他一下車,鮮紅色外套便明白地顯示他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在巧看來,他主動學習劈柴的行為,實在矯情到不行。在烏冬店職員看來,他讚嘆烏冬美味得教人如沐春風,也極之虛偽。當私密之事到了公共場域,便無可避免地獲取了社會意義。語言變得曖昧而複雜,真誠變成虛偽,示好變成進攻,無邪也能激發出邪惡。

電影的另一個重點,是兩度提及的「半箭鹿」概念。即野鹿溫馴怕生,不會主動攻擊人,但若果中槍後未即時斃命(半箭),就會具有攻擊性。資本作為外來者,對大自然巧取豪奪,就如同射殺鹿群的獵人。末段花的失蹤使劇情急劇轉向,原本風光明媚的午後暮色漸濃。但當巧正焦急地尋找女兒,女職員仍在心念營地,說到雖然營地建在鹿的通道上,但既然鹿怕人,那自然會躲開,不就沒問題了?「那牠們能夠去哪裡呢?」「總會找到地方吧。」然後巧沉默,如中槍的鹿。
入夜後,獵人發出第三槍。音樂響起、大自然低鳴,花看著受傷的鹿,緩緩脫下帽。巧為制止欲營救的男職員,動了殺機。鏡頭一轉,花已受傷墮地。然後巧抱起女兒,步入樹林。月光穿過枝椏、映出樹影,天裂之間有夜空與白雲。大提琴聲猶如樹木低鳴,風葉碰撞竊竊私語。
濱口提出問題,卻將答案隱藏在濃霧之中。在無邪之境,人自有生活方式與節奏,大自然也自有運行的規律,各取所需,沒有善惡對錯。但當獵人射出子彈,也就破壞了平衡,即使是溫馴的鹿,也會拼命反撲。正如村長所言,水向低處流,處於食物鏈上層的人類,終需為自己所作之事負責。濱口以「邪惡不存在」作為謎面,謎底卻是邪惡之存在。開槍的獵人、無知的子彈、殺人的鹿,邪惡者隱身幕後,卻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