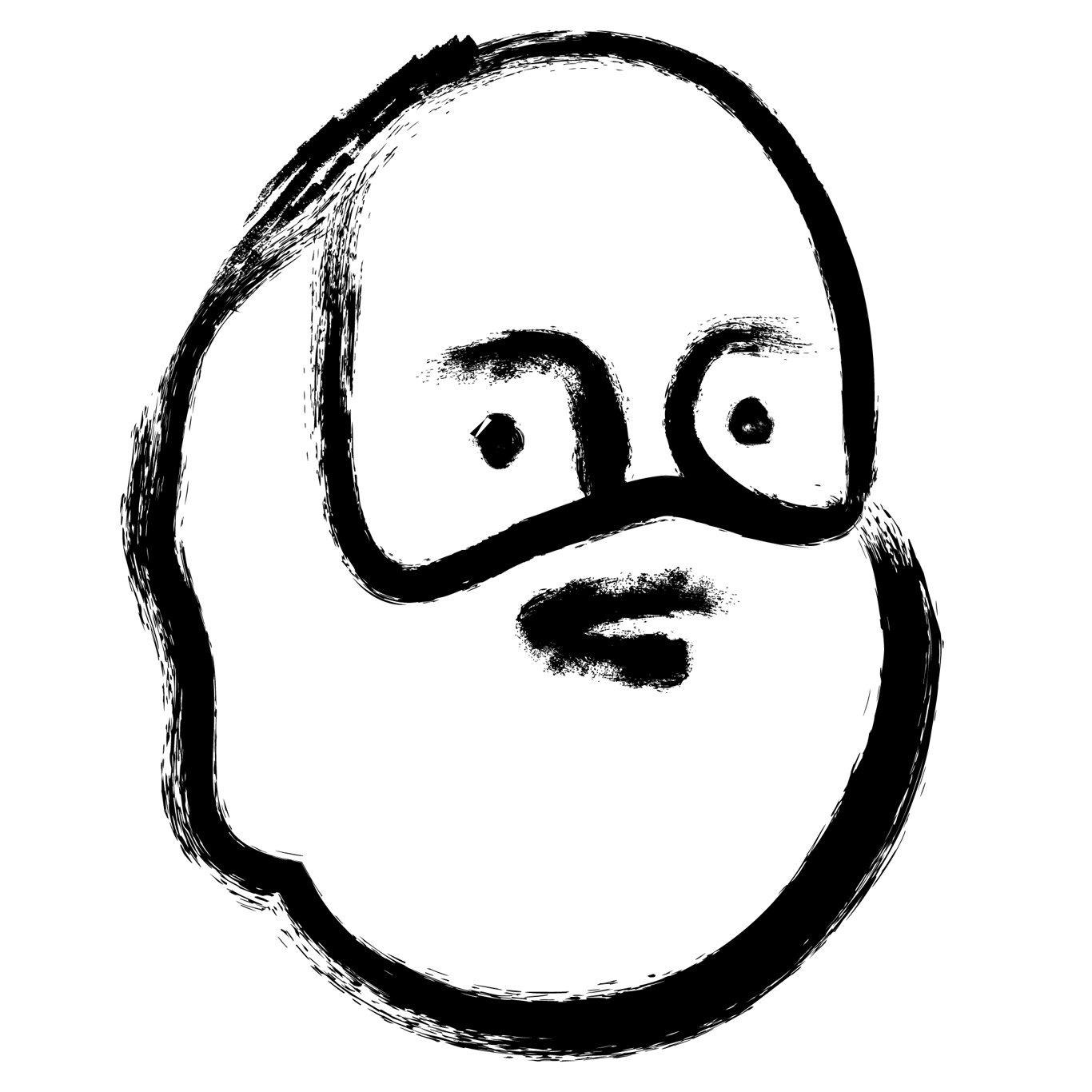哲學樹洞:薛西弗斯的自由

室友 Victor 問:
早前借了一本關於卡繆的書,內有薛西弗斯的神話的四篇短文。短篇中說到「我的熱情,我的自由,我的反抗」。我的熱情是對生命的熱愛,我的反抗是對荒謬的反抗,但我的自由是甚麼?
四篇短文中不斷提到人受死亡所限,人/藝術作品最終歸於虛無,人生是徒勞無功的。人受死亡所限,何來自由?若我硬要說和自由有關的論點便是人在有限生命,達到最大的經驗量,由有限做到無限。不過於其說是和自由選擇有關,好像說成是對抗有限生命更合理吧?
再者,卡繆說希望和自殺只是逃避,而希望本身更是人限制自己,因為你的行動跟着希望的路向走。那麼人生除了抵抗好像沒有剩下甚麼選擇了?那麼人還剩下甚麼自由選擇的空間呢?卡繆說人從荒繆、習慣中走出來,變得理性清明,不過正正是理性清明的人才發現希望和自殺沒用吧?
題外話:卡繆有沒有主要關於自由的文章?而當年由朋友變敵人的沙特會有更多關於自由的論述嗎?
室友肥貓問:
卡繆說的自由好像不是自由選擇的自由?「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熱情」中自由到底是怎麼樣的自由?荒謬之中,除了在有限生命裏作最大限度的抵抗,還有甚麼自由的空間呢?
室友肥龍問:
卡繆的薛西弗斯神話四篇短文中說面對着死亡,價值判斷、希望等都無用,人不會受這些東西所限制,這可算是人內在的自由,唯一有意義的是對荒謬的反抗。不過,我覺得人不受限制並不代表自由 ── 人有不同選擇才能有自由呀。在荒謬面前人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嗎?究竟卡繆的短文或其他作品中的,自由是甚麼意思?
回覆:Yu Hui 難度:★★★★☆
幾位室友都問到卡繆對自由的看法。
首先,有時候哲學家的用字都跟日常生活中的意思有所出入。這可能是因為某詞語 ── 例如自由 ── 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就已包含很多意思,而如果我們不先弄清這個詞語在哲學討論的脈絡該如何理解,撇除一些不合用的意思,則很容易在論說中造成誤解。另外,也有可能是哲學家想提出的某些想法太過新穎,無法在日常的語言中找到確切對應之詞,所以唯有先借用一些意思類近的詞語,再把它的意思改造得更合用。
從「荒謬」到「反抗」
我想,這也是理解《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自由(la liberté)」這概念時要注意的地方。對卡繆而言,「自由」不是指「自由意志(free will)」或人的權利,更着重的反而是「行動的自由(la liberté d’action)」。例如他說:
The only one [freedom] I know is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ction. Now if the absurd cancels all my chances of eternal freedom, it restores and magnifies, on the other hand, my freedom of action. That privation of hope and future means an increase in man’s availability.
但「行動的自由」又是甚麼意思?正如這段引文提到,這種自由是「荒謬」的產物。荒謬是一種永恆的落差。人總想找到大千世界存在的意義,透過科學、宗教、哲學等等,嘗試找到解答,說明這個世界與及我們的生命存在的理由。然而,世界對我們的探求總是報以冰冷旳回答:我們發覺,所有事物的存在最後都沒理由可言。世界就只是這樣存在着。
玫瑰不為甚麼而開,
只為綻放而綻放。(Angelus Silesius)
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卡繆提出了兩種否定荒謬的行動和思想:自殺和希望。人自殺,因為他無法忍受生命無止境也無意義的荒謬。選擇自殺的人用最徹底的方法結束生命的荒謬 ── 結束生命本身。相對而言,宗教或是其他告訴人們世界必定有可以期盼的東西之教條,則是透過為這世界強加上一份價值以消除荒謬。卡繆最不能接受的,正正是這些想法。在卡繆眼中,荒謬根本就是生命的本質;任何否定荒謬的想法不單注定徒然,而且更是自欺欺人。卡繆在書中一再強調我們要時刻意識荒謬必然存在於人生,意思就是惟有永遠肯定生命的荒謬,我們才能真正的活着 ── 更重要的,是真正自由地活著。
這引申到室友問題中也提到過的「反抗(la révolte)」。關於《薛西弗斯的神話》中的「反抗」,我想我們不難找到相關文章討論。這些討論中,我觀察到為數不少都把卡繆的反抗視為「對荒謬本身的反抗」── 從室友們的問題也看到這樣的理解。當然,這種理解或許不無文本根據,而且既然《薛西弗斯的神話》是一部教人如何面對「荒謬」的書,把「反抗」的對象視為「荒謬」本身亦似乎很理所當然。然而,這種講法看來有其困難:一方面,卡繆強調荒謬就是生命的本質,生命不可能逃離荒謬,另一方面,卡繆又好像主張人要反抗荒謬,為自己的生命創造價值。但既然生命就是荒謬的,我們還如何反抗它?為生命創造價值,不正正如宗教、希望等,是卡繆極力反對的想法嗎?
我認為,薛西弗斯要反抗的,不是荒謬的生命,而是對荒謬的否定。換句話講:薛西弗斯不是要反抗荒謬,反而是要擁抱它,與及反抗一切不接受荒謬就是生命實相的看法。換個弔詭一點的講法:對荒謬最有力的反抗,就是要擁抱它。
從「反抗」到「自由」
當我們細仔考察生命的本質,發現這世界對我們必然是顯現成荒謬、絲毫沒理由可言,也絲毫沒意義可言的世界後,我們就會意識到荒謬正正是世界的本質,也正正是人的理性與冰冷的世界永恆的落差。在這基礎上,我們發現日常生活中所有指導着我們生活的規範,其實和否定荒謬的「希望」很相似。我們期盼明天會過得更好,期盼努力工作,升職加薪,仿佛為了明天,我們就有理由犧牲今天;生命仿佛永遠在明天,而今天只是為了籌備那即將降臨的明天,這即將降臨的明天才是我們的生命。然而,卡繆反覆強調,對充分認識到生命的荒謬者而言,生命根本沒有明天:「The absurd enlightens me on this point: there is no future.」 其實這句話更準確的意思,應該是「生命根本不在明天」。在認識到荒謬之後,我們應該了解到那些說有意義的人生應該怎樣怎樣的想法,全部只是空談;換個角度看,這些想法不過是遮掩生命荒謬的本相,想把我們的目光從這最赤裸、最殘酷的現實拉走。這樣說來,我們拒絕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希望時,正正就是反抗了從荒謬中逃遁。
以此角度再讀《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有關「自由」的講法,就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抱持希望時,我們並非真正的自由:那種理想人生的藍圖十分限制我們的行動和選擇。社會仿佛扮演上帝的角色,告訴我們現代人的「十戒」,告訴我們一個虔誠的現代人應該這樣活、不應該那樣活。然而,從對荒謬的逃避中覺醒,反抗這些虛假的希望和價值,解放了我們。這一刻,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手中。雖然我們無法逃離生命的荒謬,但認清生命的荒謬卻讓我們獲得「行動的自由」── 把自己荒謬的生命從神、社會、他人手中搶回來的自由。而我認為這亦是《薛西弗斯的神話》最有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味道的一環。我們要做怎樣的行動,要過怎樣的生活,要擁抱怎樣的價值……種種都是我們的自由。在荒謬的世界?,我們有「自由」做任何的選擇。我選擇做醫生、選擇做藝術家、選擇讀哲學、選擇花十數分鐘看這篇文章……這些都是我的選擇。在這意義上,卡繆主張的反抗,並非不接受生命和世界的荒謬,反而是要承認甚至擁抱這種荒謬,從而換來一種心態上的超脫,把握「行動的自由」。
然而,這樣是不是代表任何不道德的事也可以做呢?卡繆引述唐璜(Don Juan)── 大抵就是一個為了親近女色不擇手段的人 ── 的故事,說在這種極端的例子中,我們也可以嚐到他「荒謬精神」的味道。但唐璜是否自私、不道德的人呢?卡繆的回答饒有趣味:「I let it be decided whether or not one can speak of selfishness.」
Yu Hui
無法容忍自己的平庸。興趣是了解比自己聰明的人想了些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