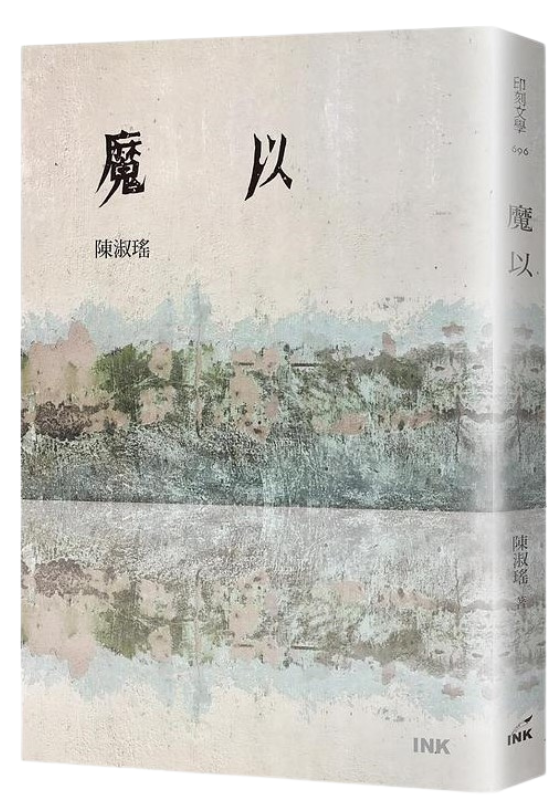對談》陳淑瑤X童偉格說《魔以》:作品只為閱讀而生的書寫美學,及筆訪陳淑瑤

成長於澎湖,曾自稱「生著翅膀的掘井人」的作家陳淑瑤,2023年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與作家童偉格進行對談。童偉格從文學評析的角度精闢解讀《潮本》、《雲山》及陳淑瑤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魔以》。陳淑瑤每部作品都有各自的聲腔與細緻高明的修辭調度,《魔以》更讓讀者隨著返鄉奔喪後,留守荒涼家鄉務農的女主角看盡鄉土日常,躊躇回望生命地景,感受難以言詮的沉重與孤寂。本文是Openbook編輯部將書展對談菁華、筆訪作家陳淑瑤的內容進行彙整後而成,邀請大家一起來讀。
主題:魔以與童話—小說的出版魔法
與談人:陳淑瑤(《魔以》作者)/童偉格(作家)
整理:趙俐雯
➤從《潮本》到《雲山》:老廢荒壞的日常及一起蒼老的觀察者
童偉格:鄉土文學的基本寫作命題,是從70年代台灣工業化過程,逐漸加劇的城鄉人口移動,及鄉村地方的掏空化著手。另一種則是專注於美學探索、具魔幻寫實色彩的寫作方法,千禧年後被命名為「新鄉土」——少年少女在應該熟悉的家鄉時空裡漫遊,但所有事都發生過了,充滿亡靈幽魂。陳淑瑤的寫作在兩者之外,告訴我們:在家鄉被掏空後還在原處生活的人,必須將老廢荒壞的現象當成每天日常的時候,怎麼正常地活著?這是相當難以書寫的鄉土文學,但《潮本》這個安靜的寫作,為此做了準備。
陳淑瑤的寫作非常特殊,用細緻的聲音,像刺繡一樣,一點一點地將很少有人留心的細節甚至宏大的主題,比方時間本身、宏觀宿命性,情感飽滿、晶晶亮亮地帶進她的寫作裡。在《雲山》的序文中,我把修辭調度、她的基本設想,跟也許對讀者提出安靜閱讀的要求,命名為「陳淑瑤化的美學」。

我發現要理解陳淑瑤小說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她這樣的小說作者是怎麼判斷、評判事物。只要跨越修辭的障礙,閱讀淑瑤的作品其實會帶給我們非常多收穫。這對剛拿到書的讀者構成了挑戰,但如果願意花心思讀的話,會發現挑戰有它的道理。
《潮本》的大規模演練,接著就到了《雲山》。對我來說,《雲山》轉向了更難寫的主題,即是隨著鄉土時間一起蒼老的觀察者本身。年輕時,隱隱約約的傷懷,感到死亡、失去的威脅,在邁向老年的過程中變成每天具體的身體感受。於是一個哲學問題來了:人怎麼在對自己而言漸漸陌生的世界裡,達成某種形式的和好相處?
現代文學規範了少年式的狂飆,寫相當多成長挫敗、青春的過早壞損。《雲山》其實用帶有感情的方式書寫了對文學而言很難觸及的東西——人怎麼邁向熟老?具體到來的「年老」到底是什麼?淑瑤把觀察重心往歲月的後方移了,可以這樣說嗎?《魔以》則是更具體地寫已經年老的家鄉。
☁️延伸閱讀☁️ 2019Openbook 年度好書.中文創作》雲山
➤滾燙、變化的原鄉生活,有著純度最高的現代孤寂
陳淑瑤:其實我很怕海,比較喜歡山,山對我來講就是另一種鄉土。《雲山》好像是我寫作的分水嶺,之後我把最多力氣放在描寫離島。
「離島」這兩個字太美了,本身就充滿鄉愁。《魔以》可以說是我描述鄉土的文學作品裡最近代的、此時此刻的離島。魔以:某嶼,某個島嶼。我希望它是任何一個沒有名字、荒涼的離島。
寫完《地老》(2004)後,以為隔10年就會寫關於離島的故事,沒想到一耽誤這麼多年。《地老》後的時代好可怕,三五年就一次大更新,地景或人的心理產生很大的變動。跟偉格私下聊過,他提到《魔以》有些地方跳動或壓縮快了一點,我才意識到寫東西的時候,可能處於自己也想像不到的緊迫心理狀態。之前沒有這種時間壓力,是在《魔以》回看離島的時候,突然驚覺時間過了這麼久。

剛在場的朱嘉漢先生跟我提到(從前)在澎湖當兵,近年回去怎麼變那麼多?一個外人覺得改變那麼多,在離島曾經生活過的人,那種在心裡的衝擊更大,非常大。
童偉格:《魔以》比《雲山》相對薄,但不見得比《雲山》好讀。因為《雲山》比較悠緩,會有很多時間去追溯《雲山》描述的資訊,但《魔以》是很奇怪的構圖,裡面有種相當緊迫的狀態。
為了召喚大家的記憶,來說點當兵的事。那時在馬祖北竿當野戰砲兵,我學到當地的福州話中少用「島嶼」這樣的詞彙。對居民來說,生活空間就是一個又一個孤島了,不會特地指稱(海中的陸塊)。他們的語彙中,島嶼就是山,因為從霧茫茫的海上看過去,會覺得每個突出海面的島嶼都是一座山頭。他們也少用「出海」、「開船」、「泅一段路去」這樣的動詞,從島到島的動詞他們叫「走」。島上當兵一年多,天天看著那片海,突然明瞭了文學理論的說法。
我們太常將都市跟鄉村生活區隔開來,以為那是二分對立的生活。但什麼叫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就是純度最高、最孤寂的現代生活。想想被工業化掏空以後的原鄉,過年回去的時候,其實很孤獨:沒有城市的公共空間,在獨立透天厝裡匿名生活而不會碰到其他人。去哪裡找現代生活的荒壞?淑瑤所感興趣,每隔幾年好像換血過一遍,非常緊迫的狀態,其實會在鄉下找到。為什麼?都市生活比起鄉下是更不變動的。蓋好台北101的時候,都市人會設想這棟大樓起碼會立在這裡百年之久,不會去更動它。但在鄉下,每個倉促造成的農舍,可能明年就不在了。記憶中的原鄉,沒有情感上的意義了。
回到《魔以》,在這樣一個滾燙、變化的土地,女主角川金國中畢業就離家到高雄工廠工作,直到有天母親過世了,50多歲的川金返家奔喪。她的兄弟都希望她在家多陪陪老父親,誰知道這樣一陪,可能就十幾、二十年過去了。

➤無法言說自己的主角川金,困守家鄉的痛苦與荒涼
陳淑瑤:《魔以》是2019年4月動筆,那時媒體一直在寫川普跟金正恩會面的「川金會」,我就決定女主角名字叫川金。川金沒有好學歷,在家族裡很卑微,常常在土地上一個人不停地忙東忙西,在同學群中也沒有聲音,川普跟金正恩卻是那麼有權勢的人,所以這名字是很大的諷刺。
當書接近完成,就發生(烏俄)戰爭。世界上沒有人不感受到戰爭的威脅,特別是台灣。第一章名叫〈揮單〉,是最後取名的章節。「揮單」這兩個字猛一看很像「揮軍」,「揮單」好像貫徹一個人的意志,戰爭也是從一個人的意志開始,我就取這名字。
童偉格:謝謝淑瑤的解釋,才知道川金原來是從川金會來的。川金她非常勤勞,很肯做事,正因為這樣,造成她是最後困守家鄉的人。所有人都離開了,所有人都對她有歉疚感,但沒有人有辦法幫助她。在我自己的閱讀經驗,我想不起有像這樣的角色,太特別了,即便不放在鄉土文學的系譜來看,都是關於角色典型非常好的創造。
川金跟其他角色比起來,格外沒有語言去說明自己。如果有人可以找到語言,幫我們描述川金每天看出去的世界是什麼,我猜想在台灣小說界裡就只有陳淑瑤了,她會告訴其他人,那種確實會遇到卻沒有語言去說的孤寂是怎麼一回事。
《魔以》描述的每個人都像是貴重的時間層疊下來剩餘的東西。每次讀淑瑤的小說的時候,我都會想起夏目漱石描述過一種「沒有痛苦的痛苦」。

夏目漱石最後遺作《明暗》寫一個男人開刀,醫師打了麻醉藥,要確定還能不能感到痛苦,就問:「那你現在有感覺到痛苦嗎?」因為麻醉藥效力發作了,這個男人就說:「沒有痛苦,只有沉重的感覺。」好像在這個男人的想法當中,沉重這個詞是痛苦的替代詞或反義詞,沒有痛苦了反而更沉重。體內沉甸甸「沒有痛的痛」該怎麼形容?或許就像沒有神經的皮膚,被人類徒手挖掘,失去痛苦的沉重感。
《魔以》當中有著大量挖掘、整地、灌溉、重新耕種的描述:家鄉的土地經過了漫長的時間,人類離去又回來,在一片荒壞中,一個人嘗試要將農業復甦起來。在某個意義上,土地內裡的神經被抽走了,而人帶著某種記憶、某種情感,移動到這裡,重新想起了世世代代之前,我們的親人到底都怎麼耕作這土地的?你會發現,這如今變成一件非常荒涼的事,感覺到的只是一種抽離的痛苦——你知道它是沉重的,卻找不到任何身體感受來用以形容那樣一種親近鄉土的感覺。特別是川金開著那台鐵牛(耕耘機)在犁田的時候,帶給我這樣的感覺。淑瑤想要如實描述此時此刻能摸到土地的人,他們內在並不輕鬆的狀態是什麼,這是《魔以》特別不可思議的地方。
➤不給甜頭,只為閱讀而生的小說,讀者必須字字跟隨
童偉格:《魔以》修辭的演練,是比《雲山》更困難的調動。讀《魔以》首先會遇到的挑戰,是頻繁換用的第三人稱敘事:每次「他」出現的時候,都要停下來想這篇章所描述的「他」是哪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角色的感知同時非常明快地被切換到另個角色的感知,一種奇怪的流動因而被小說的行進所串接起來了。所有感知總結起來,就是要描述用以替代痛苦的沉重感。
淑瑤在《魔以》相當靈活的調度,有大量採用「換喻」的傾向。換喻,就是把隱喻抽換運用,比方我長得很像一隻鳥,之後提到「我」就用「鳥」來代替。陳淑瑤會把牛比喻為神桌,下次寫到牛的時候就寫神桌。在這情況下,物與物的性格得到貫通,像進入一個萬物生長的時代。
有時候,作者必須帶著某種費洛蒙,將很孤獨的經驗渲染成遊樂園,以便讓艱難的主題「生命本身的壞毀」變得可口許多,讓人比較願意去服用。可是淑瑤的寫作探索,在我看來其實是站在這種方式的反面,是那種準備給文學讀者讀第二次的小說。這樣一想,淑瑤的小說CP值很高。因為你可以反覆琢磨。
陳淑瑤:一直以來,我創作散文、小說,沒有寫詩,但生活中我常常閱讀的都是詩。我一直想在我的小說裡寫詩,或把文字更凝聚。之前成大台文的老師(編按:應指成大台文系副教授劉乃慈)說我的作品都不給讀者甜頭,我以為這次《魔以》給了很多甜頭,簡直像吃冰淇淋一樣,結果竟然有這麼大的落差,太不可思議了。

我一定要先符合對自己文字的要求,才來談其他東西。幾乎每個關於鄉土或鄉村的故事都會出現井,這本也有。我想創作是掘井,之前自我介紹,我就說自己是掘井人,閱讀也是一種挖掘,如果輕鬆地閱讀的話,井是枯的、是不來泉水的。去挖掘到一個深度,泉水泌流出來才會變成一口井。我想我還是會很堅持這樣的寫作。如果不先要求文字,光是用更簡單的口吻、更容易明白的描述讓別人知道劇情發展,對我來講,寫作就不再那麼快樂了。
童偉格:必須強調,我倒滿希望陳淑瑤繼續「陳淑瑤化的美學」,繼續進行嚴謹、而且有自己規則的探索。誠實說來,我覺得這正是《魔以》所獨有的價值。如果大家已經習慣《魔以》的腔調與美學特色,我想鄭重推薦大家帶著嚴肅的心情讀它。
現在很多IP小說有高潮迭起的故事,其實是為了影像化改編做準備。但淑瑤的小說是「只給閱讀用的小說」,多年來也是純文學寫作的一個重要島嶼,一個魔以。她的修辭調度好像要求讀者去實踐現當代很難實踐的那種閱讀狀態,就是更安靜地閱讀。這是非常嚴格的要求,稍有一點意志潰散——忽然想起簡訊沒回跳開了——再回來就會發現「陳淑瑤的小說已經拒絕我了」。因為這些書是為了未來更長久的閱讀時光而寫的,作為讀者,你要一字一字地跟隨她。我們已經知道註定不好讀,但是,這些書會讓我們得到輕鬆作品所沒有的那個豐饒世界。
陳淑瑤:我認為《魔以》其實沒有像他講的那麼困難(眾笑),《魔以》非常幽默、可愛,真的真的!有點政治性就是。雖然魔以是個離島,也許你覺得很遙遠,但是其實人性是相通的。裡面的人物有自己的生活,有真實性,你會看到你認識的人的影子,有太多故事都可愛而且諷刺性很強的,願你們可以在故事當中找到很多樂趣。
➤OB筆訪陳淑瑤《魔以》:紙本寫字是土壤作業的延續

Q:為什麼希望「魔以」是「任何一個沒有名字、荒涼的離島」,而不直接與故鄉澎湖連結?
A:許久以前我就許諾自己可以不必再用明確的地名,當然是有一些事引起我這樣的心理障礙——居「木」「寸」之間的苦,只有木寸中人才懂。書中主角川金,對那太過專業的攝影師說:「你為什麼不能想像呢?」攝影師則叫他「注意符號」。
當飛機接近小島,你是認得土地,而不是名字啊。我以為無名能擁有我想要的自由,其實很有限,只有在虛構幾個村名時好開心,比如:那個航向離島的地方叫「沙騰」,沙騰是一種嘴巴尖尖身體長長的魚,在我小時候算是一種便宜的雜碎魚仔,現在也稀少珍貴起來了。不給地名,又描寫地景,多矛盾啊我。
Q:身為曾經在離島生活過的人,您如何消化物換星移、地景變動帶來的衝擊,融入《魔以》一書的寫作中?能不能談談關於「緊迫的心理狀態」?
A:我有個同學爸爸是民意代表,她告訴我們,過不久就要興建連接台澎的海底隧道了。交通不便使離島保有那麼一點孤寂,現實的問題是,返家這種日常行為,無不變成大費周章的返鄉。疫情較不嚴重的小島,對疫情蔓延的大島關起門來,完全忘了生大病時是要飄洋過海去看病的。
《魔以》書中除了「骨科」、「眼科」兩章,還有其他醫療科別散布在各章節,顯示身在離島就醫時缺乏信心,徬徨無助,往往多了一層心病。那幾個篇幅大一點的作品,都是從澎湖回來之後,毫無預警,隔天就動起筆來,也許再度與鄉土隔離形同漂流讓我不安,也許不能再等待了。
Q:書寫土地與農忙,對您來說最大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會設定《魔以》主角川金曾經離家又返鄉?
A:假如我只是一個單純的離島人,不曾手爪腳爪的接觸農作,也許就不會有寫作這回事了,紙本寫字是土壤作業的延續。現今農地大幅縮水,回家我總要去摸一摸,感覺自己可是有土地的人。若要說最好的時光,鐵定是小時候在田野亂跑亂跳、有意無意的驚起草蜢滿天飛舞。現在哪止蜜蜂不見了,昆蟲都變得好少好少。《魔以》書中,川金與小犬去尋找異味的那趟路程,沒遇到半隻昆蟲,何止荒涼。
之前我的鄉土故事皆以居鄉者為描寫對象,這次出現了交叉。不論偏鄉家族乃至整個離島,外移人口多於在家鄉等待的人,我的旅外時間也已多於外島日子。這次只是擇兩組人馬來做一個返鄉試驗,看他們回不回得去。
Q:您在活動提到「揮單像貫徹一個人的意志。」能不能更詳細地向讀者說說「一個人的意志」指涉什麼?
A:有人將「揮單」做揮別單身解釋,也行,返鄉使得如川金這般原本單身的人,突然增加了天上地上一整家族的負擔。這跟時有所聞的爭奪家產完全相反——她揮單(乍看像揮軍)整頓家園,將孤獨的力量,獨裁的力量(她特有的卑微的獨裁)發揮到極致,既瘋狂,又報復似的。另外,小說中所有主要人物都有一段重要的具轉折性的獨處時光,深切的與孤島產生連結,得到了某種神祕指令。
Q:請向未看過書的讀者說說,您在《魔以》中用心特意釋出給讀者的「甜頭」,還有「幽默、可愛」的地方。這次寫作有割捨哪些過往的習慣,或者給自己哪些要求嗎?
A:也許我以為的甜頭一點都不甜,自己的迷思罷了。《魔以》採取一種戲耍的、不屑的、近乎荒謬的口吻,表達對人世人性的憎惡和譏諷,以單數和偶數篇章,一片土地兩個故事交織成一條繩子一根髮辮。結繩時會有一部份線索是隱去的,我任性的任其不解。
Q:最後,請談談透過《魔以》一書,最希望傳達給讀者、讓讀者感受的訊息。
A:迷信一直都存在,各種迷信造成各種戰亂。專注其實是一種逃逸,魔以是返航,更是逃逸。有一詩句我很喜歡,「她住在那裡,非常安靜地過她自設的日子⋯⋯」。就表面看來是這樣的,我們何曾知道她的內在呢?她花多少力氣方能安靜下來自設日子呢?●(原文於 2023-02-21 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魔以
作者:陳淑瑤
出版:印刻出版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陳淑瑤
來自澎湖,現居台北,她在書裡描寫迷濛的木麻黃。已出版《雲山》、《潮本》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