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席華筵終散場:讀Anne Meneley《價值競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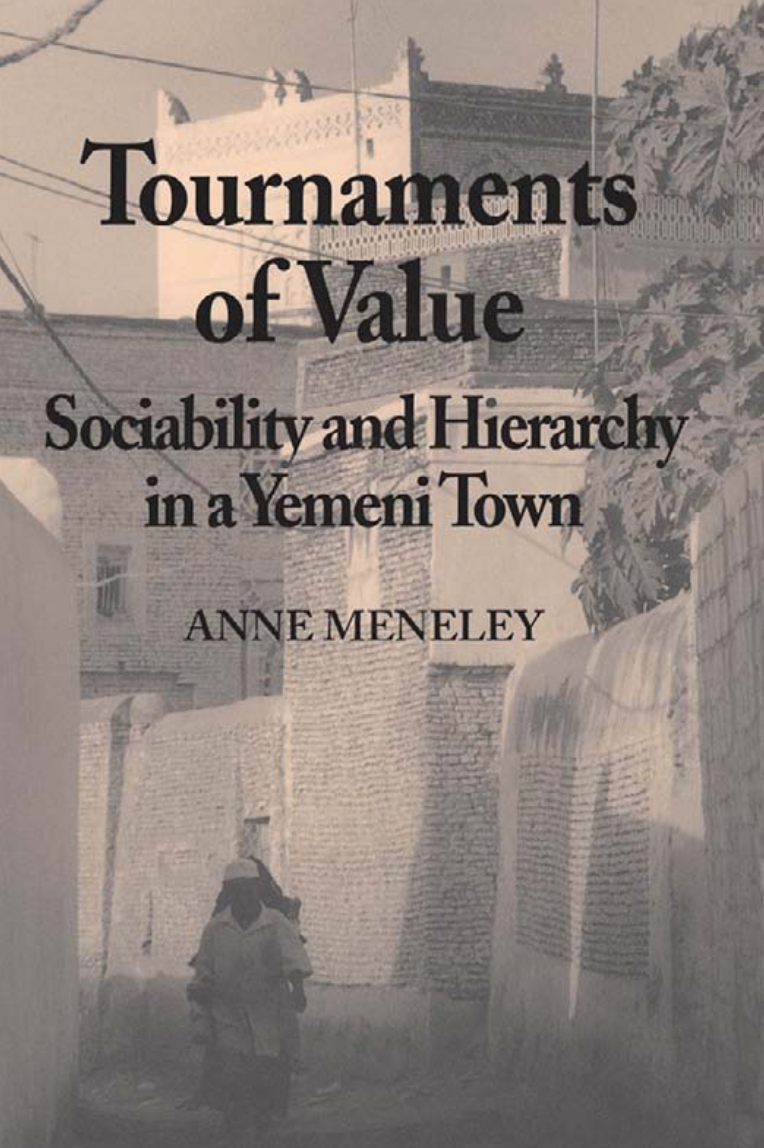
Anne Meneley, 1996, Tournaments of Value: Sociability and Hierarchy in a Yemeni Tow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曾經有那樣一個太平盛世。1980年代的尾聲,人類學家Anne Meneley在葉門鄉下的Zabid展開她的田野工作。說是鄉下,Zabid其實是一座典型的阿拉伯古城,居民約一萬人。在黃金時代,它曾經是遜尼伊斯蘭、特別是莎菲懿派的學術重鎮,至今城裡仍然有超過八十座清真寺。
1962年葉門革命之後,共和國試圖淡化身分區隔,但階級劃分依然清晰:奴僕(akbdam)、底層工作者(mazayanah)、城外的部落鄉民(qabail)、商人(tujjar)、先知穆罕默德的子孫(sadab),還有佔了絕大多數的平民(nas)。即便如此,平民之間貧富懸殊,在整個Zabid,大約有二十到三十戶、屬於菁英地主階級的大戶人家(bayt kabir)。
所謂的「大戶人家」與其說是一個恆定狀態,更像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個往上爬升、逐漸獲得肯認的聲望競賽,體現在中上階層女性例行性的「串門子」(khuruj)聚會中。在田野裡的每一天,Meneley都得在五到十個各方邀約之間取捨。這個取捨的過程是每位Zabid成年女性都必須面對的權力遊戲。
慷慨、榮譽與屈辱向來是中東民族誌的經典議題,但Meneley認為,許多研究過度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她指出榮譽與羞恥不是二元對立,更不是榮譽屬於男人、恥辱歸於女人。事實上,男女雖然嚴格分離,但葉門女性並沒有被侷限在「私領域」裡面。「串門子」聚會作為徹底由女性掌控的公共範疇,對各家族的名譽與聲望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葉門,一個理想的家屋(bayt)由父系三代或四代同堂組成。大戶人家bayt kabir中的kabir,字面意思是遼闊寬敞。宅院必有高牆環繞,從外面觀望,只能看到高過於圍牆的二樓。迴廊百轉千折,確保家中成員的隱私。高牆內,有數量不等的挑高房間(murabba’),外立面是用石灰洗得白淨的精美浮雕,室內則裝飾著石膏雕刻(naqsb)。這些房間是臥室,但有時也會作為接待女性賓客的場地。房間或相對或並列,剩下的大片面積便是庭院(qabal)。院裡椰棗、萊姆、無花果與羅勒樹影搖曳,可供賓客小憩乘涼。
宅院雖有高牆,但大門多半不鎖。女人與小孩可以自由穿梭在左鄰右舍之間。但男人的情況正好相反,進入自家門前,他必須在門外高喊:「有人嗎?」如果還有女性賓客逗留,他不能進門。也因此,大戶人家多半設有男性專屬的客廳,以確保男賓客不會跟屋內的女性接觸。男性客廳裡通常配有電視,但最好的電視與電話卻在女性的起居空間裡。
Meneley花了很多篇幅,帶領讀者參觀一場又一場盛會。不僅在婚喪喜慶與齋月(Ramadan)有筵席,一年到頭都有以各種名目舉行的大小聚會。Zabid人在早上工作,把黃昏與晚上的時光留給社交。第一個聚會的時段被稱為「asr」,約莫在下午晡禮後一小時開始。到了日落的昏禮(maghrib)時刻,賓客們會告辭,回家換裝、禮拜,接著轉移陣地,出席被稱為「layl」的第二場聚會。晚場聚會通常在九點到十點之間結束,特殊日子則會狂歡通宵。
Meneley的當地友人Nagla產下嬰兒後的「四十日」(arbayin)滿月酒,便是一場典型的宴會。滿月酒在大約十二乘以八公尺的寬敞庭院裡舉行。暮色裡,剛重新粉刷的牆白得發亮,點綴幾棵椰棗翦影。庭院四周圍繞兩排沙發,沙發上鋪滿布料、枕頭與軟墊,沙發與沙發之間放著水煙與各色煙草。在Zabid,當一個客人是一種享受。女主人無微不至地提供各種服務,才剛坐下,一杯加了荳蔻提味的甜茶就已經送到眼前。賓客們三兩成對而來,有的殷切問候彼此,有的怒目埋怨對方何以在自己臥病時沒來探望。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們也走進了庭院,她們身穿時髦華服,總是成群結隊光臨,要求最好的沙發座位。
宴會的主角Nagla迤然登場,她渾身散發光芒,被妝點得像是新娘一樣,禮服、茉莉花、手腳上紋上了指甲花。眾賓客紛紛讚嘆打趣,一邊分享著葉門獨特的、帶有興奮作用的卡特草(qat),很快地,沙發旁便有草梗堆積而成的小山。嚼食卡特草令人發熱口渴,所幸女主人準備了冰水、甜茶、可樂、烤過的西瓜子、口香糖與各種飲品零嘴。席間薰香裊裊,女人們輪流捧著小爐,爐裡有燃燒著混合了樹膠、木質與油的昂貴香料。

Meneley仔細梳理了Zabid不成文、但無比正式的待客與作客規範。對一個派對的最高讚譽是「像是天堂(jinan)一樣」或「房子都塞滿了」。好的khuruj意味著賓主盡歡:主人全面展示好客之意,客人全盤接受主人的殷勤。對Zabid人來說,khuruj不僅是社會生活的核心,更是社會生活中好的那面最極致的展現。據說在葉門,Zabid是唯一一個在晚上的時候,女人出門而男人待在家照顧孩子的地方。人們認為女人不該獨自待在家裡,此外,女人更必須擁有離開自己丈夫與小孩的自由時段,「不然我們會瘋掉的。」一位報導人說。
但慷慨裡面隱藏著競爭關係,享樂與危險並存。女人們常說,Zabid必定是地球上八卦最氾濫的地方,眾人戰戰兢兢面對流言蜚語。好幾次,在宴會後的回程路上,Meneley瞥見女人走進家門後馬上脫下長袍、呼出一口大氣的同時癱軟在離門口最近的沙發上。家中的女性親屬會聚集過來,仔細聆聽聚會中或大或小的鄙夷、讚美、批評、善意、羞辱,甚至是一個眼神。這些未必會直接動搖家族地位,但總是被人們嚴肅以待。
事實上,拜訪與否本身就是階序競逐的一環。賓客進入到女主人的家中接受款待,等於認可了女主人以及她的家族(至少暫時性地)超越了自己的地位。也因此,女主人願意招待名聲不好的女性來訪,但絕不可能親自前往對方家中。反過來說,如果地位與自己相當的對方從不回訪,你就不能繼續去拜訪她,因為那等於是自取其辱。
Meneley寫活了葉門女性的情緒表達方式。一般來說,端莊(istihya’)是最被女性推崇的價值,「請自重」常被掛在嘴邊。然而,她也注意到無所不在的「憤怒」。幾乎每個場合,她都會聽見賓客們彼此指責:「我對你很不滿。你為什麼去了那戶人家,但沒有來拜訪我?」或者「在我父親生病的時候,你怎麼不來探病?」女人們也時常討論誰拒絕參加誰的婚禮,誰又只派了自己的兒子來參加婚禮。有次,Meneley終於忍不住問一位朋友為何Zabid人這麼愛生氣,對方笑著回答:「如果她們不愛你的話,她們根本不會因為你沒去拜訪而生氣。她們根本不在乎。」
原來,憤怒其實是出自於愛(hubb)?

讀《價值競賽》的前幾章,有種誤入大觀園的錯覺。才情俱佳、各懷鬼胎的罩袍金釵們在大宅院裡抽著水煙嗑著瓜,暗地裡勾心鬥角,更不怕檯面上當眾互撕。但Meleney提醒我們khuruj的歷史特殊性:傳統的地主階級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來,因為灌溉技術革新,原本的高粱與粟米耕地轉種芒果、香蕉、木瓜、萊姆、番茄、哈密瓜等經濟作物。這些大戶人家因此累積了財富與時間上的餘裕,能夠參與由精細的禮數所規範的榮譽競賽。
然而,誠如開頭所言,大戶人家的地位是動態競逐的過程。榮譽來自於物質資源,但財富並不直接等同於榮譽,它必須被正確地投資、消費與分配。聚會中的消費雖然可以被轉化為地位,但倘若放蕩馳縱、賣地求榮,下場是富不過三代。書末,Meneley描繪了幾戶人家的興衰,鏡頭一轉,吵吵鬧鬧的清宮劇成了紅樓夢後四十回。老婦人Aysha的庭院裡仍然備著擦拭得閃亮的水煙壺,家中一塵不染,彷彿可以隨時接待大批客人。但她的老宅門可羅雀,家道中落加上不成材的未婚兒子,Aysha早已跌出了這場價值競賽。
從更大的尺度來看,要到1967年,南葉門的內戰才結束,不到三十年,南北葉門之間又爆發了戰爭。至今,Zabid地區戰亂仍頻,大觀園蒙塵,煙硝取代薰香。盛席華筵裡的談笑算計,那都是水中月鏡中花。
曾經,有那樣一個太平盛世。
Anne Meneley現任加拿大特倫特大學(Trent University)人類學教授。她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取得人類學博士,受業於Fred Myers、Dale Eickelman與Lila Abu-Lughod等學者。Meneley的研究領域包括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性別、消費與交換理論、文化與食物,田野地點在阿拉伯半島與義大利。《價值競賽》是她的第一本書。
關鍵字:性別、階序、榮辱、伊斯蘭、中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