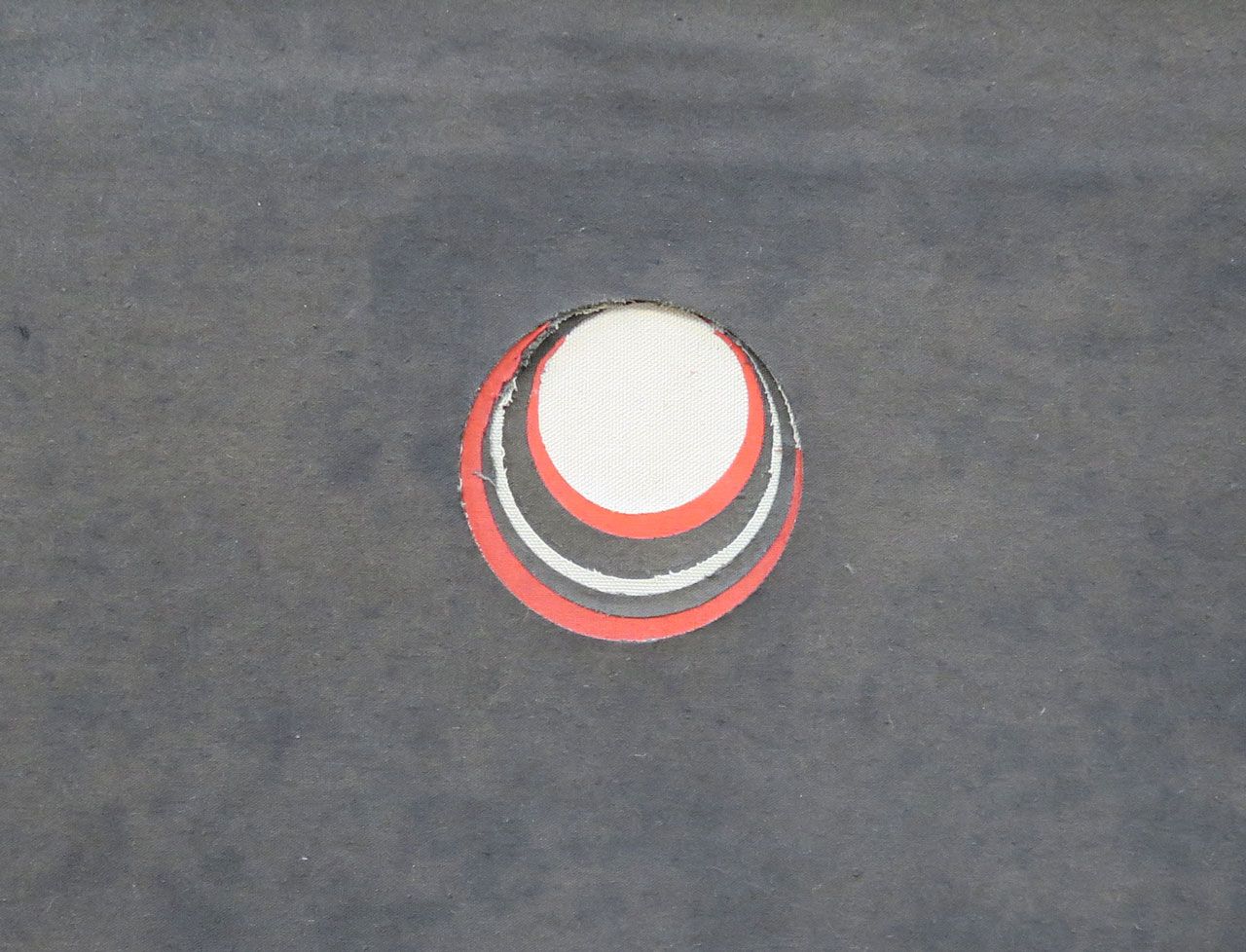哈日族的記憶
說起來我們家並不是那種接受日本教育的家庭。我媽媽那邊是,但我從母系那邊得到的文化影響很少,而父系這邊,我爺爺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他能讀古文,也能寫詩,但不會講日文。唯一的日本時代痕跡,是我爸爸都稱呼爺爺「父さん」,稱奶奶「母さん」,僅止於此。
我對日本的偏好,完全是時代氣氛的感染,1980到90年代是台灣被日本流行文化攻陷的時期,流行音樂、綜藝節目、卡通漫畫、電動玩具、衣著時尚,全部都深受日本影響。但我真正有興趣的反而不是流行文化,而是當時比較不容易接觸的傳統日本文化。1992年,坂東玉三郎曾來台灣演出,台灣刊出大篇幅的新聞報導,這大概是我對歌舞伎的初接觸,卻極為傾心。歌舞伎所呈現的高度裝飾性的傳統日本樣貌,簡直是我的終極理想。我彷彿一輩子都在追尋那個理想的日本,找尋那個東洋美的典範。

但我實際去日本的時間很晚,1998年我才第一次踏上日本國土。那時候中華民國護照還不受日本承認,日本海關會在護照上浮貼一張紙,上頭再蓋章,通常上面會寫「滯在90天」,也就是辦一次旅行簽證可以滯留90天。由於是跟團,其實頗為無趣,我們參加的是那種蜻蜓點水式的行程,短短七天從東京一路點到九州,絕大多數時間是坐在遊覽車上看著高速公路沿途的景色(或者是一直睡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某日到達京都,已經傍晚,我們在平安神宮附近下車,但時間太晚,平安神宮已經關門,只能在外面廣場走動(我到2019年才真正走進去平安神宮的御苑),然後就入住飯店。晚上吃完飯難得有個放風的時間,我跟家人很興奮的去逛街,主要是想坐一趟當時台灣還沒有的地鐵(雖然已經有木柵線,但畢竟木柵線是高架段)。走路走到一半,看到馬路對面有一個疑似地圖之類的東西,我急著想去看看,跑過去沒有注意到人行道邊有鐵鍊,勾到鐵鍊跌了個倒栽蔥,左手撞到地面脫臼。結果之後幾天,我就以失去左手的狀態走完剩下的行程,直到回台灣後才把手接回去。
這是我的日本初體驗,非常糟糕,卻澆不熄我對日本的熱衷。但我當時內心暗自許願,決不要再跟團行動,一定要自助旅行。就這樣一路到我研究所時,才終於有機會可以自助旅行去日本。

研究所的日本之旅幾乎是洋溢玫瑰色的行程,雖然第一次自己出國,處處省錢很刻苦(還自己從台灣帶泡麵去吃),碰到有點雷的旅伴,最後兩天還得了重感冒。但我非常滿足,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自助旅行,第一次可以這麼盡情遊覽,沒有人趕、沒有無謂的購物行程。我還記得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看正倉院展,當時同行旅伴沒有興趣,所以他們去了東大寺後面的二月堂、三月堂,我則是宛如朝聖一般,擠在重重人群之間,帶著敬畏的心看著那些展品,非常感動的買了紀念品跟圖錄。這件事情我後來做了非常多次,要不是武漢肺炎阻撓,我會繼續做下去。
由於正倉院展是我去日本最大的動力,奈良就成為我最常去的地方,甚至到最後,我選擇國外交換學生的學校,也在奈良。奈良嚴格來說是個農業縣,雖然號稱是日本大和文明發源地,但不像京都市區就有很多名勝古蹟,奈良的景點多半散落散田間鄉野,縣治所在的奈良市,如果沒有旅客到訪,就是個靜謐的小鎮。我對這種悠閒恬靜的日本風景相當著迷,以至於對大阪或東京那種繁華都會頗不習慣。

東京我去的次數很少,而且後來幾乎只待在上野,專門去東京國立博物館跟周邊的美術館。上野是個有趣的地方,一方面精心規劃的上野公園,提供東京一處廣闊的綠地與完備的公共設施,包括博物館、美術館、音樂廳、學校、動物園,疏朗而綠意盎然,但同時上野是有著阿美橫丁這種濃厚下町風味商店街的地方,晚上這裡非常熱鬧,充斥著給上班族聚餐的餐廳與居酒屋,對比鮮明。
疫情之前,我曾在奈良的大學交換半年時間,雖然當時也專程跑了一趟東京,去了三重的伊勢神宮,如今仍舊覺得可惜沒有再多去幾個地方,世事難料。如果要再去趟日本,我想我會先去東北,或是四國,雖然不免也有些目的性,但最終還是希望能夠有自在出國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