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米蘭昆德拉】文青的界線,並悼米蘭.昆德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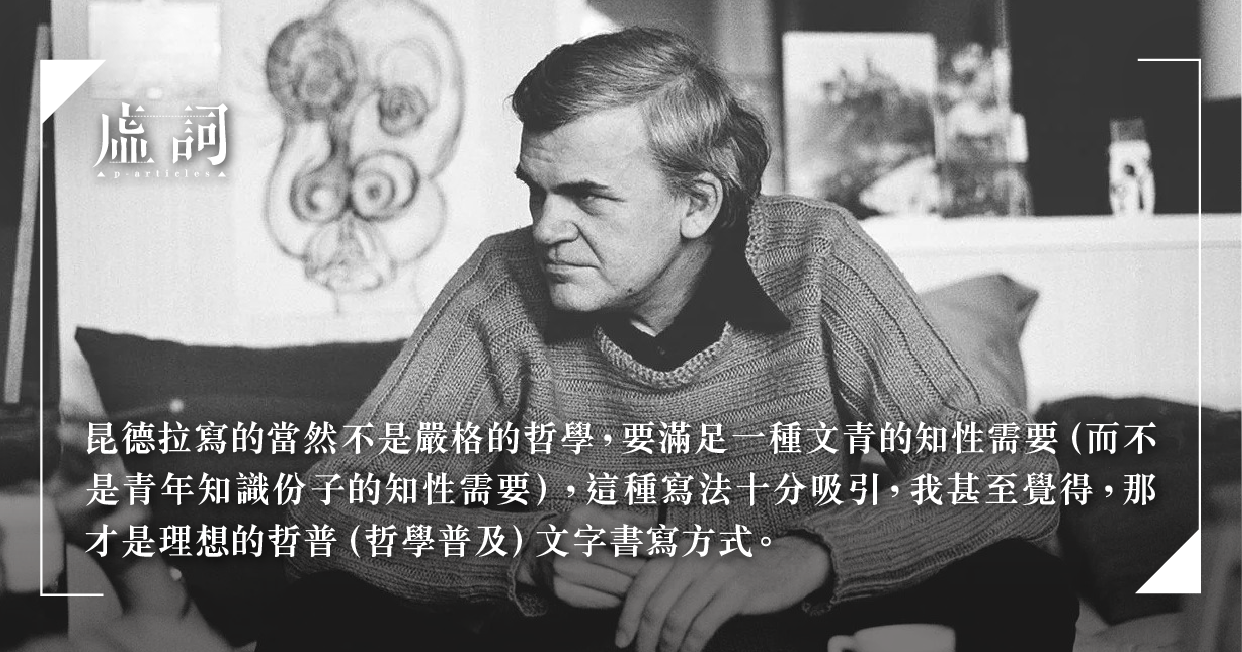
文|鄧正健
悼念一個自己文青時代的偶像之死,當然不是媚俗,只要你不流淚,尤其是第二行眼淚。因著米蘭‧昆德拉辭世,我才知道曾為他而文青的人,遠比我想像中多,也才知道討厭他的人,比我想像中更討厭他。我是理解的。我也曾一度討厭過這位我曾一度喜歡過的文青偶像,就是在我要為報紙撰寫一篇關於他最後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的書評時。那時小說中譯本剛出版,我囫圇吞棗地讀完它,幸好篇幅短,沒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那種部頭,我不用化上太多時間。書評很快寫好,刊登,直至多年後網友忽然在悼念潮裡分享這篇短短的書評,我才記起,昆德拉高壽,從我帶著對他的一絲厭惡去寫那篇書評至今,那種討厭原來早已消失了,消失得不著痕跡,彷彿我是從一而終,也喜歡著這位小說家似的。
我曾經討厭昆德拉,是因為他虛無。請記住我讀《慶祝無意義》時是2014年仲夏,那是一個「意義」 滿溢的時空,我的心思惦念著如何為眾生天地生產意義,「無意義」於我的情感而言,就是令人厭惡的虛無。再往記憶裡追溯,有幾年我細讀過哈維爾,昆德拉的同國同代人,卻象徵了截然不同的知識份子精神面貌。兩人年輕時有過筆戰,後來他們各有生涯,卻引來閱讀他們的旁人墨客說三道四,聲稱要信仰哈維爾的脊椎,輕蔑昆德拉的嘴臉。然後,更莫說我後來才得知,昆德拉曾捲入一件被稱為「德佛哈塞克事件」的風波,他被指在共產捷克時代向政權告密,累得異見者德佛哈塞克鋃鐺入獄。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又怎樣呢?文學理論告訴我,文本跟作者不是同一的,文本跟作者之間有一種意識上的斷裂,那可以是互為曖昧、相互矛盾、互相補充或各自表述,當文本被生產後,作者就應當被置於文本的脈絡之外,因為在文學意義下,「作者」已死,然後⋯⋯好吧,那是我試圖用一種抽象的理論語言,去解釋我為什麼可以饒過昆德拉可能曾經失節的事件於不理,以及姑且忘掉他看似擁抱虛無的晚年,繼續將他喜歡到底。「別因人廢言」,中年的我終於學會用簡單的話去解釋我的情感,又或者說,當我聽說昆德拉逝世的時候,一切關於他的不好,都自動在我的記憶中被擠到一旁,我只用心記住他的好,於是簡簡單單在網上寫的幾句悼念話,也是溢美之言。跟某些人洋洋灑灑長文寫他們怎樣怎樣討厭昆德拉相比,我覺得自己快樂得多。
書架上的昆德拉著作不齊,起碼就沒有了《不朽》。我記得那本是台灣時報「大師名作坊」版,卻在某次搬屋時送人。當時我跟友人討論昆德拉,我讀了《不朽》,他讀了《緩慢》,我們各自都覺得不錯,就把手上的書交換來讀。後來我還他《緩慢》,並告訴他我不喜歡,《不朽》好得多了。然而他卻沒及時還我《不朽》,很久之後我說要搬屋,就乾脆不用他還。我懷疑心中開始醞釀對昆德拉的不喜,是來自《緩慢》。當時我給自己的解釋是,《緩慢》由法語寫成,不是昆德拉的母語,他那哲理敘事融入小說敘事的寫法沒能發揮,結果《緩慢》寫出來,分量太輕,文字太白,沒有讀《不朽》時的沉重感。
沉重。生命是輕,但因為不能承受,所以讀來沉重。我其實不十分確定《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是否我第一本讀的昆德拉,可能不是,因為那有可能是源於太多人說過那是他/她讀的第一本昆德拉,致令我產生錯誤記憶。但亦可能真的是,因為書架上我還留著《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這書,也是時報版的中譯本,內地小說家韓少功翻譯。此譯本是韓少功根據英譯本翻譯,大約在1985年間完成,而時報版初版於1988年,我手上的書則已是三版十六刷,1999年的出版,年期吻合我在大學時代冒死狂啃文學經典的時光——該說是文青經典吧。馬奎斯,卡爾維諾,村上春樹,(堪稱文青四大偶像(!)),都是那段時間讀的。事後看來,媚俗嗎?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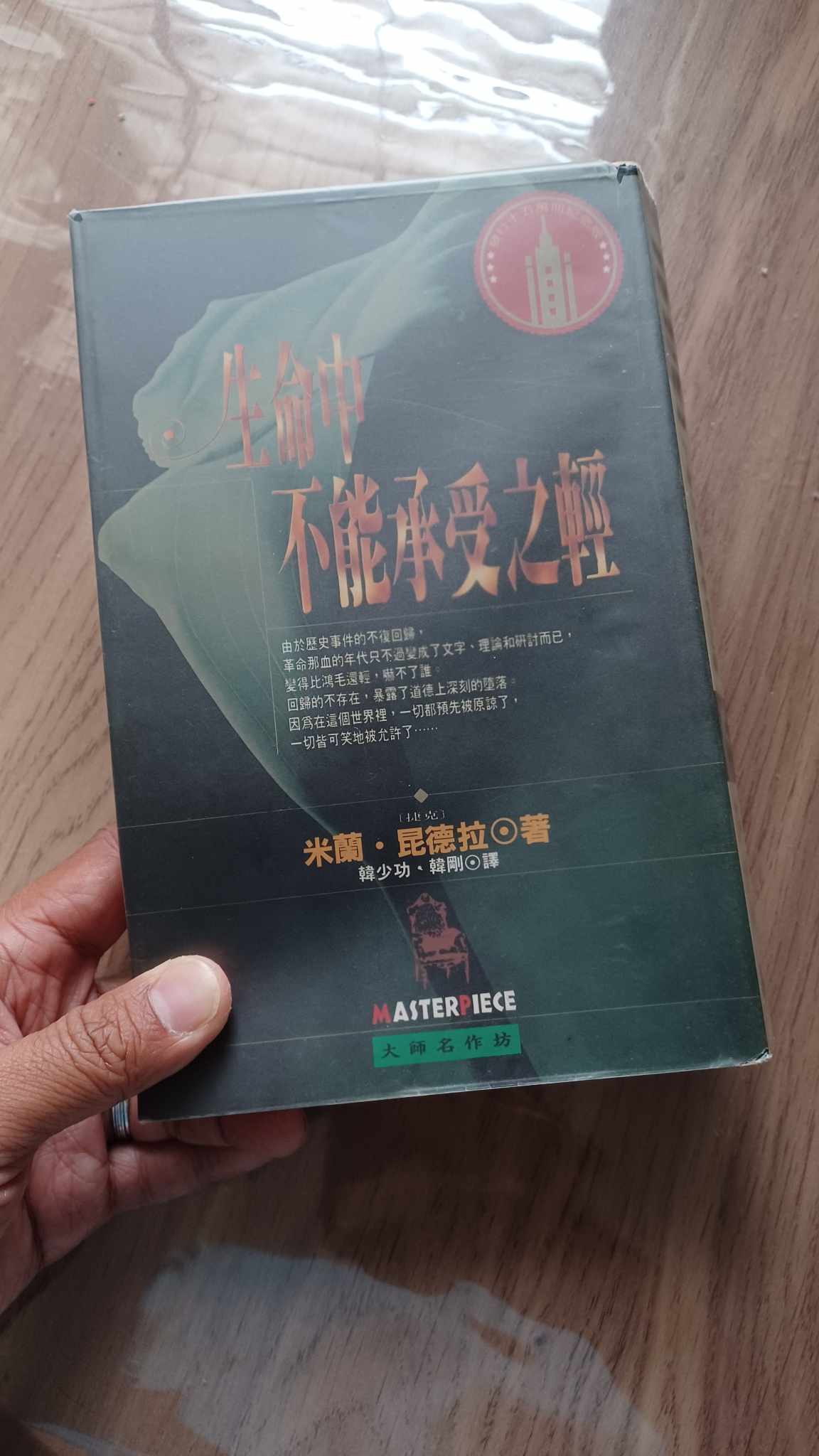
但有一點,昆德拉比其他三人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小說敘事最為貼近我的文青情意。馬奎斯《百年孤寂》時空穿透得太遙遠,造就的是難以企及的崇高感;卡爾維諾有一本書著作以 《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作譯名,跨度也遼闊。至於村上春樹,抱歉,我最初確是用讀言情/色情小說的心態去讀《挪威的森林》,畢竟博益版的袋裝書太符合那種想像了。然而,《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卻是不同的,我始終記住了書的譯名是「的輕」,而不是韓少功真正的用字「之輕」,那「的」字,沒「之」字的文謅謅,也為書名建立起頌讀時的節奏: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讀起來,有一種先把生命快速沉下去至不能承受,然後再慢慢浮回地表的感覺,很符合我在文青時代的自我想像:總覺得自己的生命很沉重,但硬要把生命壓到沉重的位置時,生命又有如一個被硬壓下去的氣球一般,稍稍鬆手,又輕飄飄的浮上來。
因此我絕對討厭後來內地版把書名譯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又「的」又「之」咁,沒了那種節奏。不好。
又,我也必得懺悔,初讀《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能讀明白的地方不算很多,但就是被他那種敘事所吸引,我最初知道「永劫回歸」、「媚俗」這些概念,都是來自此書。書中愛情和性愛描寫不少,但比之言情/色情化的村上春樹,昆德拉的好處是有哲學論述包裝,成件事就變得好有品味啦——我說的當然是當年文青時代初讀小說的直觀感覺,而絕非正式的評論分析,因此日後有不少haters拿「用哲學論述裝模作樣」去攻擊昆德拉時,所真正攻擊到,其實只是haters自己的文青式膚淺。
而讓我真正開始進入《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 是一本名為《沉重的肉身》的書。書的作者是劉小楓,就是那個後來經常用施密特政治學說去為專制政權說項、被很多人貶為文棍學棍的內地學者。這本書的封面是感覺高雅的紫色,躺睡的半裸女體低調而不低俗。書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度是牛津出版經典的長條型,單手可打橫抓住書,這亦令排版中每行字數較少,讀起來比較容易行雲流水。書紙是刻意的粗糙,多年後我從書架上找回此書,翻開,發黃紙香撲鼻而來。我翻到書中同是題為「沉重的肉身」的一章,此章裡劉小楓借用了一些希臘哲學概念書解釋《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的愛情故事,尤其是托馬斯在薩賓娜和特麗沙之間的抉擇。論述中旁涉不少倫理學、身體論和現代性話題,我經過多年對哲學和理論的涉獵,再趁悼念昆德拉時重讀劉小楓,只覺得他雖言之成理,卻再 沒了當年初讀此書那時那種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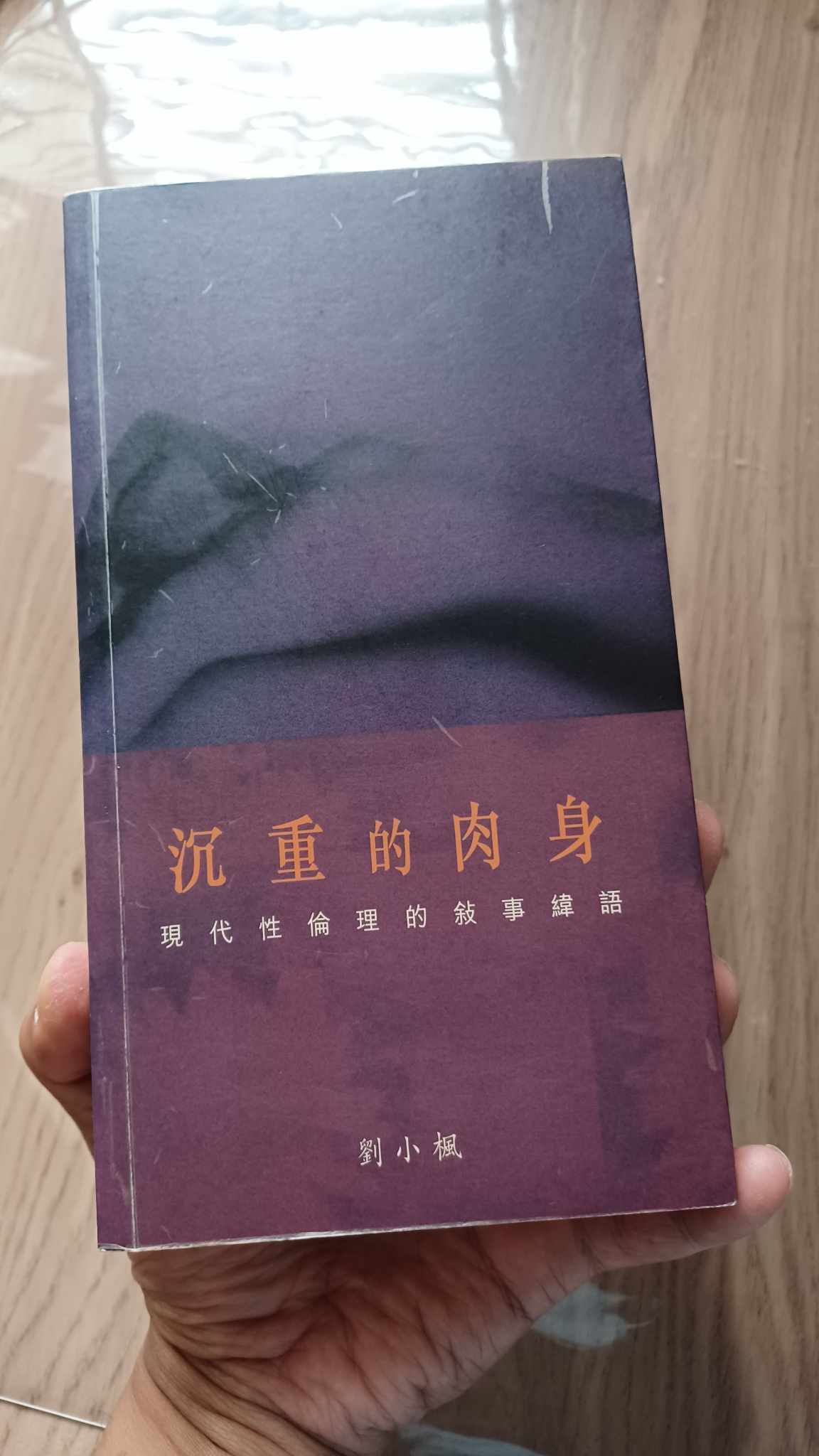
然後,我終於明白了,昆德拉之所以能在我的文青時代紮根在心,是因為他為我展示了一種文學哲學化的敘事可能:昆德拉寫的當然不是嚴格的哲學,要滿足一種文青的知性需要(而不是青年知識份子的知性需要),這種寫法十分吸引,我甚至覺得,那才是理想的哲普(哲學普及)文字書寫方式。而劉小楓的《沉重的肉身》則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敘事形式的豐沛度,沒記錯的話,《沉重的肉身》當年也是文青群體的一時之選,或準確一點說,是知性文青群體的一時之選,因為劉小楓將《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那種質感很強、卻難以一時三刻理順的哲學思辯,用一種半散文半文學評論的方式書寫出來,令文青讀者們醍醐灌頂,喚醒文青情意中的知性面目,叫他們不致沉溺於絕對的文青式躁動,而不至中年仍不能自拔。
我感激這段閱讀史。多年來,我甚至懷疑,我經常追求的散文化評論書寫形式,有好一部份的原型是來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和《沉重的肉身》這兩個文本。是故多年以後,我持續閱讀昆德拉,把他的最前期和最後期的小說,以及他的論文集都差不多讀遍了,我仍然想念著我那本送人的《不朽》,還有後來才讀的《笑忘書》,而不是更後來多數在電子書檔案上所讀的其他昆德拉作品。感性上說,《笑忘書》、《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跟《不朽》並非因為都是昆德拉出走法國後,仍以捷克寫成、向被評論界普遍認為是他成就最高的三部著作,我才特別偏愛,而是這三部小說最能展示昆德拉的文字魅力。這種文字魅力很吸引文青,卻又如醇酒一般有著撓樑多年的韌性,足以讓很多人在成年乃至中年(如我)以後,依然沒有因為他象徵著文青時代,而羞於承認對他的長期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