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一百周年紀念版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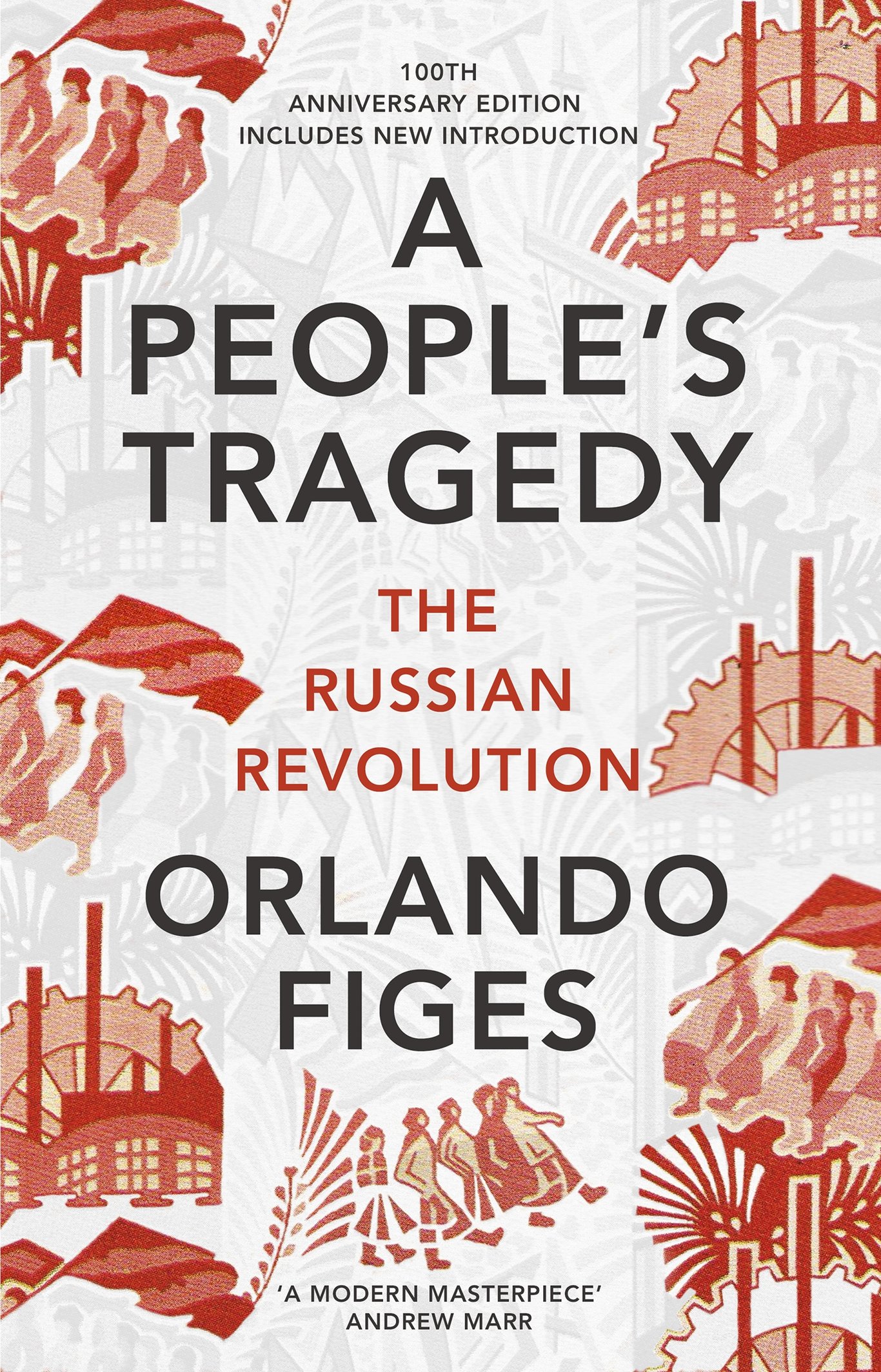
很難想像有什麼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比1917年的俄國革命更深刻地影響了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在蘇聯體制建立一代人的時間後,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或多或少)奉其為圭臬的政權下。對布林什維主義的恐懼是法西斯運動興起的一個主要原因,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從1945年起,列寧主義模式向東歐、中國、東南亞、非洲和中美洲輸出,將世界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冷戰,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方暫告一段落。我在1996年《人民的悲劇》第一版的序言中寫道:“1917年的革命決定了現代世界的形態,而我們才剛剛走出它的陰影。”如今,即2017年,這一陰影仍然籠罩在俄羅斯和從前蘇聯誕生的、脆弱的新民主國家的天空。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和恐怖主義運動中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正如我在《人民的悲劇》最後一句話警告的那樣,“1917年的幽靈在世界遊蕩”。
可在蘇聯解體最初幾年,許多人並不這樣認為。至少在西方,有一種普遍的感覺,即俄國革命已經被民主所推翻,徹底跌下了神壇。在那個民主歡慶勝利和自我陶醉的日子裡,法蘭西斯·福山寫下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書《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1992年),他在書中宣佈,自由資本主義在與共產主義偉大的意識形態鬥爭中取得了最後勝利。“我們正在見證的,”福山寫道,“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或戰後歷史的一個特定時期的結束,而是歷史本身的結束:即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普及。”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在1989年至1996年期間撰寫《人民的悲劇》時,確實有一種解放的感覺,我的主題不再為冷戰意識形態鬥爭所定義。隨著蘇聯解體,俄國革命正以一種嶄新的方式成為“歷史”:它終於可以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歷史軌跡——有開始和中間,有現在和結束——可以更自由地研究,不再受制於當代政治的壓力或蘇聯學的局限,當蘇聯還存在時,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俄國革命的研究僅囿於政治科學的框架內。
與此同時,開放蘇聯檔案為研究俄國革命史提供了新途徑。我的方法是利用普通人的個人故事,他們的聲音消失在冷戰時期的歷史中(包括蘇聯和西方),這些歷史都聚焦在抽象的“群眾”、社會階層、政治黨派和意識形態上。自1984年以來,我一直在蘇聯檔案館工作,我對能否發現關於列寧、托洛茨基甚至史達林的驚曝內幕持懷疑態度,而這正是訪問閱覽室的新人最想看到的。但我對有機會接觸俄國革命中的小人物——次要領導人、工人、士兵、軍官、知識份子甚至農民——的個人檔案感到興奮,其數量遠遠超過以前允許的。我得以在《人民的悲劇》中採用傳記方法,為全書增添更多“人性化”的內容。通過把這些個人的故事編織進歷史敘事當中,我希望把俄國革命表現為一系列戲劇性的,不受參與其中的人控制的事件。我所選擇的人物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渴望影響歷史的進程,但後來卻無可避免地淪為犧牲品。通過關注他們,我們可以發現俄國革命悲劇性混亂的一面,它吞噬了多少生命,粉碎了多少夢想。
我之所以把俄國革命稱為“人民的悲劇”,即是為了證明俄羅斯的宿命:它未能克服其專制的過去,未能在1917年穩步發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反而一步步走向暴力和獨裁。在我看來,造成民主失敗的原因根植于該國的歷史,根植於其薄弱的中產階級和公民組織,最重要的是根植於占俄羅斯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而孤立的農民,我在自己的第一本書《俄國農民與內戰》(1989)中詳細研究了那場農村革命。
《人民的悲劇》問世後,一些評論家認為本書對俄國革命民主性的評述過於悲觀。這種回饋部分源于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觀點,即1917年十月革命是一場基於社會革命的人民起義,只是在1924年列寧去世和史達林上臺後才失去了民主性質。部分則是由於各利益集團對俄羅斯在後蘇聯時代實現民主寄以厚望,其中包括那些資深的理想主義者,即俄羅斯知識份子,他們試圖相信一旦俄羅斯擺脫了史達林主義的遺產,必然發展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民主國家;還有西方商業領袖們,他們非常務實,但對俄羅斯一無所知,他們需要抱以同樣的信念,才能把資金挹注進去。
這些希望很快被證明是南柯一夢,在2000年當選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重新回到了一個更專制、更熟悉的統治形式。正如我在《人民的悲劇》中指出的那樣,這次民主失敗的原因與1917年相仿,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與1917年2月沙皇政權的垮臺不同,1991年蘇聯政權的崩潰不是由人民或社會追求民主革命造成的。事實上,這是共產黨精英階層對權力的一種退讓,至少在俄羅斯,沒有出臺像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那樣的清算法來阻止其擔任公職,他們很快就以新的政治身份,恢復在政治和商業中的主導地位。普京職業生涯起步的克格勃,在蘇聯時期即不受任何公眾監督,它被允許進行自我改造,最終成為聯邦安全局,其人員並無根本性變化。
與1917年一樣,普京政府倒向專制是由後蘇聯時代俄羅斯中產階級和公共組織的簿弱促成的。屈服於市場的壓力,知識界被證明比它想像的要軟弱得多,影響力也小很多,並失去了為人民道德發聲的可信度,而這是它自19世紀以來一直承擔的角色:當權力和權威越來越被國家控制的大眾媒體所定義時,它生活在一個書的世界裡。在蘇聯解體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俄羅斯公共組織的發展一直非常緩慢。專業協會、工會、消費者組織、真正的政黨在哪裡呢?俄羅斯民主的問題既在於公民力量的薄弱,也在於國家機器的壓迫。
但是,1991年民主的最大問題,就像1917年一樣,是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即俄羅斯人沒有真正的民主經驗。無論是沙皇政府還是蘇聯政府,都不曾經歷甚至瞭解議會制、政府問責制或受法律保護的自由。1917年流行的“民主”概念根本不是一種政府形式,而是一個社會標籤,相當於“平民”,其反面不是“獨裁”而是“資產階級”。在此基礎上,接下來的六、七十年間,就其或多或少提供全民就業、住房、醫療保健和社會平等而言,人們能夠相信蘇聯體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也正因如此,伴隨蘇聯制度崩潰而來的經濟危機,破壞了資本主義版的“自由”和“民主”的可信度,沒有可替代品。
對大多數普通俄羅斯人來說,特別是那些自認為是“蘇聯人”的年齡層的人來說,上世紀90年代幾乎是一場災難。他們失去了一切:熟悉的生活方式;保障安全的經濟體系;給他們帶來道德確定性,甚至希望的意識形態;一個擁有超級霸權地位和“大一統”民族身份的強大帝國;以及蘇聯在文化、科學和技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們努力適應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嚴酷現實,那裡沒有偉大的思想,沒有國家制定的集體目標,他們懷念舊蘇聯。許多人渴望回到史達林時期,回到他們記憶中或想像中神話般的過去,他們認為史達林時代物阜民豐、安定和諧,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幸福的時光”。根據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42%的俄羅斯人,以及60%的60歲以上的人,希望出現一個“像史達林那樣的領導人”。
從執政伊始,普京就旨在重新樹立對蘇聯歷史的自豪感。這是他復興俄羅斯大國偉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重新恢復包括史達林在內的蘇聯歷史,為普京自己的專制政府提供了合法化,使其成為俄羅斯長期以來,甚至上溯至1917年以前的沙皇時代的強大國家權力傳統的賡續。根據這個神話,國家提供的秩序和安全比西方自由主義所謂的人權或民主更受俄羅斯人重視,後者在俄羅斯歷史上沒有根基。
普京的歷史倡議很受歡迎,極大地鼓舞了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對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愛國主義自豪感和對前蘇聯的懷舊之情。當他在2005年向俄羅斯聯邦議會宣佈“蘇聯解體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時,普京表達了四分之三人口的意見,根據2000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他們對蘇聯解體感到遺憾,並希望俄羅斯擴張領土,將克裡米亞和頓巴斯等納入“俄羅斯”版圖,這些領土已經“丟失”給烏克蘭。2014年,打著新蘇聯旗幟的志願者將跨越俄羅斯邊境,為收復這兩塊烏克蘭土地而戰。
重寫蘇聯歷史也讓那些俄羅斯人松了一口氣,他們對戈巴契夫“公開化”時期“抹黑”國家歷史感到不滿,當時媒體充斥著對“史達林罪行”的揭露,這破壞了他們在學校學到的蘇聯版教科書。許多人惶惶不安,因為他們被強迫問及自己的家庭在史達林統治時期的行為,他們不想聽那些關於他們國家的歷史有多“壞”的道德說教。通過恢復對蘇聯歷史的自豪感,普京幫助俄羅斯人再次感受到作為俄羅斯人的美好。
他首先從學校著手,教育部拒絕批准被認為對蘇聯時期過於負面的教科書,實際上是將其從課堂上移除。2007年,普京在一次歷史教師會議上說:
至於我們歷史上的一些問題,是的,我們有些歷史問題。但哪個國家沒有呢?況且我們的問題比其他[國家]要少。我們的問題也不像其他[國家]那麼可怕。是的,我們有一些歷史問題:讓我們記住1937年開始的事件,讓我們不要忘記它們。但其他國家的問題也不少,甚至更多。無論如何,我們沒有像美國人那樣,在越南數千公里範圍內傾倒化學品,或朝一個小國投下比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多七倍的炸彈。我們也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的黑暗一頁,比如納粹主義。每個國家歷史上都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事情。我們不能讓自己背負罪惡感……
普京並沒有否認史達林的罪行。但他認為沒必要糾纏不休,而是將這些罪行與史達林作為國家建設者所取得的“光輝的蘇聯歷史”成就相平衡。在一本由總統委託編寫並在俄羅斯學校大力推廣的歷史教師手冊中,史達林被描繪成一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在保衛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合理地採取了一些恐怖行動”。
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人對革命暴力也持有類似的態度。根據2007年在三個城市(聖彼德堡、喀山和列寧的出生地烏裡揚諾夫斯克)進行的一項調查,71%的人認為1917年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創始人菲力克斯·捷爾任斯基“保護了公共秩序和公民生活”。只有7%的人認為他是一個“罪犯和劊子手”。更教人不安的是,調查發現,儘管幾乎每個人都很瞭解史達林統治下的大清洗——大多數人承認有“1,000萬到3,000萬受害者”遇難——但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堅持認為,史達林對國家是有貢獻的。許多人聲稱,在史達林統治下,人們“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即使知道有數百萬人被殺害,俄羅斯人似乎仍然接受布爾什維克的理念,即為了實現革命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大規模使用國家暴力。
2011年秋,數百萬俄羅斯人觀看了《時間法庭》,這是一個模擬法庭的電視節目,由辯護人、證人和從觀眾中選出的陪審團,對俄羅斯歷史上的各種人物和事件進行審判,通過電話投票作出裁決。結果國家電視臺發現,這次審判並沒有給俄羅斯人改變態度帶來多少希望。面對史達林鎮壓農民起義的證據和強制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數百萬人死於饑荒,更多的人被送往古拉格集中營或偏遠的勞改營),78%的觀眾仍然認為這些政策是合理的,是實現蘇聯工業化“可怕的必要條件”。只有22%的人認為它們“有罪”。
在政治上,革命可能已經死亡,但它的某些觀念仍然具有生命力,這些觀念將繼續主導俄羅斯政壇許多年。
那麼,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們應該怎樣紀念它呢?1889年,為慶祝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埃菲爾鐵塔在當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入口處落成。這座塔象徵著源自1789年第三共和國的價值觀。在俄羅斯無法建造這樣的地標,自蘇聯政權垮臺後,紀念十月革命的活動使俄羅斯陷入分裂。1996年,伯里斯·葉利欽將11月7日的革命日改為“和諧和解日”,“以緩和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對抗並實現和解"。但是,共產黨人繼續以傳統的蘇聯方式舉辦紀念活動,他們高舉紅旗進行大規模的示威。普京試圖通過在11月4日(1612年波蘭結束對俄羅斯的佔領之日)設立“民族團結日”來平息這一爭端。從2005年起,它取代了官方日曆中11月7日的假期。但民族團結日並沒有流行起來。根據200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只有4%的人能夠說出這一節日的由來。十分之六的人反對取消革命日。儘管普京努力重塑蘇聯時期的輝煌成就,但沒有任何關於十月革命的歷史敘事可以讓國家團結起來:有些人認為它是一場國家災難,也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偉大文明的開端,但整個國家仍然無法接受其暴力和矛盾的遺產。
同樣地,在如何對待蘇聯國家締造者的問題上,也沒能達成共識。葉利欽和俄羅斯東正教會支持關閉莫斯科紅場上列寧陵墓的呼籲——自1924年以來,列寧的遺體一直在那裡展出,並遵照列寧自己的遺願,將他葬在聖彼德堡沃爾科夫公墓的母親旁邊。但共產黨人組織起來,堅決反對這一做法,所以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普京反對將列寧從陵墓中移出,理由是這將冒犯為蘇聯制度做出巨大犧牲的老一代俄羅斯人,暗示他們懷有錯誤的理想。
在這種分裂和混亂的局面下,2017年俄羅斯的十月革命紀念活動可能會被淡化。在西方似乎也最有可能如此,俄羅斯革命在我們的歷史視野中已經退居二線,部分原因是自冷戰結束後媒體的關注度下降,我們的注意力被轉移到了中東和伊斯蘭教極端主義問題上;而部分則可能是因為我們對人權越來越關注,這主導了我們關於政治變革的道德討論,導致我們不太理解其他價值觀的情感力量,如社會正義和財富再分配,這些都會助長革命暴力。
但正如近年來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革命的時代尚未過去。巴爾幹半島、烏克蘭、格魯吉亞和黎巴嫩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和烏克蘭的“歐洲廣場運動”提醒我們,大規模抗議往往演變成暴力推翻政府的力量。所有這些運動都可以拿來與1917年作比較,讓世人從中汲取教訓或啟迪。例如,他們使用社交媒體組織群眾,此舉必得列寧青睞。正如雅各賓派是十九世紀革命者的榜樣,布爾什維克也成為二十世紀所有革命者——從中國到伊朗,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恐怖主義分子——的榜樣。伊斯蘭國採用的所有方法——通過戰爭和恐怖來建立一個革命國家,其追隨者的狂熱奉獻和軍事紀律,以及精湛的宣傳手段——都是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內戰中首先掌握的。
我們不應洋洋自得地認為,革命不會對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構成威脅。最近歐洲各地民粹主義群眾運動的興起提醒我們,革命隨時隨地可能爆發:它們從未遠離。歐洲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民主是多麼的脆弱。如果說歐洲在偉大的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那也只是極其微弱的優勢,而且它的勝利絕不是預設的:結果可能不是這樣。正如我1996年在《人民的悲劇》最後幾段所寫的那樣,“我們必須努力加強我們的民主,使之成為自由和社會正義的源泉,以免弱勢者和幻滅者再次拒絕它”。
2017年1月於倫敦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